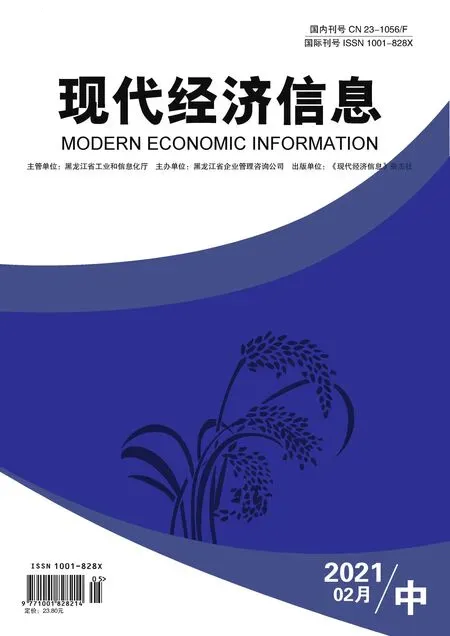經濟變量對人民幣匯率的時變沖擊分析
張 宇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
一、前言
隨著我國金融開放進程的推進和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人民幣匯率政策和匯率的形成機制已經日漸被大眾所關注,近年來我國外匯市場邁進加快開發的階段,人民幣在全球范圍內的地位有所上升,已經發展成二十國集團經濟體當中最強勁的貨幣,也是目前全球范圍內升幅最大的貨幣之一,2020 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年中觸底后強勁反彈,走出了先抑后升、后低后高的走勢。
事實上,國內外有許多學者利用泰勒規則分析,Giesenow(2019)[1]使用泰勒規則模型中的前瞻性和實時數據來估計央行的行為,并使用允許各國間異質性的估計量。國內學者李小林(2018)[2]理論闡述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成因,并實證檢驗了在長短期內的不同。經典匯率模型的性能很差是由于他們忽略了時變關系,而且缺少解釋性的信息。國內學者王紅(2017)[3]通過,中美利差、匯率預期對我國資產價格的時變影響在方向與程度上具有明顯差異性;司登奎(2019)[4]內生地植入國際資本流動以考察人民幣匯率的動態決定機制。
理論分析表明,國際資本流動等對即期匯率的影響均取決于利率平滑操作的程度、除此之外,國際資本流動、產出缺口差及通脹差對匯率的影響還與貨幣政策的反應程度有關。王少林(2015)[5]、劉金全(2012)[6]采用時變參數狀態空間模型(DMS)對構建的時變泰勒規則模型進行參數估計,結果表明我國當下的貨幣政策、產出缺口、通貨膨脹對人民幣匯率具有時變的特征。
本文將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闡釋人民幣匯率的動態時變特征,將從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兩個層面進行經濟變量對人民幣匯率時變沖擊特征的研究分析。
此研究將利于更加全面化了解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變動的情況下,資本流動、中美產出缺口之差、中美息差、中美物價水平之差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關系,有助于拓展泰勒規則模型的應用范圍,對了解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狀況、有效地防范金融風險、完善我國的匯率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變量選取與誤差向量模型
(一)變量選取
本文選用的樣本區間為2005 年1 月至2020 年6 月的月度數據,共186 個觀測值。因變量人民幣兌美元月末匯率(直接標價法)本文中的解釋變量說明如下:解釋變量包括中美產出缺口之差,用工業增加值代替產出缺口差,對于變量中美利差(ID)采用的數據是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差值來表示,對于變量中美通貨膨脹之差(CPI)選取中美兩國CPI環比增長率的差值來代表;在變量資本流動(CFUS)的衡量方面,采用中國新增外匯儲備與中美貿易順差及實際利用 FDI 的差值來衡量。
(二)誤差向量模型
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是由 Engle 和 Granger 所提出將協整與誤差修正模型相結合的一種計量研究方法。本文通過脈沖響應分析不同變量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VECM 分析的前提條件是方程所運行得到的所有根都能落在單位元內,這一過程為平穩過程,但在利用數據差分以求得數據平穩的過程中會失去一些有效信息,且更多的關注變量之間的短期變動過程,往往對長期變動過程關注較少。為了保持數據原有的樣貌且得到時間序列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從而可建立VECM 考察時間序列向量之間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進而選擇恰當的滯后期數對VECM 的估計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VAR 模型滯后期的選擇方面,根據LR、 FPE、AIC、SC、HQ 準則標準綜合判斷,最終選擇滯后期數是P=3,進行協整檢驗時的滯后期數選擇是(P-3)期,即滯后3 期。
(三)JOHANSEN 協整關系檢驗
為判斷資本流動、中美息差、中美產出水平之差、中美物價水平與人民幣匯率之間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本文采用 了Johansen 協整檢驗方法分別對變量的每一組數據進行檢測。基于具有協整關系的VAR 模型在不對變量進行差分的前提下,直接對相同單整階數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在 95%的置信水平下,各變量之間至少存在一個長期協整關系,說明構建的 VAR 模型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因此VECM 可被構建。
(四)關于誤差向量模型的評述
文章選擇在泰勒規則模型的基礎上構建VECM,VECM 的本質是具有約束性的VAR 模型,通過對VECM模型的構建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CPI 的系數是負的,中美物價水平之差擴大對人民幣匯率上升是負相關的,應當維持物價水平的平穩,縮小物價水平之差有利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CPI 的系數是負的,中美產出缺口之差對人民幣匯率上升是負相關的,從長期來看,應該維持產出的穩定,如果產出缺口過大,對中國經濟增長不利。
(五)單位根檢驗
為了檢驗VECM 的穩定性,對模型進行單位根的檢驗,除了VECM 本身所假設的單位根之外,伴隨矩陣的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單位圓內,并且大部分的結果都遠離單位圓,從而說明構建的VECM 具備穩定性,即可以繼續進行脈沖響應及方差分解的結果分析。
三、實證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表示一個變量的沖擊對模型內外變量當前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沖擊影響,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可以反應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帶來對內生變量的影響,本文滯后期選10 期來考察資本流動(CFUS)、中美物價水平之差(CPI)、中美產出缺口之差(GAP)和中美息差(ID)對人民幣匯率(ER)沖擊的脈沖響應。
(一)國際資本流動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國際資本流動在2—4 期內的沖擊對人民幣匯率是正向的影響,在1—2 期內是負向影響,之后負向影響開始慢慢減弱。1 單位標準差的正向沖擊,導致人民幣匯率的迅速下降,此處人民幣匯率選用直接標價法,即資本流動的正向沖擊帶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在3.5 期達到峰值,之后影響程度有所下降并趨于平穩,表明資本流動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具有持續性。原因是中國的匯率制度在2005 年進行調整由固定匯率制度轉向浮動的匯率制度,與此同時確立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導致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加大,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經濟能夠在短期內恢復到平穩水平,世界其他經濟體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增強,短期內資本流入,帶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
(二)中美通貨膨脹水平之差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中美通貨膨脹水平之差一個標準差正向的沖擊在10 期內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了負向影響,并且沖擊短期的負向影響顯著于中長期,這說明新冠肺炎疫情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是非常短暫的,長期來看還是依賴于宏觀經濟基本面,在2020 年2 月中國CPI 維持在5.2%的高位,但隨著中國復工復產的推進,物價恢復到平穩水平,這符合泰勒規則的本質思想,當一國出現偏離平均水平的通貨膨脹時,貨幣當局會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來縮緊銀根,降低貨幣的流動性。例如提高利率,導致對人民幣匯率需求增多,帶來匯率的升值。由此可見當中國的物價水平超過美國時,人民幣匯率升值;當物價水平低于美國時,人民幣匯率呈現出不平穩的狀態。
(三)中美產出缺口之差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中美產出缺口之差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在10 期內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了負向影響,中美產出缺口之差在短期內對匯率的負向沖擊要大于長期,在5 期之后的負向沖擊趨向于平穩。這表明中美產出缺口之差對人民幣匯率維持穩定具有負向影響,這個負向影響較小且有一定的滯后性。當中國的產出增速高于美國時,會出現短期內人民幣匯率升值的現象,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一方面為了刺激出口,消化國內過剩產能,人民幣匯率將有走向貶值的勢態,另一方面,中國產出速度的持續提升會帶來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同樣會帶來人民幣匯率走向貶值。在2020 年2 月中國的貿易順差迅速下降。
(四)中美息差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中美息差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在10 期內對人民幣匯率主要產生負向影響,負向影響在4 期內達到了最大。中美息差越大,即人民幣利率比美元利率高時,人民幣升值。這是由于當人民幣利率升高,對人民幣的需求增多,導致人民幣呈現升值趨勢,這符合利率平價理論。中美息差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具有時滯性,在5,6 期內出現了短暫的正向沖擊影響,這主要依托于宏觀市場經濟環境的變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美息差縮減,公眾對人民幣匯率持有貶值的預期,這加速資本流出,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
四、結語
綜上所述,人民幣匯率對資本流動的沖擊響應最為迅速、在短期內反應程度最高。對匯率的沖擊存在時滯性。隨著國內疫情的持續爆發,對2020 年第一季度的經濟沖擊尤大,疫情造成的市場情緒波動和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加大了中國匯率市場的震蕩。依托購買力平價理論,通貨膨脹率長期上升會帶來人民幣的貶值。
本文針對分析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一是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監管和監控,避免資本流動的劇烈波動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保證經濟的平穩發展,貨幣當局可以考慮將納入資本流動的泰勒規則模型作為逆周期調控的參照體系,以弱化外匯市場的沖擊。二是中國政府應該在新冠疫情有所控制的前提下促進出口產業發展,保持產出的長期穩定,維持公眾對于人民幣幣值的信心。三是我國貨幣政策的實施應該考慮不同變量的敏感程度,例如當中美利差縮小,人民幣匯率出現預期貶值時,應該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強對人民幣匯率預期的管理,保持貨幣政策實施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