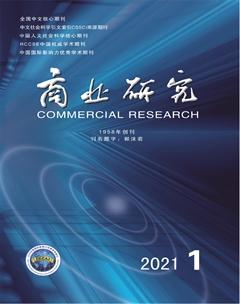FDI、工資扭曲與勞動收入份額
安孟 張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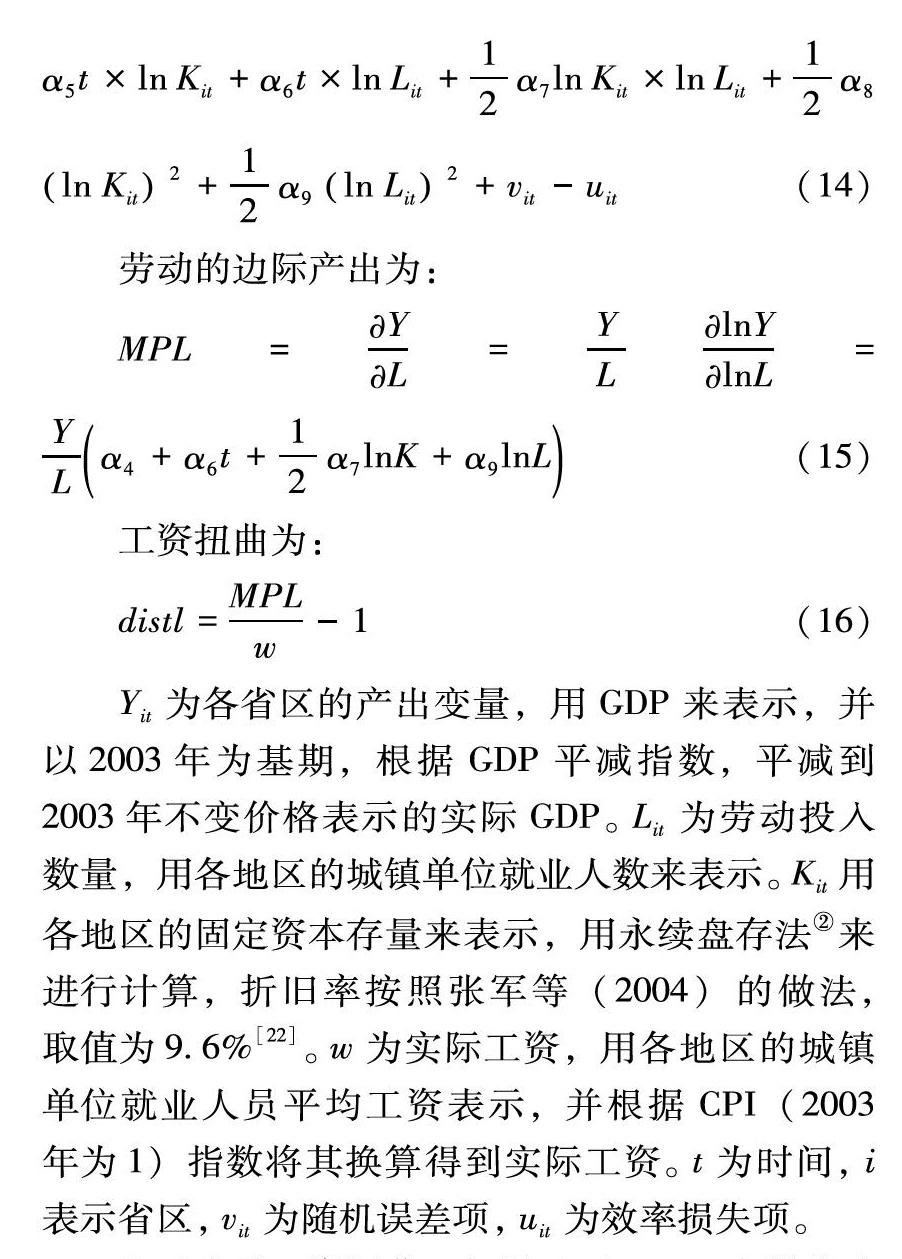
內容提要:本文將FDI、勞動力的工資扭曲納入統一的框架,系統分析其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采用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的隨機前沿方法對中國大陸31省(市、自治區)的勞動力工資扭曲指數進行測算,利用2003-2017年的中國省級動態面板數據檢驗各因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結果表明:外資的進入和工資扭曲都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但隨著工資扭曲的加劇,外資對勞動收入份額的負向作用得到緩解;除此,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政策、勞動要素使用數量下降、資本深化、高水平人力資本缺乏、勞動力流動不暢和配置效率不高等因素,都抑制了勞動工資份額的提升。因此,在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背景下,須在招商引資政策、推進要素市場建設、加大財政金融支持上進行必要的制度改進。
關鍵詞:FDI;工資扭曲;勞動收入份額
中圖分類號:F24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21)01-0127-08
作者簡介:安孟(1992-),女,山東泰安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國投資;張誠(1962-),本文通訊作者,男,山西靈丘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跨國投資。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勞動收入份額代表的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者收入的占比。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出現大幅的下降,從1990年的54.08%降至2007年的44.92%,2008年之后有所回緩但幅度較小[1]。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說明多數人沒有同步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這限制了居民的消費需求能力的提升,也會導致收入分配不均衡、貧富差距加大,進而引發勞資沖突,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因此,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和決定機制進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國內外學者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產業結構變化。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在排除了核算方法的影響后,認為1995-2003年期間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原因是產業結構從勞動收入占比較高的農業部門向占比較低的非農業部門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對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作用達到61.31%[2];羅長遠和張軍(2009)認為1996-2003年一產比重較大程度的下降導致了勞動收入占比的下降[3];李稻葵等(2009)發現,產業結構的轉變和勞動者談判能力的共同作用導致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化呈現“U型”[4]。第二,有偏的技術進步。王林輝和袁禮(2018)認為有偏的技術進步影響了不同部門的要素生產效率,引致了要素的跨部門流動和重新配置,推動產業結構的變遷,進而對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產生結構效應[5];姚毓春等(2014)認為1997-2011年工業和制造業存在資本偏向性的技術進步,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0.1061和0.1246[6];Bentolila和Saint-Paul(2003)對12個OECD國家的13個產業的數據進行檢驗發現,資本增強型的技術進步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了負向的影響[7]。第三,全球化。Rodrik(1977)認為全球化使得資本比勞動具有更強的流動性,資本會有更多的獲利機會,資本所有者的談判能力較強,勞動者的工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從而勞動者的收入份額持續下降;戴小勇和成力為(2014)使用1999-2007年的工企數據研究發現,出口和外資使勞動這種要素對最終產品分配權的相對地位下降,從而引起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8];蔣為和黃玖立(2014)認為國際生產分割是中國加入全球化的特征,國際生產分割的上升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9]。
毫無疑問,上述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但也存在一些方面的不足。首先,產業結構的變化可以解釋部分轉型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卻不能解釋同時期發達國家在穩定的產業結構中所出現的相同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問題[10]。其次,在技術進步的偏向性對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研究中,大多數文獻都選用CES生產函數來計算技術進步的偏向性,一方面沒有考慮到不同的經濟體可能滿足不同形式的生產技術;另一方面,由于技術變化、要素的質量以及環境制度的改變,不同的時期勞動和資本的彈性可能無法保持不變,因此,CES函數的假定限制了要素替代彈性可變的屬性。再次,從開放經濟的全球化視角,學者們得出的結論也不一致。有學者認為由于地方政府為吸引外資而進行的惡性競爭以及外資負向“工資溢出”效應,降低了勞動者的談判能力,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11];然而,部分學者認為,外資與勞動收入份額之間呈現“U型”或者“倒U型”,且不同的區域之間存在差異性[12-14]。
本文嘗試拓寬研究的視角,從開放經濟和勞動力的工資扭曲①兩個方面,為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提供一種不同于現有文獻的解釋,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去論證外資和工資扭曲是導致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邊際創新之處主要有:(1)立足于開放經濟視角,從外資和勞動力工資扭曲的雙重視角,重新研究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決定機制。(2)選用更符合生產實際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的隨機前沿分析方法對勞動力的工資扭曲指數進行了計算。(3)在實證分析方面,選擇長達15年的省級動態面板數據,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內生性問題的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檢驗了各影響因素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有助于相關部門有效解決實際存在的勞動收入份額偏低問題。
二、FDI、勞動力的工資扭曲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機制
外資進入對勞動者的報酬具有正負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正向影響。外資企業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和先進的技術,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量較大。因此為了吸引東道國高技能的勞動力,外資企業有動機提高工資水平[15]。而且,外資進入通過工資溢出效應,加快了東道國市場化改革,生產率較低的企業會被淘汰出市場,釋放生產要素,勞動力也會轉移到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并獲得相應的報酬,這有利于提高工資水平[16]。二是負向影響。由于生產要素的定價權被政府掌握,東道國的不同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給予外商政策優惠時更可能忽視甚至侵犯勞動者的權益[17]。此外,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外資企業不僅可能產生擠出效應更有可能對勞動市場進行壟斷,勞動力的報酬被限制在偏低水平,縮小了工資的上升空間[18]。因此,外資對勞動報酬的影響取決于正負兩個方向的共同作用。
外資進入對勞動生產率具有正向的影響。一方面,外資帶來國外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其通過產業鏈的前后關聯擴散至其他企業乃至行業,東道國的生產技術得到提升,從而提高了東道國的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本地企業通過模仿外企的技術和管理,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二)勞動力的工資扭曲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機制
勞動力工資扭曲對勞動者報酬的影響。首先,從工資扭曲產生的原因看,戶籍制度的存在、城鄉二元分割的現狀,勞動力在行業、區域之間不能自由流動,導致勞動者不能獲得與自身邊際產出相當的工資。其次,由于地方政府為了引資,通過壓低勞動者的工資,以低廉的勞動成本吸引國外資本,這都會降低勞動者的報酬。
勞動力的工資扭曲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一方面,由于長期存在的工資“向下扭曲”,勞動力的價格被低估,企業就會傾向于使用有形的生產要素,勞動密集型企業就會過度發展,企業長期位于生產活動的低端,沒有動力進行技術研發并提高勞動生產率[19]。另一方面,由于工資的扭曲,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較低,他們可能會尋求新的工作機會,尤其是高人力資本的勞動者,由于得不到預期的工資,他們會選擇“用腳投票”,導致企業人力資本流失,沒有可以進行技術研發的人才,抑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最終,外資進入和工資扭曲對勞動者的收入份額的影響,還要取決于其對工資和勞動生產率影響的大小。如果對工資的影響大于勞動生產率,則會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反之,則會降低勞動收入份額。
(三)外資、勞動力的工資扭曲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機制
外資進入對工資扭曲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對勞動者的邊際產出和實際工資的影響發揮作用。外資的進入帶來先進生產技術,會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提高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水平,加劇了工資的扭曲程度;但是,外資的進入還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優化勞動市場的配置,勞動力被配置到所需的部門,其獲得的報酬也將隨之增加,這又會緩解工資扭曲。
外資企業通常具有較高的生產技術和先進的管理制度,通過工資溢出和制度溢出,加速了東道國市場化改革進程,市場的作用會促使生產率較低的企業退出市場,釋放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也會流入到更高效率的企業,獲得較高的報酬。外資的進入緩解了中國的工資扭曲,工資扭曲得到緩解又會通過上述的機制影響勞動收入份額[20]。
三、模型的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的設定
為了研究外資、勞動力的工資扭曲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結合前文的理論推導,設定如下基本模型:
(二)變量的選取說明
1.勞動收入份額(ls)。用各地區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在GDP中的占比表示。
2.外商直接投資(fdi)。用外商直接投資在GDP中的占比表示,并根據當年的匯率將其換算成人民幣,然后進行相關的計算。
3.勞動力的工資扭曲(distl)。由于工資扭曲是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和實際工資之間的偏離,對工資扭曲的計算關鍵在于選擇適合的生產函數對邊際產出進行計算。考慮到生產技術的存在的效率損失和生產要素之間的替代性,選擇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其具體的形式為:
4.控制變量。除了外資和勞動力的工資扭曲,考慮其他因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作為控制變量加入進行考察,否則會導致變量遺漏的偏誤。各控制變量的選取說明如下:
資本密集度(lnkl)。反映的是資本和勞動的相對投入數量,當勞動和資本互補時,資本密集度與勞動收入份額同方向變動;當勞動和資本存在替代關系時,資本密集度與勞動收入份額反方向變動,計算方法為固定資本存量與城鎮單位就業人數之比,并取對數[23]。
融資能力(finance)。融資能力越強,更容易獲得外部資金,企業才會有資金投資生產,雇傭勞動力,支付工人的工資。但是如果融資能力過強造成的過度借貸,就要承擔沉重的債務負擔,處于低端發展的處境。用金融機構本外幣年末貸款余額在GDP中的占比表示。
人力資本(hu)。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勞動者的議價能力和生產率越高。此外,較高的人力資本能夠更好的與其他生產要素匹配,邊際產出也就越高,相應的勞動報酬份額也就會越高。用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hu=ln(∑7j=1(ajit×mj)),把教育層次分為7個,j=1,2…7分別對應沒上小學、小學、初中、高中、專科、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分別對應的學習年限mj為0、6、9、12、15、16和19年,ajit表示的是在第t年i地區的就業人數中j教育層次的勞動力所占的比重,并取對數。
貿易開放度(open)。對外貿易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有兩種解釋,一是,根據赫-俄(H-O)理論,對外貿易會使得相對豐富要素的價格得到提高,對中國來說,會提高勞動收入份額;二是,對外貿易強化了資本的談判力量,勞動力的談判能力減弱,從而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用進出口總額在GDP中所占比重表示。
財政支出(gov)。政府的財政支出將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對發達國家則不然,甚至出現赤字對勞動收入占比的提高也有正向的促進作用[24]。用政府的財政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來表示。
本文選取除西藏外2003-2017年中國大陸31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為樣本;工資扭曲的原始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勞動收入份額、外商直接投資、融資能力、貿易開放度以及財政支出的原始數據來源與各省歷年統計年鑒;資本密集度和人力資本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以及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同時使用線性插值法補齊少量缺失數據。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四、實證檢驗及分析
就上文對外資、勞動力的工資扭曲以及其他因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進行的理論分析,進行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初步估計的結果如表2所示,在依次控制了省份和時間固定效應,R2值逐漸增大,外資和勞動力的工資扭曲都顯著的抑制了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這印證了前文的機制分析。但是,由于外資和工資扭曲都抑制了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較低的勞動收入份額,降低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甚至高素質人才的流失,限制了企業的生產和利潤的提升;進而又由于企業利潤的低下,勞動者的報酬更得不到相應的保障,這就加劇了工資的扭曲。由于存在上述的雙向因果關系,可能會存在內生性問題,因此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內生性問題的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進一步檢驗。
(二)系統廣義矩估計的結果
使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前提是殘差項存在一階序列相關但是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而且要求工具變量的嚴格外生性,因此首先進行Arellano-Bond序列相關檢驗和Sargan檢驗。根據實證的結果,AR(1)p值為0.0000,小于0.05,模型存在一階序列相關;AR(2)p值為0.2864,大于0.1,因此不存在二階相關,Sargan統計量的p值為1.0000大于0.1,這表明所選擇的工具變量及滯后期數是合理的。
由表3可知,滯后一期的勞動收入份額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上一期的勞動收入份額會影響到當期,存在明顯的“路徑依賴”。由于工資具有黏性,不會在短期內瞬間進行調整,加上工資的制定會受到前期工資的影響,因此,勞動收入份額表現出動態延續性。
無論是靜態面板的固定效應模型還是動態面板的系統廣義矩估計模型,都表明外資的進入、勞動力的工資扭曲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理解這一結果。
外資的進入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第一,從對勞動者報酬的影響看,外資進入要和內資爭奪勞動力,加大了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因此,為了吸引勞動力尤其是高技能的勞動力,外資有提高工資的動機;外資的進入還加快了東道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生產效率較低的企業就會從市場退出,勞動力也會相應的被轉移到生產效率更高的企業,這都有利于勞動收入的提高。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可能在給予外商各種優惠時損害勞動者的利益,以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促進外資的進入,加上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外資可能會壟斷勞動力市場,勞動者的談判勢力被弱化,這樣工資水平就會處于比較低的水平。第二,從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看,外資的進入帶來的先進的技術和管理,這會通過技術溢出至其他企業,且國內企業進行的模仿創新,都會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對式(9)中的α和β進行估計,其值分別為1.4064和3.1959,因此外資的進入對工資產生的正向影響小于對勞動生產率的正向作用,因此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
工資扭曲也會降低勞動收入份額。第一,從對勞動者報酬的影響看,由于戶籍制度、城鄉二元邊際等因素所導致的工資扭曲,使得勞動者不能在城鄉、區域和行業之間自由的流動,不能獲得與其邊際產出相等的工資水平。第二,從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看,由于長期存在的勞動價格扭曲,勞動密集型企業就會發展過度,企業長期位于生產活動的低端,沒有動力進行研發、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力的工資水平較低,他們會去尋求新的工作機會,尤其是高人力資本者,由于得不到預期的工資水平,會選擇“用腳投票”,導致企業高人力資本流失,抑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通過估算,得到工資扭曲對勞動報酬和生產率的影響分別為-0.3343和-0.2411。
從外資和勞動力的工資扭曲的交互項看,兩者的共同作用顯著的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外資進入對工資扭曲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和邊際產出來實現的。一是,外資的進入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水平,通過技術溢出提高了資金流入國勞動者的邊際產出,加劇了工資的扭曲;但是外資的進入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被配置到所需的部門,所獲得的報酬也會增加,這緩解了工資的扭曲程度。二是,外資企業通過工資溢出和制度溢出,加快了東道國的要素市場改革進程,生產率較低的企業退離市場,同時釋放生產要素給生產率較高的企業。隨著勞動和資本流動到生產率較高的企業,獲得較高的報酬,外資的進入緩解了工資扭曲,外資和工資扭曲的共同作用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fdi×distl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了勞動力工資扭曲的加劇會弱化外資對勞動收入份額提升的抑制作用。由方程(13)可以得到,lsfdi=φ1+τdistlφ1<0,τ>0,這表明,隨著工資扭曲的加劇,外資對勞動收入份額的抑制會得到緩解,原因可能是勞動的邊際產出的增速大于工資的增速,外資的進入對工資的影響要大于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最終導致隨著邊際產出的不斷增加,企業的銷售收入和利潤也隨之增加,根據租金分享理論④,以及外資進入的工資溢出效應,勞動者的報酬水平及份額也會得到提高。
其他因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資本密集度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勞動和資本之間存在替代關系,隨著資本使用數量的增加,資本不斷深化,勞動的使用數量就會減少,導致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25]。融資能力的系數顯著為正,融資能力較強,企業容易獲得資金來投資生產,增加勞動力的使用數量,支付勞動力的報酬。人力資本的系數顯著為正,人力資本的增加會提升勞動收入份額。雖然我國的勞動力數量較多,但是人力資本還是比較短缺,特別是擁有高人力資本者,往往代表著較高的勞動技能,其具有較高的工資談判能力,從而對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產生正向作用[26]。貿易開放度的系數顯著為負,這主要是由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對外貿易強化了資本的談判力量,勞動的談判勢力被削弱,從而使得勞動報酬份額下降。財政支出的系數顯著為正,這一結論與已有研究一致,財政支出對于改善一國尤其是貧窮國家的勞動報酬份額具有正向作用[27]。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得到穩健的結果,要檢驗外資和勞動力的工資扭曲對勞動收入份額影響的穩健性,本文采用剔除異常點和更換工資扭曲的度量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1.剔除異常樣本點。我國經濟發展區域差異較大,勞動力的工資扭曲程度也不同,同樣考慮勞動收入份額可能會受到異常高低值的影響,把樣本區間內工資扭曲程度低于均值3%或者大于97%的分位數剔除,對剩下的樣本重新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的(1)列所示。
2.勞動力工資扭曲的再度量。通過生產函數所計算的工資扭曲指數可能會由于所選擇的函數具有不同形式而使得所得到的結果不穩健,因此我們選用C-D生產函數對工資扭曲指數重新進行計算,并將得到的結果代入模型(13)重新估計,結果如表4的(2)列所示,這兩種方法都證明本文所得到的結論是穩健的。
五、結論和建議
研究表明:(1)外資進入和工資扭曲都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但隨著工資扭曲的加劇,弱化了外資對勞動收入份額的負向作用。(2)地方政府為以低成本吸引外資,影響和控制勞動力價格,不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3)隨著資本密集度的提高,資本深化,替代了勞動要素;人力資本,特別是高水平人力資本缺乏,工資議價能力較弱;戶籍制度、城鄉二元分割導致勞動力流動不暢,勞動力配置效率不高等,都抑制了勞動工資份額。另外,現實地看,中國的外資有將近40%是“回流型”的(Xiao,2004),看中的是中國低價的勞動力和政府給予的各種政策優待,這種外資的進入使得工資提升的空間非常有限[28]。
應該說外資的進入對我國經濟發展,無論是在規模還是在質量上的作用是極大的,促進勞動份額的提高有利于經濟質量的提升和產業發展方式的轉型,在發展中解決問題。除此,有關政策制度也須相應改進。首先,要抑制地方政府在引資上的惡性競爭,讓外資流入在彌補資本不足的同時,削弱資本的談判地位,同時有效的與勞動要素結合改善勞動收入分配現狀;其次,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加快要素的市場化改革進程,推進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的建立,加強工會的力量來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此外,繼續加大財政支出,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保持良好的融資環境都是政府可以改善勞動收入份額的可選手段。
注釋:
① 經作者計算,絕大多數省份都存在工資的向下扭曲,因此,本文所提及的工資扭曲均為工資的向下扭曲。
③ 這里不再詳細展示工資扭曲的計算結果,歡迎有興趣的讀者向作者索取。
④ 如果企業的盈利能力增加,那么工資水平也會通過利潤分享而得到提升(McDonald和Solow,1981)。
參考文獻:
[1] 鄒薇,袁飛蘭.勞動收入份額、總需求與勞動生產率[J].中國工業經濟,2018(2):5-23.
[2] 白重恩,錢震杰.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統計數據背后的故事[J].經濟研究,2009(3):27-41.
[3] 羅長遠,張軍.經濟發展中的勞動收入占比:基于中國產業數據的實證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9(4):65-79,206.
[4] 李稻葵,劉霖林,王紅領.GDP中勞動份額演變的U型規律[J].經濟研究,2009(1):70-82.
[5] 王林輝,袁禮.有偏型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變遷和中國要素收入分配格局[J].經濟研究,2018(11):115-131.
[6] 姚毓春,袁禮,王林輝.中國工業部門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基于技術進步偏向性視角的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14(8):44-56.
[7] Bentolila S. and G. Saint-paul.Explaining Movements in The Labor Share[J]. B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3(1):1-33.
[8] 戴小勇,成力為.出口與FDI對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影響[J].世界經濟研究,2014(8):74-80,89.
[9] 蔣為,黃玖立.國際生產分割、要素稟賦與勞動收入份額:理論與經驗研究[J].世界經濟,2014(5):28-50.
[10]Karabarbounis L. and B. Neiman.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1):61-103.
[11]邵敏,黃玖立.外資與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基于工業行業的經驗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0(4):1189-1210.
[12]郭玉清,姜磊.FDI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理論與中國的實證研究[J].經濟評論,2012(5):43-51.
[13]徐圣.外商直接投資的階段性與區域性特征——基于勞動收入比重的視角[J].世界經濟研究,2015(3):38-46,127-128.
[14]Decreuse B. and P. Maarek. FDI a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 Mpra Paper,2008.
[15]王雄元,黃玉菁.外商直接投資與上市公司職工勞動收入份額:趁火打劫抑或錦上添花[J].中國工業經濟,2017(4):135-154.
[16]Dasgupta K. Learning and knowledge diffusion in a global econom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2):323-336.
[17]Neumayer E. and Soysa I. De.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ght to free Associ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J]. World Development, 2006(1):31-49.
[18]Brown D. K.,and A. V. Deardorff, and R. M. Stern. The Effects of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on 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NBER Working Paper, 2003.
[19]高帆.什么粘住了中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翅膀[J].當代經濟科學,2008(2):1-10,124.
[20]安孟,張誠.外資進入能改善中國的工資扭曲嗎?——基于中國省級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9(8):63-75.
[21]楊振兵.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分割與產能過剩治理[J].國際貿易問題,2015(11):121-131.
[22]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35-44.
[23]Harrison A. E. 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r,s Share? 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R].UC-Berkeley and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24]Diwan I. Labor Shares and Globalization[R].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0
[25]王宋濤,朱騰騰,燕波.制度環境、市場分割與勞動收入份額——理論分析與基于中國工業企業的實證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17(3):70-87.
[26]魏下海,董志強,趙秋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勞動收入份額:理論與經驗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12(2):100-119.
[27]方文全.中國勞動收入份額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結構調整抑或財政效應?[J].金融研究,2011(2):32-41.
[28]Xiao 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Round- Tripping FDI: Scal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R].LAEBA Working Paper, 2004.
Abstract: The paper brings FDI and labor′s wage distortion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andanalyzes systematically their impact on labor income share.Using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method of surpassing logarithmic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wage distortion index of Chinese mainland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s calculated, and China′s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of 2003-2017 years are used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labor income share.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entry of foreign capital and wage distortion reduce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but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wage distortio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foreign capital o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s alleviated; in addi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vestment policies, the decline in the use of labor factors, the relatively large deepening of capital, the lack of high-level human capital, the poor flow of labor, and the low allocation efficiency all inhibit the increase of labor wage share.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necessary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in the policies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ctor market, and increasing financial support.
Key words:FDI; wage distortion;labor income share
(責任編輯:嚴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