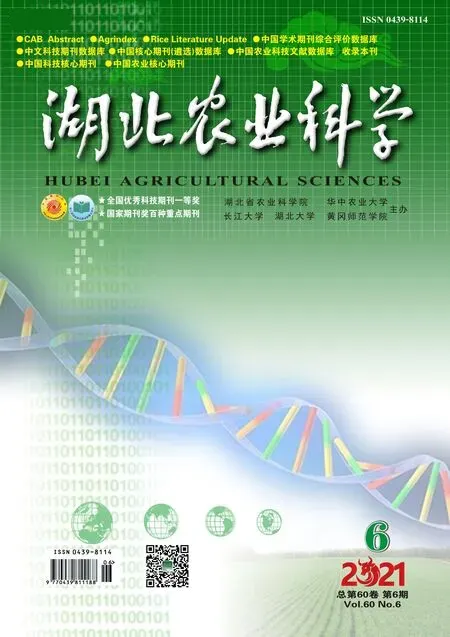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時空特征分析
王清君,杜 筱
(河海大學理學院,南京211100)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資源、環境密不可分,環境在為人類提供物質基礎的同時,也會通過自身承載力對人類活動起到約束作用。合理開發及利用資源和環境可以造福人類;反之,過度開發資源會帶來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等一系列問題,從而影響人類自身發展[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人口數量持續增加且生活條件不斷改善,對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再加上工業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對資源的開發利用強度,環境問題日益嚴重,這使得人地關系趨于緊張,矛盾更加突出[2]。
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物質保障和不遺余力追求的目標,如何協調三者之間的關系備受關注。在研究區域方面,對中國東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研究較多,多涉及山地、高原等[3-5],如陳武蘋等[3]通過主成分分析法研究2006—2015年黔西南州人口、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度,指出該區域協調發展穩定性不高,波動性較大,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等問題。在空間范圍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級、市級、城市群等尺度[6-10],如秦泗 剛等[7]利用耦合協調度 模型分析2000年以來克拉瑪依市人口、經濟、環境系統的耦合協調狀況,結果表明該市發展類型依次分為人口主導經濟滯后型、人口主導環境滯后型、經濟主導環境滯后型。在研究方法方面,關于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關系的評價方法多樣化,包含變異系數法、模糊及灰色理論法、系統動力學方法、數據包絡分析法等[11-14],如王利香等[12]利用灰色關聯度模型測算2013年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人口結構與資源、環境的系統耦合度,結果顯示人口結構中與資源、環境關聯度最大的是中等教育人口數量和城鎮人口數量,關聯度最小的是文盲人口數量。目前,學術界關于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富,但由于中西部地區資源、環境較為脆弱,關于中西部地區的研究明顯多于東部沿海地區;此外,已有研究大多關注系統協調度在時間或空間單一維度上的變化趨勢,而涉及時空二維特征的研究較少,不能充分揭示協調度的時空變異屬性。
江蘇省位于中國大陸東部沿海中心,水資源充沛,且動植物資源豐富。作為人口大省和經濟強省,2018年江蘇省常住人口位列全國第五,達8 050.7萬人;地區生產總值位列全國第二,達92 595.4億元,僅次于廣東省。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江蘇省人口規模不斷擴大,人均資源減少、環境狀況惡化等問題日趨嚴重。此外,江蘇省存在明顯的蘇南-蘇中-蘇北區域分化,加上受自然條件、經濟發展及社會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各地區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發展差異明顯。
從時空角度出發,探討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關系,對該區域系統的協調發展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構建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結合協調發展度測算模型,計算江蘇省2010、2015、2017年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度,進一步分析其時空特征。
1 指標體系及研究方法
1.1 構建指標體系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15-17],根據數據的系統性、層次性、發展性及可獲取性等原則,結合江蘇省的發展特征,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指標框架設定為3個系統。其中,人口系統主要考慮人口規模、人口結構和人口素質3個方面;資源系統主要考慮資源稟賦和資源利用2個方面;環境系統主要考慮環境壓力和環境響應2個方面。具體指標名稱及指標屬性見表1。

表1 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1.2 研究方法
1)數據標準化。由于指標有正有負,因此采用較為穩健的標準化公式,即陳守煜[18]提出的標準化公式來消除指標的正負性,具體公式如下。
正向指標:

負向指標:

式中,xij為第i個系統第j個評價指標的指標值,xˉij為xij標準化處理后的結果。
2)指標權重。由于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在計算指標權重時,將立體數據轉化為平面數據存在缺陷。基于此,引入郭亞軍[19]提出的基于時序動態視角的縱橫向拉開檔次法來確定指標權重。
假設關于n個被評價對象,取定m個評價指標r1,r2,…,rm,且按時間順序t1,t2,…,tN,獲得數據{rij(tk)},構成時序立體數據表。對時刻tk取綜合評價函數:

式中,qi(tk)為tk時刻第i個評價對象的綜合評價值,rij(tk)為tk時刻第j個評價指標經過標準化處理后的指標值,wj為第j個評價指標對應的權重。
構造qi(tk)的總離差平方和:


若限定ωTω=1,當ω取對稱矩陣的最大特征根對應的特征向量時,σ2取值最大;當Hk>必有H>0,且有正(經歸一化處理)的權重向量ω。最后經歸一化處理后的特征向量即為指標權重。每個系統的最終得分為:

式中,Ui為第i個系統的最終得分為第i個系統第j個評價指標標準化處理后的結果;wij為對應的指標權重。
3)協調發展測算模型。變異系數協調度又稱為離散系數協調度。對3個系統而言,變異系數協調度為:

當U1=U2=U3時,協調系數為1,3個系統呈最佳協調狀態。當U1、U2、U3數值不全等時,樣本值越接近,協調度越大,反之則協調度越小。然而,在有些情況下,協調度C很難反映人口、資源、環境的整體發展水平,因此,引入協調發展度D,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T為調節系數,反映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的整體水平,D為協調發展度,C為協調度,α、β、γ由縱橫向拉開檔次法計算得到。根據式(9)計算出的協調發展度介于0~1,數值越大表明系統間的協調發展度越高,反之則協調發展度越低。
1.3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江蘇統計年鑒》(2011—2018年)、《江蘇省人口生命表匯編》(2010年)、《江蘇環境狀況公報》(2010、2015、2017年)以及各省轄市《環境狀況公報》(2010、2015、2017年)等。
2 結果與分析
2.1 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
根據式(6)計算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江蘇省13市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逐年上升,但變化情況略有不同。
1)2010年蘇南人口系統綜合評價得分稍高于其他地區,隨著時間的推移,2015年蘇南地區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的快速增加,使得該區域人口系統得分不斷提高,與蘇中、蘇北的差距不斷擴大,逐漸形成蘇南高、蘇中蘇北低的格局,并持續至今。
2)3個時期江蘇省資源系統綜合評價得分均呈蘇南最低、蘇北次之、蘇中最高的態勢。其中,由于鹽城市較高的人均房屋建筑竣工面積,其資源系統綜合評價得分相對高于蘇北其他4市。

圖1 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
3)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江蘇省各市不斷加強環境保護力度,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和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等指標逐漸提高,環境質量有所改善,但環境治理并非朝夕之事,因此環境系統綜合評價得分雖然在不斷提高,但變化幅度不大,區域發展基本均衡。
2.2 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度
根據計算出的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結合協調發展度測算模型,得到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度,見表2。
由表2可知,江蘇省整體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度逐年提高,且13個省轄市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度均呈上升態勢。其中,南京市作為省會城市,人口、資源、環境的發展程度相對匹配,其協調發展度在3個時期一直居于首位,2010年南京市的協調發展度比排名最后的徐州市高0.107 3,可能是由于徐州市較大的人口規模與較低的人口素質導致其人口系統發展緩慢,與資源、環境系統發展不同步。
為更好地運用協調發展度來探討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情況,在參考已有研究[20,21]的基礎上,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度劃分為6個等級,如表3所示。不同類型對應不同的協調發展度等級,等級越高表明該地區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態越好,反之則表明該地區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態越差。
2.3 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時空特征分析
根據協調發展度等級劃分結果,通過ArcGIS軟件繪制得到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時空分布,如圖2所示。
整體來看,2010—2017年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等級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區域協調發展變化速度不一致。具體而言,2010年徐州市的協調發展度最低,僅為0.477 4,處于I等級;南京市、鎮江市、揚州市3市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度相對較高,分別為0.584 7、0.554 4和0.564 6,同處于III等級;其他城市的協調發展度介于0.50~0.55,處于II等級,這表明江蘇省絕大部分城市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度不高。
2015年13個省轄市的協調發展等級發生明顯變化。南京市與鎮江市由于人口系統的大力發展,與資源、環境系統更加匹配,協調發展等級由III等級迅速發展為V等級;蘇南其他地區與蘇中3市均加入到中級協調行列,處于IV等級;蘇北地區人口系統發展較慢,與資源、環境系統的差距較大,系統協調發展狀況較差,淮安市的協調發展度由0.534 8提高到0.543 9,但協調發展等級未提升;除淮安市外,連云港市、宿遷市、淮安市、鹽城市的協調發展度均在0.55~0.60,處于III等級。雖然2015年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況已得到改善,但仍未有城市的協調發展度達0.70(VI等級)以上,這表明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態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表2 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度
2017年,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況進一步優化,總體呈南高北低的格局。與2015年相比,蘇南的南京市、鎮江市逐漸發展到VI等級;蘇錫常則由IV等級發展到V等級;蘇中3市的協調發展等級未發生變化,仍處于IV等級;淮安市的協調發展等級由II等級提高至III等級,蘇北其他地區的協調發展等級同處于III等級。至此,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等級南高北低的格局初步形成。

表3 協調發展等級劃分

圖2 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時空分布
2.4 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影響
人口-資源-環境系統與經濟系統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一定數量與質量的人口會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但如果區域人口數量過多,增長過快,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加劇將不利于資金積累,嚴重阻礙經濟發展。資源和環境是經濟發展的源泉,經濟依托于資源和環境,資源和環境對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堅定的支撐作用,而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將會制約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為進一步探討人口-資源-環境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影響,擬采用回歸估計進行分析。由于沒有足夠多的數據進行條件最大似然估計,而無法進行固定效應面板Tobit回歸,可選擇混合面板Tobit模型和面板隨機Tobit模型。本研究利用江蘇省2010—2017年13個省轄市數據進行分析,屬于短面板數據,可以認為各個城市之間存在個體差異,故采用面板隨機Tobit模型進行分析。以人均GDP為被解釋變量,以人口、資源、環境3個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與協調發展度為解釋標量,運用面板隨機Tobit模型,對江蘇省13個省轄市相關數據進行回歸估計。其中,模型1只對人口、資源、環境3個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進行回歸,模型2加入協調發展度,回歸結果見表4。

表4 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回歸結果
1)從回歸結果來看,模型1人口-資源-環境系統對人均GDP的影響都為負,而模型2顯示協調發展度對人均GDP的影響為正。這表明任何一個單一系統對經濟系統而言都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但3個系統的協調發展度對經濟系統起到促進作用。因此,要想使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需正確處理好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實現3個系統的高質量協調發展。
2)模型2的參數估計數值顯示資源系統的彈性系數最大,人口系統次之,環境系統最小。一方面,可能是在計算協調發展度時資源系統的4個指標都是正向指標,而人口系統和環境系統的指標有正有負,在一定程度上負向指標會削弱正向指標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能與資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有關,隨著資源的不斷消耗,經濟發展緩慢,效益降低,需要大量資金和高新技術來開發利用新能源,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因此,資源系統回歸系數高于人口系統與環境系統。
3)總之,實現區域經濟發展不是單純依靠某一系統,應保證各系統之間相互協調,彌補其他系統的不足,這就要求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合理利用現有資源、發展綠色新能源、保護生態環境、提高環境質量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可持續經濟,最終促進區域經濟整體的進一步發展。
3 小結與討論
本研究從人口、資源、環境3個方面構建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縱橫向拉開檔次法計算3個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運用協調發展測算模型對江蘇省及13個省轄市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度進行測算,探討人均GDP與人口、資源和環境系統的關系,得到如下結論。
1)江蘇省及13個省轄市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逐年上升。其中,人口系統綜合得分呈蘇南高、蘇中蘇北低的格局;資源系統呈蘇南最低、蘇北次之、蘇中最高的態勢;環境系統區域發展相對均衡。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江蘇省整體及13個省轄市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度均呈上升態勢。其中,南京市作為省會城市,人口、資源、環境的發展程度相對匹配,其協調發展度在3個時期一直居于首位。
2)從整體來看,2010—2017年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區域協調發展變化速度不一致。2010年,江蘇省絕大部分城市3個系統的協調發展度并不高,且無空間分化;2015年,這一局面有所改變,3個系統的協調發展度逐步形成蘇南蘇中高、蘇北低的態勢;2017年,3個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況進一步優化,總體呈南高北低的格局。
3)人口-資源-環境系統對人均GDP的影響為負,而3個系統的協調發展度對人均GDP的影響為正,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單一系統對經濟系統而言存在一定抑制作用,實現區域經濟發展不是單純依靠某一系統而言,必須保證系統之間相互協調,在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的同時,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最終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4)江蘇省人口-資源-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度逐年提高,但仍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且區域分化較為明顯。基于此,江蘇省應強化蘇南-蘇中-蘇北三大區域互動發展,以創新引領和轉型升級為重點推進蘇南提升,以融合發展和特色發展為重點推進蘇中崛起,以“四化”聯動和開放帶動為重點加快蘇北振興,同時繼續推動資源共享,利用“飛地經濟”模式促進區域融合發展,不斷加強區域合作,縮小區域差距,促進江蘇省整體高質量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