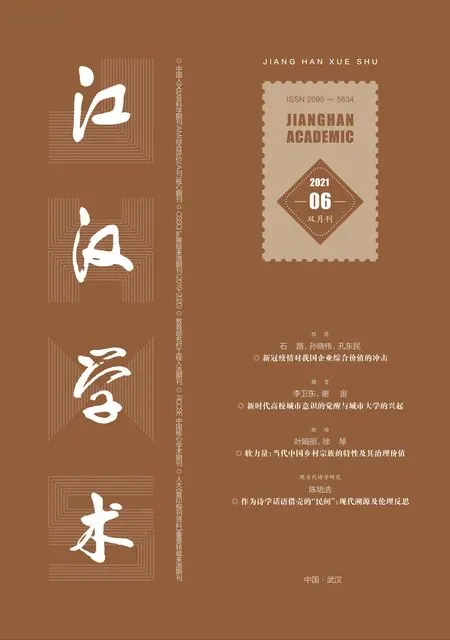論司法裁判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
——以一審二審法院對“電梯勸阻吸煙案”等的不同判決取向為考察中心
徐肖藝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法學院,武漢430073)
2017年5月2日,河南鄭州醫生楊歡在電梯內勸阻老人段肖禮吸煙并與之發生爭執。調取發生地和發生時段的監控視頻,可以看到楊歡在整個勸煙過程中語氣較為溫和,與段肖禮僅僅發生語言上的爭執,未有肢體接觸。被勸煙者段肖禮由于情緒激動不能自制,引起心臟病發作而猝死。段肖禮家屬訴至法院,請求楊歡予以侵權賠償。2017年9月4日,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一審,一方面否認楊歡行為與段肖禮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另一方面又肯定段肖禮猝死于二人爭執之后。依照《侵權責任法》第24條公平責任原則①,在行為人和受害人對損害的發生均無過錯情況下,判決楊歡向死者家屬補償1.5萬元。一審判決后,原被告雙方均表示不滿,但被告方并未上訴,反而是原告方段肖禮家屬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一審錯誤適用《侵權責任法》第24條的規定,楊歡在密閉的公共場所內勸阻吸煙,符合社會一般倫理規范要求,勸阻行為并無語言或肢體上的不當,在通常情況下不會造成他人情緒激動而發生猝死的后果,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因此不滿足公平責任原則適用的構成要件。且楊歡的勸阻吸煙行為是在自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本應受到鼓勵,一審判決要求楊歡承擔補償責任是對這種行為的打壓,不僅挫傷公民依法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積極性,而且還有悖于民法的立法宗旨。故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適用法律錯誤為由撤銷一審判決,駁回上訴人全部訴訟請求②。這個案子的典型性在于,一審法院依據公平原則判決沒有過錯的一方向死者家屬補償1.5萬元,會挫傷公民依法維護自身和社會公共利益正當行為的積極性,二審法院在沒有當事人請求的情況下直接作出改判也反映出本案的獨特性。此案被寫進了201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入選《人民法院報》編輯部評選的2018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之首,其影響大大超過其他同類型案件,是分析比較一二審判決效果取向之不同的典型案件。
這個案件引發人們的思考:一審法院為何明知適用公平責任原則有構成要件瑕疵,卻依然選擇適用該款作出裁判?二審法院在一審被告未上訴的情況下對該案改判,直接做出不利于上訴人的判決,是基于何種考量標準?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需要從一審、二審法院肩負的使命以及對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在不同審判階段的考量入手。
一、一審、二審法院裁判中的司法效果定位
依據《民事訴訟法》,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實行兩審終審制,這里的“兩審”指“一審”和“二審”兩次有先后順序和不同審級的審判。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以下三種情形的第一審民事案件,分別是: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除這三種情形外的第一審民事案件均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因此對于絕大多數的一般民事案件,一審法院是基層人民法院,二審法院是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二審法院作為不同的審判層級,代表同一案件不同的審判階段,分析他們對同一案件的認定過程中考量因素的變化,可以發現不同層級法院的功能及所承擔職責的“天然”差異,以及在不同階段的不同側重最終對案件走向的影響。
(一)一審法院側重社會效果
一審法院綜合該案的案件事實,且著重注意到了該案實際產生了猝死的不利結果。基層法院作為接觸社會民意最前線的法院層級,肩負著快速解決糾紛,平息當事人激情憤懣的使命。法官作出裁判的重心并不完全是法律所要求的結果,而更多是社會所要求的結果,需要充分發揮法律“定分止爭”的社會調控功能。通常會要求一方在法律面前“退一步海闊天空”來補償另一方所受到的損害,從而達到平衡雙方利益的社會效果,以息事寧人,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一審法院在對該案進行法律依據找尋時,發現法律規則不適用于該案,但是“潛意識”里又期盼作出有利于雙方接受的判決結果,公平責任原則當然是不二之選。原因在于,公平責任原則在無明確法律規則可依的具體案件中的適用是相對“保險”的,法官可以依該原則達到平衡雙方當事人的效果,作出的裁判更易被接受。尤其是在造成人員傷亡等不利后果的案件中,在“死者為大”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驅使下,不僅大眾更容易對有傷亡一方的當事人給予同情,而且該方當事人也需要法律的“安撫”,甚至法官自身的情感偏向以及追求裁判穩妥性也會讓他們有這種顧慮——若嚴格以法律為據,作出的裁判可能會違背社會公眾意愿和法律預期,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爭論,對司法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同時也會對自己的審判生涯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在處理這類案件時,法官通常的做法是采取一種相對柔和、不易出“大差錯”的手段。在該案中,一審法院其實也不過是采取了維護社會效果的最常用的方法,即行為人的行為即使與損害結果并無因果關系,也要給予受損害一方補償。如果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有因果關系,那么行為人給予受損害一方的就不是補償而是賠償了。“補償”取代“賠償”,說明判決不是基于法律效果而是社會效果。
該案中如果依“社會公共利益”進行裁判,會得到完全相反的判決結果,即楊歡的行為是出于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承擔了文明社會中公民應承擔的義務,該行為是值得贊揚的,因此勸煙者楊歡不必承擔1.5萬元的補償責任。然而,一審法院的法官并未以此為依據作出判決,而是選擇了裁判可能引發的社會效果作為著重考量的標準,以期完成對良好社會效果的維護。究其原因,本文認為有如下三點:第一,出于情、理的考量。被勸阻吸煙者段肖禮在該案中由于心臟病突發而猝死,此情形下若勸阻吸煙者楊歡不承擔一定的責任,從道義上來講,段肖禮的死亡似乎太讓人唏噓。對于造成死亡的案件,公眾在情感上引發的共鳴和道德上對案件的審視,使得審判法官無法跨越社會效果而直接強硬地追求法律效果。第二,出于對判決可能引發的社會效果的“預測”。“民事司法的方法是一種社會活動,而不是單純的司法概念邏輯的推演,這就意味著民事司法需要更緊密結合社會的需要。”[1]判定楊歡無責可能會在社會上引起對判決公平性的質疑,不利于平訴息訟。而基于公平責任原則由雙方分擔損失,是對亡人家屬的慰藉,勸阻吸煙者楊歡在此判決下未遭受太大損失,不僅裁判做到了對雙方利益的兼顧,同時法院的工作也更易得到雙方當事人的認同和理解,能更快推動該案的解決。第三,鄉土社會下對基層法院的“功能期待”。在當前,基層法院的大量工作仍是接收、處理最基層的民意和訴求,發揮的主要功能依然是解決糾紛,如果糾紛的處理無法得到雙方當事人的認同,即使法官是依法公正裁判也可能無法取得滿意效果。是嚴格依據法律規定作出判決,將法律效果視為裁判的根本目標,還是在裁判中對有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提前預判,在判決形成過程中加以考量,這對基層法院的法官們提出了相對較高的衡量要求,使法官們背負了除精準用法、依法裁判外更多的負擔。一般說來,一審基層法院直接處于基層社會的包圍之中,身臨其境的現實、和雙方當事人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現實、能夠直接聽到對判決評頭論足的現實,都迫使法官在判決時向社會效果傾斜,主要關注點落在如何解決糾紛和穩定社會。在這里,法律規范的選擇和案件事實的定性雖然很重要,卻并非判決結果的首要考量,判決結果的首要考量是拿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方案,以便雙方都能夠接受法院的判決以定分止爭,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有關的法律規定往往只是法官處理問題的一個正當化根據,或是一個必須考慮甚或是在一定條件下必須有意規避的制約條件[2]。過分拘泥于法律規定和讓步于法律規則所具有的空白、不良、矛盾、模糊四大缺陷而忽視中國當下的國情、社情、民情、輿情,即使嚴格做到了依法審判,也可能陷入機械司法的泥潭,也可能達不到司法所追求的效果,甚至可能激化社會矛盾。中國的一審基層法院處于鄉土社會,這是一個熟人社會,解決糾紛以便日后和睦相處是法院的一個重要目標。
在本案中,法官綜合衡量后選擇適用公平責任原則,雖發揮了一審法院的糾紛調解作用,初衷是好的,但卻違反了公平責任原則的立法價值和內在精神,造成了法律價值的缺位,法律效果的折扣。且判決一出引起了強烈的社會輿論抨擊,嚴重沖擊了公眾的道德觀念,裁判結果不僅無法令當事人滿意,而且使社會普遍善良情感遭受沉重打擊,因此本案的一審判決相當于“賠了法律效果又折社會效果”。
(二)二審法院側重法律效果
追求判決的法律效果,要求法官在進行司法活動時要牢固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嚴格依據法律規范對案件開展審判,根據案件特性準確找尋法律依據,作出的裁判也應于法有據,符合法律的內在標準和價值要求;確定作為大前提的法律規范和作為小前提的案件事實之間的嚴格邏輯關系,并根據這種邏輯關系得出確定且正確的判決結論。通過司法判決實現個案正義和社會公正,維護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權威性。追求判決的法律效果,就是要求判決結論來自案件事實與法律規范的邏輯關系,而不是來自法外的各種社會因素的考量。
事實因素是指導案件裁判的基礎和核心,也是指導法官選擇法律適用的類型以及具體適用條文的基礎,法官需要以案件事實為基礎進行法律適用的選擇。而一審法院由于對事實的邏輯結構把握不清晰,導致適用法律時未能正確援引法律規范,破壞了規范背后蘊藏的價值理念,所以該判決是不能被支持的。楊歡電梯勸煙并非社會異類或特例,一個有責任心、具有道德風尚的公民遇此情形可能都會采取勸阻行為,他不僅在維護自己的健康權益,也是在維護他人的健康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本應值得贊揚,一審判決卻予以打壓。不僅法律效果不佳,而且在社會效果上,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會穩定,但在弘揚正氣等社會效果上卻是負面的。段肖禮的猝死本是無法預見的,正常的勸阻吸煙行為與突發的猝死結果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鏈條被切斷,而“公平責任原則”的適用是以當事人一方的行為確實導致了另一方損失為基礎,所以一審法院適用公平責任原則,讓在法律范圍內勸阻吸煙的楊歡承擔部分損害補償責任,是不正確的。“如果為了實現某個具體的價值目標而動輒使法律的安定性受到損害,則法治就成了一個無意義的名詞。”[3]
從二審法院對一審判決的改判來看,二審判決嚴格依照法律規定,遵循演繹推理的邏輯方法,加之以充分的說理,使得該案中“法律”與“事實”之間的裂縫得以彌補,完成了對裁判法律效果的追求。二審判決否定了一審法院對公平責任原則的適用,將一審法院的判決結果予以修正,阻止了可能引發的道德風波。對于該案來說,這一判決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又存在兩個不可回避的問題。第一,二審法院在被告未上訴的情況下,免除一審判決中對被告楊歡的判罰,是否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干預,值得探討;是否有違《民事訴訟法》中的程序正義要求,也值得思考。第二,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由作出裁判,是否會造成“公共利益”的濫用,值得深入研究。既然一審法官以《侵權責任法》第24條作為該案的判決依據,二審法院的判決也應在侵權責任的認定上斟酌,“我們一定要明白楊先生是在電梯這個特定地點勸段先生不要吸煙的,且是和平的話語。我們都知道電梯里吸煙的各種特定意義,尤其是楊先生作為醫生對電梯里吸煙危害性的理解,因此楊先生的這種行為不是侵權而是維權,他當然是維護自己的權利,其實也是維護他人的權利,維護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法律應該鼓勵而不是懲罰楊先生的維權行為。如果說此案中有侵權責任,那也是段先生侵犯了楊先生的生命健康權,而不是一個反向的理解”[4]。二審法院如果給出這樣的判決理由,可能會有更好的法律效果。
二、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三種關系評述
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作為司法裁判中兩個重要的考量因素,兩者孰輕孰重、考量時各個效果所占的比重以及在遭遇不可兼顧的適用矛盾時該如何取舍等問題,一直都備受關注。“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之間的關系走向,以及如何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在理論界引發的爭論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類。
第一,“工具論”。簡而言之,即法律效果是最終達成社會效果的工具,強調法律是服務人民的工具,司法活動的目的是通過審判完成法律效果向社會效果的轉換。這相當于給法律戴上“面具”,司法判決借“法律之名”來實現某種社會目的。法律與社會之間所具有的特殊關系,決定了在司法活動中,不能僅僅對法律進行“公式般”的機械套用,把法律看作死板的計算公式,把法官當成只會簡單運用該計算公式得出結果的工具,這是對法律的完全錯誤認識。“工具論”強調社會效果是目的,法律效果是手段,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因此法律效果只是達到社會效果的工具而已。倡導“工具論”的,認為“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是“主從關系”,“法律效果”要為“社會效果”讓路。“工具論”者為了社會效果可能會放棄“法律至上”的司法底線,將違法辦案粉飾為“追求社會效果”,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法律能夠實現社會效果就適用,不能夠實現社會效果就不用,對法律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這就偏離了法治的軌道,是“工具論”最顯而易見的弊端和風險所在。且社會效果的衡量標準不易把握,它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對于審判的社會效果如何衡量,是該觀點下極易引發的另一問題。不同主體由于其生活經歷、社會認知等的不同,對社會效果的預判可能也不同,相同的一份判決,在有些人眼中可能是合理且滿足了社會效果的,但是在另一些人眼中可能恰恰相反。社會效果的把握與法律效果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
第二,“分離論”。“分離論”看起來是對“工具論”的背反,但與“工具論”一樣是對二者關系的極端認識。“分離論”強調法官嚴格按照法律裁判,法官只是法律的奴仆,在裁判中只是“自動售貨機”式的角色,不能夠有自由裁量權,是機械司法而非能動司法。判決的唯一考量是法律效果,所追求的判決結果僅僅是合法而不需考慮其他因素,如此可能導致判決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對立。其主張兩個效果是可以并且應當分離的,忽視司法實現個案正義的天然使命,對司法權威帶來了較大的損害[5]。“分離論”的實質是通過分離“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而將“社會效果”驅逐出判決的考量,“分離論”所分離的是“社會效果”而非“法律效果”。堅持“分離論”可能會產生法律與社會完全脫節的風險,法官只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任何法律價值判斷,無視司法判決實現正義的目標追求。法官判案時機械地適用法律得出判決結論,當法律規則存在缺陷時,“分離論”仍然堅持機械司法而可能損害社會正義。如環境法等法律適用具有很強的時代性,而立法又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這就導致司法實踐中的機械司法不能夠保護環境侵權中受害人的權益,因此“環境侵權行為即使沒有造成現行侵權責任法上認定的人身與財產損害,但公眾(尤其是潛在買家)普遍形成了該財產承受極大環境風險的擔憂與恐懼所導致該財產價值的貶損,這本身屬于環境侵權行為對承擔環境污名的財產主體導致的損失”[6]。就是說,現行的環境法對于環境污名沒有作出規定,面對該法律漏洞,要反對機械司法,將環境污名造成的價值貶損納入損失賠償范圍,這樣的司法判決才能維護社會效果。
第三,“統一論”。“統一論”強調判決中事實、規范與價值的統一,從而兼顧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是一種“中庸之道”的認識方法。“統一論”要求判決既是依法判決又是可接受性判決。依法判決就是根據案件事實與法律規范的邏輯關系所得出的必然結論,確保司法判決的確定性和判決的法律效果,維護法律權威。可接受性判決就是通過正當程序和商談對話等方法,在判決中吸收各方訴求,考慮各種較為特殊的社會情形和社會的接受程度,確保判決的正確性和判決的社會效果,讓司法真正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
司法判決時片面追求法律效果會導致機械司法,扭曲人們對法律的正確理解,也違背法治所要求的良法善治和法律正義的價值訴求;司法判決時片面追求社會效果會導致“后果主義”司法,消解了法律的權威性和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司法效果的一體兩面體現在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上面,又在司法實踐上相統一[7]。具體表現為:第一,司法判決必須堅持法律效果,判決的唯一準繩和依據是法律,法律之外的各種社會因素只是考量不是依據。社會效果只能來自法律效果,沒有法律效果的判決觸及“依法判決”的底線,也最終沒有社會效果可言。必須承認,我國的立法技藝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立法的科學性不斷增強,制定的法律具有優良性,嚴格依據優良法律所作出的判決是能夠維護社會正義和保證社會效果的。然而繞開法律所作出的違法判決不僅背離法律效果,社會效果也會很糟糕。也就是說,不要把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嚴重對立起來,似乎“取”社會效果就必須“棄”法律效果。恰恰相反,現代法治是良法之治,實現正義是司法的價值追求,社會效果不僅不對立于法律效果,而且是依附于法律效果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為社會效果而放棄法律效果,是主次顛倒和本末倒置。第二,法律具有正義、自由、人權、平等等價值,司法判決要實現這些法律價值,在通常情況下可以做到。但我們也要承認法律規則的缺陷以及法律一般性與個案特殊性之間的縫隙。法官在審理案件時,當依據法律條文所作的形式推理的結果無法實現社會正義,會出現負面社會效果的審判[8]。判決結論是否符合民眾對法律的理解和預期,是否能夠塑造公民的良好行為,是否以正能量引領社會風尚,是否呈現出“看得見的正義”,都是判決正確性和可接受性的衡量指標,也決定著司法判決是否具有可期的社會效果。因此,追求社會效果只是反對機械司法,不是反對依法判決,相反必須堅持依法判決。
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合理共存于司法活動中,產生的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當然這一美好愿景往往在付諸實踐時面臨困境,解決之道是既要依法判決又要反對機械司法。要善于運用法律方法提高適用法律的水平,確保在公正司法中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把握兩個效果,判決的社會效果衡量標準如何統一,在兩者遭遇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時如何取舍,是現在最需考慮的問題。
三、司法實踐中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偉大愿景,需要找到二者統一所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困難,以積極的舉措清除二者統一道路上的障礙。目前最大的問題在于社會效果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導致司法中很難對其與法律效果的統一做到精準把握。“統一論”也有表述不夠明確、理解可能出現歧義、操作顧慮重重等缺陷。一言以蔽之,“統一論”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統一”,是將“法律效果”統一于“社會效果”中,還是“社會效果”統一于“法律效果”中,或者“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在統一體中保持大致相同的比例。無論哪一種情形,都是說起來不難,行起來不易。在平衡統一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中實現司法公正,肯定是有極大難度的,但遠非無路可走,在三種都很艱難的情形中存在較為合理的選項,那就是將“社會效果”統一于“法律效果”中。這是因為:其一,法治社會依法治國,司法權依法獨立行使是司法的首要原則,正如馬克思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9]法律效果是司法判決的首要考量,如果把社會效果放在法律效果之前,那無異于把馬車放在馬的前面,這是對法治社會的消解。其二,法治是良法之治,法治的目標是實現正義,這意味著具有良好法律效果的判決必然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果,反之則不然。因為現代司法判決同時提出了確定性(合法律性)與正確性(合法性)的要求,二者的統一體現出法律效果,而二者中的正確性(合法性)確保判決符合社會正義,實現了判決的社會效果。其三,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只要我們有良好的方法認識法律、解釋法律和適用法律,就能夠克服司法判決中確定性與正確性的矛盾,實現二者的統一,判決在實現法律效果的同時也實現了社會效果。也就是說,司法判決對正確性的要求本身就是反對機械司法,反對違背正義,克服法律規則的四大缺陷,實現社會正義。適用法律的方法較多,如類型化的法律方法,即把法律規則的表述類型化以填補法律規則的漏洞、不良等缺陷。例如,“紅燈停”“公園禁止機動車輛進入”等規定,看起來是概念式的針對所有的車輛,其實是類型式的,即某一類型的車輛。這一規定里的類型并不包含救護車、警車等,因此救護車闖過紅燈、警車進了公園,從法律類型化的角度看,絕非違規而是符合規定,這樣的判決不是損害法律效果而是維護法律效果。這樣的判決保障了救護車及時救人和警察及時打擊犯罪,當然是維護了社會效果。
不能把社會效果簡單地理解為解決糾紛和息事寧人,公平原則也不應成為一審法院為社會效果而開啟的萬能鑰匙,還必須承認社會效果自身具有的強大張力,相反的社會效果往往會同時顯現。以“勸阻吸煙案”的一審判決來說,它確實能夠對受害一方進行一定的補償,平息受害一方的怨氣,具有解決糾紛的社會效果。雖然一審的原告對一審法院所作的出于社會解紛效果的判決并不領情,但也不能否認一審判決的解紛作用。因為一審法院如果一開始就像二審法院那樣判決,原告一方的情緒和憤懣豈不更大?一審法院作為和社會民情最接近的基層法院,它所做出的具有社會效果傾斜性的判決是可以理解的。這起案子的一審如果放在其他法院,大概率也會這樣判。但是正如前述,社會效果自身具有強大張力,一審判決雖然有助于平息糾紛,卻阻礙公民敢于維護自身權利的社會正氣的形成。如果一審判決不被推翻,那么誰還敢在電梯上勸人不吸煙?就如當年的彭宇案導致人們因為害怕被訛詐而不敢救人,或救人之前被迫耽誤寶貴的救助時間先去拍照以防訛詐。因此,筆者并不否認基層法院在一審判決中所具有的社會效果傾向,但不能將社會效果僅僅放在解決糾紛上,還要放在引導公民善良行為和樹立社會正氣等其他社會效果上。否則就會顧此失彼甚至得不償失,為某一方面較小的、暫時的社會效果而失去另一方面較大的、長遠的社會效果。
四、結 語
無論是一審法院還是二審法院,無論是追求社會效果還是法律效果,都應該堅持依法判決。那么,二審判決在被告并未上訴的情況下作出對上訴人不利的改判是不是依法判決呢?這是本不應該有的疑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款第2項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二十三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圍繞當事人的上訴請求進行審理。當事人沒有提出請求的,不予審理,但一審判決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者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權益的除外。”因此,我國的二審法院有超出當事人的上訴請求范圍來作出裁判的法定權力。本案的二審法院認為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和損害公共利益而進行改判,是于法有據的依法判決。本案二審判決一方面糾正一審判決的適用法律錯誤,維護了判決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又糾正了一審判決的損害公共利益錯誤,維護了判決的社會效果。該二審判決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是具有可接受性的判決。本案一審判決一方面為追求息事寧人的社會效果而錯誤適用公平原則,損害了判決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又對維護自己和公共利益的正當行為作出給予對方“補償”的判決,客觀上有損害公共利益的導向,產生了相比“息事寧人”更不利的社會效果。一審判決割裂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關系,是不具有可接受性的判決,被二審法院改判是必然的。二審判決以法律效果為取向,在追求法律效果時也實現了社會效果,且是相比一審判決所追求的社會效果更高的層次;一審法院判決以社會效果為取向,在追求社會效果時也損害了法律效果,且是相比二審法院判決的社會效果較低的層次。“以實現社會效果為由犧牲個案公正的裁判,其所謂的社會效果也難以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可以說,首先確保個案依法裁判的法律效果,是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基礎。”[10]
經此比較,二審法院判決具有更高的境界和質量,對其他類似的判決具有方向引領的作用。例如,此案后又發生一案,路人攔住了與兒童相撞后欲離開的老人,期間老人發病猝死,老人家屬將阻攔者孫某告上法庭。又如2019年12月30日,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人民法院公開宣判了劉某某、郭某甲、郭某乙等訴孫某、物業公司生命權糾紛一案,判決駁回劉某某、郭某甲、郭某乙的訴訟請求[11]。這起案子發生在“電梯勸阻吸煙案”之后,兩案有類似之處,這起案子的一審法院并沒像“電梯勸阻吸煙案”那樣依據公平原則判處被告“補償”原告,而是直接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這也說明“電梯勸阻吸煙案”二審判決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無論一審、二審法院,判決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都是應該統一和能夠統一的。只是在目前,法治國家、法治社會仍需不斷建設完善,一審、二審法院對于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并在當今的司法判決中具有普遍性,也是可以合理解釋和理解的。但這種不同應該是暫時的,隨著法治進程的加速和法治的完善,最終會是統一的。
注釋:
① 此案發生在《民法典》頒布實施前,原《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24條規定:“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
② 參見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2017)豫0105民初14525號民事判決書和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終14848號民事判決書,載中國裁判文書網,訪問日期:2020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