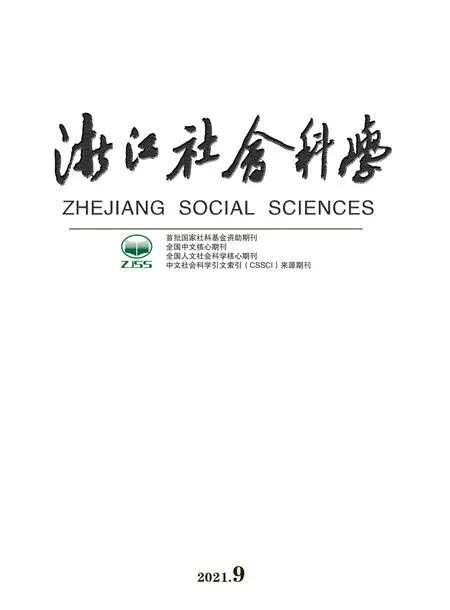巴赫金“對話論”再釋*
□ 周啟超
內容提要 巴赫金的“對話”已然被無邊界征用。巴赫金的“對話論”內涵不時被簡化,外延常常被泛化。這一現象召喚學者們對巴赫金“對話論”進行深度開采,在巴赫金的概念場中來理解“多聲部對話”,“對話關系”意義上的“對話”,“超語言學”界面上的對話,主體間相對位、相應和而不融合、不同一的對話。巴赫金的“對話”具有文化哲學品位,具有倫理導向性,具有在文學文本與文化現實之間自由穿越的闡釋力。近些年來,俄羅斯、美國、英國、波蘭諸國巴赫金專家對“多聲部對話論”的新解讀,顯示出國際斯拉夫學界在巴赫金這一核心理念上的深耕路徑。
巴赫金文論,以其獨特的“對話論”、強大的跨學科輻射力、廣泛的跨文化覆蓋面,已成為深刻影響當代文學研究乃至整個人文科學學術生產與話語實踐的一個“震源”。巴赫金文論的跨文化旅行已進入常態。這種常態,體現為“巴赫金學”界的學術交流一如既往,體現為“巴赫金學”的文本建設不斷拓展,體現為“巴赫金學”的文獻整理進入收獲季節。新世紀以降,國際“巴赫金學”在學術交流、巴赫金文本系統開采與注疏、巴赫金研究成果的全面清理與集成諸方面的收獲,可謂十分豐碩。這里,我們且駐足于近十幾年來國際斯拉夫學界對巴赫金“對話論”的新解讀,對俄羅斯、美國、英國、波蘭幾位著名“巴赫金學”專家在巴赫金這一核心話語上的深耕路徑作一番檢閱與梳理。
一、多聲部相應和之關系中的“對話”
“對話論”即“多聲部對話”,或“對話主義”,堪稱巴赫金理論大廈的一塊基石。“復調”“狂歡化”“外位性”——巴赫金文論這些核心話語都源自“對話主義”這一核心理念。
提起巴赫金的“多聲部對話”,自然會令人想起“復調小說”理論建構者巴赫金筆下的“對話”,會令人想起巴赫金所探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中“作者與主人公的對話”,所謂“作者與其所塑造的人物平起平坐的對話”。創造人物的作者怎么能與人物平起平坐呢?多年來,這個問題一直是學界質疑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的關節。俄羅斯科學院版《巴赫金文集》第六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20世紀六七十年代論著》(2002)的編選者、哲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Л.戈戈吉什維里,對當年蘇聯學界不同陣營的學者對巴赫金“復調說”的反應與批評的具體細節展開清理,提出如何進入巴赫金視域中“作者與主人公之對話”之深度理解的一條新路徑。
Л.戈戈吉什維里在其學術史的清理中發現,“復調”這一范疇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蘇聯學界總體上已被接受且流行起來,但學界流通中的“復調”已失去巴赫金筆下“復調”的哲學內涵,而被普遍地用來泛指文學文本的品質。“復調”在形式建構層面上的觀念性意義卻遭遇評論界普遍地降低。于是,我們看到,巴赫金的批評者們明確提出,不存在純粹的“復調小說”,一如不存在純粹的“獨白小說”。在任何一部小說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則甚至比起許多前輩與同時代人更強烈地響起作者的“聲音”①。我們也看到,巴赫金的贊同者也批評巴赫金在其對“作者”這一術語的使用上有些“不加區別”(В.柯日諾夫)。
Л.戈戈吉什維里將接受者視野中對“復調”的解讀同創建者本人心目中賦予“復調”的蘊涵進行對比。她在對巴赫金晚年的幾本筆記的檢閱中梳理出,晚年的巴赫金并未公開回應學界對其“復調”的解讀,而是繼續獨自思考其“復調”所隱喻的蘊涵。巴赫金堅持,他的“復調”遠不是一種敘事策略:所謂將意義的生發源頭交到“不同人的手里”(賦予不同的聲音);他的“復調”已然是一種體裁樣式,是小說發展史上新的對話型作者著述樣式。
如何理解這一對話型著述樣式?就是“作者與主人公平起平坐的對話?”身為哲學研究者的Л.戈戈吉什維里從形式建構之觀念性層面上看出:巴赫金所謂“作者與主人公的對話”,并不是像大多數人所理解的那樣,是作者直接進入作品而與人物進行對話。作者只是在功能上被改造之后——作為客體化的人物,才可能進入所描寫的對話。“對話”,在巴赫金這里已然被選定為描寫對象;為了去描寫這對話,身為審美主體的作者實則應當走出這對話,放棄所有直接的與間接的表達自己立場的形式。“復調理論”更準確的建構,見之于巴赫金晚年第3 本筆記,他認為復調小說這一體裁的觀念性條件,并不是恰恰以作者身份出場的作者同主人公們的對話,而是作者從對話中走出來,自覺地放棄所有的自身話語樣式。②
現在看來,之所以當年曾出現對巴赫金的“復調理論”那么多質疑與批評,之所以現如今還有對“作者與主人公平等對話”的困惑與不解,其中一個重要“堵點”也許就在于這些困惑者、質疑者、批評者心目中的“對話”,與巴赫金視域中的“對話”尚不在一個界面。可以說,對巴赫金視域中的“對話”之獨特內涵的深度解讀,實屬“巴赫金學”乃至文學學界多年持續的一個期待。著名巴赫金專家、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瓦列里·秋帕(В.И.Тюта)教授2018年撰寫的一篇短文《相應和之對話》(Диалог согласия),對巴赫金的“對話論”的梳理與闡釋令人耳目一新。В.秋帕在該文強調,巴赫金的“對話”實則指的是“對話關系”,它有別于“對話言語”,應當在“巴赫金的概念場”中來梳理巴赫金的“對話”理念與范疇、“對話關系”、“對話等級”。В.秋帕指出:“問題的本質在于,與獨白和對話這樣的語言哲學范疇不同,巴赫金的獨白主義和對話主義概念屬于超語言學,因為‘對話關系比對話言語更寬泛’”③。
“對話關系”具有“無窮的差異漸變譜系”。“對話關系”在巴赫金那里有一個明顯的等級。В.秋帕清理出對巴赫金視閾中不同等級的“對話關系”。
無聲的喜劇對話,是這個等級中的“零對話關系”,“其中雖有實際的對話接觸,但對答之間卻沒有任何意義上的接觸(或想象的接觸)”④。
“貧乏而無效”的分歧,屬于對話關系最低一級,還有爭吵、論爭、諷刺性模仿這些“明顯但更粗俗的對話形式”⑤。
豐富多樣、內涵各異的相應和,堪稱“對話關系”的最高一級。這種相應和本質上是自由的,“它總是在克服距離感并尋求彼此的接近(交集)”⑥。這種相應和的對話,就是巴赫金所說的“意義的疊加”、“借助融合(但不是同一)的強化”、“多種聲音的聯合(多種聲音的通道)”、雙向的理解。⑦
В.秋帕認為,“相應和”的交集,比“相融合”的“同一”更準確地傳達了巴赫金的理念。⑧一如巴赫金所說,“復調中的相應和不會使多種聲音融合在一起,它不是同一化,也不是機械的傳聲筒”。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中,即便是相應和也保留著對話性質,也就是說,永遠不會導致多種聲音和真理融合為一個統一的無個性差異的真理,像在獨白小說中那樣”⑩。
В.秋帕看出,巴赫金視閾中“一切對話的終極目的”就是進入“相應和之對話關系”?。這種對話關系,應置于巴赫金的“對話主義”概念場中逐層闡釋:
第一,最基本的相應和可以被認為是對話的必要條件(共同語言,至少能夠相互理解的語言),因此它實際上也是一切交往中具有意識導向性的思想。?
第二,從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闡釋的觀點來看,“最高意義上(‘黃金時代’‘天國’等等)的自由之相應和”?的前景是面向永恒的?,因此爭論永遠是具體條件下的,是暫時的。
第三,“在相應和之中實現獨立、自由和平等,比爭論中的對抗更難”,“俗語說眾人齊心鬼都害怕,但這齊心卻是要喪失個性……”?。
В.秋帕強調:“相應和”是“最為重要的對話范疇”,是“對話關系”的最高形式。“對話關系”這一最高形式,應置于巴赫金的大對話哲學之中來理解,應置于巴赫金的“對話主義”思想體系之中來把握。“對話主義”的“對話”實則比言語上的對話更寬泛,它也包括言語上的“獨白”。“對話主義”的“對話”并不等同于“對話言語”,它強調的是“對話關系”。“對話關系”也存在于深刻的獨白性言語作品之中,且不僅僅存在于語句之間,也滲透于某些語句內部。反之,對話言語不見得一定就會表現“對話關系”,對話言語的結構形式有時也會是“獨白主義”。與“獨白主義”對他者聲音的聽而不聞相對立,“對話主義”尊重交往行為所展示的個體間意識的彼此平等、主體間聲音的相互傾聽。如果說,“獨白主義”是壟斷話語,在“最終話語中對他者的拒絕”?,把他人變成自己思想之無聲的客體,而扭曲了人與人之間的本真關系,“對話主義”則是尊重他者的主體地位,與他人平等地分享話語權利,體現出具有人道主義特點的交往關系。
質言之,巴赫金的“對話”遠非言語對話,遠非日常現實的對話。這“對話”實則指理想的交往行為應展現的意識個體之間的關系,主體之間的關系。?
這“對話”實則是同“獨白主義”相對抗。
這“對話”追求具有倫理導向性的多聲部“復調性”的相應和。
這“對話”已然超越語言學,而走向文化哲學。
В.秋帕的這一梳理,顯然有助于我們深入思考巴赫金的“多聲部”或“復調說”與其“對話主義”理念、“對話論”之間的關系。
對“相應和的對話”這一對話范疇的梳理,不僅在理解巴赫金的“對話論”上具有學術史價值,也有助于認識巴赫金倡導的這一形態的“對話”之思想史意義。
巴赫金筆下的“對話”,實則具有獨特的內涵,不應被簡化,不應被泛化。這不是母親與嬰兒的對話,不是中小學課堂上教師與學生的問答,也不是外交談判桌上的對話。巴赫金視閾中的“對話”,是“對話關系”界面上的“對話”,是“超語言學”意義上的對話。
二、具備文化哲學品位的“對話”
正是“多聲部相應和的對話關系”,使巴赫金的“對話”具有倫理導向性,具有在文學文本與文化現實之間穿越的闡釋力,具備文化哲學品位。文學批評家、文學理論家這樣的頭銜尚不足以涵蓋巴赫金這位思想家的真實體量。巴赫金本人曾申明,他從事的是哲學人類學。著名巴赫金專家、英國倫敦大學加林·吉漢諾夫教授則將巴赫金的理論探索稱為“文化哲學”。有別于瓦列里·秋帕緊扣“對話關系”來對巴赫金的“對話論”蘊涵進行聚焦式闡析,加林·吉漢諾夫采取的是宏觀視角,力圖經由其對巴赫金在文學理論與文化理論中的遺產的總體回望,來通觀“巴赫金的理論建構風格”,在對“巴赫金理論建構風格”的考察之中來闡述巴赫金“對話論”的獨特品位。G.吉漢諾夫寫道:
巴赫金潛心的領域首先是文化哲學。作為思想家的巴赫金位于一個獨特的空間,即諸學科之間。正是在這個空間里,他創造出他專有的隱喻。那些隱喻使得巴赫金自由地游弋于各種不同的理論界面,而潛心探索那些超越學科所確定的知識域極限的問題。巴赫金時常不動聲色但總是絕對具有召喚力地提出一些范疇。正是這些范疇超越了它們所屬學科之觀念性的局限,被賦予新的生命,改變了其先前的觀念上的身份。
我們不妨以被巴赫金移置到各種不同學科“音區”的對話思想為例。?
有趣的是,首先進入G.吉漢諾夫視野的也是巴赫金理論大廈的基石——“對話論”。這位英國學者也看到巴赫金的“對話”范疇具有“超語言學”品位。他從學術史維度梳理巴赫金與其同時代其他蘇聯學者在“對話”范疇使用上的共通之處與不同點:巴赫金與列夫·雅庫賓斯基以及另一些早期蘇聯語言學家一樣從語言學起步,而使“對話”范疇的使用具有語言學基質,可是巴赫金對這一范疇的闡釋要寬廣得多。“對話”在巴赫金筆下被運用于多種多樣的敘事,被運用于作為整體的文化。
這位英國巴赫金專家同俄羅斯學者一樣認為,僅僅定位于語言學層面,難以闡明巴赫金“對話主義”的魅力。關注“對話”并不是巴赫金的專利。熟悉現代斯拉夫文論學術史的這位英國學者,將文化哲學家巴赫金看取“對話”的視界同符號學家穆卡若夫斯基看取“對話”的視野加以對比:穆卡若夫斯基寫過以《對話與獨白》為題的專論,其術語、其文本更具“學科規范”,但其思路卻被夾在狹隘的語言學界面上的對話與獨白的對立之中。巴赫金則邀請我們去聽取每一個說出來的話語內部的對話,去聽取在那些表達相反的世界圖景的聲音之中被呈現的對話。巴赫金創造性地刷新了學界對“對話”的理解。
在“對話”這一范疇的使用界面上,巴赫金何以成功地實現這樣的開拓呢?G.吉漢諾夫從理論建構的風格這一層面來闡釋。吉漢諾夫看出,巴赫金看取“對話”的視界其實是一種轉換,它使術語服從于內在的生長;在這一轉換過程中,概念擴展其相干性程度直至變成隱喻,成為范疇。這種轉換是巴赫金理論建構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正是這一改造性的能量,使得巴赫金比他在語言學、社會學、神學或藝術學的前輩勝出一籌。吉漢諾夫由此主張,要從思想史維度對概念與范疇如何在巴赫金思想的熔爐里經歷的轉換進行深度勘探。
G.吉漢諾夫十分推崇巴赫金善于在各種見解的熔爐里提煉,善于在不同學科中穿越的能力。吉漢諾夫敏銳地看出:巴赫金之所以善于穿越、善于提煉,得力于身為一個大思想家的獨創性,身為一個偉大的綜合者的獨創性。這樣的綜合者能自由地運用來自語言學、藝術史、神學等不同學科的話語,改變并擴大這些話語相互作用的場域。追溯巴赫金學術思想的發展進程,可以發現他的理論建構經歷了由早期著述中的倫理學與美學走向成熟期著述中的文化哲學這一演變。
巴赫金是如何由倫理學與美學走向文化哲學的?G.吉漢諾夫在這里回到思想史維度進行了清理:巴赫金的整個思想演變,可以說,就是在同心理主義、同主觀性堅持不懈地做斗爭這一旗幟下展開的。巴赫金本人曾對瓦基姆·柯日諾夫坦言,在他作為一個思想家,作為一個對心理主義深刻懷疑的思想家的成長中,埃德蒙德·胡塞爾與馬克斯·舍勒可是起了關鍵性作用的。?巴赫金1929年那部專著的書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強調了小說家十分罕見而不可復制的創作性元素。1963年這部專著易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則表明研究者走向對詩學特征的考察,走向人格化的體裁記憶。這一修訂,顯示了巴赫金思想演變的軌跡。
以吉漢諾夫之見,巴赫金的整個理論建構堪稱同主觀性作斗爭的戰場。在巴赫金心目中,長篇小說的命運完滿地體現了對主觀性的拒絕:單個作家不過是一個工具,借助這個工具,體裁得以使其自身物質化;單個作家不過是一個傳聲筒,經由這個傳聲筒,體裁記憶得以發聲說話。巴赫金對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拉伯雷這樣杰出的創作個性甚有興趣,但在念想之中巴赫金實則是有心去寫一部無名文學史的。
經由對巴赫金其文形象的總體性勾勒,對巴赫金學術探索軸心旨趣的分析性清理,G.吉漢諾夫進入對巴赫金其人形象的整體性描寫,對巴赫金這位思想家個性的概括:巴赫金理論建構風格的一大特征在于,他漸漸地而且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更優秀地構筑了一個理論平臺,可以將之稱為無主觀性的人文主義。?巴赫金之“對話論”乃孕生于這種獨具一格的人文主義而具備文化哲學品位。
巴赫金是其獨具一格的“對話論”建構者,是獨具魅力的“對話主義”倡導者,也是這一理論的積極踐行者。作為現代斯拉夫文論中“形式論”學派與“結構論”學派的同時代人,巴赫金與所謂“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關系,一直是國際斯拉夫學界在探討的話題。近些年來,在這個話題上又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新論新說呢?
三、同“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對話之中的“對話論”
巴赫金同俄羅斯形式論學派的“對話”一般要分為兩個層面。其一是所謂“巴赫金圈子”?當年對形式論學派的批評; 其二是巴赫金本人作為署名作者但在后來才面世的那些文章與著作里對形式論學派的回應。
《俄羅斯文學批評史:蘇聯與后蘇聯時代》第二章“四個流派與一種實踐”的作者,著名巴赫金專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凱瑞·愛默森(Cayyl Emerson)教授不久前對當年“巴赫金圈子”對形式論學派的批評,進行了新的清理。這一清理聚焦四個層面:基本的主導、支撐性學科或親緣的學科、在藝術與生活之間關系上“誰服從誰”、文學科學中個人與“物”之間關系上的最佳尺度。?
從全部四個參數來看,對照特別顯著。如果說,形式論學派的主導理念指向自足的自治性話語,那么,“巴赫金圈子”則推崇對外開放的、互相依賴的、主體間的人格姿態。如果說,正統的形式論者當年都感到與結構主義語言學有血緣關系,那么,“巴赫金圈子”那時則體驗到與德國道德哲學的親近。兩個學派都清晰地區分藝術與生活,兩家都堅持兩種現實彼此為對方絕對地必需。如果說,對于形式論學派來說主要的是物與物或者物與個人之間的關系,那么,對于“巴赫金圈子”來說,其出發點與落腳點還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
“巴赫金圈子”對形式論學派之追根究底的回應,見之于梅德維捷夫的著作《文學學中的形式主義方法》(1928),這一回應也帶有折中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背景。對于形式論學派最為敏感的幾個話題在這里都被觸及。
在C.愛默森看來,梅德維捷夫的批評,盡管在很多層面是有論據的,終究是直線的與粗暴的。他針對的是形式論學派那些早期的、最具有進攻姿態的取向。然而在1928年形式論學派作為一種流派已處于被粉碎的威脅之中。僅僅因為形式論者推重“原本意義上”的聲音,以二元對立方式思考,尤其看重戲擬的翻轉,就指責他們在對待內容上與意義上的“虛無主義”,這是不公正的。?
C.愛默森指出,巴赫金對形式論學派的回應其實并不曾為梅德維捷夫的批判與否定所窮竭。巴赫金當年撰寫了《話語藝術創作中的內容、材料與形式問題》,擬于1924 發表。然而這篇專論直到1975年才面世,可以說,它從半個世紀的文學爭論中脫落了。在該文里,巴赫金建構出其對二元對立的獨特理解。這不是物與物,也不是物與個人,寧可說,這是兩個人格范疇——“我”(我本身,內在地感覺到的進而是開放的、模糊不清且未完成的)與“他者”(從外部可見的因而總好像是被發聲的與被表達的)之間的創作性張力。
C.愛默森認為,巴赫金公開地將形式論方法同康德、謝林這些他十分尊敬的哲學家的思想旨趣拉開距離,巴赫金將形式論學派對藝術的理解界定為“材料美學”,帶有顯著的“原始主義”與“幾分虛無”。有別于梅德維捷夫,巴赫金在四年之后并未為完成指定任務而站出來反對這樣的視界,卻給予日爾蒙斯基與托馬舍夫斯基的作詩法研究高度評價。
C.愛默森在其簡約的梳理中特別提示:在20世紀二十年代末,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1929)這本專著本身就帶有“形式主義的”任務。它明確地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某些方面(道德哲學、神學、畸形心理、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闡說排除在外。巴赫金將這些文學外的話題放在一邊,將自己的注意力聚焦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話語的分析上。帶著這樣的目的,他提出對小說話語加以系統化,其系統被分層與細化的程度并不亞于雅各布森那些表格(在1929年的版本里,這個表格收入該書第2 編第1 章(小說語言類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話語?)。依巴赫金之見,發出的話語,原本意義上的話語,要到它被發送至另一個已然開放而準備接受的意識(或者,在其在場時已然誕生的意識),才會存在。巴赫金“復調說”的膽識在于這樣一種設定:話語確實能創造出不受控制的、自由發展的“生命”,這生命只是由小說家給出,它卻是被主人公們作為他們自己生命的生命、未完成的生命來感覺的。主人公是由作者為使讀者驚奇而創作出來的,主人公們能應答、能反抗。長篇小說的復調,——巴赫金認為這是話語領域里真正的哥白尼革命,——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最精彩的形式上的手法。
從C.愛默森這番梳理中,不難發現,今日國際斯拉夫學界在更為細致的清理中已經觀察到:巴赫金與形式論學派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對立對峙,巴赫金當年對形式論學派的理論與實踐其實是一種有批評、有反對,同時也有借鑒、有吸收的復雜交集。
無獨有偶。《巴赫金與俄羅斯形式論者:一個未被察覺的交集》(2017)正是著名的巴赫金研究專家、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葉琳娜·波波娃一篇文章的題目。該文針對的是上世紀最后二三十年里國際“巴赫金學”中一個頗為流行的現象:“巴赫金VS 形式論者”這一方法論上的對立,在一些學者筆下被激化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它要求研究者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擇:誰要是“等距離地’援引形式論者和巴赫金的著作,誰就會被認為是專業上不在行,或者是專業上的溫情。葉琳娜·波波娃則主張,應當歷史地直面巴赫金同形式論派的真實關系,要厘清事件的歷史現實性。?
作為俄羅斯科學院版《巴赫金文集》第四卷第2 冊《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拉伯雷與果戈理(話語藝術與民間笑文化)》(2010)的編選者,葉·波波娃基于對巴赫金的文章《拉伯雷與果戈理》(1940,1970)寫作史的梳理,基于對相關檔案資料的檢閱,發現了在對果戈理小說詩學特征的解讀上巴赫金同艾亨鮑姆的交集:
巴赫金和艾亨鮑姆之后的其他研究者一樣,從曼德爾施塔姆的書中,找到了對拉伯雷的語言和果戈理的語言進行比較分析的例子,這里運用的不是原始實證方法,而是嚴格的形式論詩學概念體系。巴赫金的一系列研究尤其關注語言游戲的聲音手法、面部表情和聲音手勢。在建立他自己的果戈理風格概念時,巴赫金不曾完全擺脫“形式主義方法”的理論。?
經過一番悉心清理與論證,葉·波波娃明確指出,20世紀30年代與40年代,巴赫金在其小說研究里描述長篇小說話語“對話關系”的形成過程中運用的一個關鍵概念“多語”(雜語),就是巴赫金當年吸收形式論學派思想成果的一個例證,在這之前,艾亨鮑姆已經運用“多語”(雜語)概念而將拉伯雷風格和果戈理風格問題理論化。
四、作為人文科學獨特認知路徑的“對話”
作為潛心于“文化哲學”理論建構的大思想家,巴赫金的“對話論”或“對話主義”不僅體現于他對具體的長篇小說話語“對話關系”的探討,體現于他對多聲部“復調小說”理論的構建,還體現于他對人文科學獨特認知對象、獨特認知路徑的深度思考。“對話論”的一個起點就是“對話”與“獨白”之對立。這一對立,緣起于巴赫金對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這兩種知識形態在認知路徑上的區分:
巴赫金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區分上提出獨白與對話這一對概念,而使得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這兩者之區別的理解得以豐富起來。自然科學被巴赫金界定為獨白型知識形態,人文科學呢——則被界定為對話型知識形態。前者的獨白性在于,“人以智力對物進行觀察而表達對這物的看法。這里僅僅有一個主體——在認知(在觀察)而在言說(在表達的)主體。與之相對的僅僅是無聲之物。自然科學認知是典型的“主體—客體”關系,人文科學認知是典型的“主體—主體”。因而,人文科學作為認知者同被認知的主體之相遇,乃是對話型認知形態。?
著名巴赫金專家、波蘭格但斯克大學博古斯拉夫·祖爾科教授以其《巴赫金觀點系統中的人文科學》(2016)一文,對巴赫金運用“對話論”探討人文科學的特質與認知路徑的思索進行了再檢閱。
Б.祖爾科觀察到,在何為人文科學對象的探討上,巴赫金采取的是有別于狄爾泰的新視界。狄爾泰已經指出,人文科學也擁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這就是文化作品里被體現出來的“精神”,諸如體驗、表達、理解。巴赫金在狄爾泰之后繼續深化人文科學之對象的探討,他認為“精神”是不確定的,它要在文化作品里得以客體化。在巴赫金這里,人文科學的對象應是“有表達力而能言說的存在”?。
人文科學——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學,而不是研究無聲之物與自然現象的科學。人帶有其人的特性總是在表達自己(在言說),也就是在創建文本(即便是潛在的)。舉凡人是在文本之外而被研究,不依賴文本而被研究,這已不是人文科學(而是解剖學、生理學以及其他的學科)。?
這也就是說,在巴赫金視閾中,人文科學的對象就是在創建各種各樣文本的人。文本在這里至關重要,它成為人文科學的第一性現實。由此看來,人文科學遠非直接同“精神”打交道: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與“精神”之間的關聯,總是經由特定人在特定時刻所創建出的文本來荷載。
精神(自己的或他人的)不可能作為物(自然科學之直接的客體)而得以提供,只能以符號性的表達而得以提供,在為自己也為他人的文本中而得以實現。?
質言之,人文科學所考察的正是人的“精神”之“文本”的表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便可以理解巴赫金為何將人文科學稱為“語文科學”?。這一界定,顯然是從另一維度強調:文本實則是人文思維的根基。
經由人文科學的對象是人的“精神”之“文本”這一界定,巴赫金實則是以“語文科學”的維度來深化狄爾泰將人文科學看成“精神科學”的定位,而強化人文科學的科學品格,這是對狄爾泰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這一繼承與發展更體現于巴赫金在人文科學認知路徑上的探討:以狄爾泰之見,人文科學的路徑是“理解”。文化作品不可重復,它總要被賦予個性。它由清一色的特例構成,任何“普遍性”都無法對它們加以“解釋”。闡釋學理應成為人文科學的基本方法。巴赫金則接著狄爾泰的“理解論”往下說,提出其“對話論”:
在進行解釋時——僅僅存在一個意識,一個主體:在進行理解時——則存在兩個意識,兩個主體。對客體不可能有對話關系,因而解釋已失去對話元素(除了形式—修辭學上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具有對話性。?
波蘭學者再次觀察到巴赫金理論建構的一個特征:善于把重要的理論范疇具體化。在這里巴赫金是用語文學的維度來轉換狄爾泰的范疇。在Б.祖爾科看來,甚至都可以來談論巴赫金的學術思維帶有獨特的語文學化特點:巴赫金善于用語文學精神來對基本哲學范疇進行再闡釋(人文科學的對象——“能言說而有表達力的存在”;人者——“亦即能表達自己(能言說)者也”;人文科學——“語文科學”;解釋——“獨白性的關系”;理解——“對話性的關系”,等等)。?
可見,“對話”與“獨白”,“對話性關系”與“獨白性關系”這些“對話論”基本思想也被巴赫金運用于他對人文科學同自然科學在認知路徑上的區分。
那么,有自己的認知對象,有自己的認知路徑,也具有獨立科學品格的人文科學,同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在堪與自然科學并列之際,人文科學同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界限嗎?Б.祖爾科在其對巴赫金理論體系的梳理中發現巴赫金對此是予以否定的。這里的問題,也不僅僅在于現實中已經發生一些量化的(數學的)方法對人文科學的入侵。
以巴赫金之見,在以人為主體的文化世界中的任何現象,都可以置于物與個性、客體與主體這兩極而加以考量。包括文本在內的任何對象,都可以被置于這兩個向度中的一個而得以研究。物與個性——正是兩個極、兩個向度,而遠非靜止不動的、實體性的立場。
一旦接近個性這一極,文本便在其中被人格化——以巴赫金之見——便會聽見個性的聲音;一旦接近物這一極,文本便得以物體化,物化。在第一種(人格化)情形下,我們要做的事是以對話性態度看取文本,人文科學所致力的正在于此;在第二種(物化)情形下,則是以獨白性態度看取文本,而把文本變成無聲之物。?
波蘭學者看出,不論是致力于文本的人格化,還是傾心于文本的物體化,巴赫金都沒有截然否定,只要它們守持住自己的界限。結構主義傾心的“文本解剖學”,將文本物體化,其實是對實證主義科學模型的延續。這種“文本解剖學”,完全正當合理,只要它守持在自己的界限里,而并不去奢望成為對于事物之完整的、完滿的認知。這不禁令人回想起巴赫金當年對于形式論學派根本立場的批評:形式論者的“材料美學”在一些局部性問題上是有理而正確的,在話語創作的某些“技術性”層面的分析,是有理而正確的,但不可能成為整個文學作品理論。文學作品不僅有其外在的物質層面,還含有非物質性的審美客體。
通過檢閱巴赫金在文本的人格化與文本的物體化這兩個向度上的態度,Б.祖爾科的梳理已然直面巴赫金對人文科學之“準確性”的思考:巴赫金繼續推進,將在“物與個性”這兩個向度上考量文本的潛能同人文科學的“準確性”關聯起來,并由此提出人文科學更有對“深度”的追求。“準確性”是對文本進行描寫的目標:在其“材料的”、物的現實這一維度上進行描寫。它要求的是物與其自身的吻合。“準確性”實則為“實踐上的把握”所需。“深度”則是文本之涵義的、表達力的、“個性的”層面所具有的特征。“深度”原本就是人文科學的突出標記。?
經由這番清理,波蘭學者對巴赫金有關人文科學的“準確性”的思想作出相當到位的闡說:在文學批評、文學研究這樣具體的人文科學話語實踐里,“準確性”,一如在數學學科里人們對之理解的那種準確性,只是在對文本之“物的”層面進行描寫時才有可能,且是適當的。人文領域里的文本,諸如詩、小說這樣的文學作品以及繪畫、音樂這樣的藝術作品,其文本的價值涵義方面則不可能領受“準確的”描寫,“因為它是不可能被完結的,而且它也不會與其自身相吻合(它是自由的)”。?
結語
在巴赫金的概念場中來理解“多聲部對話”,就會看到,巴赫金的“對話”實則是多聲部相應和之關系中的“對話”,是具備文化哲學品位的“對話”;巴赫金的“對話論”是在同“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對話這一具體的歷史語境形成的;巴赫金“對話論”的思想史價值則在于它能闡明“對話”是人文科學獨特的認知路徑。
注釋:
①Г.弗里德連捷爾、Б.梅拉赫、В.日爾蒙斯基:《巴赫金著作中的詩學與小說理論問題》,載《俄羅斯學者論巴赫金》,周啟超編選,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8頁。
②周啟超:《“巴赫金學”的一個新起點》,《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4期。
③⑧?瓦列里·秋帕:《共識性對話》,劉錕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原文題目中的согласия一詞有“同意、和諧、共識、相應和”等義項,在巴赫金理論體系中宜譯為“相應和”。
④Бахтин М.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7 т.М.,1996-2002.Т5,С.336.
⑤⑦Бахтин М.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7 т.М.,1996-2002.Т5,С.332.
⑥??Бахтин М.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7 т.М.,1996-2002.Т5,С.364.
⑨?Бахтин М.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7 т.М.,1996-2002.Т5,С.302.
⑩Бахтин М.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7 т.М.,1996-2002.Т6,С.108.
?Бахтин М.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7 т.М.,1996-2002.Т5,С.353.
?Бахтин М.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7 т.М.,1996-2002.Т2,C.156.
?Бахтин М.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7 т.М.,1996-2002.Т5,С.362.
??加林·吉漢諾夫:《在不同的學科之間自由地游弋》,周啟超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瓦·柯日諾夫:《巴赫金與其讀者·思索及部分的回憶》,《對話·狂歡·時空體》1993年第2-3期。
?“巴赫金圈子”指的是20世紀20年代,比巴赫金更為知名的幾位同事:語言學家瓦列京·沃洛希諾夫(1895—1936),文學批評家巴維爾·梅德維捷夫(1892—1938),與古典作家研究者、文學形式理論專家里沃夫·蓬皮揚斯基(1891—1940)。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советская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эпоха Под ред.Е.Добренко,Г .Тиханова М.НЛО,2011,С.220.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советская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эпоха Под ред.Е.Добренко,Г.Тиханова М.НЛО,2011,С.22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列寧格勒:激浪岀版社1929年版,第127頁。
??伊琳娜·波波娃:《巴赫金與俄羅斯形式論者:一個未被察覺的交集》,鄭文東譯,《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5期。
????博古斯拉夫·祖爾科:《巴赫金觀點系統中的人文科學》,周啟超譯,《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4期。
??Бахтин М.М.,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Москва:Искуство,1979,С.410.
?Бахтин М.М.,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Москва:Искуство,1979,С.285.
?Бахтин М.М.,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Москва:Искуство,1979,С.284.
?Бахтин М.М.,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Москва:Искуство,1979,С.363.
?Бахтин М.М.,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Москва:Искуство,1979,С.289~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