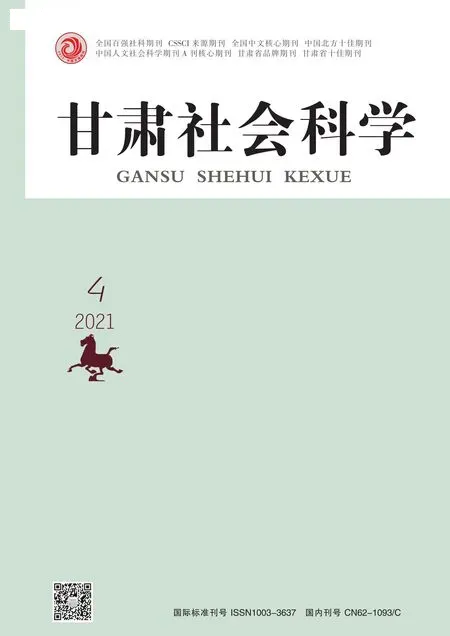“資本主義”問題的新剖析
——弗雷澤與賈基“資本主義”批判哲學的對話
馬云志 王 寅
(蘭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蘭州 730000)
提要: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人類社會持續前進、不斷發展的生命動力,是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推進的歷史必然邏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批判理論家在北美的傳人,南茜·弗雷澤圍繞“資本主義”問題同批判理論家拉赫爾·賈基展開了一場全新剖析和批判性哲學論辯。弗雷澤和賈基采取馬克思主義“前景—背景”的方法,從資本主義總體性認知和“前景—背景式”結構入手,全面厘清資本主義危機發生的根源,以期實現對資本主義問題的系統性追蹤和全面性診斷。兩者對資本主義問題的追溯雖有考量之差異,但其爭辯語境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總體性批判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對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豐富。然而,受所處時代和話語背景的影響,其批判理論亦存在著“宏大敘事”理論化,未能有效落地生根等缺陷。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全球性的周期性危機,自從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后金融經濟危機在當前甚囂塵上,資本主義的問題愈發嚴重,甚至引發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局面中走向了人類考量自身未來發展的輿論焦點,曾經以資本主義引以為榮的各國自由主義者不再信誓旦旦地為選舉自由主義的代言人搖旗吶喊。相反,各地選民開始集體反抗新自由主義,試圖將左翼政黨和精英主義者綁架至民粹主義發展的軌道上,走民主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模式。面對新自由主義引致的全球政治霸權危機,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批判理論家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和拉赫爾·賈基(Rahel Jaeggi)以人類的共同幸福為基點,站在時代發展的戰略高度,從資本主義發展桎梏的現實層面,圍繞資本主義當前形勢下“什么是資本主義,怎樣重構資本主義”等重大問題作出了新的剖析和科學回答,把人類對資本主義問題的認知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開啟了法蘭克福學派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使其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性批判進入了一個全新發展視域。
一、批判性緣起:深化“資本主義”問題的總體性認知
當前“全球性”合作認知遭到挑戰,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性生態危機和金融危機的到來。基于全球性的社會動態,對資本主義的認知不能停留于溫情的資本主義“壞惡”層面,而應該立基人類命運發展的抉擇層面去戰略考量資本主義危機,這種危機并非簡單的社會危機,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特殊形式危機。因而,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考量不僅是時代之需,更是人類命運之盼。鑒于此,依弗雷澤而言,資本主義是“危機”和“矛盾”的概念。對資本主義問題的關注不僅要在微觀層面(涉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變化的淺層結構性紊亂和功能性失調)予以正視,而且更應該在宏觀層面(涉及現實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深層結構和系統性危機)予以挖掘。在弗雷澤看來,對資本主義問題的認知應該從資本主義本身出發,在回應時代之詰問的同時,全面深度挖掘資本主義的概念,對“什么是資本主義,怎樣重構資本主義”等涉及資本主義重大問題應該有其科學的分析和辯證的認識,不能將其表面化和淺層化,要在堅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同時,科學認識和重構資本主義批判理論。誠然,對資本主義的反思需要借助資本主義危機理論,對資本主義問題的回應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意味著是否重構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確定了資本主義危機是否是資本主義所面臨的真正危機。所以,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了一場嚴重的系統性危機的陣痛之中。在弗雷澤與賈基看來,傳統上,對“資本主義”一詞的使用主要是修辭上的,現如今,必須對資本主義一詞進行系統化診斷和實質化解構。
第一,對“資本主義”一詞應該從概念上建構其理論形態和實踐形態,深化資本主義概念認知,有效解蔽資本主義內涵,建構其系統化的批判性體系結構。對資本主義的認知,弗雷澤與賈基各有其側重點,弗雷澤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秩序’,存在著多種危機傾向”[1]14,而賈基則表達了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各種流派的映射,以及它們各自的內部邏輯和相互關系。賈基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生活形式”的“實踐—理論”。然而,何謂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具體建構是什么?在弗雷澤看來,它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秩序”;在賈基看來,不應該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生活形式”;對于馬克思而言,“誠然,這個進步同以前一樣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機所中斷:1857年有一次危機,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這種危機的反復出現如今已經被看成是一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這種事情是無法逃脫的遭遇,但最后總是又走上正軌”[2]。所以,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不是人類所關注的資本主義的衍生議題,即:經濟危機、全球化、現代性、分配正義或市場經濟等,而是關乎資本主義本身的、重大的且具有系統性的深層次結構。對資本主義深層結構的系統性挖掘和剖析,不僅有助于人類更好地認知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有助于透過制度本身深度挖掘潛藏于資本主義內部的根源性矛盾和沖突。對此,弗雷澤認為:“資本主義的驅動力是一種廣泛的深刻和普遍的危機感——不僅是一種部門危機,而且包括我們社會秩序的每一個主要方面。”[1]18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認知應在考量資本主義驅動力的基礎上有序跟進,不是因為驅動力是一種無形的智能化力量,而是因為資本主義每發生一次經濟危機,就必須借助資本主義自身內在的驅力來實現資本主義的正常化運轉,否則,資本主義在無法借助驅力來進行自身改良時,資本主義勢必就會走向制度性的滅亡和消失。為此,對資本主義的深層認知不僅是對資本主義危機周而復始的客觀了解,更是對資本主義驅動力的客觀呈現。
第二,事物發展總是表征出兩面性,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必須立基于資本主義的問題,從資本主義的內構性和外延性著手,深化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客觀回應資本主義深層性結構矛盾,全力促動資本主義問題的邏輯認知和體系建構。沒有資本主義何來資本主義問題,反之亦然。所以,對資本主義問題的了解則深化了對資本主義本質的認知和發展。在新世紀,資本主義問題的加劇似乎意味著社會公平正義的議題再一次得到正視和凸顯。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就不可避免地與經濟產生聯系,這似乎是一直以來形成的價值共識,但認識資本主義決不能簡單地植根于經濟議題,而應該摒棄固有的內在模式化思維,從資本主義本身具有的內在特性去把握資本主義,否則資本主義固然地淪為了經濟危機的代名詞。誠然,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直都有社會運動和團體協會關注各種形式的社會或經濟正義。畢竟,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危機是促使資本主義繼續前進的驅動力。基于此,對資本主義的認知,不應該停留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以及各種不平等(包括失業、分配不均或不公等)。相反,我們應該從資本主義的核心本質著手,即“什么才是財富,以及財富是如何產生的”。當然,在誰從哪種勞動中獲得多少報酬的問題背后,存在著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什么才是勞動,它是如何組織的,它的組織現在對人們的要求是什么,對人們做了什么等。進一步而言,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僅面臨著如何幸福地生活、學習、工作等一系列民生難題,而且從更深層次而言,人類面臨著資本主義的深層結構問題,即整個社會再生產的組織問題。對此弗雷澤深刻指出:“我們也不應忘記諸如市場力量在兩個層次上掏空民主的政治問題:一方面,在領土國家一級對政黨和公共機構的集體占領;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在跨國一級篡奪政治決策權,這是一種對任何人民都不負責的力量。”[1]19從上面窺測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的核心危機不全部是經濟問題,還應包括政治問題。當然,回歸資本主義并不是為了解決這些表層問題,而是透過事物發展的表面現象深刻認識事物發展的本質,即潛藏于資本主義背后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這是制約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性難題,它深刻影響著社會秩序的重構和資本主義腐朽的全面暴露。從深層結構而言,對資本主義問題的揭露是對人類走向更高一級社會形態的正面回應,是對人類走向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種理論探索。
第三,全面加強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研究,在合理關切資本主義表層問題的同時,強化資本主義深層結構矛盾分析,將資本主義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進行系統性追蹤,科學架構其資本主義總體性認知結構體系。面對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賈基這樣問道:“這些多重危機迫使我們問,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否存在某種更深層次的失敗。”[1]19當整個生命形式可能已經變得功能失調時,只關注資本主義的不良影響已經不足以破解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構性問題。當然,對資本主義的審視不應該僅僅關注于表層社會治理問題,而應該以此為基礎,深度挖掘其潛在的由資本財富系統所造成的系統生成沖突。面對諸如此類的資本主義問題所產生的資本主義危機,人類應該深刻反思資本主義,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去洞察資本主義,真正深入了解資本主義危機背后的結構性矛盾和系統性失調,這就需要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性建構。當然,過去對資本主義也有批判,但批判的程度和深度難以從根源性層面得以追蹤,其批判未能深入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所以,在過去的歷史長河中,資本主義為了實現其自身的正常運轉或發展,資本家開始對資本主義的經濟“黑箱”(black box)進行改良,使得資本主義在外界看來有了明顯的轉變和跟進。從表層結構看,這似乎是經濟正義的回歸與勝利,尤其對于哲學自由主義和其他狹隘地關注“分配”問題的思想學派來說,這無疑是正確的。以左翼羅爾斯主義者或像G.A.科恩(G.A.Cohen)這樣的社會主義者為例:他們只關注“黑箱”的運行過程,但對“黑箱”的深層結構沒有進行深度解構和剖析,對其“黑箱”運作程序和運思沒有清晰的認知。于此,這就導致了資本主義的批判是柔性的,是帶有經濟目的的資本回歸批判。至于左翼學派的批判更是對表層結構的了解,沒有深入事物發展的源頭進行追根溯源。然而,從深層結構而言,雖然實現其對資本主義的改革,但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矛盾并未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必將暴露,甚至引致社會性倒退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分崩離析。
回溯資本主義歷史發展批判理論的內在邏輯,資本主義從馬克思到盧卡奇,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再到早期的哈貝馬斯,都處于其研究的中心地位。可觀的是,對其批判亦一直延續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此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便進入了低谷時期,尤其是依賴功能分化系統理論思想的哈貝馬斯,他不自覺地將資本主義的經濟領域從批判性理論中移除了。在哈貝馬斯那里,經濟被理解為自主運行的東西,一個“由自身邏輯驅動的‘自由’領域”[1]20。從這種意義上來講,這相當于將經濟放任不管或自由化了,抑或是我們前述中所指出的另一種“黑箱”(black box)方法。
總之,對資本主義的界定不用刻意追求語義上的邏輯概念問題,而應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改良來揭示資本主義的實質化運行問題。當然,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威脅,我們不僅要對癥下藥,而且要刨根問底,切實追求資本主義的實質化解構。否則,對資本主義問題的解決仍然是曇花一現,因此必須將資本主義的真正內涵和本質徹底暴露和挖掘出來。正如賈基所言:“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只需要通過政治或其他外部手段‘馴服’的‘老虎’。”[1]20當然,“被馴服的”資本主義是否能改頭換面,繼續充當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進動力仍然有待觀察。但“馴服”資本主義的想法并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民主和資本主義仍然是表象的依舊,并不能改變人類對幸福美好生活的真正追求。因此,對資本主義必須從深層結構和驅動機制兩方面著手,挖掘潛藏于深層結構中的隱性內容,并從批判理論的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的驅動機制。
二、批判性建構:科學構建“前景—背景式”的二元結構體系
在弗雷澤看來,對資本主義的認知決不能停留于對資本主義現象的表述和認知,更應該對資本主義結構有一個清晰的界定和認識。當然,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不應該僅僅從其字面意義上去解讀,而更應該去挖掘資本背后的真實含義和價值意蘊。首先要明確資本主義的核心特質才能證明當前社會的危機是資本主義的真正危機,而絕非其他方面的危機。所以,對資本主義核心特質的定義不僅有助于理解資本主義的理論概念,而且有助于從理論層面出發去探索真正的資本主義危機。對此,應該根據“資本主義”社會廣泛存在的一些核心特質來定義資本主義。然而,賈基對資本主義特征的定義有其自身的見解和看法,他認為,對資本主義的考量要遵循兩個維度,“一個是垂直的,另一個是水平的”[1]30。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是多元性的,在面對多元性的資本主義時,必須考察資本主義也共存于不同的社會。所以,弄清楚資本主義的核心特質關涉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
根據上面所談到的資本主義問題,弗雷澤指出,資本主義本質上是歷史的,其核心特質隨著歷史的發展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并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軌跡而做出適時調整。“一開始出現在中心位置的特征可能會在之后顯著性下降,而那些一開始看起來無足輕重甚至沒有的特征可能會在之后變得非常重要。”[1]30為此,對資本主義的核心特質不能一概而論,應隨時代、語境的發展變化而作出適應性的動態調整,但這絕不是說沒有固有的核心特質存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是隨著資本主義之間的激烈競爭而煥發出自身存在的驅動力的,這種驅動力就是資本主義間的競爭,更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驅動機制。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競爭加劇,在20世紀,它逐漸被壟斷資本主義的主要領域所取代。相應地,金融資本亦成為新自由主義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每個歷史發展階段嵌入和組織資本主義的治理體制已經發生了多次轉變,即從一開始的重商主義到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到國家主導的干預主義,再到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從上面窺測可以得知,資本主義的發展軌跡也遵從語言學所遵循的歷史性和共時性特征。資本主義是具有歷史性的,他們在資本主義路徑依賴的順序中可能并排存在著“資本主義的變體”(“varieties of capitalism”),但都表征出相互聯系的潛在特征。當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序列中,資本主義的給定轉變都是由政治所驅動的,不可回避的是,在其轉變過程中,任何子項目或子結構的升級改造都是由不同支持者之間相互斗爭的結果。正如弗雷澤強調的那樣,“但這個順序也可以被重新構建為一個方向的或辯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先前的形式遇到困難或限制,它的后繼者克服或繞過這些困難或限制,直到它也遇到一個僵局,并依次被取代”[1]30。有鑒于此,資本主義的共時性特質并非按照事物發展的既定方向依次前進,而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因事物的發展變化作出重大歷史調整,對資本主義出現的問題可能無法予以現實的根本性回應,在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對影響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羈絆作出必要的調整、克服,抑或是繞開當前存在的矛盾,走向一個溫和的社會改良道路,雖不能實現對資本主義主要矛盾的解決,但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資本主義發展、化解當前社會矛盾的作用。直到資本主義在其本身制度框架內無法挽救資本主義繼續生存的生命形式時,它才可能走向僵局,走向滅亡,并逐漸被更高一級的社會形態所代替。
基于此,資本主義核心特質的定義絕非簡單明了,它需要謹慎對待,以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來探索其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性和邏輯性規律,決不能妄下結論。針對資本主義出現的結構性難題和系統性紊亂,弗雷澤和賈基將其根本原因解釋為資本主義的制度化秩序所造成的“前景—背景式”的結構性矛盾。“前景”和“背景”一詞并非弗雷澤的專用,在馬克思《資本論》中,馬克思視生產和交換的邏輯轉換是產生剩余價值的“前景”方式,當然剝削在其交換過程中亦隱顯于此。而弗雷澤則明確提出了“前景—背景”的邏輯轉換概念,“他(馬克思)帶領我們從我指稱的‘前景’(在第一種情況下是交換,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剝削)轉而揭示相關的‘背景’(首先是剝削,然后是征用)。在每種情況下,其效果都是使曾被遮蔽的東西變得明白可見。”[1]30弗雷澤對資本主義交換是如何進行的并不想作以探究,相反更關注“前景式”的元結構,即側重生產是如何實現原始資本積累的。所以,弗雷澤根據早期階段的“三維正義理論”,即“將代表性的政治層面與分配的經濟層面和承認的文化層面結合起來。包括代表的政治維度,分配的經濟維度和承認的文化維度”[3],在深入分析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維度后,將其自身早期“三維正義論”思想全面對接后資本主義階段所建構的二元結構理論。換言之,即在立基“經濟前景式”的元結構理論基礎上,全面消解“政治背景性”的社會性危機(如政治、生態、安全、社會等),科學構建“前景—背景式”的二元結構性理論。
第一,借助馬克思《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將資本主義的核心特質以“前景—背景”(foreground-background/front story-back story)的理論模型來全面運思資本主義的理論結構和系統內核。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過分強調生產、交換、分配、消費所引致的剩余價值產生方式,即強調通過“經濟前景式”的資本主義研究來全面揭露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然而,在弗雷澤看來,我們應從資本主義發展的內質性結構層面深度挖掘資本主義的剝削。對此,弗雷澤指出,資本主義并非單純地經濟剝削,而是在更深層次上實現了經濟的掠奪,即實現經濟征用(Expropriation)。所謂征用,是“將沒收(confiscation)和強征(conscription)融入(資本)積累之中”[1]46。經濟剝削是一種隱性的物質剝削,而經濟征用則從實質上強化了剝削的內容,不僅征用人力勞動,而且征用一切非物質資源,通過其暴力形勢掠奪一切資源,不管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其征用內容進一步擴大化,其征用情勢日趨暴力化,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掠奪。誠然,這種形式的“經濟前景”已經由原來的“剝削前景”置換為“征用前景”,其實質比過去的資本主義更為扭曲,其經濟控制力、經濟壟斷力更為殘酷和嚴重。不僅造成了資本主義系統性結構紊亂,而且引致了階級分化和種族分化。對此,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前景式”結構予以解蔽,在堅持馬克思“經濟主義”分析方式的基礎上,必須加強“經濟前景式”的深度剖析,全面挖掘“經濟征用”內涵,促動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全面暴露,從而深化人類認知方式。
第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絕非是固化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批判,相反,對資本主義批判應在繼續堅持“經濟前景式”的元結構基礎上,深化“政治背景性”的社會危機批判,從經濟和政治的雙重維度努力消解“政治背景性”社會危機,從而建構資本主義總體性批判框架。這里言及的“政治背景性”社會危機比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更為嚴重,它牽涉強權政治、生態破壞、安全危機、社會扭曲、軍事霸權、長臂管轄等一系列資本主義亂象行為。在弗雷澤看來,資本主義已經將自然生態置于人類的一切任意宰割之中,生態成了資本價值增值的變相手段,資本已經發生扭曲,弗雷澤指出:“經過三個世紀的資本掠奪,加上新自由主義目前對剩余的生態公地的攻擊,積累的自然條件現在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危機的中心節點(central node)。”[1]36自然生態已成為資本掠奪的公地,在大規模無人性的摧殘自然生態時,嚴重惡化的自然生態就成為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點。對此,馬克思認為,“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對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認為是自為的力量”[4]。因此引致生態破壞的非人性行為就是資本主義的最大人性斷裂。當然,資本主義的擴張行徑也在弗雷澤所堅持的傳統“威斯特伐利亞”框架結構下發生了質的變化,傳統上弗雷澤堅持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但在資本主義強權政治的邏輯使引下,弗雷澤意圖通過政治維度(代表權)來提升經濟維度(再分配)、文化維度(承認)等“三位一體”式的三元結構來促動政治公共領域的發展,并以此實現其傳統“威斯特伐利亞”框架向“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系統重構。但鑒于目前“政治背景性”的社會危機需要從政治層級對資本主義開展批判,構建多元一體的、可流動性和諧融共生的“全球公共領域”就顯得蒼白無力。
第三,堅持以“經濟前景式”元結構理論為基礎,在全面消解“政治背景性”社會危機的同時,科學構建其“前景—背景式”的二元結構理論體系。在弗雷澤看來,長期以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一直傾向于“經濟前景式”的經濟剝削,雖實現其馬克思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批判,但這種批判是一元性的,并未上升至經濟批判的高度和深度。基于此,弗雷澤強調要從“經濟征用”的角度全面重構資本主義批判概念,將資本主義批判引向戰略內涵層級。然而,一味地“經濟前景式”批判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有必要將資本主義批判擴展至“政治背景性”的社會危機批判,從而實現其“前景—背景式”的二元結構化批判。畢竟單純的經濟批判仍舊困囿于資本主義固有的危機理論之中,并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系統性紊亂和結構性矛盾的根源。只有將“前景”和“背景”相接榫,從“前景—背景式”的內構性上揭示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才能實現資本主義問題的真正認知;只有將“前景—背景式”的經濟性和政治性危機和盤托出,資本主義危機的真實面貌才能為世人所知,才能更好地揭露資本主義,更好地為人類自由而全面地構鏡未來社會擘畫圖景。所以,資本主義的制度化秩序所造成的“前景—背景式”的結構性矛盾,是制約人類社會繼續向前發展的一道枷鎖。必須深入挖掘其資本主義的內源性矛盾,全面打破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認知,將資本主義放置在“前景—背景式”的結構性矛盾之中予以解構,從而實現對資本主義總體性危機的戰略認知和清晰判斷。
總之,弗雷澤和賈基在堅持傳統資本主義危機理論和批判理論的基礎上,重構了資本主義的批判方式,解蔽了傳統的資本主義批判框架結構,通過融合“前景”的經濟維度和“背景”的政治維度等二位一體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將“前景—背景式”理論模型導入了資本主義診斷。其目標是在堅守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將資本主義總體性危機予以解蔽,從而實現人類社會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種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的診斷,從表層結構而言,實現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解決,將“經濟征用”凸顯以示其經濟改革力,將“政治背景”挖掘凸顯其社會危機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然而從深層結構而言,科學構建“前景—背景式”二元雙重結構,則從實質上實現了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科學診斷,深化了資本主義矛盾的結構化治理,從而為促進人類全面解放和實現全球正義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三、批判性反思:對話的貢獻、地位和意義
針對資本主義出現的結構性難題,弗雷澤將其根本原因解釋為資本主義的制度化秩序所造成的“前景—背景式”的結構性矛盾。于是,弗雷澤借鑒馬克思《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試圖從理論的“宏大敘事”高度建構出一種滿足“前景—背景式”的二元結構性批判理論新框架。同時,在深刻揭露資本主義危機和挖掘資本主義表層結構面紗時,對資本主義本質及其發展歷程進行全面問診,以期揭開資本主義“重大系統性危機的深層結構根源”,并滿足時代對于“批判理論的渴望”[1]2。如何從理論層面和現實層面全面把握和認識弗雷澤和賈基的對話,從實踐層面建構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有效理論破解,是擺在當前北美法蘭克福學派領導人面前的頭等大事。為此,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應從批判理論自身發展層面、批判理論承襲馬克思主義層面、批判理論復興西方左翼層面等三個維度全面衡量和引領資本主義總體性批判理論的建構與發展。
第一,從批判理論自身發展層面而言,這場關于資本主義的批判性政治哲學對話開啟了資本主義總體性批判理論的新征程,創新了批判理論發展的新模式,建構了批判理論的新構架,堅持了作為批判理論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標志著新世紀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發展進入了最新發展階段。弗雷澤和賈基的貢獻不僅是學術上的重大理論創新,而且在政治實踐層面提供了絕佳的范例。在學術層面而言,他們恢復了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重視社會批判的經驗傳統,汲取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開創了“前景—背景式”的二元結構性批判理論新構架,實現了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結構轉型和系統升級,建立了新的去正統化的“前景—背景式”理論模型。盡管弗雷澤和賈基的理論構架源自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前景”基礎,但他們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和人類命運的關鍵抉擇中,積極謀劃和深度挖掘隱藏在資本主義“經濟前景”中的深層結構,即對資本主義深層結構中的“非經濟背景”進行系統性挖掘和解構。當然,資本主義的認知決不能從資本主義的“經濟前景”單純入手,而應該從一種“非經濟背景”進行戰略縱深拓展和挖掘,使其潛藏于隱形結構之下的資本主義特征得以解蔽。有鑒于此,弗雷澤試圖從資本主義的“經濟前景”去解構資本主義,真正實現批判理論的多元化,即在強調資本主義“經濟前景”的元結構層面,實現“前景—背景式”的二元結構互補發展和融會貫通。
第二,從批判理論承襲馬克思主義層面而言,這場關于資本主義的批判性哲學對話開拓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視域,發展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批判的一元性結構,創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發展的新視域,建構了一種全新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基礎性和硬核性的牢固地位得以重新確立。作為新左派民主社會主義派別的一分子,弗雷澤以“再分配、承認與代表權”的三維正義論而著稱。然而,相較于此前的正義論,現如今,弗雷澤開始直面審視資本主義的問題,資本主義社會是弗雷澤批判的直接對象,她將資本主義社會稱之為理論化的明確前景。似乎弗雷澤已經將文化承認的維度淡化了,將再分配納入“經濟前景”的視域中,將政治代表權歸屬于“政治背景”。當然,在強調“經濟前景”的“前景性”經濟危機同時,弗雷澤則將政治、文化、安全、生態、社會等一系列關涉人類社會發展的“背景性”的社會性危機領域全部囊括其中,其目的就是強調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前景性”的經濟危機,而且在更深層次上是多樣化的多元危機。誠然,弗雷澤在建構資本主義的總體性危機理論時,一直強調“前景性”的經濟危機與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邏輯”有著一脈相承性,在某種程度上是承襲創新的理論發展和科學建構。其根本目標是在堅守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同時,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實現集成化創新和實踐化運行。當然,弗雷澤的政治圖景是實現對經驗性的社會理論與規范性的政治理論相互諧融,走向資本主義的生活形式,追求人性的真善美和人類在資本控制下的徹底解放。基于此,第三代批判理論家仍然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和人類擔當,以資本主義批判為中心目標,深化社會主義維度的平等、公平、正義、友善等核心理念,努力同資本主義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做堅決的斗爭,在一定意義上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發展和壯大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
第三,從批判理論復興西方左翼層面而言,這場關于資本主義的批判性政治哲學對話從理論上恢復了法蘭克福學派一直倡導的資本主義“宏大敘事”觀,建立了資本主義的總體性批判理論框架,拓展了西方左翼的馬克思主義視野,客觀上奠定了北美學派在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術地位,從而為批判理論復興西方左翼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價值索引,標志著西方左翼學派從此實現了理論的指南化和實踐的革命化。作為法蘭克福學派在北美的傳人,弗雷澤自始至終以人類徹底解放為目標,以挖掘資本主義的根源性矛盾和系統性危機為動力,試圖要用自由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融合方法來解決社會自身問題。正如她強調:“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這兩個陣營的聯合所取得的智力優勢有效地扼殺了左派黑格爾主義的計劃。”[1]22(此處兩個陣營分別指:自由主義者和后結構主義者)所以,弗雷澤在內心里一直堅持社會科學“宏大敘事”,其目的不是為了解決一國之內的資本主義問題,而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去深度考量人類自由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第三代批判理論家是既跳出法蘭克福學派傳統,又回歸“宏大敘事”傳統的一次新飛越。從根本上實現了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理論回應和現實探索,將西方左翼堅持的全球正義觀從“一元”走向了“多元”,實現了西方左翼在正義理論和危機理論的全方位發展。誠然,在總體性批判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弗雷澤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采取了一種“兼而有之”的方法,在堅守的基礎上,努力深化、完善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基于此,第三代批判理論家在西方左翼普遍“拋棄”總體性批判理論的關鍵時刻,仍然以一種生命政治的擔當姿態全面復興資本主義的總體性批判理論,這不失為一種戰略思考和價值旨歸。深化馬克思主義研究、發展西方當代馬克思主義是其永恒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
歷史的發展是由人類創造的,歷史與現實的接榫是事物發展的不竭動力。關注人類社會的發展就必須深度挖掘當今世界所現存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脈絡,為此,重構認識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發展的新樣態,重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邏輯必須以人類發展為己任,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發展道路。其一,全面深化對資本主義的認知能力,科學構建具有馬克思所揭示的“前景性”的經濟危機理論(如利潤率下降、大規模失業、“繁榮—蕭條”的周期等經濟危機),并以“前景”為元結構,努力消解弗雷澤所關注的“背景性”的社會性危機(如政治、生態、安全等破壞性危機),科學構建“前景—背景式”的二元結構性理論,從而實現對資本主義總體性危機的戰略融合和有效化解。其二,全面防范和抵御新一輪全球性危機,科學制定社會發展政策,積極促動正義理論、危機理論與現實實際的接榫,努力使理論轉化為實踐,有效破除制約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合力促進矛盾的解決,將西方左翼所關注的公平正義理論在西方有效落地生根,合力促進矛盾的解決,實現西方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名副其實的公正平等和社會和諧。其三,全面升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價值追求,科學矯治左翼學者所提出的文化承認、公平分配、社會團結、政治代表權等代表全球正義的西方概念,擴大民間共識,深入文化交流,在互學互鑒互聯互通中強化彼此合理關切,努力匡正社會道德失序和政治倫理失范,以一種社會公民的高素養姿態全面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將人類徹底解放作為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判斷標準。
總之,弗雷澤和賈基認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構建是一項人類“新政工程”,在保持資本主義總體性批判理論的同時,科學構建第三代批判理論家所提出的“前景—背景式”結構性理論框架,從資本主義總體性認知和核心特質入手,全面厘清資本主義危機發生的根源,以實現對資本主義問題的系統性追蹤和全面性診斷。誠然,任何理論都絕不會完美無瑕,更不會有效實踐,在對待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批判理論家的觀點時,不能固執地追求一成不變的教條化式理論,不能按照西方左翼學者的思維固化我們的思維模式,不能生搬硬套地套用弗雷澤和賈基的“前景—背景式”結構理論來實現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性批判。相反,對弗雷澤和賈基的批判性哲學對話應保持一種客觀態度,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觀去分析、判斷、運思;對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應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用馬克思主義運動變化發展的觀點來求是、求實、求新,深化其理論基礎,擴大其實踐效能,從而真正實現“宏大敘事”落地生根,為人類幸福謀求理論指南,為人類解放擘畫大同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