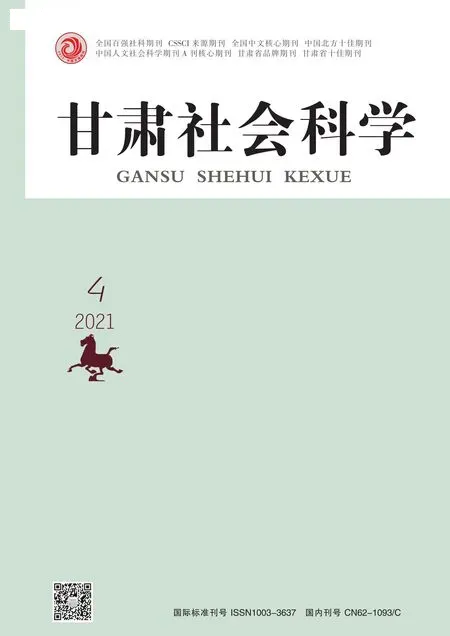“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在全域絲綢之路的時空維度和多重意義
程金城
(蘭州大學 文學院,蘭州 730020;陜西師范大學 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西安 710061)
提要: 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之間形成了具有世界影響的大河文明走廊。它是中國人的大地母親,是中華文明主要交往互動區,是多元一體民族共同體形成的腹地,是形塑中國社會結構和穩定國家統一的核心區。“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將綠洲絲路、草原絲路、南方絲路、高原絲路、冰上(東北亞)絲路和海上絲路連為一體,向西、向北經西域-河西走廊貫通阿姆河-錫爾河走廊、尼羅河-印度河走廊和草原文明走廊,向東、向南連接東亞、東南亞貫通海洋文明走廊,構成絲綢之路全域。如果這一假設成立,以蔥嶺為界的絲綢之路東段及亞洲文明的交流圖景可能被重新理解,絲綢之路格局及在人類文明體系中的位置可能被重新認識和評價,絲綢之路研究也可能由點向面輻射全域,拓展新的學術增長點和發展空間。
引言:重識文明體系和重釋文明價值
人類歷史的發展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當今世界遇到的諸多重大問題,都與“文明”相關。這迫使人們重新思考文明的含義和反觀文明的歷程,重識文明體系和重釋文明價值。
“文明”被高度重視的表征之一,是有關人類文明研究著作的暢銷并產生重要影響。僅就筆者閱讀所知,影響大者,如德國學者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對西方文明的評價及其反響,雅思貝爾斯《歷史的起源和目標》提出“軸心時代”理論及學者對其的多重闡釋;英國學者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人類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文明的接觸》《文明經受考驗》《亞洲高原之旅——文明的興衰》等對人類文明的系統研究及關于“挑戰”與“應對”模式的論述,凱倫·阿姆斯特朗的《軸心時代 塑造人類精神與世界觀的大轉折時代》對軸心時代理論的具體闡發,彼得·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通過二十幾條“之路”的研究對新的世界史的建構;如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產生的重大影響和激烈爭論,法國費爾南·布羅代爾的《文明史》對文明的重新定義和現象研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寫的多卷本《中亞文明史》對中亞文明的定位和全方位研究,以及日本宮崎正勝的《人類文明史 八千年來六大人類文明轉折》對世界文明的概括與前瞻等等。與此同時,各種版本的“全球史”暢銷,如全球史奠基者美國麥克尼爾父子的《麥克尼爾全球史:從史前到21世紀的人類網絡》,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 從史前史到21世紀》,斯提芬·D.希斯洛普等的《見證歷史 從遠古到現代》,英國喬治·威爾斯和美國卡爾頓·海斯的《全球通史 從史前文明到現代世界》,孫隆基《新世界史》等。還有一些對世界歷史有重大影響的斷代研究,如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 記述游牧與農耕民族三千年碰撞史》,伯納德·路易斯的《中東兩千年》、斯圖亞特·戈登《極簡亞洲千年史》等等。這些現象表明,“文明”的含義和價值闡釋及文明史研究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特別關注的領域,其整體性建構的特點完全不同于后現代主義的“解構”,“建構”意識和價值指向十分明顯。換個角度來看,“文明熱”與全球化進程相關,而全球化遇阻與爭議又使理論問題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助推文明歷史研究并影響對其闡釋的價值取向。如此,文明研究不僅僅是歷史陳述,更是價值判斷,其“當代性”顯而易見。
國際重要文明研究成果的中譯及產生的持續影響,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現象之一,也成為中國文明研究的重要語境。當此之際,中國考古和中華文明的研究生機勃勃,并經歷著從“黃河中心論”到“滿天星斗論”向“多元一體論”的轉變。諸如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的結論與爭議,重大考古發現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廣泛關注,各種各樣的品評歷史和對文明的熱議,表明了中國文明史也在豐富、重構和普及中。這一學術語境使得中國文明史的研究面貌一新,其成果數不勝數,如“中國文明研究叢書”(東方出版社)、“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學術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科學出版社)、“中國文明的歷史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中華文化元素叢書”(長春出版社)等;如《文明的足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果集萃》,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嚴文明《略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中國青銅時代》《藝術、神話與祭祀》,陳星燦、劉莉《中國考古學》,張舜徽《中國文明的歷程》,李濟《中國文明的開始》,易中天《易中天中華史》,朱乃誠《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葛蘭言《海外中國研究文庫:中國文明》等;如許倬云的《萬古江河》《歷史大脈絡》《觀世變》等,如葛劍雄的《黃河與中華文明》,李零的《我們的中國》《我們的經典》系列叢書,葛承雍的《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系列叢書,石云濤的《漢代外來文明研究》,林梅村《絲綢之路十五講》,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方文化交流》,等等。與之相關的還有“天下”觀念重提、“天下體系”及“世界秩序”深入探討。如果將這些現象置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絲綢之路考古與研究、“天下體系”的重釋及其哲學思考的語境中,則可以看出,中國文明研究在逐步納入世界文明體系研究之中,以人類意識、全球史觀和絲綢之路視域來探討中國文明及其價值,已然成為新的趨勢。
本文提出并探討的“黃河-長江文明走廊”①的命題,是由筆者在絲綢之路藝術研究中遇到的相關難題觸發的,對其思考則是基于人類文明史和全球史觀、中華文明探源和絲綢之路視域的學術背景,借鑒考古和歷史研究成果,在綜合相關知識基礎上的大膽假設,有待小心求證。其主旨是,世界文明主要起源于大河流域,“黃河-長江流域走廊”是絲綢之路上與“尼羅河-印度河流域走廊”“阿姆河-錫爾河流域走廊”等大河流域走廊相對而存在的人類文明走廊,是貫通絲綢之路東段中國文明與東亞文明的區域文明走廊,是凝聚多元一體中華文明與文化共同體的原發文明走廊。圍繞這一主旨,本文將探討的具體命題主要有:黃河-長江流域是相通相依的生物圈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自然走廊,是文明“流動”的走廊,是民族融合的走廊,是形塑中國社會結構并維系大一統格局的政治文化走廊,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連相通的走廊。其學理依據是:考古和歷史學界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討從“中心論”走向“多源論”,從散點認知趨向整體意識;不同學科對中國文明形成過程和文化歷史圖景的勾畫使得“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呼之欲出。這一假設如果成立,東方文明基因及生成機制也許會成為人類文明研究的原點之一,絲綢之路東段的歷史格局和網路之間的關系將可能被重新認識,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理解也會多一些思路,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將可能拓展出新的理論空間和學術增長點。
一、世界大河流域文明中的“黃河-長江文明走廊”
從全球史觀和絲綢之路視域看,人類從東、西兩端相向而行,共同拓展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明交匯和文化交流通道,大河流域走廊是連接人類不同文明的橋梁。
學界對全球史觀還有不同看法,但全球史所產生的積極影響不可否認。麥克尼爾全球史勾勒出人類交往逐步形成越來越復雜網絡的進程,其中論述了大河流域的重要性:大約在公約前3500—前3000年期間,形成歐亞大陸上的大都市網絡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尼羅河-印度河走廊”相連的三個地區和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都市網絡是最重要的現象。“尼羅河-印度河走廊”相連的“這三個地區分別是位于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地區、位于埃及的尼羅河地區和位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及其支流地區……沿海航行再加上內陸穿越陸地的商隊,使上述這三個地區彼此保持著一定的交往,應當把這些交往看作剛剛形成的一個相互交往網絡的組成部分。我們就將其稱為‘尼羅河-印度河走廊’,這是歷史上第一個大都市網絡”[1]55。在世界的東方,“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黃河中游地帶的中國北方黃土地區也出現了一個類似的交往互動的區域……中國文明對于其周邊的各個民族產生了激勵的作用,其結果就是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都市網絡持續地向外部新的地域擴展,并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就是歐亞大陸的第二個都市網絡體系”[1]55。麥氏全球史在研究舊大陸的各種網絡與文明的時候,特別注意了人類早期文明與大河流域之間的關系,提出與流域相關的“走廊”文明概念,大河流域走廊構成都市網絡,也形成文明體系。
從人類文明史看,絲綢之路大河流域走廊傳導了不同文明并使之具有了歷史聯系。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主張把“文明”作為歷史研究的單位,這一觀點在其《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中有具體論述,特別是對文明之間的聯系做了進一步研究。湯因比指出,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隨著蘇美爾-阿卡德人的商業向西北方向擴展,新的區域文明就已經在小亞細亞和塞浦路斯誕生。同期誕生于克里特島的新文明也許不僅從蘇美爾-阿卡德獲得了生存活力,而且從埃及汲取過精神養料。湯因比將埃及、蘇美爾、地中海與印度河流域聯系起來,描述了幾個大河流域之間的聯系,與麥克尼爾全球史的觀點大體一致。湯因比說:“如果蘇美爾文明的影響在東南方通過海路輻射,在西北方通過陸路輻射,那么就不可能不考慮印度河文明也具備由于蘇美爾的文化刺激而產生的可能性……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發端于蘇美爾文明的刺激,但與之有關系則是無疑的。”[2]65他進而講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黃河流域文化與歐亞大平原文化乃至與西南亞文化經過傳導而產生聯系,認為產生于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起源似乎更早,在中國最西北的省份甘肅持續的時間似乎更久,其例證就是彩陶。湯因比指出甘肅彩陶與誕生于公元前三千紀末以前烏克蘭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因為甘肅和烏克蘭位于歐亞大平原兩邊,而大平原也像海洋一樣,是可傳導的。”[2]69湯因比的這種推斷說明不同文化藝術之間傳導的可能,他的推斷將絲綢之路西段與東段聯系起來,體現出廣闊的歷史視域。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也論及絲綢之路史前史,說至遲在公元前5世紀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時代,希臘人就已經隱約地知道有一種“北方”文明,一條橫穿歐亞平原的小道把它和黑海北岸的希臘殖民地諸城邦連接起來。所謂“北方”文明,并不在“北風吹來的方向”,而是位于歐亞大平原東部,實際上就是中國,后來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人和羅馬人把它們稱作“賽利斯”和“希娜”[2]23。湯因比說的橫穿歐亞平原的小道,當是創辟期的絲綢之路。
從人文地理的角度看,絲綢之路大河流域走廊不僅孕育和滋養了人類及其文明,也與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和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關系密切。中國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指出:“一條大河與其他大河、其他文明區的距離,也是一個起著經常性作用的因素。如果與另一條大河的距離較近,中間沒有太大的地理障礙,就便于兩個流域之間的來往、交流和互補,也可能引起不同利益集團間的競爭和沖突。”[3]8他在論述黃河與中華文明的關系時,將其和尼羅河與西方文明的關系作參照,指出尼羅河三角洲“為埃及文明奠定穩定的物質基礎,滋養了綿延數千年的埃及、迦太基、希臘、羅馬、拜占庭、伊斯蘭文明”[3]8,“幼發拉底、底格里斯兩河流域與尼羅河流域、小亞細亞、愛琴海、希臘、羅馬之間距離不是太遠,兩河流域的早期農業帶動了尼羅河流域、環地中海地區的農業開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與埃及、希臘、羅馬等文明之間有密切、頻繁、有效的交流、傳播、傳承和相互影響”[3]9。葛劍雄與麥克尼爾、湯因比都將大河流域與人類文明的孕育聯系起來,指出其在溝通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傳播和相互影響中的重大作用。
從全球史、人類文明史和絲綢之路史的視域綜合來看,大河流域與人類文明的發生、發展具有天然的聯系,并具有普遍性,大河流域是文明流動的走廊。黃河流域“交往互動的區域”可視為“黃河流域走廊”;從這一視域繼續延伸,以“尼羅河-印度河走廊”為參照,在世界的東方,或者絲綢之路的東段,存在一個類似“尼羅河-印度河走廊”的大河流域走廊,這就是“黃河-長江流域走廊”。“黃河-長江流域走廊”既是自然走廊,也是文明走廊,兩者雖有阻隔,但并不截然分離,特別是文化的交往互動,更是相通相連相互影響,這為考古文物所證實,也由非物質文化遺存所傳承。
概觀絲綢之路全域,在其東段的“黃河-長江流域走廊”,孕育了中華文明并輻射東亞文明;在其“河中”地帶的“阿姆河-錫爾河流域走廊”,聯系著中亞文明,發揮了重要的橋梁和樞紐作用;在其西段,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地中海沿岸形成了既有區隔又有聯系的“尼羅河-印度河走廊”,聯結了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等文明。黃河-長江文明走廊作為東亞核心區,向西、向北經西域-河西走廊,與阿姆河-錫爾河走廊、尼羅河-印度河走廊和草原走廊交匯貫通,向東、向南連接東亞、東南亞貫通海上絲綢之路文明,將綠洲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冰上(東北亞)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連為一體,構成絲綢之路全域。大河流域走廊文明滋養著人類的精神家園,引領和矯正著人類前進的航線,而絲綢之路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融通作用。
二、黃河-長江走廊是中國人的大地母親
黃河和長江是地球上靠得最近的兩條大河(葛劍雄語,后詳),在自然地理上有阻隔也有連接,遙相呼應聯通草原和海洋,形成巨大的生物圈和生存空間,是中國人的大地母親,是孕育和承載中華文明的腹地。黃河和長江都發源于青藏高原。黃河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山東9個省區;長江流經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上海11個省區市,數百條支流延伸至貴州、甘肅、陜西、河南、廣西、廣東、浙江、福建8個省區的部分地區,一共輻射到19個省級行政區,淮河大部分水量也通過京杭大運河匯入長江。黃河、長江及其支流共同連接的省區市有20多個,其中青海、四川、甘肅、陜西、河南等省既有屬于黃河流域的地區,也有屬于長江流域的地區,形成黃河與長江之間局部區域的連接。長江和黃河,南北相往,橫貫東西,其干流和支流流經的廣大區域,牽挽高原、草原、平原和大海,擁抱著中華大地,蜿蜒曲折而相映成趣,各具特色卻并行不悖,整體上構成了相互聯系的遼闊地理走廊。黃河與長江,確有地理上的阻隔,黃河、長江本身就是“天塹”,形成了河東河西河南河北,江南江北江西等等,但是,中國民族的奮斗史、中華文明的形成史就包括了試圖逾越大江大河天塹的阻隔和戰勝江河自然災害的歷史。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祖先的“天下”意識從黃河流域逐漸擴大到長江流域等其他區域。在認知上,黃河、長江流域空間中的“地域”與觀念空間中的“知域”有著差別,地理上某些地段的阻隔,在文化或文明的聯系上并不構成障礙,而更多的是溝通或相互影響。著名學者許倬云說:“中國文化的發展有如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源頭相距不遠,都在巴顏喀拉山區,一向北流,一向南流。這兩條大河的水系,籠罩了中國的大部分疆域,然后殊途同歸,傾瀉于太平洋的黃海(黃河今注入渤海,但歷史上也曾注入黃海)與東海。兩個水域分別在中國的北部和中南部,界定了兩個地理環境,呈現了自己的文化特色。”[4]ii關于黃河與長江的地理人文關系,葛劍雄在《黃河與中華文明》一書中有一段精辟論述,其中包含幾個重要觀點:第一,“黃河和長江是地球上靠得最近的兩條大河,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在很多地段是直接相接的,它們的不少支流之間就隔著一道分水嶺。多條運河的開鑿和交通路線的開通,更使兩個流域連成一體”[3]8。第二,兩個流域從公元前221年開始,大多數年代都處于同一個中央集權政權的統治之下。第三,在兩個流域產生的文明萌芽相互呼應,匯聚到當時自然條件更優越的黃河流域,形成早期的中華文明,以后又擴散到長江流域。第四,“黃河流域的人口一次次大量遷入長江流域,為長江流域的開發提供人力和人才資源。當長江流域獲得了更有利的自然條件,經濟文化的發展后來居上時,又反哺黃河流域,幫助它重建和復興”[3]8。李零則指出,舊石器時代研究的主題是人類起源、擴散和定點,各自尋找各自的家園。“我們的祖先選擇歐亞大陸,選擇它的東部,選擇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中國的兩河流域,這個地點選得好。新石器時代的主題是農業起源和農業革命。中國是農業起源的三大中心之一,一點不比兩河流域晚。”[5]16黃河流域的黍類與長江流域的水稻共同代表了新石器時代中國農業文明的水平。筆者以為,這些學者的重要觀點,包含了對中國江河兩大流域在中華文明和中國歷史文化形成過程中共同發揮關鍵作用的深刻理解,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跳出區域文明中心論的思維定式,回歸大河流域與文明關系的自然狀態,參照對人類其他大文明系統的定位視角——比如兩河流域“新月”形的美索不達米亞與西亞文明,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河中地帶”與中亞文明,從更宏闊的視域觀照黃河與長江之間的關系,或許我們對黃河-長江流域走廊的提出就不會感到突兀,對這一走廊與中華文明及東亞文明之間關系的理解會有新的認識。
三、黃河-長江流域是中華文明主要交往互動區
從歷史長時段來看,中國文明在空間的起源分布和在時間中的傳播延展,都以黃河與長江的中間地帶為主要通道,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過程中,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交往互動區”是文明流動并嬗變的走廊,也是文明的主體。正如嚴文明所說:“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國古代文明是以黃河、長江的中下游為主體、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多中心聯合體,或稱為多元一體。”[6]
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中,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無疑是兩支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文明體系。它們各有其不同的內涵、形式、作用和歷史發展進程,但卻不是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干的。在長達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它們既相互對峙,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補充,使中華文明絢麗多彩,并給北方草原文化和沿海及海外文化以深遠的影響。中國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交流互動發展起來的。費孝通肯定黃河流域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指出黃河流域對長江流域的影響及其不同文化區系之間的聯系,他說,《禹貢》中總稱的“九州”,“大體包括了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下游的地區,奠定了日益壯大的華夏族的核心”[7]。許多考古發現也在不斷證實黃河與長江文明走廊的關系。2016年9至10月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三星堆博物館共同推出的大型展覽“青銅的對話——黃河與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展”,精選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湖北盤龍城遺址和湖南寧鄉遺址的青銅器,對不同區域文化面貌和特色青銅器物進行展示,勾勒出商代晚期黃河與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的格局和概貌。這些器物表明,在公元前16世紀,湯創立商代并向長江流域擴張,先是在長江岸邊即今武漢東部的盤龍城安營扎寨,隨后渡過長江,進入江南腹地②。發達的鑄銅術和復雜的禮器制度影響了長江流域青銅文明,而長江流域基于自身的文化傳統并未對黃河流域的青銅文明全盤接受,而是對其進行了選擇與創新,并反哺中原。“長江流域還將青銅這一物質載體與本土精神信仰、生活傳統和審美趣味相結合,進行文化創新。”[8]這有力地說明了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交流互動關系。其他相關的研究也得出相近的結論。如李學勤認為,良渚玉器和商代青銅器的饕餮紋,有很多共同的特點,不能用偶合來解釋,它們之間顯然有較密切的關系。“良渚文化和商代之間,存在著一段時間距離,在年代上居于良渚文化與商代之間的,有山東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饕餮紋……山東龍山文化乃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續”[9],而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之間也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提出的“中國相互作用圈”的觀點也有助于我們理解黃河-長江流域文明的相互關系,他提出,公元前4000年發生了兩個趨勢,“第一個趨勢是所有區域性文化的分布范圍都在擴大,彼此之間的互動關系增強;第二個趨勢是每個區域的新石器文化更加復雜化,導致各地都產生了獨具特色的文明。張光直將這種相互聯系的區城文化發展稱作‘中國相互作用圈’或‘龍山形成期’,最顯著的表現是兩種典型陶器——鼎和豆的廣泛分布(陳星燦2013)。從考古記錄看,這些陶器似乎是從黃河流域向南傳播的(Chang1986w:234—242)”[10]。王子今研究了秦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的融并問題,指出“大致在漢武帝時代,秦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融并而一。以‘漢’為代表性符號,以‘輝煌的漢代文化’為時代標志的文化體系出現在世界東方,并顯現了長久影響后世的基本風格”[11]。這些觀點與湯因比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看法是相似的,湯因比認為:“中國社會的原始家園在黃河流域,從那里擴展到長江流域。這兩個流域是遠東社會的源頭,該社會沿著中國海岸向西南擴展,也擴及東北方,進入朝鮮和日本。”[12]許倬云指出:“這兩個文化區之間,只有一些像秦嶺和伏牛山這樣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許多通道相通,所以黃土的中國和長江的中國,雖似隔離,卻能持續不斷地交流、沖突,相互刺激終于并合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要地區。黃土中國和長江中國,一硬一軟、一方一圓、一絕對一相對,這兩條路線的交織,使得中國思想既能謹守原則,又能應付時代的變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來發展的水墨畫,既有具體的寫實,也有抽象的寫意,相互交織成既復雜又豐富的藝術傳統。”[4]6中外學者的研究說明,黃河與長江文化是雙向互動的,在歷史進程中相輔相成、互為依托、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最終與古代中國其他區域文明融合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黃河-長江流域是文明流動的走廊,是孕育、影響并連接東亞文化圈的文化走廊,在人類文化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發揮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其相互依存、交往互動、交融互補、和而不同、取精用宏的精神是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至今依然有啟迪意義。
四、黃河-長江文明走廊是多元一體民族融合和文化共同體形成的腹地
在中華民族融合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民族大家庭,少數民族融入漢族,漢族也融入少數民族,而黃河-長江文明走廊為此提供了廣闊的融合之地,可以說是廣義的民族走廊。費孝通在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形成過程中意識到我們需要一個宏觀的、全面的、整體的觀念,看中國民族大家庭里的各個成分在歷史上是怎樣運動的,為此提出了“民族走廊”的概念③。他認為東西向的西北走廊、南嶺走廊與南北向的藏彝走廊是中國民族三大走廊,而這幾個走廊與絲綢之路有緊密而復雜的關系。費孝通在論述黃河流域文化重要性的同時多處并提黃河與長江流域相互聯系及其意義,觸及大河流域與民族走廊的關系。他說:“在相當早的時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它在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系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7]他認同谷苞等專家的觀點,認為在秦漢時代中原地區實現統一的同時,北方游牧區也出現了在匈奴人統治下的大一統局面,南北兩個統一體的匯合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的存在。他還指出,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作為漢族前身的華夏族,“其勢力已經東到海濱,和贛江流域、長江中下游甚至遠達山東沿海等地諸原始文化,不斷發生直接、間接的交往和相互影響,并且越到后來聯系越廣越遠”[7]。費孝通雖然未明確提出黃河-長江民族走廊的概念,但在論述民族融合過程中,反復提到黃河與長江流域的關系及其重要性,而這些關系也是絲綢之路研究中常被觸及的重要問題。李零的考古研究則提供了另一種認識民族關系的視角,他簡約而清晰地概括:“中國的民族分布,特點是四裔趨中,所有人,臉都朝著中原,眼都盯著中原。東北,遼寧是頭,黑龍江是尾;蒙古高原,內蒙古是頭,外蒙古是尾;新疆和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頭,新疆是尾;青藏高原,青海是頭,西藏是尾;云貴川,四川是頭,云貴是尾;湖北、湖南,湖北是頭,湖南是尾;東南沿海,浙江、福建是頭,兩廣、越南是尾。”[5]22這種東西南北“趨中”的圖景,也有助于我們思考黃河-長江流域走廊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關系。
中華民族共同體(許倬云有中國共同體的概念)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有政治、經濟、民族、語言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也與地域關系很大。“相對于其它幾個共同體,中國人大體上居住在同一地區,只有擴張而沒有遷移。中國內部區間的人口流動,使得不同的人群有混合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促使文化產生了共同性……”[13]3“中國共同體一直有一個相當堅實的核心,在同一個地區繼長增高……經過四百年的統治,秦漢皇朝終于將‘中國’的核心確定為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尤其是黃河、長江中游一帶,更是核心中的核心。”[13]209需要指出的是,說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并不是否認文化的差異,而是說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和而不同、你中有我的中華文化整體。即使在石器時代,黃河和長江史前文明已經有較多的相互聯系,在進入文明時代之后,逐漸融合的特點更加明顯,趨勢不斷加大,加上黃河的多次改道為交往融合提供了地理上的條件,使得黃河文化在與長江周邊的楚湘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文化體系不斷交匯融合。長江流域的吳文化、越文化、楚文化、江右文化、三星堆文化都與黃河文化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如吳文化中有中原商周文化與吳地本土文化融合的因素,越文化有商周文化與越地本土文化融合的因素,楚文化也有中原文化與楚地本土文化融合的印跡,江右文化是吳越楚文化融合的產物,三星堆文明也有與中原文明交流的跡象。這說明,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在民族融合和形成中國文化共同體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作為核心和“場域”的歷史意義。
五、黃河-長江文明走廊是形塑中國社會結構和穩定國家統一的核心區
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就生成的農業文化和生產方式,成為民族凝聚和社會結構形成的生態基礎,對中國家庭關系和大規模社會結構起到了形塑作用,成為民族凝聚力來源的重要因素。進入文明時代之后,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的意義不言而喻,對穩定國家大一統的格局發揮的作用顯而易見,黃河-長江流域走廊是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運行走廊。
農業經濟是中華民族凝聚力來源的重要因素。“黃河中下游的新石器遺址中已找到粟的遺存,長江中下游的新石器遺址中已找到稻的遺存。”[7]“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成為春秋戰國時期齊魯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質基礎。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成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質基礎……兩河(黃河、長江)是中國的兩條母親河,由她們哺育出的兩大體系的原創性文化構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14]黃河流域的菽粟農業、長江流域的水稻農業生產和生活方式,共同對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形成發揮了奠基作用。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黃河和長江兩個流域從公元前221年即秦開始,大多數年代都處于同一個中央集權政權的統治之下,社會的組織結構的變化及其政治運行、經濟活動、文化傳播都離不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聯通的核心區域。李零在《茫茫禹跡 中國的兩次大一統》中講:“中國文明,由兩條大河哺育,與南亞和西亞一樣。”“中國北方(黃河流域),先是周、夏、商三大塊并列,后是秦、晉、商三大塊并列。中國南方(長江流域),先是蜀、楚、吳三大塊并列,后是蜀、楚、越三大塊并列……加上北方邊疆,南方縱深,就是八大塊。”[5]10他提出的中國兩次大一統與禹行天下的觀點中,潛在地觸及一個重要問題,黃河與長江在同一的王朝統治下的貫通性。中國大一統是國土大,疆域大,“‘一統’是制度統一、政令統一、文化統一”[5]26。大一統之下的兩條最大的流域,不可能是彼此隔絕的,或者說其阻隔只是某些地理環境的,而政治統一、經濟一體、人員交往、民族融合、文化互動則是確定的,因此,黃河-長江流域走廊是中國社會結構的生成和形塑的走廊,也是政治文化貫徹運行的走廊,在吸引、凝聚各方面力量、穩定國家統一方面是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區域,其寬廣的回旋空間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重要保障。
六、黃河-長江文明走廊會通南北非遺、傳承活態文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黃河-長江文明走廊的重要構成部分和活態呈現。作為“遺產”的各種非物質文化形態既有地域的標識含義,更是不同文化的存在形態,各族群和社區在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形成有特色的非遺現象,表明文化內涵的地域性和多樣性,彰顯出價值意義的多維性。但同時應該看到,黃河-長江文明走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相通性和共融性,某些非遺事象則具有流域特征和同源關系。一個顯而易見卻習焉不察的現象,是許多由地方單位申報的非遺項目實際是跨越行政區劃而具有流域走廊特點的,比如民間文學和民俗中的神話、傳說、民族史詩,以及傳統舞蹈、音樂、傳統手工技藝等等非遺現象,許多是貫通黃河-長江流域的。如關于炎帝神農氏的神話,涉及黃河中下游如陜西寶雞、山西高平、河南拓城,直到長江流域的南方。因為其活動范圍有北方炎帝說、南方炎帝說,其中潛藏著部落與文化在地域上聯通的可能性和淵源的共同性。再比如,大禹治水是婦孺皆知的傳說,在甘肅的積石山,在四川的理縣,在浙江紹興,都有大禹治水的傳說,都有廟宇和紀念塑像。這些神話傳說作為觀念表達,其輻射的地理穿越了黃河-長江流域走廊,形成具有相通性的文化和心理空間。再比如儺舞和皮影戲,廣泛分布于黃河、長江流域,在不同區域的長期演化過程中,形成了不同流派。最典型的例子是獅子舞,從南到北,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各地都有,而獅子及獅子形象則是從西亞、南亞傳到中國的,與絲綢之路的開通有極大的關系。如此等等,表明非遺作為精神文化現象和族群社區的文化空間,其生成和傳承,既有特定時空限制的獨特性,也有跨越時空的相通性。目前的行政區劃和具體的保護單位只是便于申報和保護的便利,并不是非遺存在的自然區域。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構成了非遺的走廊,其活態性一直賡續著幾千年的文化之根和共同的情感基礎。
另外,對人類文明的理解,甚至對歷史場景的呈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或許是對考古的補充,二者的融合或許有助于理解某種文明和文化。自然,非物質文化不如考古文物那樣能作為“確鑿”的歷史證據,特別是有些非遺現象本身就被質疑或有爭議,但是,不能因此否認大部分非遺確有文化活化石的價值,非遺中有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原型意象,也常常具有大河流域的共同性,某些重要非遺的貫通現象是我們理解黃河-長江文明走廊整體性的重要視角。
七、百年考古和歷史研究對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共識的孕育
近百年來的中國考古和歷史研究,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討從“中心”走向“多源”,對中國文化歷史圖景的認識從散點認知趨向整體意識,這為黃河-長江文明走廊的認知提供了學理依據和學術史背景。
關于中國早期文明、特別是民族融合的探討在百年間提出了各種學說,先有夷、夏東西說(傅斯年),上古文化河洛、海岱、江漢三系說(蒙文通),華夏、東夷、苗蠻三分說(徐旭生);后有六大區系說(蘇秉琦),五大互動圈說(張光直),多元一體說(費孝通等),“重瓣花朵”說(嚴文明),兩次大一統說(李零),以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相近的觀點(李學勤)等。
傅斯年(1896—1950)的夷、夏東西說,通過古史與地理考察,提出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前期,大致有東、西兩個不同文化系統,夷與商屬于東系,夏與周屬于西系;提出歷史憑地理而生,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并無南北之限。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爭斗,因爭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這一學說后來受到一些質疑,但是,他提出的東西關系說,包含了地理與文化上相互關聯的因素和整體思維意識。蒙文通(1894—1968)上古文化河洛、海岱、江漢三系說,提出中國上古民族以河洛、海岱、江漢分為三系,其部落、姓氏、居處地域各不相同,其經濟文化各具特征。三系說對上古民族構成的地域認知包含了黃河、長江流域。徐旭生(1888—1976)的華夏、東夷、苗蠻三分說,認為中國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南蠻三個集團,逐漸同化,形成后來的漢族。其中經歷的變化就包括華夏族與東夷族漸次同化,氏族漸次合并,形成大部落的含義。這些學說既是說文明起源,也說文明傳播、對峙,既是說相對獨立的文明體系,也關乎文明之間的相互交流、融合。它們或許不是直接論述黃河-長江流域走廊文明,但是,卻觸及或者暗含著關于黃河與長江流域文明走廊關系的因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考古發掘及歷史研究的深入,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認識逐步深化,發生了從黃河流域“中原中心”向“滿天星斗”式到多元一體觀念的轉變。其認識變化的背景是其他大河流域考古遺址的不斷發現,如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如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和金沙文化遺址,以及近年來許多重要的考古發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過程的觀點逐漸被認可,也為黃河-長江流域文明走廊的觀點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三千余年前,周代開國,中原的華夏與東方的文化,融合為黃河流域的主流文化。稍后,楚文化集合江漢與南方文化的力量,成為長江流域的主流文化。更稍后,東南的吳越文化,一度向這兩大主流文化挑戰。中國本部幾個大文化圈終于在秦漢時代開始融合,但至今中國各地文化的差異,仍可以回溯到新石器時代。”[4]36-37許倬云的這個概括,言簡意賅地說明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國文化與大河流域的關系,而后來的歷史發展,進一步說明江河流域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這已經比較接近黃河-長江文明走廊的概念了。
八、學科協同、呼之欲出的黃河-長江文明走廊
多年來,學者們從不同學科和視角對中國文明形成過程和文化歷史整體圖景進行了富有特色的勾勒和描繪,雖然這些觀點當初的目的和含義有很多不同,但是,許多理論中潛藏著黃河-長江融通一體的意識,一些方面接近形成“走廊”共識,“黃河-長江文明走廊”的概念呼之欲出。概而言之,大致有這樣一些相關的論點。
第一,“胡煥庸線”的整體意識。1935年,地理學家胡煥庸(1901—1998)提出了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他通過計算,畫出了一條從黑龍江璦琿(后改名黑河)到云南騰沖的直線,這條線的東南,以36%的土地養活了96%的人口,其西北以64%的土地養活了4%的人口。這條線被稱為“胡煥庸線”。后來這條線也被用來標示自然生態線和民族分布線。相關人士對胡煥庸線也有一些爭議,但其影響深遠。筆者在這里提及胡煥庸線,主要認為這條線的劃分體現了一種整體觀念意識和思維方式,其中也包含了打通東西南北界限、穿越黃河長江的宏闊視域的意味。正是這種整體觀及其思維,影響了后世學者對中國歷史文化和人文地理的把握方式。
第二,童正恩“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視角。20世紀80年代,童恩正在《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一文中提出了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觀點,他認為,在從青海的祁連山脈、寧夏的賀蘭山脈、內蒙古的陰山山脈,直至遼寧、吉林境內的大興安嶺等東北方向,與西南部的橫斷山脈之間,一北一南形成半月形,“屏障著祖國的腹心地區——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這一地帶則自有其淵源,帶有顯著的特色,構成了古代華夏文明的邊緣地帶”[15]。“盡管這一高地綿延萬里,從東北至西南成一半月形環繞著中原大地,但是從新石器時代后期直至銅器時代,活動于這一區域之內的為數眾多的民族卻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處是如此的明顯,以至難以全部用‘偶合’來解釋。”[15]這就是著名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理論。童正恩從地理地貌特點,到文化因素的相互聯系,勾畫出了一個具有整體性的圖景,其中特別提到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作為祖國的腹心地區的意義。筆者認為這一視角,已經向黃河-長江流域文明走廊的意識靠近,只是他當時主要聚焦在東北至西南邊地的半月形。這一觀點在此后產生了很大影響,重要原因也在于他突破了一般人文地理研究的模式而體現出宏觀視野和整體意識。
第三,李零“兩個半月形文化帶”與“大十字”的圖式。李零在《茫茫禹跡 中國的兩次大一統》中勾畫出了中國歷史脈絡和文明融合的輪廓,包括中國文明由兩條大河哺育、中國民族四夷趨中、中國兩個半月形文化帶、中國由東南為陽、西北為陰的兩半構成,以及西周就有的“大十字”格局。李零在童正恩半月形文化帶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觀點,他說:“童恩正講,中國大地,從東北到西南,有個半月形文化傳播帶,這是講中國的西北和西南,即中國的高地。其實,中國沿海,也是個半月形的文化傳播帶,同樣值得重視。”“高地的半月形地帶,主要是戎、狄文化;沿海的半月形地帶,主要是夷、越文化。北中國海,渤海和黃海,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是夷的天下,南中國海,東海和南海,從浙江到越南,是越的天下,這兩條弧線,畫出個大圓,中間是中國的核心區。天下輻輳,各種族群都往里跑,有如漩渦,有些被吸進去,有些被甩出來。吸進去,變成華夏;甩出來,變成蠻夷。夷夏之辨,不在種族,而在文化……中國,一面山,一面海,西北是歐亞草原,東南是南島諸國,后面有更大更深的背景。”李零兩個半月形文化帶的視域,用兩個弧形畫出大圓,而中間的中國核心區,使人很容易想到黃河-長江流域走廊。他還講過:“西周有個大十字,橫軸是今寶雞—西安—洛陽—鄭州—開封—徐州—連云港一線,縱軸是大同—太原—長治—洛陽—南陽—襄陽—荊州一線。當年,周公站立的坐標點,北面是黃河,中國的東西大通道是傍著黃河走;南北大通道分兩段,北段是胡騎南下必走的山西大通道,要穿太行陘,從晉城到沁陽,從沁陽到洛陽。南段是宛洛古道接宛襄古道,宛襄(中國的地圖都是方圖,強調經緯坐標、計里畫方,所謂方位,都是四方八位加中央。)古道接荊襄古道。”[5]23筆者認為,李零勾勒出的上述圖景,特別是兩個半月形與一個“大十字”,其核心部分可以理解為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交流互動區,這已經接近營造出黃河-長江文明走廊的意象。
第四,楊義的“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之對角線效應”的觀點。楊義在《吳文化與黃河文明、長江文明之對角線效應》一文中提出,泰伯開吳,從陜西即黃河流域的中上游出發,來到長江中下游的太湖流域,即在中華民族黃河長江的土地上走了一條對角線。這條對角線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本質性的重要性。“它由北而南、由河而江、由陸而海,在三個維度上啟動了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的互動,啟動了江南與中原的互動,使中華民族在古代承受南北民族沖突時,有得天獨厚的回旋余地而使歷史傳承不曾中斷。”[16]“中華文明保持了五千年川流不息,綿延不斷,從而具有舉世驚為一絕的超時間長度的生命力,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擁有一個巨大的腹地,腹地中擁有黃河和長江的兩水并流,使這個文明在應對民族危機時具有了廣闊的回旋余地和重振的潛力。黃河使中華文明生根,長江使中華文明成為參天大樹。”[17]楊義是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大家,他對黃河與長江流域文明在中國社會歷史中關系的認識和眼界,其透徹和概括力不輸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他的視域穿越了黃河和長江。楊義的這種宏闊視域和超常思維運用到中國文學的研究中,便在舊材料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且高屋建瓴,他在《屈原詩學與湖湘文化》一文中指出:在詩學領域,把長江文明引入中華文明發展的總進程中的首功是屈原。屈原豐富、改造、拓展了中華民族精神結構中詩的神經。他的上下求索并不僅限于楚國,而是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出入無礙。屈原的楚辭“開發了中國詩歌的長江,從而與開發中國詩歌的黃河的《詩經》并列為詩騷傳統,給中國詩脈注入影響深遠的影響力和生命力。自從有了以屈原為首席詩人的楚辭,中華大地上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的互動互補、共造繁榮的聯系,又多了一條強大的精神紐帶”[17]。楊義的研究,從中國先民神話思維、詩性智慧、情感理想、審美追求等精神層面切入,貫通了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聯系,以“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豐富想象和開闊視野,闡釋了自然地理的黃河-長江走廊與文化精神的黃河-長江走廊之間的豐富聯系。由文學研究入手而對黃河-長江流域走廊貫通的多維度價值和意義的闡釋,不僅重繪了中國文學傳播和嬗變的路線和圖景,也從人文領域和審美共通感的視角,詮釋了黃河-長江流域走廊的存在及其意義。
綜上所述,地理學家從中國自然地理和社會狀況的角度對人地關系的分析,歷史學家對中國民族文化要素與地理關系的勾勒,考古學家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時空的宏觀統攝,文學史家對江河兩種文化特質及其詩意表達的闡釋,似乎都在以歷史整體觀從不同的向度朝一個方向接近,“黃河-長江流域文明走廊”呼之欲出。
九、黃河-長江文明走廊與絲綢之路研究
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并不是想當然地臆測,而是基于歷史、考古、民族、人文地理等領域的研究基礎進行學術探討。大凡人文地理學的啟示,考古發掘的物質文化遺產的物證,考古學、歷史學和人類學、民族學界接近共識的相關觀點,活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等豐富現象,以及對早期文明“不過江”觀點的反撥、天下體系的探討,都已經隱含黃河-長江文明走廊整體觀的因素,有些觀點在客觀上觸及黃河-長江流域連通的內容。不同學科對黃河-長江文明走廊的探討,也是學術意義及價值維度的多樣拓展。近年來黃河-長江流域的考古發現,不僅含有“城市”“文字”“復雜的禮儀建筑”這些西方文明的標志物,也還有冶金術、青銅器及其裝飾藝術等對文明“標準”的補充,特別是藝術在其中的重要地位日益顯現。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在人類文明的構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其研究成果有可能充實和豐富關于“文明”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黃河-長江文明走廊作為一個整體,其器物層面、制度層面、精神層面具有共同性和全域性。絲綢之路從長安到羅馬只是絲綢之路空間地理路線的起始和終點,而非絲綢之路作為網路的全區域。絲綢之路上的絲綢、陶瓷器、金銀器、動植物、香料、茶葉以及各種宗教文化、雕塑、繪畫、音樂、舞蹈等等的交流,東西方人員的交流,都以黃河-長江走廊作為核心區并聯系四面八方、五湖四海,輻射全域。絲綢之路離開黃河-長江走廊文明走廊的貫通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黃河-長江文明走廊”這一假設可以成立,那么,以蔥嶺為界的絲綢之路東段的面貌和東亞文明的交流圖景或許將會重新繪制,進而可以認為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孕育的華夏文明及其拓展的中國文明和東亞文明,與西段的兩河-尼羅河-印度河走廊及地中海文明,共同奠定了新大陸發現之前東西方兩端的世界區域文明體系。中國境內的綠洲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冰上(東北亞)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之間將不再被視為是各自分隔的道路體系,而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時斷時續、相互聯系的整體網路,絲綢之路輻射的區域應該是全域性的。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對內凝結各區系文明,向外連成絲綢之路廊帶。基于此,絲綢之路研究應該打破“點”的限制,由“點”到“面”,輻射絲綢之路全域。“從點到面”的意思,涉及兩個主要方面:
第一,絲綢之路地理層面的“點面”關系。這與對研究對象空間范圍的理解有關。在這個層面,“點”是“起點”或者重要“節點”,“面”是絲綢之路輻射的全域,是絲綢之路輻射和連接的整體區域,而黃河—長江走廊則不僅使各“路”貫通,而且使各方連為一體。這里觸及關于絲綢之路研究的思維方式和認知閾限的問題。學界曾經有過關于絲綢之路、包括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討論和爭議,弄清楚這些問題是有意義的。但是,這也只是絲綢之路研究的具體問題之一。絲綢之路之于中國,其代表的意義和它涉及的內容,基本相當于古代中外交流史,或者古代中國對外關系史。不管在哪個朝代,在絲綢之路上交流的品種有何不同,與不同地區有何關系,在絲綢之路視域中,都涉及中國與外界的關系史內容,關乎絲綢之路上的“中國”整體。漢、隋、唐時期的長安、洛陽,宋元時期的東京(開封)、臨安(杭州)和元大都等,在絲綢之路重要時期都是國都、中心,雖然它們也是“點”,但統攝全國,在相當意義上就代表中國。還有一些“點”,如敦煌、涼州、西域和泉州、漳州、寧波、揚州等等也都是重要的節點(青龍鎮遺址證明現在上海附近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不管這些點有多少,其重要程度如何,都是統一政權之下的絲綢之路交流交往。也就是說,絲綢之路從點到面的研究,就是不同時期中國對外關系的全域和整體研究。這在絲綢之路研究中實際已經有所體現,但是在認知和理論上應該進一步明確,英國學者弗蘭科潘將絲綢之路視為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的歷史觀、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對此有啟示意義。
第二,絲綢之路內容方面的“點面”關系。這與研究維度和層面有關。絲綢之路不僅僅是絲綢的交易,“絲綢”與“路”聯系起來,就成為東西方交流通道的代稱和象征,這已經是基本的共識。絲綢之路研究的內容涉及的方面不僅僅與考古、歷史、交通、軍事、經濟等等有關,也與人文有關。絲綢之路的研究,不同學科關注的內容和方法不同,考古、歷史、交通史等等的研究,重視證據,重視與“路”“路網”相關的路線、節點、交匯點等的事實考證,這是學科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流傳下來的物質遺留物是不完全的,而口傳方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神話、傳說、史詩、歌謠等等,可以作為考古的補充互證。比如,關于藝術形象中的動植物和器物造型、紋飾,如獅子形象、馬的形象、羊的形象、鷹的形象、菩提樹、金桃等等形象或者意象,都是與這些動植物在絲綢之路上的流動相關,也與這些動物形象的生成過程相關,這些過程背后有大量的屬于文化觀念、審美意識、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因素。有許多形象在中國化之后,生成文學藝術的原型或者主題、模式,這些方面就需要其他領域介入研究。絲綢之路研究的其他一些人文領域,比如藝術、文學、語言、宗教的傳播等等,可能需要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因為人類在絲綢之路上活動和交流,特別是與人類歷史的關系是復雜的,主觀動機與實際后果、當時的價值與后世意義之間不完全是簡單地因果對應關系。所以,“面”也涉及研究對象、內容和層次及其研究方法的問題。
黃河-長江文明走廊的文明成果和文化體系有自己的特質,對人類有重要而獨特的貢獻。文明互鑒,相向而行,交流包容,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化解沖突;敬天贊物,以人為本,尊祖崇道,激流勇進,不畏艱險等是黃河-長江文明走廊在歷史的長河中形成的共同體意識和經驗基因,是優秀的精神內蘊和文化傳統。面對未來,撫今追昔,為了應對當代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我們有必要在人類文明史與絲綢之路視域中重識黃河-長江文明走廊體系,重塑黃河-長江文明走廊文化意象,重釋黃河-長江文明走廊文化價值。這有待于學人共同切磋探討。
注 釋:
①關于“走廊”的概念,筆者認同李紹明的解釋:“走廊原本是建筑學的一個概念,指一種通道式的建筑形式;后借用到地理學中成為一種地理學概念。”見李紹明:《藏彝走廊民族歷史文化》,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頁。“文明走廊”則是文明生成、流動與傳播的走廊。
②此處參考了“青銅的對話——黃河與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展”之“展覽推薦”詞,見《美成在久》2016-09-15。另參見參考文獻[8]。
③“民族走廊”概念的來由,李少明做過這樣的解釋:“關于民族走廊,10年前,筆者在《西南絲綢之路與民族走廊》文中下了一個定義,是這樣說的:‘民族走廊是費孝通先生根據民族學界多年來研究提出的一個新的民族學概念。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長期沿著一定的自然環境如河流或山脈向外遷徙或流動的路線。在這條走廊中必然保留著該民族或族群眾多的歷史與文化沉淀。’”后來他補充說:“我個人以為,民族走廊雖是一個民族學概念,但它必須與地理學有關的概念有所掛鉤或有所對應方能成立。即這一走廊必須首先是自然地理的,然后才有可能是人文地理的,如果運用到民族或族群的長此以往沿此環境遷徙移動研究上,則民族走廊就成為一個民族學概念。”見李紹明:《藏彝走廊民族歷史文化》,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