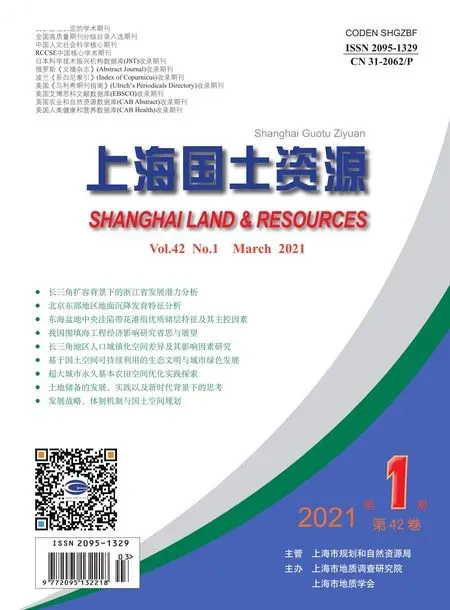城鎮化背景下欠發達縣域土地利用結構與經濟績效關聯度及優化分析——以江西上饒市萬年縣為例
戴 蒙,陳榮清
(東華理工大學測繪工程學院,江西·南昌 330013)
2020年4月3日國務院印發《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中提出優化城鎮空間格局,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提出了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推進社會經濟轉型發展,引導地方政府逐漸摒棄靠大量土地要素投入帶動城鎮化。相比發達的縣域,欠發達地區在資金、技術及區位存在一定短板,社會發展模式轉型的難度和程度都較大。因此,如何通過土地利用結構與經濟關聯度分析,協調好土地、資本和技術之間的相互關系,是當前欠發達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
針對上述問題,學界從諸多角度開展了研究,包括土地結構變化的特征[1-6]、土地利用結構的驅動因子[7-10]、土地結構優化[11-15]、土地利用績效[16]、土地結構與產業結構[17-21]等。而已有研究大多期限較短,不利于觀察土地結構與經濟績效的動態變化,且大多通過土地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未深入探討區域哪類土地與經濟發展最相關。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延長了研究期限,以五年土地利用數據,利用信息熵理論對數據進行處理,分析萬年縣不同時期地類結構的變化規律及有序度。通過灰色關聯分析法,將地類結構變化與土地經濟績效之間的關聯充分展現,并且為了更加具體地了解哪類土地與經濟的關聯度最大,還對二級地類與經濟績效的關聯度進行了測算分析,以期為區域經濟上漲,提供更加合理的土地結構調整建議。
1 研究區概況及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萬年縣是江西省上饒市下轄的一個縣,地處江西省東北中部,東與弋陽縣、鷹潭市的貴溪市毗鄰,南與鷹潭市余江縣交界,西與余干縣接壤,北與樂平市相連、與鄱陽縣隔樂安河相望,面積1140.76km2,轄六鎮六鄉。縣城距南昌93km,是貢米之鄉。2019年末,全縣戶籍人口44萬人,常住人口37.27萬人,其中:城鎮人口19.9萬人,鄉村人口17.36萬人。全縣地區生產總值165.55億元,比上年增長7.8%。萬年縣土地總面積為170.95萬畝,其中:耕地31.92萬畝,占18.67%;山地105萬畝,占61.42%;居民點、工礦及交通用地23.03萬畝,占13.48%;水域11萬畝,占6.43%。
1.2 數據來源
本研究中的土地利用結構數據來源萬年縣自然資源局土地變更調查數據,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江西省萬年縣統計年鑒(2011~2017)。
2 研究方法
2.1 土地信息熵模型
信息熵起源于物理學的一個概念,用來測度有機整體的復雜性和均衡性,熵值和系統的有序度表現為反比,值越高,系統就越紊亂。研究區域中的每種地類的動態轉化關系,都能夠詳細完整的在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反映。
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Bi是i種類型土地的占地面積;B是某地區土地總面積;Qi是i種類型的土地面積與當地土地的總面積的比值;H代表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根據信息熵的計算公式,得出當地土地利用結構的均衡度和集中度:

式中:J是均衡度,它反映了該地區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變化。其值在0到1之間。J的值越高,本地土地利用均衡的水平越高;I表示集中度,解釋的是土地利用集中程度。
2.2 多因素加權平均法
以末端最值為基本單元,將各評價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再根據所述原理得出萬年縣土地利用經濟績效的指數:式中:Cj是土地利用經濟績效指數;Iij是第i年第j個指標經過標準化后的值;Wj是各指標權重。
2.3 灰色關聯度模型
對于兩個系統之間的元素,隨時間變化或不同對象產生變化的相關性大小的度量,稱為關聯度。在系統優化過程中,如果兩個組成部分的變化趨勢穩定,則可以說兩者高度相關;否則較低。所以,作為測量元素之間的相關程度的方法,灰色關聯度分析法是基于元素之間變化趨勢的異同程度,即“灰色關聯度”。根據灰色關聯的概念,擇取經濟績效指數作為母序列,把左右地類以及其信息熵值作為子序列,則母序列和子序列在同一時刻的關聯系數為:

其中:ξi(k)是x和xi在k點的關聯系數;|xk-xik|表示母序列與子序列之間的絕對差;分別表示絕對差中的最小值以及最大值;ρ記為分辨系數,在此次研究中選取ρ=0.5,可得關聯度:
3 結果分析
3.1 土地利用結構熵變分析
根據2.2中的公式,代入萬年縣各類土地面積,可得出表1中各項數據和圖1的信息熵變化。由此可知,信息熵和均衡度都是“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化趨勢,其中信息熵增長了0.0079,均衡度增加了0.0039,集中度的數值變化與前兩者相反,最終減少了0.0039。通過分析可知,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變化的直接原因是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體現在耕地、城鎮村及工礦用地、交通運輸用地和其他土地等4類土地面積的增加,林地、園地、草地和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等4類土地面積的減少。耕地面積從2011年的32482.27hm2增加至2017年的33185.63hm2,凈增加703.4hm2,城鎮村及工礦用地從2011到2017年增長了616.2hm2,交通運輸用地從2011到2017年增長了312.6hm2。

表1 萬年縣2011~2017土地利用結構及信息熵Table 1 Land use 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entropy of the Wannian county from 2011 to 2017(單位:公頃)

圖1 萬年縣2011~2017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Fig.1 Land use structure information entropy of the Wannian county from 2011 to 2017
研究期內萬年縣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變化幅度較小,說明該期限內社會經濟活動對土地整體結構的影響并不顯著。信息熵在2011~2012年表現上升趨勢,且變化幅度較大,說明土地利用在該時期內有較大變化;2012~2014年表現為下降,說明區域的土地結構有序性不斷增加;2014~2017年土地結構又表現上升趨勢,但是上升的速率越來越小,說明區域的土地結構越來越合理。
上述變化主要是因為:在發展早期,土地利用的發展主要受自然因素的影響,表現為各種地類均衡發展,沒有很大的差異性和層次性,土地表現為無序性較高;但隨著城鎮化越來越深入,人類活動的影響越來越大,地類向著人類希望的方向發展,對于人類影響較大的工業用地的地類發展較快;而包括農業用地在內的其他地類逐漸減少,這就使得各個土地利用地類之間發展逐漸表現出差異性和層次性的特點,使得區域土地利用系統的信息熵發生變化。信息熵變化幅度越來越小,土地結構越來越合理,土地利用的有序性逐漸增強,這與萬年縣這幾年的發展情況是可以相互印證的。萬年縣依托自身的自然地理條件,立足本縣農業立縣的大前提,前期的發展更加注重農業產業的發展,后為了響應中央號召,當地政府大力推進城鎮化的發展進程,使縣域內城鎮區規模得到擴大,萬年縣的土地利用結構日益合理,土地利用結構的無序度也在下降。
3.2 土地經濟績效分析
選取單位土地面積的GDP、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固定資產投資額等指標作為萬年縣土地利用經濟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

表2 萬年縣2011~2017土地利用經濟績效評價指標Table 2 Econo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land use in Wannian county from 2011 to 20(17單位:萬元/km2)
根據2.3中公式,將表2中數據代入,得到圖2。可知在研究期間,縣區內土地經濟績效隨時間不斷增加,且在研究期末達到最大值,凈增0.4908。表明萬年縣近期社會發展前進方向與土地內部結構調整變化趨勢相適應,現行土地政策以及土地管理方式合理,應該繼續保障其總方向不變,結合城鎮化發展需要,對土地利用結構做出適宜地瞻前性調整,優化土地利用結構,實現土地利用系統合理有序循環,使土地承載力、土地利用產能與經濟相協調,加強土地利用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力。

圖2 萬年縣2011~2017年土地經濟績效指數Fig.2 L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dex of Wannian county from 2011 to 2017
3.3 關聯度分析
根據2.4中公式,將萬年縣土地利用結構表征值信息熵與土地利用經濟績效代入,得到表3中各一級地類數據,可知土地利用結構與土地經濟績效之間相關性顯著。在研究區域的所有一級地類中,與經濟績效的增長相關性最大的是交通建設用地,關聯度最高0.7572,其他土地第二0.6799,城鎮村及工礦用地第三0.6401和耕地第四0.6328。為更加清晰了解哪類土地與經濟發展更加密切相關,繼續探討二級地類的關聯度,其思路方法與前述相同,其中公路用地關聯度最高0.8032。結合萬年的發展趨勢對上述結論分析可知,隨著城鎮化發展日趨深入,外部投資不斷引入以及居住環境的改善,萬年縣的吸附效應也隨之加強,各類建設用地需求進一步擴大,與之對應的交通運輸用地和城鎮村及工礦用地經濟效益不斷上升,所以交通建設用地與經濟的相關性顯著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表3 萬年縣2011~2017土地利用結構與土地經濟績效的關聯度表Table 3 Correlation degree table between land use structure and l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Wannian county from 2011 to 2017
4 優化建議
4.1 優化思路
鑒于公路用地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突出。本文將選取2011、2017年萬年縣各鄉鎮的公路用地面積變化趨勢及變化幅度,與各鄉鎮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對比分析,為未來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提供建議。具體方案如下:
(1)公路用地的增量越大,經濟增長越慢,說明該地區公路用地要素投入飽和,對經濟發展的刺激效果下降,應該控制該類用地的擴張。
(2)公路用地的增量越大,經濟增長越快,說明兩者變化方向一致,為了刺激經濟持續快速的發展,應適當加大該類用地的要素投入,滿足發展需求。
(3)公路用地增量較小,經濟增長較快,應加大公路用地投入,為經濟快速發展減輕交通障礙。
(4)公路用地的增量越小,經濟增長越慢,此類地區最應加大公路用地的投入,輔助經濟發展。
從表4可知,2011年各鄉鎮的公路用地現狀,面積前三的分別是湖云鄉、石鎮鎮、汪家鄉;占比前三的分別是湖云鄉、汪家鄉、齊埠鄉。2017年各鄉鎮的公路用地面積,相比2011年基本有所增加,少數鄉鎮有所減少,其中面積前三分別是陳營鎮、湖云鄉、石鎮鎮;占比前三的分別是湖云鄉、陳營鎮、汪家鄉。公路用地占比增量,陳營鎮>珠田鄉>裴梅鎮>大源鎮>石鎮鎮>梓埠鎮>青云鎮>汪家鄉>蘇橋鄉,且有齊埠鄉-0.018%>湖云鄉-0.021%>上坊鄉-0.053%等三個鄉鎮表現出下降趨勢。由于各鄉鎮GDP難以獲取,所以選取萬年縣各鄉鎮的可支配收入總量,作為衡量其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增長比陳營鎮<石鎮鎮<青云鎮<蘇橋鄉<上坊鄉<汪家鄉<梓埠鎮<裴梅鎮<湖云鄉<齊埠鄉<珠田鄉<大源鎮。

表4 萬年縣2011~2017年優化指標表Table 4 Optimization indicators of Wannian county from 2011 to 2017
4.2 調整建議
依據前述優化思路,將萬年縣各鄉鎮分為四個優化等級,一級:公路用地變化量超過1%,經濟指標變化量低于50%;二級:公路用地變化量在0.2%~1%,經濟指標變化量超過100%;三級:公路用地變化量低于0.2%,經濟指標變化量超過100%;四級:公路用地變化量低于0.2%,經濟指標變化量低于100%。如圖4所示。

圖4 萬年縣各鄉鎮優化圖Fig.4 Optimization map of each township in Wannian county
分析可知,東西部有較大差異,總體而言西部對公路用地的需求更大,東部次之。其中陳營鎮屬于一級優化區域,其公路用地增長比在研究期內是最大的,但是其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增長比最低,表明陳營鎮的公路用地有飽和趨勢,對經濟發展的刺激效果較弱,應該控制該類用地的擴張。二級優化區域包括珠田鄉、裴梅鎮、大源鎮,這三個鄉鎮公路用地和經濟指標都有較大增長,兩者變化方向一致,這些鄉鎮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可以適當加大交通運輸用地的投入和對公路的建設,來刺激經濟更加快速的增長。三級優化區域包括齊埠鄉、湖云鄉,這兩個鄉鎮的公路用地表現減少趨勢,但是其經濟增長卻比較快。根據2.3節所述結論,可以通過增加對公路用地投入,使得這兩個鄉鎮的經濟發展速率進一步提高。四級優化區域包括石鎮鎮、梓埠鎮、青云鎮、汪家鄉、蘇橋鄉、上坊鄉,這六個鄉鎮對公路用地擴張需求比前三個級別要大,因為這六個鄉鎮的公路用地占比增量較少,經濟增長比排名靠后,因此為了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調整土地結構,加大對公路用地的投入。
5 結論
本文通過信息熵模型對萬年縣土地利用結構有序性進行分析,再利用多因素加權平均值法對萬年縣的經濟數據進行分析,最后利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分析土地利用結構與經濟績效的關聯度,深入探討哪類土地與經濟發展最相關,并結合分析結果,以刺激經濟高速協調發展為目的,對區域未來土地利用結構調整方向提出相關建議。具體結論如下:
(1)區域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化趨勢,總體而言增加了0.0079,導致信息熵變化的直接原因是建設用地增加和農用地減少,且信息熵變化幅度在研究末期逐漸下降,表明土地利用的有序性逐漸增強,土地結構日益合理,社會經濟發展方向與土地內部結構動態變化趨勢相適應,區域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2)萬年縣與經濟績效關聯性最大的不是占地面積最大的地類,也不是面積變化最大的地類,而是與各經濟績效直接相關的地類公路用地。通過劃分優化等級發現,研究區域東西部交通用地和經濟增長速率不平衡,其中2011~2017年石鎮鎮、梓埠鎮、青云鎮、汪家鄉、蘇橋鄉、上坊鄉等六個鄉鎮的公路用地占比增量較少,經濟增長比排名靠后,因此為了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調整土地結構,加大對公路用地的投入。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楊奎,張宇,趙小風,等. 鄉村土地利用結構效率時空特征及影響因素[J]. 地理科學進展,2019,38(9):1393-1402.YANG K, ZHANG Y, ZHAO X F, et al.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ructural efficiency of rural land us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38(9):1393-1402.
[2] 毛鴻欣,賈科利,高曦文,等. 1980~2018年銀川平原土地利用變化時空格局分析[J]. 科學技術與工程,2020,20(20):8008-8018.MAO H X, JIA K L, GAO X W, et al. Analysis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use change in Yinchuan plain from 1980 to 2018[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2020,20(20):8008-8018.
[3] 郭榮中,申海建,楊敏華. 長株潭地區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時空測度與演化[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9,40(9):92-100.GUO R Z, SHEN H J, YANG M H. Spatial and temporal entropy measurement and evolution of land use structure information in Changzhutan area[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9,40(9):92-100.
[4] 陳仙春,趙俊三,陳國平. 基于“三生空間”的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多尺度分析[J]. 水土保持研究,2019,26(5):258-264.CHEN X C, ZHAO J S, CHEN G P. Multi-scale analysis of land use spatial structure in central Yunnan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ree-life space[J]. 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2019,26(5):258-264.
[5] 譚遠模,謝思梅,謝榮安. 土地利用時空變化與城市化發展分析[J]. 測繪通報,2020(4):139-142,146.TAN Y M, XIE S M, XIE R A. Analysis on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land use an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J]. Bulleti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2020(4):139-142,146.
[6] 付永虎,姚瑩瑩,劉俊青,等. 江蘇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及其效率與城市化耦合協調性測度與評估[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20,25(9):187-199.FU Y H, YAO Y Y, LIU J Q, et a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urban land use structure and its efficiency and urbanization in Jiangsu[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0,25(9):187-199.
[7] 陳磊,孫佳新,姜海,等. 南京市土地利用結構時空格局及驅動因素[J]. 水土保持研究,2020,27(1):197-206.CHEN L, SUN J X, JIANG H,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land use structure in Nanjing city [J].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20,27(1):197-206.
[8] 黃曉峰,林皆敏. 泉州市土地利用結構的量化分析與評價[J]. 上海國土資源,2012,33(2):83-88.HUANG X F, LIN J M.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land use structure in Quanzhou city[J]. Shanghai Land &Resources, 2012,33(2):83-88.
[9] 歐聰,張坤. 城市土地利用結構演變分析及其驅動機制研究[J].上海國土資源,2015,36(3):39-43.OU C, ZHANG K. The evolution analysis and driven mechanism of city land use structure in Changsha[J]. Shanghai Land &Resources, 2015,36(3):39-43.
[10] 宋具蘭,陳時彬,楊靖,等. 新型城鎮化驅動下西部欠發達地區土地利用結構與形勢分析[J]. 上海國土資源,2020,41(4):29-33.SONG J L, CHEN S B, YANG J, et al. Analysis of land use structure and situation in western underdeveloped area driven by new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Zunyi city[J]. Shanghai Land &Resources, 2020,41(4):29-33.
[11] 賈克敬,何鴻飛,張輝,等. 基于“雙評價”的國土空間格局優化[J].中國土地科學,2020,34(5):43-51.JIA K J, HE H F, ZHANG H, et al. Land spatial pattern optimization based on double evaluation[J]. China Land Science,2020,34(5):43-51.
[12] 魯學孟,劉學錄,張晶,等. 甘肅省慶陽市土地集約利用與土地利用結構的耦合協調關系[J]. 水土保持通報,2019,39(6):240-245.LU X M, LIU X L, ZHANG J, et al.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nsive land use and land use structure in Qingyang city, Gansu province[J].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9,39(6):240-245.
[13] 田曉宇,徐霞,江紅蕾,等. 退耕還林(草)政策下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28(S2):25-30.TIAN X Y, XU X, JIANG H L, et al. Optimization of land use structure under the policy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grass)[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28(S2):25-30.
[14] 唐麗靜,王冬艷,楊園園. 基于“多規合一”和生態足跡法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J]. 農業工程學報,2019,35(1):243-251.TANG L J, WANG D Y, YANG Y Y. Land us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based on multi-planning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9,35(1):243-251.
[15] 賈寧鳳,曹蓉,王曉雅. 區域生態和經濟系統耦合效應下的土地利用優化配置[J]. 山西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9,42(2):454-464.JIA N F, CAO R, WANG X Y.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nd use under the coupling effect of regional ecology and economic system[J].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19,42(2):454-464.
[16] 匡兵,周敏,陳丹玲. 岳陽市土地利用結構變化與土地利用績效的關聯度分析[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17,36(1):137-142.KUANG B, ZHOU M, CHEN D L. Analysis on the correlation degree between land use structure change and land use performance in Yueyang city[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17,36(1):137-142.
[17] 殷閩華,肖志明. 福州自貿片區用地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互動機制研究[J]. 華東經濟管理,2018,32(7):35-39.YIN M H, XIAO Z M. Research on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lan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Fuzhou free trade zone[J].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2018,32(7):35-39.
[18] 徐馨裔,劉志有,董露,等.國土空間規劃視角下產業結構與土地利用結構相互關系研究[J]. 生態經濟,2020,36(4):69-74.XU X Y, LIU Z Y, DONG L, et 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nd use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space planning[J]. Ecological Economy,2020,36(4):69-74.
[19] 鐘文,鐘昌標,鄭明貴. 土地財政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扭曲效應研究——基于經濟集聚與產業結構視角[J].華東經濟管理,2020,34(10):105-111.ZHONG W, ZHONG C B, ZHENG M G. Study on the distorting effect of land finance on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J].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20,34(10):105-111.
[20] 薛建春,侯思杰,吳彤. 基于VECM模型的內蒙古土地利用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的動態關系分析[J]. 內蒙古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0,51(2):129-134.XUE J C, HOU S J, WU T. VECM model-based dynamic relationship analysis of land use carbon emissions with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Inner Mongolia[J].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20,51(2):129-134.
[21] 廖喜生. 基于STIRPAT模型的土地集約化利用效應實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8,34(2):94-97.LIAO X S. Empirical analysis of land intensive use effect based on STIRPAT model[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8,34(2):9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