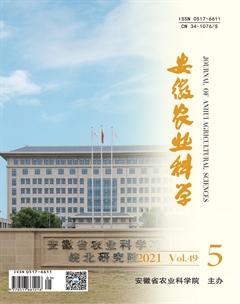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發展的問題研究
岳慧詩 鄒新陽



摘要 建立完善的農村普惠金融體系是城鄉協調發展、縮小城鄉差距、促進農村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和有效途徑。在現實層面,農村經濟得不到有效信貸資金支持仍然是農村金融亟待解決的問題。據此,通過考察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的發展現狀,從供需雙方和基礎設備建設兩個方面揭示了農村普惠金融發展的現實困境,提出了創新農村普惠金融產品和服務、健全普惠金融業務支持體系、加強農村普惠金融宣傳與教育等針對性的政策和建議。
關鍵詞 農村;普惠金融業務;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 S-9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0517-6611(2021)05-0225-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05.063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YUE Hui-shi, ZOU Xin-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rural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is the necessary premise and effective way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growth. In reality, it is still an urgent problem for rural finance that rural economy can not get effective credit fund suppor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areas, reveal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from both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innovating rural inclusive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improving inclusive financial business support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Rural area;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Problem;Countermeasure
2016年以來,連續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要求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加快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發展農村普惠金融。我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體,二元金融長期困擾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金融市場供求失衡,多層次、全方位、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體系還未建成,農村“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長期制約農村健康可持續發展,影響了農村人口收入水平和生活幸福指數的提高,阻礙了政府鄉村振興戰略和全面脫貧的實現。要破解這個難題,調整農村金融結構是一個有效手段,特別是在當前扶貧攻堅階段。普惠金融從2005年正式提出,已經發展了15個年頭,在支農助農、扶助弱小方面已經體現了一定的優勢[1]。隨著農村普惠金融的不斷創新,各涉農金融機構的普惠金融業務涉及存貸款、保險、理財等越來越多的業務類型[2],能夠以更合理的成本將被傳統金融業務排斥在外的弱勢群體納入服務范圍。但農村普惠金融業務自身發展中也還存在一定的問題,需要調整和完善,以適應新時期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盡早實現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3]。
1 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發展現狀
隨著普惠金融的不斷推進,各主要農村金融機構均根據自身性質、涉農特點,開辦適合本機構發展的普惠金融業務。
1.1 農村普惠金融業務構成
普惠金融強調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業務設計強調多維度和包容性,從當前金融實業和學界的共識來看,農村普惠金融業務涉及范圍不斷擴大,從最初的小額信貸[4],發展到保險、匯兌、轉賬、代理、理財和養老金等業務。從當前主要農村金融機構的普惠金融業務拓展來看,農村普惠金融業務是以信貸為主,擔保和保險為輔,為更多的農民、農村低收入者提供包容性金融服務。信貸業務仍然是普惠金融的典型,如中國農業銀行的惠農e貸、金穗惠農卡、農戶小額貸款和農村個人生產經營貸款;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的傳統農戶貸款,生產合作社貸款等;各農村商業銀行小微金融中涉農的各類易貸產品,各農村信用社的農戶聯保貸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等[5]。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興起,“互聯網+普惠金融”是農村金融未來的發展方向。積極開發和利用數字技術,實現互聯網金融服務“三農”創新突破。如中國農業銀行的“農銀惠農e通”平臺,為涉農產業鏈“生產、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客戶群體提供全流程的供銷經營服務、線上線下支付服務以及網絡融資服務,平臺客戶規模約267萬戶,交易金額達5 863億元,增長幅度分別為71%和135%。
1.2 農村普惠金融發展態勢
我國普惠金融自2005年提出以來,發展力度持續增強,政府積極引導農村普惠金融的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涉農貸款余額從2007年末的6.1萬億元增加至2018年末的32.7萬億元,平均年增速為16.46%,與各項貸款余額的比重從22%提高至24%(表1)[6],農業、農村、農戶貸款余額與涉農貸款余額同向變動,但增長速度卻逐年下降。隨著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的不斷創新,“兩權”抵押貸款和農業保險成為新的普惠金融業務增長點。截至2018年末,232個農地抵押貸款試點縣貸款余額520億元,59個農房抵押貸款試點縣貸款余額292億元。農村普惠金融業務除了信貸外,逐步發展起來的農業保險,普惠效果也在逐年增加。2007—2018年,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從53.3億元增長到571.4億元,參保農戶從4 981萬戶次增長到1.95億戶次,市場規模迅速擴大,農業保險風險保障金額從1 720億元增長到3.46萬億元[7]。除傳統農業保險外,成本保險、收入保險、價格指數保險等新型產品逐步推向市場,農產品價格保險試點地區于2016年末覆蓋至全國,試點品種有生豬、蔬菜、糧食作物和地方特色農產品共四大類50多種。
2.3 農村普惠金融業務支持體系
農村金融機構發展普惠金融業務,需要農村基礎設施、支付結算設備等硬件和征信體系、金融法律及監管制度等軟件的支撐[8]。在基礎設施方面,交通便利度和互聯網普及率是影響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發展重要指標。截至2018年末,全國農村公路里程404萬km,基本覆蓋全部鄉鎮。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 2018年 12 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29 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 59.6%,農村網民數量逐年增加,由2014年的1.78億人增長到2018年的2.22億人,但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相對城市仍較低,僅有38.4%(圖1)[9]。為了彌補互聯網普及的不足和充分利用智能移動終端的優勢,2017年“普惠通”APP上線,推出“普惠金融,服務三農和惠農惠民”的戰略理念。農村地區是金融服務覆蓋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金融供求雙方結構失衡問題在區域層面的表現。截至2018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覆蓋全國3.08萬個鄉鎮,覆蓋率達到95.7%;基礎金融服務覆蓋53.85萬個行政村,覆蓋率達到99.2%,基本實現村村有服務。保險服務覆蓋3.07萬個鄉鎮,覆蓋率達到95.5%,銀行卡助農取款服務點共有82.3萬個[10],降低了農村居民因存取現金不便需頻繁奔波銀行網點和鄉鎮所帶來高昂的交通成本,農村人群獲得金融服務進一步得到提高。
伴隨著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的提高,銀行卡、第三方支付平臺等非現金支付也得到了進一步推廣,為農村電商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2019年上半年,農村地區發生網銀支付業務63.54億筆,金額達74.27萬億元;發生移動支付業務47.35億筆,金額為31.17億元;銀行機構辦理農村電商支付業務3.57億筆,金額4 030.33億元;銀行卡助農取款服務點發生支付業務(含取款、匯款、代理繳費)2.14億筆,金額為1 713.24億元[10]。
為了促進農村普惠金融發展,在征信體系、法律法規和監管制度等方面的建設也在逐步推進。在征信方面,建立農村地區信用等級評價機制,建設“信用村”“信用鄉”和“信用鎮”,在現有農戶信用評價基礎上,為農村貧困農戶量身定做評價授信標準,以提高農村經濟主體信用意識。截至2018年末,通過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已為1.84億農戶建立信用檔案(圖2)[7]。在金融法律法規方面,國務院先后發布了《關于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提出要大力發展普惠金融,進一步提升農村金融服務的能力和水平,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增強農村貧困人群的幸福感。在監管層面,強調建立“比例”監管體系,政策向中西部落后地區傾斜,根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和優惠的稅率,長期化、制度化普惠金融政策,形成穩定的政策預期[11]。
3 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發展面臨的問題
從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現狀來看,我國當前農村普惠金融整體發展態勢良好,但由于普惠金融的關鍵點是“普惠”,是以可負擔的成本為農村發展、農民群體提供適當和有效的金融服務,受到供需雙方和基礎設施條件等多方面的限制,“適當和有效”的目標還沒有完全實現。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 農村普惠金融業務創新不足
從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發展涉及的相關政府層面、金融行業層面的相關政策法規來看,各級各類農村金融機構都屬于農村普惠金融業務供給方,包括商業性質的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合作性質的農村信用合作社、資金互助社,也包括政策性質的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等銀行類金融機構,還包括開展傳統農業保險、農產品價格保險等的保險公司、從事涉農擔保的信用擔保機構[12]。隨著普惠金融的深入發展,未來開辦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還將繼續增加。但各級各類開辦普惠金融業務的農村金融機構在普惠業務創新上,整體表現為能力不足。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縣域的分支機構自主決策權有限,只能被動地按照總行統一設計的標準產品,“三農”產品主要包括傳統的農戶小額貸款、農民專業合作社貸款等,貸款金額僅夠維持日常生活開銷,無法因地制宜地根據不同金融需求的農村居民推出特色化、差異化的服務,缺乏對個人金融業務的創新[13]。農村信用合作社向農戶提供的聯保貸款和小額信用貸款主要集中于高收入農戶,其獲得貸款的比重遠遠高于貧困和低收入農戶,并未針對貧困和低收入農戶設計一套既有利于改善其信貸約束、又能保證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創新型金融業務[14],普惠金融業務沒有普及不同收入階層的農戶。此外,農業企業所獲得的信貸資金在產品和期限上與農業經營不相匹配,并且申請貸款業務中,各種條件限制、審批流程大大增加了農民的交易成本,變相提高了“三農”業務的準入門檻[15]。保險公司開展農業保險的險種較為單一,以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主要糧食作物為主,對茶葉、生豬、牛、羊等特色農業產品的保險業務開展甚少[16],并且多數特色農業產品并未列入中央財政補貼范圍,價格保險、成本保險、收入保險、基于區域產量與天氣指數制定的指數保險等創新型業務的試點工作進展緩慢。信用擔保機構由于沒有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從事涉農業務的積極性不高,普惠金融業務支持力度不足[17]。
3.2 配套設施仍不完善
普惠金融所需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地理排斥,在人口密集度較低的農村投入人力、物力、財力來設立營業網點,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經營成本和維修成本較高,如何合理布設物理網點,兼顧公平與效率,在實踐層面仍然存在很多困難[18]。再次,由于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遠遠低于城市,通信手段、網絡設備工具相對落后,在農村地區利用和開發數字信息技術條件還不夠成熟,制約了“互聯網+普惠金融”的發展。最后,目前各地的信用體系建設基本上是在區縣內展開,沒有客觀、標準的科學信用等級評價,采集的信息較分散,難以形成部門之間的有效溝通,也沒有專門的機構領導農戶信息采集工作,數據難以統籌流通[19]。建立信用檔案的農戶中獲得信貸資金的農戶占比仍然未得到明顯提升,農戶信用意識薄弱,受傳統思想的束縛,認為市場中征信體系所需提供的個人信息是對隱私的泄露,不配合信用數據采集,農民參與積極性不高,征信問題并沒有得到重視。
3.3 普惠服務宣傳有待增強
普惠金融主要的目標客戶是被傳統金融排斥在外的偏遠地區、弱勢低收入群體,該類群體受教育程度低,自身金融知識匱乏,這就導致普惠金融的有效需求不足且層次較低,制約了農村普惠金融的發展。由于農村金融機構花費人力、物力、財力來宣傳普惠金融服務的力度不強,致使大部分農村弱勢群體無法深入了解普惠金融業務,產生了“普惠金融等同于銀行貸款”的錯誤思想,造成農戶僅通過貸款衡量普惠金融服務發展[20]。除了基本的存取貸業務外,農村居民對其他金融服務的了解、接觸過少,主動尋求不熟悉、程序煩瑣的非信貸等金融服務的意愿不強,甚至出現排斥心理。加之,農村地區居民自身金融風險意識較弱,缺乏抵御風險能力,遭受詐騙現象屢見不鮮,造成自身無法承受的經濟損失。
4 對策建議
4.1 創新普惠金融產品和服務
針對普通農戶、農業新型主體等不同需求主體,應不斷創新普惠金融產品。對于貧困人群和低收入等弱勢群體,應以政策扶持為主,提供扶貧貼息貸款;對于不同類型的農民自主創業,提供差別農村創業貸款;對于農村企業,需要創新科技貸款、短期周轉貸款、價格保險等。另外,金融機構應盤活農戶手中的金融資產,對信用評價良好的農戶放寬產權抵押品的限制,變相降低了農戶的準入門檻;還結合當地農村金融需求,考慮自身資產情況和風險承受能力,發行“三農”專項金融債券,籌集的資金應與農業生產周期相匹配,多元化的金融產品才能實現服務質量的全面提高。基于金融機制的角度,推廣非銀行金融機構下鄉入村,與擔保機構、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加強聯動,創新更多可行的金融方式,如“信貸+保險”“信貸+擔保+保險”“信貸+期貨+保險”等,綜合發揮各種金融機制的優勢,實現金融機構之間的良性循環,推動“三農”現代化可持續發展。鼓勵其他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開展普惠金融業務的重心向“三農”傾斜,如加大中國建設銀行開發的“科技助農貸”“裕農易貸”“供銷支農貸”等創新產品的投入,平安銀行的“i貸款”“萬商貸”的貸款用戶延伸到信用良好的農戶以及經營穩定的農業企業。除了維持農民人群基礎的金融服務外,還應該適當提供理財、基金等其他金融服務,讓農戶真正受益于普惠金融。
4.2 健全普惠業務支持體系
金融服務覆蓋面和可得性是衡量普惠金融的關鍵標準。首先,優化鄉鎮縣域金融機構網點布局,在人口稀疏的地區設置銀行卡助農服務點,滿足農戶小額提現轉賬、余額查詢等基礎的金融服務需求;在人口密集的鄉鎮把銀行卡助農服務點升級成綜合服務站。其次,積極開發和利用數字信息技術,提高農村互聯網金融的普及程度,依托互聯網、手機、大數據等現代信息通訊手段,推廣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等非現金支付工具的使用。建立農村金融信息服務平臺,既有利于降低農戶的交通成本,還有助于增進金融服務供求雙方的溝通,防范信息不對稱引致的道德風險。全國應建立統一的信用信息數據庫,地方農村金融機構應建起當地的信用評價體系,整合農戶的交易信息,建立信用檔案,劃分信用等級,為農村產權抵押貸款提供數據支撐。另一方面,加大對失信農戶的懲罰機制,農戶一旦出現違約失信狀況,很難從其他渠道獲得信用支持。此外,建立政府扶持、市場主導的普惠金融擔保體制,完善風險補償機制鼓勵各類信用擔保機構開展農村擔保業務,提高農村金融機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最后,進一步推廣農村支付體系建設,推出“智能終端+銀行APP”的服務模式,改善農村支付環境,開通線上掃碼收付款、生活繳費、線上線下采購等功能,加大互聯網的輻射范圍,加速農村信貸技術創新。
4.3 加強農村普惠金融的宣傳與教育
農村整體金融知識落后于城市,不僅僅是農戶,基層政府的工作人員金融知識也很有限,這給農村普惠金融業務的推進帶來很大的阻力,加強農村普惠金融的宣傳和教育顯得非常重要。首先,政府、金融機構和媒體應組織專人對包括普惠金融在內的金融知識進行普及,特別是應對偏遠鄉鎮、經濟落后地區開展金融知識宣傳教育,使得更多的農業經營者了解可以通過金融手段改變生產狀態。同時,進行金融知識宣傳,還可以增強農戶抵御風險能力,樹立收益與風險共存的意識,指引農村人群根據自身資產情況和風險承受能力理性消費和投資,避免因不理性的金融行為產生無法承擔的經濟損失。其次,政府應設立普惠金融知識普及與教育資金。政府對進行普惠金融知識普及的金融機構劃撥一定的資金,提高金融機構參與積極性,并做好風險監控工作。最后,運用各種媒介手段拓寬金融知識獲取途徑。在人工入村入戶宣傳教育的同時,充分發揮電視、微信、微博等網絡通訊工具的作用,對金融知識進行推廣和宣傳,逐步提升農村居民整體金融素養。
參考文獻
[1] SHARMA A.Challenges:For building financial inclusive India[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9,24:436-437.
[2] 杜曉山.建立普惠金融體系[J].中國金融家,2009(1):140-142.
[3] 焦瑾璞.構建普惠金融體系的重要性[J].中國金融,2010(10):12-13.
[4] 馬會,何廣文.建立普惠金融體系應搞活小額信貸[N].中國經濟時報,2010-01-12.
[5] 王曙光,王東賓.金融減貧:中國農村微型金融發展的掌政模式[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
[6]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金融學會.中國金融年鑒2009-2018[M].北京:中國金融年鑒雜志社有限公司,2009-2018.
[7] 中國人民銀行農村金融服務研究小組.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2018[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9.
[8] 林秋萍,謝元態.普惠金融視角下農村金融發展與改革研究[J].金融教育研究,2014,27(6):26-33.
[9]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J].中國科技信息,2018(5):6-7.
[10] 銀保監會,人民銀行.2019年中國普惠金融發展報告[R].2019.
[11] 焦瑾璞.普惠金融的國際經驗[J].中國金融,2014(10):68-70.
[12] 杜曉山.發展農村普惠金融的十大建言[J].中國銀行業,2015(9):30-33.
[13] 曲小剛,羅劍朝.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制約因素和對策[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0(2):137-146.
[14] 吳國華.進一步完善中國農村普惠金融體系[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4):32-45.
[15] 劉萍萍,鐘秋波.我國農村普惠金融發展的困境及轉型路徑探析[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1(6):33-40.
[16] 韓俊.加快建立普惠型的農村金融體系[J].教學與研究,2008(12):10-14.
[17] 周孟亮,張國政.基于普惠金融視角的我國農村金融改革新方法[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9(6):37-42.
[18] 潘曉健,杜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我國農村普惠金融縱深發展[J].經濟縱橫,2017(2):17-21.
[19] 董曉林,朱敏杰.農村金融供給側改革與普惠金融體系建設[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6(6):14-18,152.
[20] 羅劍朝,曹瓅,羅博文.西部地區農村普惠金融發展困境、障礙與建議[J].農業經濟問題,2019,40(8):9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