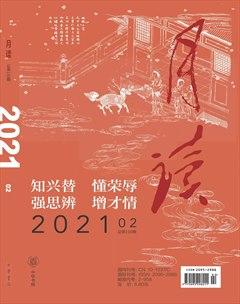唐代書學的鼎盛
葛承雍

唐代書法的淋漓酣恣,空前繁榮,不僅體現在書家人數眾多且水平很高上,也反映在理論研究的高度發展上。這一時期書法研究的內容比過去更細致,更深入,并且出現了有系統的書論,這不單是書法家開始注意對自己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整理,更主要的是書法理論及思維方式有了很大的發展和進步。
唐代書學鼎盛的主要標志,首先是從朝廷帝王到文化各界都對書法研究進行提倡和重視,許多文學家以詩文等手段歌詠、評論書法,像杜甫《李潮小篆八分歌》精煉而形象地歌詠“大小二篆生八分”的歷史,韓愈《石鼓歌》探討“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的石鼓文書法,等等。其次,唐代的書法理論探討已不是前代浮光掠影式的泛泛而論,也不是一些不切實際的夸大的形容比喻,而是深入到用筆、結字、執筆的技法原理,其中有不少是書法大家實踐中的切膚之談。再次是闡述楷書筆法及結構規律的著作增多,這無疑是楷書成熟的必然結果。特別是研究和探討書法藝術的本質及創作規律的著作也出現了,最為重要的是孫過庭的《書譜》,其內容之廣泛,見解之精辟,是對魏晉南北朝以來書法實踐與書法理論發展的全面總結與提高,可說是書學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價值。
初唐的書論之作,主要是從不同角度對書法技巧理論的特征及功用進行了探討與闡發,通過高度概括抽象化的漢字書寫點畫線條,來表現書家對生活的感情體驗。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以及李世民、裴行儉、王紹宗等都有著作問世。如論用筆有“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歐陽詢《傳授決》);“為點必收,貴緊而重;為畫必勒,貴澀而遲;為撇必掠,貴險而勁;為豎必努,貴戰而雄”(李世民《筆法訣》);論執筆有虞世南的《筆髓論》:“橫毫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管直鋒則干枯而露骨”,以及“指實掌虛”等原則。這正說明唐初書法理論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迫切需要從理論的高度進行總結,展開討論,以指導創作水平的提高。這種實踐和理論相互促進的情況,使得唐初書法藝術朝著更為自覺和成熟邁進。但是,無論是對具體用筆技巧的概括與解說,還是沿襲“六朝書勢體”從外部對書法藝術的不同形態進行描寫與刻畫,這類著作的共同缺點在于沒有從更深刻的美學觀念出發來把握“法”的本質特征。
任何“法”(理論)都是為適應一定內容、表現一定的美服務的,任何新“法”又反映著人們的認識能力和理論水平。唐初的書法理論還是帶有漢晉書論的模仿痕跡,喜歡將抽象的書法以形象化的具體比喻出來。
初唐書法理論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是虞世南的《筆髓論》,這篇文章通過對書法的演變、書法創作中各要素的關系等問題言簡意賅的論述,以及對當時盛行的真、行、草諸體運筆法則的概括,就藝術審美特征及境界提出一些獨特的看法。如“心為君”“手為輔”,運筆“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等。他將作為自然本體的“道”與審美主體“無為”的表現行為聯系起來,指出“學者心悟至道,則書契于無為”,而“心”則是主觀媒介和實現的前提,這就不自覺地暗示了藝術審美觀念在經過六朝時代的主體膨脹之后,又獲得了新的客體與之相統一,所謂“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這些思想,表現出初唐書法理論的某些特點,如力圖平衡藝術主體與自然客體之間的關系,以及對新的審美理想的向往。雖然在某些地方嵌入了一些儒家的思想內容,但其基本的審美精神卻仍是六朝的,統一的建立也不得不求助于“神妙”的境界,所以,虞世南那種新的審美標準似乎還沒有完全確立,表現出來的也僅僅是一種十分有限的熱情和努力而已。
在初唐向盛唐過渡的時期里,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書法理論家要推孫過庭了。孫過庭,名虔禮,做過率府錄事之類的文書,當時社會上重視士族,他因出身寒微,得不到進身機會,于是便“養心恬然,不染物累”。他自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并與當時一些著名書家過從甚密,悉心研習書藝。雖然仕途不順,生活艱苦,但個性倔強的孫過庭安之若素,以儒家的為人處世之道作為自己對所處困頓境遇的一種反抗,更以孜孜于書法的方式一吐心中郁結,借以澆胸中塊壘之意。
從傳世的孫過庭《書譜》《景福殿賦》《千字文》等作品來看,他的筆法瀟灑大方,妍美流便,這種美學思想仍受流暢達神、疏朗逸勢的晉人傳統的影響。但孫氏的書法只求王羲之的風骨神髓,不全是模仿照搬,像其《書譜》文稿墨跡,系初唐后期草書藝術出類拔萃者,行筆流美而轉圜自如,草法精熟而韻致深遠,章法無散亂之狀,全文行氣連貫,又融入“王書”草法,終成絕構。重神似而不求形似地學“王書”之法,這是藝術再創造的表現,也是中國歷史上有大作為的書家所經歷的必由之路。陳子昂贊孫過庭的書法說:“元常(鐘繇)既沒,墨妙不傳,君之逸翰,曠代同仙。”

孫過庭書《千字文》(局鄙)
《書譜》的成就和影響大大超過了孫過庭的書法本身,成為千年傳誦不輟的書學名著,現只存其序言,概述了書法源流、評書準則、寫作旨趣。全書分為六篇,上下兩卷,第一篇論鐘、張、二王書法,冠絕古今,而定其優劣;第二篇論書學功用,賢于他藝,賢者不廢;第三篇略舉世傳名跡,辨別是非,指斥偽誤;第四篇專宗右軍(王羲之)書法;第五篇論述書法哲理以及流弊;第六篇論時尚以耳為目,以嘆世無知音,作為全文之總結。這樣一部寫作計劃由于孫氏突然死于洛陽,所以只留下一個提綱挈領的三千余字的序言,但其中體現的書法藝術灼見、書法美學思想、書法哲理系統等都很有特色,包括了中國傳統文化許多積極的成分,吸收融合了先秦諸子哲學思想中的優秀部分。《書譜》中既沒有老莊思想的虛見,也沒有儒家的“安天知命”,更見不到佛教囈語,但提出了書法藝術必須合乎時代色彩以及哲學(美學)、文字學(形體)、文學(文論)的理論。
《書譜》的重要價值在于它使中國書法理論開始脫離從屬于書法實踐的地位而具有了獨立的意義。如果說從漢末到初唐前期,一般的書法著作均以“書勢”體或“書品”體寫成,其中的審美思想多從對具體書體或作品的描述與品評中流露出來,很少具有理論性,即使一些具有理論意義的著述,也只表現為靈感式的只言片語,那么《書譜》就不同了。它對書法這一藝術現象及其本質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發,通過批評前人及同時代人關于書法的種種解釋,建立起了新的審美理論。在《書譜》中到處可見作者對獨立的書法理論自覺而嚴肅地追求和探討,可以說,孫過庭在自覺建立純粹的書法理論方面,為后人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
理論的相對獨立性,還表現在它對實踐具有指導意義。孫過庭撰寫《書譜》的目的是“今之所陳,務裨學者”。對其書法理論的要求是做到“文約理贍,跡顯心通”,并使學者“披卷可明,下筆無滯”。據此,孫過庭按照新的時代要求,大膽地否定既往,提出了新的審美觀念和理論主張,反映了當時書法審美風尚的轉變以及對書法理論研究的開拓和深入。孫過庭的目的,在于從紛繁神秘的書法藝術現象中總結其內在規律,僅就理論思維變得更為現實和成熟而言,也算是中國書法理論史上的一大突破。
《書譜》所涉及的書法理論是多方面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立了新的藝術法則和審美價值標準,并使書法在理論上更趨系統和成熟,不僅使傳統審美觀在理論思維方式上表現出革新,而且有益于當世學者,對后世書法理論與實踐也有所啟發,體現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進步。
在孫過庭書法理論提出后,隨著書法藝術的空前發展,書法理論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氣象,杰出代表就是盛唐時期的書法理論家張懷瓘。
張懷瓘,開元時期任鄂州司馬、升州司馬,直至翰林供奉,與其說他是御用文官,不如說他是個封建正統的知識分子。他的書法兼善正、行、草、小篆,而且自矜“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獨步于數百年間”。然而,他留給后人的不是“新意頗多”的書法作品,而是豐富龐雜的書法理論專著,有《書斷》三卷、《書估》一卷、《評書藥石論》一卷、《六體書論》一卷、《書議》一卷、《論用筆十法》一卷等。其中作于開元中的《書斷》極為有名,其豐富的內容和完整的骨架,不僅闡述了張懷璀書法理論的實質,而且也能使人領略到盛唐文化藝術的某些特征。如果說在書法創作中,顏真卿是集大成者,那么張懷璀也企圖成為書論的集大成者,表現出盛唐氣象。
中國古代書法理論在談到書法的起源時,總要說到倉頡造字與伏羲畫卦,而張懷瓘似乎更注意卦象,他援引《周易》指出:“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文字也是從卦象里獲得啟示而創造出來的,即所謂“卦象者,文字之祖,萬物之根”。從卦象所蘊含的天地萬物變化的神秘法則中,張懷瓘意識到書法美的生命之所在,因而他對《周易》推崇備至,說自己草創《書斷》時,“觸類生變,萬物生相,庶乎《周易》之體也”。《周易》中卦象的“象”“意”“情偽”“剛柔”“變”等,使他擁有了一把認識書法藝術的哲學鑰匙。
作為一位博大精深的書論家,張懷璀對書法這門藝術的本質、規律、特征進行了探討,寫成了《書斷》。《書斷》上卷為書體論,對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章草、行書、飛白、草書十體的外在美作了簡要描述。張氏更強調書體中的“意”,強調書家的內在情意,欣賞書法的關鍵即在于“須考其發意所由,從心者為上,從眼者為下”。這種觀點體現了張懷瓘繼承了中國書法對傳情藝術特點的重視,也表明了他的“性情”觀。
《書斷》中卷為書學品評,列神品二十五人,妙品九十八人,能品一百零七人。張懷瓘從六朝書論中吸收了“神”“妙”“能”的美學范疇,發展了魏晉“九品”論書的品評方式,在人物等第中滲入了神妙、神明、神采等不同內涵,從而使評品方式具有了美學意義,能夠使讀者知人論世,理解書家的師承,明了品評等第的理由,進而從宏觀上探討書法這門藝術的特征、功用、發展等問題。
《書斷》下卷為書家小傳及其藝術特點的評價,卷末以評論的方式顯示了張氏書論的獨特性。
張懷璀能寫出《書論》這樣品評古往今來書家的大著,說明他在實踐中,深深感到書法可以把古代哲學和思想家的精神財富積累下來,可以把歷史記載下來,作為后人的借鑒,并寄托人們的情懷,產生“彼跡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的心理。尤其是他稱《書斷》“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表明他在《春秋》及《史記》等歷史著作的熏陶下,對書法藝術進行切身思考的同時,表達了自己的歷史觀。
總之,張懷璀在書法理論上的建樹是多方面的,在盛唐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他以儒家為基礎,吸收道家等各家思想,使其書論呈現出與初唐不同的特點。盡管他在書法藝術創作上的觀點還較雜亂,但其理論構架對后世產生的深遠影響,特別是其“風神說”,極有特點,既繼承了以前書論的精華,又更新了理論模式,扭轉了盲目崇拜王羲之的書風,推動了書法理論的發展。正因為此,《書斷》與張懷璀的書法美學思想,體現著從初唐理想的秀美、妍美到盛唐壯美的變化,這也是盛唐時代氣勢磅礴、宏壯豪邁的客觀形勢在書法理論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