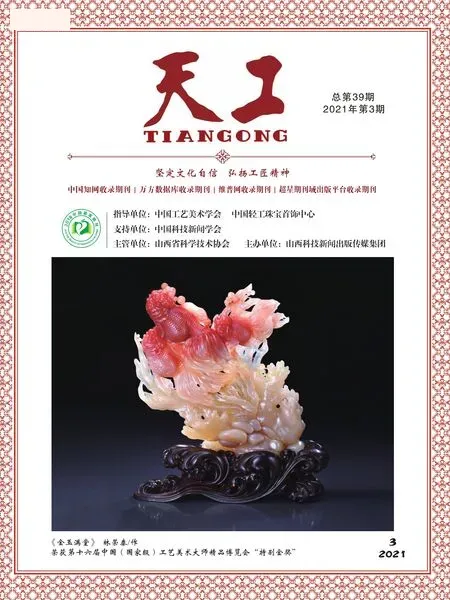蛋殼鑲嵌與漆藝的現(xiàn)代表達(dá)
文 于 泳 馬曉宇
中國(guó)漆藝的發(fā)展歷程中,從最初的防水、防腐的實(shí)用功能到千文萬(wàn)華的裝飾屬性的轉(zhuǎn)變,除了漆藝種類(lèi)繁多的髹飾工藝,面貌多樣的入漆材料更是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漆藝“材美工巧”的美學(xué)理念。在漆藝眾多的入漆材料中,蛋殼作為鑲嵌材料是年輕的。將蛋殼用于漆藝創(chuàng)作不僅拓寬了漆藝表達(dá)的路徑,更是漆藝表達(dá)的現(xiàn)代體現(xiàn)。
一、蛋殼入漆是漆藝“材美工巧”傳統(tǒng)選材理念的現(xiàn)代闡釋
作為漆藝主要材料的生漆具有超強(qiáng)的黏合性,漆膜干燥后形成的溫潤(rùn)如玉的光澤與質(zhì)感,這些特性決定了漆藝自其產(chǎn)生以來(lái)就帶有裝飾特性與綜合性。可以說(shuō)漆藝從古至今都是作為一門(mén)綜合藝術(shù)來(lái)發(fā)展的,而鑲嵌工藝是漆藝綜合性的最直觀(guān)體現(xiàn)。
考古資料表明,早在西周時(shí)期的漆器上就開(kāi)始鑲嵌蚌殼材料,這也是漆藝傳統(tǒng)鑲嵌技法的開(kāi)端。隨著漆工藝的發(fā)展,各種金屬材料、骨石材料以不同的姿態(tài)融入漆藝,從厚螺鈿到軟鈿鑲嵌工藝,自嵌金銀平脫到臺(tái)花工藝,由寶石鑲嵌發(fā)展到極盡奢華的百寶嵌工藝。可以說(shuō)漆藝鑲嵌工藝歷史之悠久、種類(lèi)之繁復(fù)、技藝之高超是體現(xiàn)漆藝裝飾性的典型工藝品種。
蛋殼作為鑲嵌材料入漆,相對(duì)悠久的髹漆工藝來(lái)說(shuō)歷史是短暫的。法國(guó)的讓·杜楠在20世紀(jì)20—30年代將蛋殼代替螺鈿材料運(yùn)用到漆藝的創(chuàng)作中,創(chuàng)作出大量的屏風(fēng)、漆器等作品。1925年,日本的今泉次郎在所著的《實(shí)用涂工藝》中介紹了蛋殼用于鑲嵌工藝的兩種方法。在我國(guó)將蛋殼作為鑲嵌材料應(yīng)用于漆藝創(chuàng)作最早的是雷圭元教授20世紀(jì)30年代創(chuàng)作的《泉邊》。
蛋殼入漆采用的方式大致分為三種,一種是將蛋殼變成彰髹工藝中的起紋材料,另外兩種均是取蛋殼的白色特征,將蛋殼打磨成粉進(jìn)行蒔粉,或?qū)⒌皻ぬ娲葩氝M(jìn)行鑲嵌。螺鈿在漆藝中的運(yùn)用,一是由于很多帶有珍珠層的蚌殼如鮑魚(yú)貝色彩瑰麗,雖不是寶石卻能呈現(xiàn)出珠寶的華彩;還有部分蚌殼如硨磲等顏色潤(rùn)白如玉,彌補(bǔ)了漆藝中沒(méi)有白色的缺憾。用蛋殼可以替代螺鈿形成漆藝作品中的高明度色,不僅是因?yàn)榇蟛糠值那蓊?lèi)蛋殼都是白色,更重要的是蛋殼隨處可見(jiàn),且蛋殼的加工處理較螺鈿材料的加工要更加簡(jiǎn)單,在鑲嵌時(shí)的操作難度也比螺鈿工藝小得多。基于以上原因蛋殼鑲嵌工藝自產(chǎn)生以來(lái)百年的時(shí)間迅速發(fā)展成為現(xiàn)代漆藝創(chuàng)作中最普及的一種髹飾工藝。
蛋殼作為入漆材料不僅豐富了漆藝的髹飾技藝,更是現(xiàn)代漆藝相較傳統(tǒng)漆藝在選材觀(guān)上的變革。在中國(guó)古代,漆器藝術(shù)一直是一種高端、奢華、顯赫的手工藝術(shù)[1]。作為漆器表面裝飾的鑲嵌工藝在選材上為了體現(xiàn)漆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更加注重鑲嵌材料的稀缺性與材質(zhì)華美的質(zhì)感。明清時(shí)期的百寶嵌工藝之所以盛極一時(shí),不僅是質(zhì)地天然、眾彩紛呈的裝飾美感,其珠光寶氣、華貴富麗的風(fēng)格更能體現(xiàn)使用者的尊貴地位也是重要的原因。而蛋殼是人們?nèi)粘o嬍持械膹U棄品,隨處可得,沒(méi)有稀缺性,在傳統(tǒng)漆藝中是不會(huì)采用這種價(jià)格低廉的材料作為漆器裝飾材料的。
蛋殼成為現(xiàn)代漆藝髹飾工藝中的重要鑲嵌材料,是創(chuàng)作者拋掉等級(jí)觀(guān)念,更加純粹地考慮材料自身的美感而進(jìn)行的材料選擇的結(jié)果,這正是漆藝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重要體現(xiàn),是漆藝傳統(tǒng)工藝語(yǔ)言向現(xiàn)代繪畫(huà)語(yǔ)言的轉(zhuǎn)化。陳勤群在《中國(guó)當(dāng)代漆畫(huà)十二家》一書(shū)中提道“傳統(tǒng)媒材的現(xiàn)代性進(jìn)程就是不斷地與各種思潮交融、激蕩、辨析、梳理與構(gòu)建的過(guò)程”[2]。蛋殼鑲嵌出現(xiàn)在20世紀(jì)20年代左右的西方,當(dāng)時(shí)正值新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裝飾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的興起。尤其是裝飾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其抽象主義造型及明亮的色彩對(duì)比對(duì)現(xiàn)代漆藝的影響,使蛋殼這種極致的白色在現(xiàn)代漆藝創(chuàng)作中變得極為重要。蛋殼的加入使漆藝的色彩在色階上達(dá)到了最大的對(duì)比度,相較于螺鈿鑲嵌的復(fù)雜,蛋殼鑲嵌便于操作、手法靈活,更適合大面積的繪制。蛋殼應(yīng)用于漆藝創(chuàng)作促進(jìn)了現(xiàn)代漆畫(huà)的發(fā)展,進(jìn)一步體現(xiàn)出裝飾性與全因素兩個(gè)重要的發(fā)展方向。
二、蛋殼鑲嵌很好地詮釋了現(xiàn)代漆藝?yán)L畫(huà)語(yǔ)言的裝飾性
漆藝創(chuàng)作的主材是由生漆精制成不同顏色的色漆,由于生漆中的漆酚在固化時(shí)會(huì)產(chǎn)生漆酚醌,而醌這種化學(xué)物質(zhì)多半為黃色,白色與透明漆進(jìn)行調(diào)和精制后的白漆會(huì)帶有棕色底色,自然明度上達(dá)不到最高階。蛋殼中如雞蛋殼及處理過(guò)的鵪鶉蛋殼都是白色,蛋殼為漆藝添加了高明度的色彩,將漆藝的色彩明度對(duì)比擴(kuò)展到極致。有了蛋殼的加入,漆藝在其濃郁深邃的東方意境中又多了一筆靚麗的白。有了漆黑與雪白,現(xiàn)代漆藝的色彩既保留了傳統(tǒng)漆藝色彩濃郁的特點(diǎn),又具有現(xiàn)代感。
在繪畫(huà)中對(duì)于白色的認(rèn)識(shí)有多個(gè)層次,色彩理論中白色是極色,代表最高的明度。在繪畫(huà)中由于畫(huà)面材質(zhì)的關(guān)系,多采用紙張、畫(huà)布等淺底色,習(xí)慣作為背景組織畫(huà)面的白色經(jīng)常被激發(fā)出“背景性”“包容力”的聯(lián)想。白色在畫(huà)面布局中也多是體現(xiàn)空間。但在漆藝中多采用黑、紅等色作為畫(huà)面的基底,用蛋殼堆砌出的白色卻成為畫(huà)面重要的色彩,具有極強(qiáng)的視覺(jué)沖擊力,在漆畫(huà)中白色的表達(dá)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揮。同時(shí)由于蛋殼采用鑲嵌的手法平鋪在畫(huà)面上,此方法分布呈現(xiàn)的白色更加具有平面性。而平面性正是裝飾藝術(shù)重要的特征。即使作為背景色,采用蛋殼鑲嵌手法繪制的大面積白色,也由于蛋殼的肌理感使背景的白色前移,強(qiáng)化了畫(huà)面的平面感,更加具有裝飾性。
三、蛋殼鑲嵌是現(xiàn)代漆藝嚴(yán)謹(jǐn)與意趣的體現(xiàn)
蛋殼鑲嵌首先作為一種髹飾工藝,從蛋殼材料的選材、清理到粘貼的平整度、拼貼的紋理調(diào)整,再到后期的填色打磨推光,成功的蛋殼鑲嵌作品呈現(xiàn)出獨(dú)特自然的紋理及微妙的色彩過(guò)渡都是在每個(gè)步驟嚴(yán)謹(jǐn)細(xì)致的工藝把控下完成的。
隨著人們審美觀(guān)念的轉(zhuǎn)變,蛋殼鑲嵌工藝在傳統(tǒng)平嵌的基礎(chǔ)上不斷豐富完善,又結(jié)合了反嵌、罩染、研磨、刻畫(huà)、堆雕等工藝。蛋殼種類(lèi)也變得多樣,如鴨蛋、雞蛋、鵝蛋、鵪鶉蛋等,正面平嵌的蛋殼,打磨推光后雞蛋殼雪白光潔、鴨蛋殼清潤(rùn)如玉,鵪鶉蛋殼紋理細(xì)膩;反嵌的蛋殼打磨后形成了外白內(nèi)黑的圓點(diǎn),增加了白色的細(xì)節(jié);層疊的蛋殼更徹底地將蛋殼推向了現(xiàn)代繪畫(huà)的實(shí)驗(yàn)性。由此可見(jiàn),蛋殼鑲嵌工藝在現(xiàn)代漆藝中的表現(xiàn)已不是色彩的替代那么簡(jiǎn)單,當(dāng)代的漆藝家在追求呈現(xiàn)出蛋殼明亮的白和美妙的裂紋機(jī)理的同時(shí),更加追求材料的意趣美和作品的審美價(jià)值。
“工藝與美術(shù)是造型美領(lǐng)域內(nèi)流淌的兩條河流,或者說(shuō)是攀登高峰的兩條山路。”[3]隨著漆藝創(chuàng)作者的不斷探索,蛋殼鑲嵌工藝日臻完善與豐富,成為現(xiàn)代漆工藝中重要的髹飾工藝品種。同時(shí)蛋殼鑲嵌的多種表現(xiàn)語(yǔ)言,使漆藝的繪畫(huà)性得到了充分的發(fā)展。漆藝家在創(chuàng)作上的苦心孤詣,使蛋殼鑲嵌工藝所表現(xiàn)的題材內(nèi)容日趨廣泛,表現(xiàn)手法與風(fēng)格形式更加多樣。蛋殼作為現(xiàn)代漆藝創(chuàng)作媒材的表現(xiàn)力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越了我們所看到的客觀(guān)表象,逐漸成了視覺(jué)美感的符號(hào)和精神情感的載體。
李秉儒的漆畫(huà)作品《記憶》(如圖1),畫(huà)面描繪了白色襯布上透明玻璃瓶中一枝淡黃色的玫瑰。作者極致地采用蛋殼鑲嵌這一手法進(jìn)行畫(huà)面的描繪。通過(guò)蛋殼的疏密排列,雞蛋殼與鴨蛋殼色彩上冷暖的微妙變化來(lái)繪制白色襯布上的一只玻璃瓶。通過(guò)在蛋殼空隙中刮灰色表現(xiàn)襯布的褶皺,刮入黃漆表現(xiàn)玫瑰的色彩,刮入黑漆表現(xiàn)花枝與花葉的暗部。整個(gè)畫(huà)面色調(diào)單純典雅中透出淡淡的哀傷,可以說(shuō)將蛋殼的表現(xiàn)力發(fā)揮到極致。

圖1 《記憶》 李秉儒/作
明代畫(huà)家董其昌在《畫(huà)禪室隨筆》中提道:“以蹊徑之奇怪論,則畫(huà)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huà)。”藝術(shù)表現(xiàn)具有無(wú)窮想象力和多種創(chuàng)作途徑,畫(huà)家在“應(yīng)物象形”的過(guò)程中,體悟到的表現(xiàn)手法可與自然、內(nèi)心存在的秩序形成微妙的對(duì)應(yīng),藝術(shù)、自然與畫(huà)家的內(nèi)心達(dá)成一致。喬十光先生的《蘇州風(fēng)景》(如圖2),畫(huà)面用蛋殼與黑漆來(lái)表現(xiàn)徽式建筑白墻黑瓦的靜謐、素雅的水鄉(xiāng)氣質(zhì)。利用蛋殼平鑲工藝產(chǎn)生的龜裂紋體現(xiàn)出石材堆砌的表面效果,為了達(dá)到畫(huà)面的統(tǒng)一將白色的拱橋、道路都用蛋殼鑲嵌的手法表現(xiàn)。天與水的處理采用鋁箔粉罩漆來(lái)烘托畫(huà)面氛圍。進(jìn)而形成了喬先生黑漆屋頂、蛋殼粉墻、銀天銀水的“水鄉(xiāng)模式”。這種藝術(shù)上的表現(xiàn)力遠(yuǎn)遠(yuǎn)超越了自然物象所直觀(guān)表現(xiàn)的美感,是藝術(shù)家表達(dá)自然的更高境界。

圖2 《蘇州風(fēng)景》 喬十光/作

圖3 《異彩紛呈脫胎瓶》 鄭修鈐/作
蛋殼鑲嵌的現(xiàn)代表達(dá)多應(yīng)用于漆畫(huà)中。而在現(xiàn)代漆器創(chuàng)作中蛋殼鑲嵌則呈現(xiàn)出更加強(qiáng)烈的裝飾性。如鄭修鈐的《異彩紛呈脫胎瓶》是一件典型的具有裝飾藝術(shù)風(fēng)格的作品(如圖3)。飽滿(mǎn)的造型、濃郁而強(qiáng)烈的色彩對(duì)比,奠定了作品強(qiáng)烈的裝飾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風(fēng)格。細(xì)節(jié)上運(yùn)用蛋殼鑲嵌成由大到小、均勻漸變的白色橢圓小點(diǎn),螺鈿與漆皮呈放射狀逐層鑲嵌,都為作品增添了豐富的細(xì)節(jié)。白色蛋殼有規(guī)律的大量運(yùn)用,奠定了作品輕松、現(xiàn)代的裝飾氛圍。正如蔡克振的評(píng)價(jià):“如鄭修鈐自身的性格和風(fēng)度一樣給人以親切感,真情而清新。”[4]
漆藝的發(fā)展離不開(kāi)新材料的引入與漆工藝的革新,同時(shí)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產(chǎn)生的新的思潮與文化同樣會(huì)賦予材料新的內(nèi)涵與工藝的嬗變。正如柳宗悅在《工藝之道》中提道:“從工藝向‘工藝美術(shù)’轉(zhuǎn)化時(shí),其過(guò)程必然會(huì)凸顯繪畫(huà)性的要素。”[5]蛋殼鑲嵌工藝即是傳統(tǒng)漆藝發(fā)展到現(xiàn)代所產(chǎn)生的新的髹飾工藝。同時(shí)蛋殼鑲嵌呈現(xiàn)出的材料的現(xiàn)代性、獨(dú)特的趣味性與繪畫(huà)性等都是傳統(tǒng)漆藝由工藝向工藝美術(shù)轉(zhuǎn)化的具體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