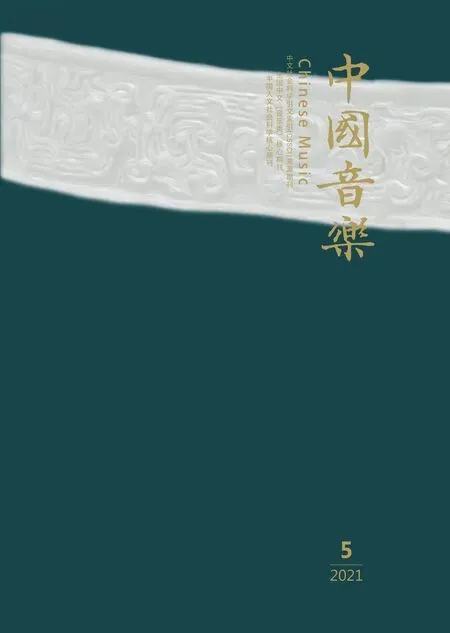音樂教育作為國家資產
——走向共同建構與協商的社群主義
○ 林小英
引言:從音樂活動到音樂教育的追問
把音樂教育與國家聯系起來并不新鮮。新世紀以來,比較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突然興起了一股對“國家”的興趣。無論是作為研究對象還是被用作解釋研究者感興趣的現象的原因,作為一個行為主體或一種制度組織的國家都受到了高度重視,來自所有主要學科不同理論傾向的學者對此進行的研究為數已十分可觀,所探討的領域也非常寬廣。①〔美〕西達·斯考克波:《找回國家—當前研究的戰略分析》,〔美〕埃文斯、〔美〕魯施邁耶、〔美〕斯考克波:《找回國家》,方力維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2;3頁。在這些學科中,與音樂的親和力比較相近的文化人類學家探究的是非西方背景下“國家”的特殊含義和行為特征,如格爾茨探討的“19世紀巴厘島的劇場國家”。音樂這個學科也不例外,也可以參與到“從社會中心理論到重新對國家產生興趣”②〔美〕西達·斯考克波:《找回國家—當前研究的戰略分析》,〔美〕埃文斯、〔美〕魯施邁耶、〔美〕斯考克波:《找回國家》,方力維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2;3頁。的道路上來。
首先從音樂與社會的關系考察。從當下中國社會普遍所見的與音樂教育相關的一些現象碎片可見,音樂活動展現出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第一,學校音樂教育的“課外化”。過去20年實行素質教育政策以來,學生在校時間縮短,音樂類課程教學時數和師資投入勉強滿足國家規定。能代表學校音樂教育水平的就是經過選拔和課外特定訓練的音樂團體,其主要功能在于代表學校參賽并作為遴選學生個體升學的額外指標。而在“課后330”政策③“課后330”政策,即解決學生每天下午三點半放學后怎么辦的問題,政府對學校課后服務工作建議時間段一般為15︰30—17︰30。實施以后,大量學校就開始名正言順地將音樂類課程進行教學外包,強化課外培訓。第二,音樂學習的“家庭化”。簡言之就是每個孩子從小就被期待學習一門樂器或者一種能進行當眾表演的音樂技能。個體被當作音樂活動參與者的唯一維度,群性的發展在個體的競爭之中逐漸衰減。第三,音樂表現的“公共化”。歌手選秀節目、廣場舞、快閃之類的節目彌漫在公眾的公共生活之中,卻并沒有成為音樂教育研究領域嚴肅的研究主題。第四,音樂品味的“考級化”。無級別,就無水平。與“公共化”相反,這種對音樂活動的個體參與者的評價體系,一方面推動了音樂技能的全面普及,另一方面是“競技場”走到極致后帶來的“零和博弈”——一些人的成功就必須伴隨另一些人的失敗,這使得音樂作為溝通人與人之間的“共鳴”載體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第五,音樂水平的“比賽化”。比賽才有名次,有名次才有名望,滿墻滿柜的獲獎證書證明的更可能是有“打敗”別人的能力。鑒別是必要的,但把鑒別代替了表現,恐怕就是本末倒置。第六,音樂素養的“無腦化”。音樂是否無需懂,會玩就行?音樂專業人才培養體系越來越“高精尖”,而大眾的音樂素養似乎在這種高門檻之下無所適從,也無從認定。音樂專業教育和音樂普通教育兩個體系之間是越來越分野,還是應該越來越融通?
這些現象的碎片所引發的思考,歸結起來就是雷默(Reimer)與其他音樂專業領導者的警告:當今音樂教育中潛藏著精英主義,盡管很少有學者將這種精英主義與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④Reimer,B..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2nd ed.).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 Hall,1989.學校音樂方案分不清教育、職業訓練和娛樂功能之間的不同取向:如果取“娛樂”的一端,則音樂稱不上值得學術探究或嚴謹調查的東西,只是娛樂時光的陪襯而已;如果取“職業訓練”的一極,那么音樂教育無可避免地淪為功利主義;如果認為音樂具備獨特的“教育”價值,那么現有的音樂教育體系是不是對音樂的教育價值視而不見了?⑤〔美〕珍妮特·巴雷特、〔美〕彼得·韋伯斯特:《音樂的經驗:重新思考音樂教學與學習》,余丹紅主編,梁菁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7-29頁。特別是在普通的基礎教育學校和普通高校之中。
回到一開始的多學科關于“國家理論”的關注點。國家是什么?國家的目的是什么?這都是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開卷第一章所要回答的問題。超越公民的身份和政治生活的成員的觀點,他認為:國家是社會團體之一,它囊括其他一切社團;既然每一個社團都以一種善為目的,則國家便是以最高的善為目的;倫理學研究個人的善,政治學則是探究人群的善。⑥吳恩裕:《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導言”,〔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viii頁。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幾乎用整個第八章來討論以音樂為代表的藝術教育在國家政治的范疇內究竟何為。在他看來,就像體育的目的絕不是訓練冠軍,而是促進青少年身心和諧發展一樣,音樂教育也應該斷然棄絕與職業藝人一較短長的虛榮心,轉而培養有教養、有品位的業余性的音樂實踐者,而這些人從事音樂的唯一原因是因為直接的藝術經驗有助于培育自己的判斷力。⑦〔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424–426頁。
亞里士多德的見解得到了許多現代音樂家的支持。他們一致認為,真正的音樂愛好者必須是實踐者,不能只坐在音樂廳的觀眾席上或者守在電唱機旁,而是必須親自演奏和演唱,哪怕他們永遠都只有笨拙的辦法。⑧〔法〕馬魯:《古典教育史》(希臘卷),龔覓、孟玉秋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95頁。不看重技能,而看重親身的參與和實踐,這就是音樂教育的公共性維度。而公共性,是現代國家的首要性質。由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傳至后世的音樂古風濃郁,不盡在技藝的層面,它負載著一種天真質樸的觀念,即音樂必須具有功利性,有益于道德的建構,能促成個體和社會自律人格的養成。教育變得越來越知識化,只有與社會生活真正連接起來,音樂的真正面貌和最活躍的樣子才能負載其功能。⑨同注⑧,第299;293–294;294–295頁。
音樂教育的“社會公正”之問
問題由此轉入音樂教育的范疇之內,從跨學科比較的角度,借用貝蒂·安妮·楊克勒關于音樂教育的哲學沉思⑩同注⑤,第11–18頁。,我們可以展開一系列的發問,然后再探究問題的根源與可能的轉向。
音樂教育的“永恒之問”:如何提高學生的音樂經驗?如何讓學生們直接參與音樂活動?
音樂的“審美教育”之問:為什么以及如何讓學生參與到音樂實踐中?
音樂教育的“自由主義”之問:如何讓學生不受一種方法的制約?如何超越表演經驗,以更多方式參與音樂?如何從作曲、即興、評論和聆聽中獲得經驗并產生意義?
音樂教育的“女性主義之問”:我們應該聆聽誰的聲音?演奏何人的音樂?誰應該執掌指揮棒?音樂經驗如何能得到釋放,又是如何受到壓抑?
音樂教育的“族群主義”之問:我們應該做些什么,去擴寬學生對音樂的理解,讓他們的眼中不再只有傳統的西歐音樂藝術?
上述發問從音樂教育直接面向個體的經驗探究漸漸轉向集體的經驗選擇,而越偏向后者,在音樂教育中越走向式微。這個變遷過程并不只是當代的中國問題,而更像是一個“歷史的必然選擇”。在《古典教育史》中,法國學者馬魯論述了音樂在文化教育中的隱退過程。
“曾幾何時,音樂在古典時代曾和文學、體育并列為教育的三大傳統分支,但到公元前2世紀就已經失去了往日的榮光。按照當時公共學校的規章,每一所學校應該配備3位文學教師、2位體育教師和1位音樂教師。一般來說音樂教師是一位游離于學校體制之外的專家。其教學并非面向所有年齡段的學生,而是僅僅針對將要進入青年學校的最高兩個年級的學生或未滿18歲的青年。教學內容被嚴格限定:對于后者,講授七弦琴技法和樂理,對于前者則只講授樂理。此時的樂理幾乎與純數學無異。音樂會也不會列入青年學校參加的種類繁多的競賽之中。”?同注⑧,第299;293–294;294–295頁。
“在音樂領域里發生的現象與體育競技經歷的變故近似:技藝的進展推進了整個領域的專業化,隨即導致了與大眾性的文化和教育的脫節。當梅拉尼皮德斯、基內西亞斯、福里尼斯、提摩泰斯等大作曲家引入了精美的和聲結構、旋律和完善的器樂技法,原先存在于音樂與文化教育之間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在他們的影響下,希臘音樂成為只有少數人才能掌握的精密復雜的技藝,一般大眾則被排除在這一領域之外。雅典和斯巴達的保守派們指責音樂的演變導致了趣味的腐化,但大勢所趨已無法挽回。到了希臘化時代初期,分離最終完成:少數職業音樂家壟斷了這一偉大的藝術,使那些即便教養良好的音樂愛好者也徹底淪為與創作無緣的純粹欣賞者,這種變遷與體育愛好者在職業選手面前的弱勢如出一轍。”?同注⑧,第299;293–294;294–295頁。
體育領域好歹最后通過創設舉世聞名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部分解決了這種對立,音樂教育由此不得不持續面對一個極為重要的選擇,如何解決參與者的分化問題?“古典音樂”的程式、框架和勢力已然形成,并且越來越走向以樂理和技法為目標的科學測量主義,但社會生活川流不息,多姿多彩,斷然不會按照古典音樂的體系來構建人們的音樂生活。那么,音樂教育是否要順應時代的潮流,追隨“現代”音樂的演變?如果放棄這樣的努力,會不會從此遠離這個時代活生生的文化,從而無法完成音樂啟蒙的使命?
因此,接續上述發問,我們還可以發出音樂教育的“社會公正”之問:當我們融入群體時,我們可以期待學到新東西、參與新的音樂活動嗎?我們想要進入“他人的世界”,是否應該本著互惠互助的原則?如何構建音樂學習環境,教學生與他人協作?這就把音樂作為一個學習科目從古典音樂的體系中拖拽出來,從現代教育原理中極為關注的“社會化學習”?“社會化學習”關注的焦點從內容的主題學習轉移到圍繞內容的學習活動和人與人互動,從而可以解釋小組學習的績效。學生在學習小組中可以提出問題,以澄清不確定的領域或困惑,從同伴那里聽取該問題的思路和答案,可以提高他們的學習效果,甚至可以取代教師的作用,還可以幫助其他小組成員,并從他們的理解中受益。“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是社會化學習的重要議題。觀念來看,來探尋以教育之名而建立的人際關系中開展音樂教育的可欲性。
音樂教育的復雜性在于,在西方古典教育中,被當作人文教育的支撐科目,負載多元化的價值,后來隱退;在現代教育中,被當作審美教育的科目,負載的是藝術性的功能。特別是在當代,當消費社會已經滌蕩各個領域時,創意文化產業經常成為一個實體經濟增長乏力的經濟體的發力點,音樂在其中向來被期待承擔極其重要的功能。審美資本主義說明了一種經濟的變革,在藝術和時尚相結合成為主要潮流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在本質上不是有用的商品流通和購得的問題,而是一個服從審美判斷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審美空間。?〔法〕阿蘇利:《審美資本主義:品味的工業化》,姜丹丹、何乏筆主編,黃琰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實際上,在審美資本化所助推的經濟增長之中,已經融合了公共性的維度,也就是說,這種增長絕不是某一個個體的行為,而是一群人、一個地區的人、一個國家的人朝向一種增長方向的邁進。
本文故而要追問的問題是:在審美資本化的一端,和公共領域融合的另一端,音樂教育的上述問題可以得到解答嗎?結合音樂活動的個體化特征凸顯,如果將“音樂考級”作為音樂水平的鑒定手段,那么這種基于科學測量運動而誕生的人文事件,能否自然而然地拯救音樂活動的公共性?進一步,從國家理論來看,國家從來都是作為可見的、大范圍的公共空間,音樂也從來都是作為國家認同和社會融合的重要手段。這并不是不承認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浪潮所構建的超越國家的、虛擬的、想象的音樂共同體?專門研究民族主義和國際關系的美國學者苯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名的《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超越一般將民族主義當作一種單純的政治現象的表層觀點,將它與人類深層的意識與世界觀的變化結合起來。他講民族主義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廣闊的“文化史”和“社會史”的脈絡當中來理解—民族主義因此不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運動,而是一種更復雜深刻的文化現象,即“文化的人造物”。安德森不但沒有像一般社會科學家那樣以實證主義式的傲慢忽視人類追求“歸屬感”的需求,反而直接面對這個真實而深刻的存在性問題,并在他的架構中為之賦予適當的詮釋與意義。這個途徑間接肯定了德國哲學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說的“鄉愁是最高貴的痛苦”的箴言。把民族國家當作想象的共同體,這對我們如何看待西方古典音樂體系、理解音樂共同體、音樂教育具有直接的啟發意義。參見〔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然而音樂的全球化并不能取代和遮蔽其獨有的“國家資產”的性質。把音樂教育置于一國之內來考察,具有深刻的情感上的正當性。就此,本文一直想要追問:音樂教育作為國家資產,如何從科學主義走向社群主義(communism)?
現代音樂教育伴隨追求社會正義的歷史進程
在20世紀,進步的教育家們公開批評教育在維護社會不公方面的作用,以及教育體系對社會公正缺乏關注。教育改革的話語焦點從自上而下的公平理念轉向了一種社會信念,即“創建公正的社會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積極參與民主進程”。?Boyles,D.,Carusi,T.,& Attick,D..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Social Justice.In W.Ayers,T.Quinn,& D.Stovall (Eds.),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in Education.New York: Routledge,2008,pp.30–42.根據杜威的觀點,學校應該是一個活躍的、積極的社區,對與社會不平等有關的問題進行審議。學校應該成為培養兒童社會意識和社會理想的一種手段。?Kahne,Joseph.Reframing Educational Policy:Democracy,Community,and the Individual.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6,pp.25–46.
在20世紀前20年,美國涌入大量的新移民,要求學校系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容納不同種族的學生。將移民融入主流文化,通常被稱為熔爐理論,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成立于1907年的全國音樂督導會議(The Music Supervisors National Conference,簡稱MSNC)于1914年至20世紀20年代末,為深入學校社區,發展歌唱文化,促進學校與社區的關系。這種活動與杜威的教育哲學相一致,包含了文化和解放社會正義的種子。涂爾干是社會學領域的創始人物,他認為:“社會只有在其成員中存在足夠程度的同質化才能生存;教育通過從一開始就將社會生活所需的基本相似性固定在孩子身上,從而使這種同質性得以延續和強化。”?轉引自Mccarthy,M.Understanding Social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Education History.Benedict,C.,Schmidt,P.,Spruce,G.and Woodford,P..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in Music Education,2015,p.35.涂爾干的功能主義教育觀符合美國化的社會理想,即所有移民通過學習語言、參加國家假日和慶祝活動、上公立學校和學習公民的價值觀而成為國家公民。
在公立學校音樂教育中,音樂被視為一種活動,通過唱歌和演奏樂器,將不同種族背景、社會階層和宗教信仰的人團結在一起,從而灌輸國家民族的理想。音樂教師通過演唱愛國歌曲和各種西歐國家的民歌來吸收移民,而這些歌曲在當時的學校音樂中占了主導地位。?Volk,T.M..Music,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Foundations and Principles.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40–44.利用國際性的民歌來實現民族主義目標是出于善意的。然而,它回避了一個問題:誰的歷史在民歌轉譯中得到了體現?民歌是如何在公立學校使用的?“異域音樂”與學校社區文化多元化的現實有什么聯系?重點不是學生在社區中的身份認同,而是通過音樂教育實現文化同質化和國家公民身份。?Mccarthy,M.Understanding Social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Education History.Benedict,C.,Schmidt,P.,Spruce,G.and Woodford,P..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in Music Education,2015,p.35.
社群主義社會理論的基本原則在教育組織和實施方式上是顯而易見的,注重的是同質性和分配正義,由此質疑教育實踐在社會公正的背景下的作為。20世紀早期出現的個人和群體在智力和能力上的差異的科學測量支持了種族排名,并為種族和族群體之間的智力和道德差異提供了“科學證據”?Williamson,J.A.,Rhodes,L.,& Dunson,M..A Selected History of Social Justice in Education.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2007(31),pp.195–224.。智力測驗、排名與剖析等教育常模(norm)對音樂教育中的思維產生了影響,這在音樂天賦與能力測試的公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隨后,兩次世界大戰強化了教育的社群主義方法和在戰時團結人民的必要性。20世紀前40年的戰爭氣候和民族、公民教育目標影響了音樂的發展方向,保持了音樂教育作為國家資產的地位。音樂的普世價值以國際和諧、正義與和平的名義,將各國人民和國家團結起來?McCarthy,M..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1953–2003.Nedlands,Wester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2004.。在此時期,音樂作為一種國際語言的強大隱喻,被音樂界和教育界人士作為一種證明音樂在國家、社會、族群、國際交往中的合理性方法而流行開來,音樂跨越國界的性質幾乎不言而喻,毋庸置疑。音樂教育既是一種國家資產,也是一種國際性的公共文化產品。
總之,音樂在教育中的方向與占主導地位的社群主義社會理論是一致的。簡言之,音樂的實質內容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讓族群之內乃至跨越族際之間的人們能夠有一種“共通感”,認為自己和他人在某種范疇和意義上是同一類人。然而,為什么現在要如此強調音樂教育的這種作用呢?這難道不是人類社會一開始擁有音樂時就具備的功能么?
回首歷史,我們會發現恰好是社群主義走向單一化的極致所導致的。這種過猶不及的做法尤其值得今天推進公共音樂活動的主導者警惕。在希臘文化和教育傳統中,音樂的重要性絕不在體育之下,而各種音樂之中又首推器樂。當然,在器樂之外也學習歌唱。與獨唱相比,希臘人最喜歡的還是合唱。從樂理上看,希臘式的合唱十分簡單,因為當時沒有復調,合唱隊要么同音齊唱,要么以差八度音混聲合唱,無論哪種情況,總會以樂器伴奏。到了后期,隨著人們對合唱藝術質量的日益重視和演唱技巧的不斷完善,合唱隊員不再從愛好音樂的普通公民中臨時選拔,他們越來越專業化,在亞歷山大大帝時期,出現了真正職業化的合唱團。合唱的功用主要是讓青少年參與祭神大典,這既是法律的命令,又是神圣傳統的要求。宗教典禮在希臘化時代青年教育中有著不容輕視的作用,合唱充當了發揮這種作用的橋梁。歷史的吊詭就在于,鑒于典禮音樂的實用性和單調性,只需事先讓一位專門的合唱教練對參加合唱隊的青年們進行快速培訓即可,而不需對他們進行日常性的音樂教育。進而,合唱教學也無需被視為教育的基本內容之一。?同注⑧,第286–291頁。音樂的典禮和儀式功能既然可以如此速成和交易,那么學校的音樂教育就可以收工了。音樂在文化教育領域就此隱退。
音樂教育作為國家資產:呼喚共同建構與協商的評價模式
對任何國家的公共空間來說,社會公正仍然是一個重大挑戰。緩解不公平、無力和歧視一直是公共教育政策的目標,音樂教育中追求社會融合不僅僅意味著承認差異,并應該允許課堂和其他教育空間具有更大的多樣性和包容性。追求社會公正是十分復雜和高難度的一連串活動,涉及對相互沖突的價值觀和利益的裁決,對政治行動和對公眾福利的關注,尤其是那些被邊緣化或受壓迫的人的福利。在音樂活動的參與者被歷史性地區分為職業音樂家和業余欣賞者之后,這項任務尤其艱巨。如果要避免自以為是和過于簡單化,那么這個議題必須從認識社會生活和分享經驗的復雜性開始,同時要關注整個“命運共同體”,而不僅僅是這個或那個群體,專業教育還是普及教育。現實情況經常是,追求社會公正只會使少數幸運的人受益,以其他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為代價。對某些人的正義很容易導致或被視為對其他人的不公正。
此外,社會正義理想本身有時被利益集團作為修辭手段加以利用,它也確實可以用來掩蓋社會不公正和不平等的長期存在。因此,這種緊張關系將社會公正定義為一種道德和倫理上的代言,而將其定位為一種理想、一系列取向和切實可行的實踐,并將其置于音樂教育改革的中心。
對于音樂教育來說,當下最根本的問題可能是公平問題。尤其是在這個貧富差距比較大的時代,音樂的可獲得性、音樂訓練的昂貴性、音樂教育的準入性等等,都涉及音樂教育實踐為什么、如何追求理想的美育目標乃至社會功能,這一點對于音樂教育的從業者來說尤其重要。對實現社會公正的關注和實踐有助于減輕社會和教育達爾文主義的惡劣影響,在教育內卷到極致的情況下,“叢林規則”曾經那么有效地通過競爭提高質量,而現在則可能導致系統性的崩潰和逃離。在統一的、標準化的、嚴絲合縫的科學測量指標之下,每個勝出者都越來越相似,如出一轍,看似是一個嚴整的共同體,實際上已經在內部缺乏交流的必要了。
如何評價的問題呼之欲出。著名的評估專家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Guba,E.& Lincoln,Y..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1989.依據建構主義方法論,針對前三代評估中存在的缺點和不足,提出“評價就是對被評事物賦予價值,它本質上是一種心理建構,評價描述的并不是事物真正的、客觀的狀態,而是參與評價的人或團體關于評價對象的一種主觀性認識,是一種通過‘協商’而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建構’”。和前三代評估比較起來,第四代在方法上主要是“通過利益相關者的互動協商確定評估參數和界限,互動過程產生一個或多個構建”;在評估產出上是“多方協商的共識”;在意義上是“提出一種全面的積極參與,各利益相關者在評估中地位平等”的評價觀。在第四代評估提出之前,教育評估的歷史發展階段可以劃分為三代:測量時代、描述時代和判斷時代。存在的不足是:評價的“管理主義”傾向太濃;忽視價值的多元化;過分強調科學實證主義的方法,而忽視其他方法的使用,使評估過程形成了嚴格的、固定不變的程序,從而使評估活動缺少必要的靈活性和彈性。
第四代評估的出發點是對利益相關者各方評估要求的“回應”。評估并沒有固定的問題、指標、方法,而是廣泛動員所有利益相關者主動參與,提出自己的關切,形成廣泛的議題,達成共識并不是唯一目標,因此第四代評估的本質是共同建構。參與評估與評估有關的人或團體基于對評估對象的認識,通過不斷的協商、對話和交流,不斷發現新問題,協調教育價值觀,縮小關于教育評估結果意見的分歧,最后形成新的共識。
第四代評估者強調,心理建構總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和條件下形成的,應該在“自然情境”中進行探究和評價。由于探究在自然情境中進行,這就決定了探究需要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必須更多地依靠人的感官和思維來做研究和評判,包括通過觀察、座談、閱讀文獻、記錄未被人注意的跡象、重視人的非言語意向等來探究問題。這種心理建構與音樂的本體論和音樂教育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不謀而合的。“探究過程”究其本質而言是建構性的,是一個“詮釋性辯證循環圈”。其運作原理是,盡可能吸收各方對評價活動的意見和見解,各方可以根據自己的觀點對其他人的觀點進行分析和評價,目的在于形成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見,形成所謂的“共同建構”。音樂向來是多向度闡釋和表達的活動,形成一致性評價并不是必然結果,反而更可能是一致的教育過程和評價指標體系“造就”的結果。詮釋性辯證循環圈也許會帶來音樂參與者的多元智能的釋放、解放和怒放,特別是解決當下的音樂教育在激發學習者表演尚且乏力之余,這種評價過程還有可能帶來普通音樂教育中學習者的音樂創作的潛能。“探究結果”是經過多重詮釋辯證的循環過程,評價的最終結果是參與評估及與評估有關的人或團體基于對對象的認識,通過協商而整合而成的一種共同的、一致的看法。這說明第四代評估充分考量評估過程所引發的社會融合功能,盡管有分歧,盡管各個評估參與者對主觀性、客觀性的追求各有不同,也會導致在評估過程中很容易滑入“絕對標準”和“第三方客觀”的老路,但這也并不表明第四代評估走向了相對主義,而是將評估過程本身當作一種行動,這種行動不是獨立于被評估者和被評估活動的,而是相互嵌套,相互糾偏,特別是被評估者自身的聲音應該被充分重視。
在把學生削平成一個樣子之前,必須先考慮學生的差異,同時確保哲學家羅爾斯所謂“公平的機會均等”?〔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根據學生的需要更公平、公正地分配教育資源。我們把這一點與被相當簡單化理解,而且往往是有害的“機會平等”概念對立起來,以便提請注意:一個傾向于讓有才華和文化特權的人獲利的過程,他們被認為最有能力從稀缺的教育資源中獲益,然而被屏蔽的才華和文化擔當者可能更多。思考社會融合和社會正義等社群主義的問題,可能會有助于打破長期主導和持續的以“教育赤字”模式為前提的經濟學邏輯。這種經濟學邏輯認為,優質資源永遠是稀缺的、不足的,那么某些個人和社區如果被視為持續缺乏資源,就順理成章地、似乎無能為力地被甩出去。然而,音樂的最首要的特征是聲音,聲音的傳播本來可以做到跨越邊界,在不同的人之中、心之內產生共鳴,而共鳴是當代批判教育學面對個體化、原子化社會所提出的最高追求。恰好,音樂作為教育的獨特途徑,在這方面可以做出無與倫比的貢獻。
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音樂教育內部來說,就得和陳規決裂,徹底擺脫自奧林波斯教的時代(公元前7世紀)起一直把它禁錮在狹小古舊的圈子里的那個狂熱傳統,進而將反映日新月異的、活生生的藝術作為己任—哪怕這種反映總是滯后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帶有變形。?同注⑧,第296;296;298–299頁。泥古不化造就了學校音樂與現實藝術之間日益疏離的結局,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原本如此獨特和生動的音樂教育,到了希臘化時代卻變得如此蒼白,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的中國。
事實上,今天也還是這樣的,早早地讓孩子練習按照難度和比賽級別而編排的曲目,似乎只是為了讓他們熟悉音樂家的語言。這也不奇怪,和眾多的教育理論家一樣,亞里士多德未能從他深刻而推理嚴謹的學說中提煉一套可供指導實踐的策略。他們除了坐等音樂教育陷入傳統的泥沼,什么也沒有做。?同注⑧,第296;296;298–299頁。既然如此,音樂從教育中被棄絕,教育從生活中被棄絕,并不會令人感到驚詫。
然而,歷史的軌跡并不是不可改變的,音樂雖然在過去從通識教育中隱退了,但并不意味著它在整個文化領域的消失—盡管林谷芳曾發出喟嘆:談中國文化,為何獨缺音樂一環?林谷芳:《宛然如真:中國樂器的生命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音樂越來越成為技藝精湛的職業人士的專屬,人們對職業藝術家的觀感總是愛憎交織。一方面,他們因其才能而受到眾人的傾慕,觀眾愿意為他們的演出付出好價錢;可另一方面他們又是被鄙視的對象,被排斥在只有“高雅人士”方可自由出入的社交圈之外。?同注⑧,第296;296;298–299頁。要化解這兩方面的沖突感,我們對音樂教育的評估過程如果采取上述社會功能和社會心理建構的取向,那么就會了解,呈現不同的聲音相比達成一致性共識可能更加重要。如果我們相信一個社會的正義首要的途徑是發出聲音,那么就有理由相信共同建構與協商的評估能夠挖掘普通的音樂參與者的多元化音樂表現,音樂教育也可以開創多姿多彩的路徑,結出豐碩的令人驚奇的果實。
結 語
正如教育哲學家馬丁(Jane Roland Martin)所言,“世界已經變得如此習慣于采用一種思想框架,其精神前提是稀缺性,我們忘記了對于文化來說,這個問題是一個極大富足(super abundance)的問題”?Martin,J.R.The Wealth of Cultures and Problems of Generations.In S.Tozer (Ed.),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Yearbook (pp.23–38).Urbana,IL: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1998,p.24.。在正規的音樂教育中,這種缺失的教育模式往往是基于合法音樂知識的過分狹隘的定義,這一認識使得缺乏適當文化資本的兒童望而卻步,而音樂教師卻忽視了在這個國家之內、不同的族群之中存在的音樂財富。文化財富確實不同于物質財富,豐富的文化構成了音樂課程源源不斷的基礎:它不僅是課程內容和主題的來源,也是教育目標和教學方法的來源。這里的重點不只是在于包容性和多樣性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在關鍵的參與、授權和創造力上。
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課程和教學實踐有助于對任何音樂和音樂教育方法進行批判性審查,從而也有助于更廣泛的參與和交流,更有可能提高個人和集體的能動性和滿意度,同時也有助于更具創造力、公平性和生產力的社會。任何國家和小世界都是一個復雜的地方,其特點往往是沖突和分布式的知識乃至某種程度的無知,我們在倡導從科學主義走向社會社群主義的時候需要非常謹慎。面對那些在具有挑戰性的環境和社會政治背景下成功地運用傳統音樂或方法來解決嚴重社會問題的文化和教育工作者,政策是否需要對他們提供資助或倉促做出判斷,我們可以考慮是否應該納入第四代評估的途徑和方法,盡可能地讓評估所涉及的參與者都納入進來,讓不同的聲音有發出來的機會。這既是過程,也是結果。
縱觀不長的歷史,測量的科學給音樂教育帶來一種廣為人知的觀念,如音樂作品習得的數量、唱奏技巧的精確等級、音樂從業人員的區分類別、音樂衍生品的社會區隔空間等等,這些概念構建了音樂教育體系的基本框架。而以描述的方法為表征的第四代評估可能給音樂教育帶來一些有吸引力但還在悄然生長的可能性,如模糊的音樂專業性地帶、多元的音樂空間/聲景、以音樂記憶的自我敘事作為身份認同、人群的社會區隔以音樂作為黏合劑等等。其實,這些可能性我們并不陌生,因為從音樂進入人類社會生活并成為一種專門的實踐領域之時,事情本來就是這樣的。20世紀以來,現代音樂教育伴隨著追求社會正義的歷史進程。因此,這個結論我們也可以用一種提問的方式來得出:音樂教育是否應該重返原初就具備的社會功能?
新世紀以來,諸多研究者公開批評教育越來越缺乏對社會公正的關注,學校致力于讓自己變得更有特色的同時也著力讓每個孩子變得與眾不同。隨著社會的快速變化,學校系統應該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容納不同類別的學生,然而,各階層、各地區、各學校乃至個人之間差異越來越大,并沒有帶來教育系統對包容性和公正性的強調。如果將音樂視為一種活動,那么學校應該通過唱歌和演奏樂器,將不同差異背景的師生團結在一起,讓學校成為“包含多樣性的整體”。
一個社會只有當其成員中存在足夠的同質化時才能存續,教育通過音樂這種特殊而又普遍的工具,從一開始就可以將社會生活所需的基本相似性固定在孩子身上,從而使這種同質性得以延續和強化。因此,音樂教育作為國家資產,要有助于實現命運共同體的理想,需要換個角度審視其獨特的本體論價值,從之前強調用科學測量的工具區分音樂等級和能力差異的技術取向,重返其以描述確認自身和群體屬性的“社會熔爐”的功能取向。
在“正常”和傳統的學校教育制度參數內外,有許多令人鼓舞的音樂教育行動途徑,可以幫助我們將杜威關于參與式、協商式的社群作為一種倫理理想和共同生活方式的理念具體化,從而釋放人的能力。替代方案和教學模式可能會對教師和其他人提出挑戰,讓他們重新思考他們對音樂教育機構、音樂教育項目的社會融合功能和公民責任的理解,從而為一個更加公平和公正的社會、共同建構命運共同體的國家理想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