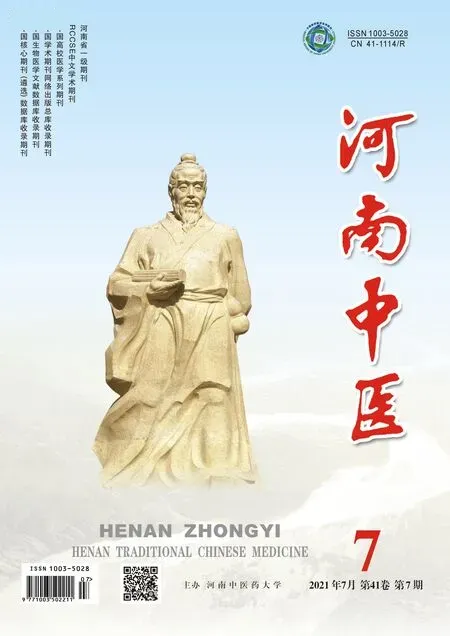“瘧疾療法”治療晚期惡性腫瘤*
2021-04-17 19:59:02王猛左玲曹文富唐志宇
河南中醫
2021年7期
王猛,左玲,曹文富,唐志宇
1.重慶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重慶 400016;2.重慶醫科大學附屬永川區中醫院,重慶 402160
惡性腫瘤是中西醫學共同關注的熱點疾病,隨 著醫學的發展與進步,惡性腫瘤患者的生存率大大提高,但對于中晚期惡性腫瘤患者,中西醫學均難以取得理想效果。20世紀初,奧地利醫生姚雷格發明了將含有瘧原蟲的血液接種到麻痹性癡呆患者的一種療法,后世稱為“瘧疾療法”,姚雷格醫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1]。20世紀末,陳小平團隊發現,瘧疾療法可以治療晚期惡性腫瘤[2]。2011年,聶作良基于陳小平的研究,進一步探索了瘧疾療法治療晚期惡性腫瘤的可行性及要點[3]。“瘧疾療法”治療惡性腫瘤是中醫“以毒攻毒”理論的擴展與應用,現筆者從“以毒攻毒”理論出發,探討“瘧疾療法”治療晚期惡性腫瘤的中西醫理論基礎及認識,論述如下。
1 “以毒攻毒”理論源流
“以毒攻毒”法是用有毒之物治療各種疾病之“毒”。《周禮》言:“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兇于鴆毒,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所用也。”中醫認為,陰陽者,為天地之道,萬事萬物均可分陰陽。無論是藥物偏性和致病邪氣都離不開陰陽屬性的劃分,所以張景岳《類經》云:“藥以治病,以毒為能,所謂毒者,因氣味之有偏也。蓋氣味之正者,谷食之屬也,所以養人之正氣,蓋氣味之偏,藥餌之屬也,所以祛人之邪氣。”如熱病用辛溫大熱的藥物,會加劇陰液的損耗,不僅起不到治病的作用,還會導致病情加重,醫家則稱此藥為“毒藥”。……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