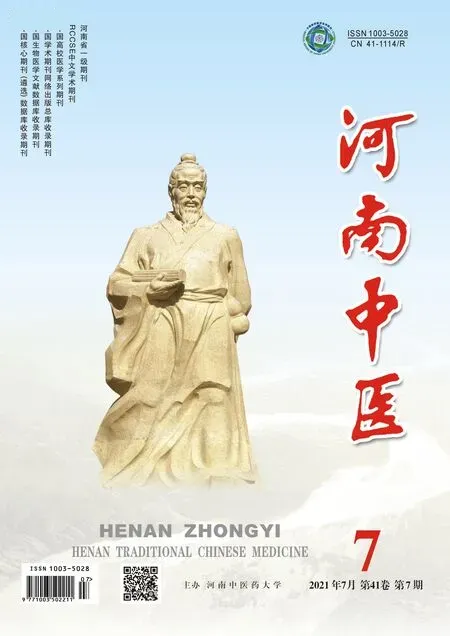以特征性要素為辨證要點治療小兒過敏性紫癜*
2021-04-17 19:59:02張建翟文生李廣劉麗雅李鵬飛楊濛張霞
河南中醫
2021年7期
張建,翟文生,李廣,劉麗雅,李鵬飛,楊濛,張霞
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河南 鄭州 450000
過敏性紫癜(henoch-schonlein,HSP)為兒童時期最常見的血管炎性疾病之一,臨床表現為皮膚紫癜,腹痛,關節腫痛,并可出現腎臟損傷[1]。本病中醫的病因病機較為復雜,眾多醫家多從毒、熱、瘀、虛等方面進行闡述[2-3]。本病常分為風熱傷絡證、血熱妄行證、濕熱痹阻證、氣不攝血證及陰虛火旺證[4],每證型辨證要素基本囊括HSP的四大癥狀。除四大癥狀外,HSP與患兒免疫功能狀態[5]、發病誘因密切相關,且皮疹出現于平常少見的部位如耳輪、外陰等處的現象,腹痛輕重程度等特征對于辨證及選方用藥的意義各有不同,目前尚沒有以這些要素為著眼點進行辨證治療的方法。本文以HSP患兒的這些特征要素作為切入點進行辨證治療,為中醫治療本病提供新的視角。
筆者認為,HSP辨治可參考以下特征性要素:①發病誘因;②皮疹的特點如遍及全身的彌漫性皮疹及耳輪、外陰等少見部位的皮疹;③腹痛的輕重程度;④患兒的發病年齡。以這些特征作為HSP的中醫辨證要點或可起到執簡馭繁的作用。
1 以發病誘因為特征
本病的發病誘因一般為外感、飲食及接觸物,外感最常見[6],感染之后常在較短時間內出現皮膚紫癜。患兒就診時仍存在外感表現,如發熱、咽痛、咽紅、咳嗽等,皮疹分布于雙下肢,以小點狀為主,亦可見有皮疹融合,辨證多為風熱傷絡證,治療以銀翹散加減為主。除風熱證表現外,亦可見以風為主及熱毒較盛的表現,治療方法也有所側重。……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