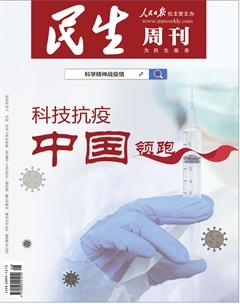抗疫,要“肉搏”更要“智斗”
賈偉

北京協和醫院感染內科主任李太生
去年疫情之初,北京協和醫院感染內科主任李太生就已投入到新冠病毒的科研工作。為了離“對手”更近一些,他主動請纓,奔赴武漢、馳援抗疫。
在李太生看來,與傳染病作斗爭,既要“肉搏”,也要“智斗”,“科研與臨床無縫對接,才能守護好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
在援鄂工作札記中,他這么寫道:
“手持科學的武器與病魔展開生死較量,盡我所學、為國盡力,勇攀科學高峰、護佑人民健康,是一名感染內科醫生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協和方案”
2020年2月7日下午5點,武漢天河機場,一架搭載北京協和醫院第二批援鄂醫療隊隊員的飛機緩緩降落。
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C9病區的32張重癥病床,是醫療隊此行的目的地。
病毒有多危險?患者情況如何?怎樣做好防護?身為隊長的李太生一路思考著。
作為一名“抗疫”老兵,李太生跟傳染病打了38年交道,先后與非典、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交過手、過過招。用他的話來說,深知“敵人”的狡猾和兇殘。
就在出發前一個月,經協和醫院委托,李太生聯合院內近30位醫學專家,經過研究和討論,形成《北京協和醫院關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建議方案》(下稱“協和方案”)對外發布。
“協和方案”首先明晰了“應檢盡檢”的重點人群,同時調整了持續關注的目標人群,“特別是3天內沒有流感癥狀以及不明原因的急性發熱者。”李太生介紹。
值得一提的是,針對一線醫護人員的防護措施,方案也進行了詳細說明。其中,醫護人員準入標準、個人防護措施、危重癥感染患者診療規范等要求,業界專家給予高度評價,并推廣至多家醫院。
然而,方案剛剛實施,李太生自個兒卻先破了規矩:準入標準中,醫療隊隊員年齡限定為55歲,李太生卻超齡了兩歲。
回憶此事,李太生說:“當時很多人勸我不要去,但是不去病房一線,哪來的基礎數據和病毒樣本呢?沒有這些作支撐,又怎樣進行相關的科研工作呢?”他頓了頓,鄭重地說:“病床就是醫生的戰場,我必須親眼去看病人!”
科學救治
到了武漢,李太生每天從早忙到晚。白天,穿著厚重的防護服頻繁往返病房之間:爭分奪秒搶救患者,觀察、記錄病情變化。晚上回到駐地,整理材料、總結重點、計劃次日工作。
“每天查完房,我都要對著筆記本發一會兒呆。這是一種新型傳染性疾病,在臨床治療上,我們必須不斷分析、總結,根據變化,再去調整、觀察。”他說。
短短6周,李太生體重驟降16斤。肩周炎的疼痛,折磨得他翻來覆去睡不著,每晚吃止疼藥才能入睡。
盡管如此,李太生始終守在病人床邊。病房里,他鼓勵患者早日戰勝“病魔”,回歸家庭;病房外,他是隊員們的“定心丸”,“看到李主任,心里就踏實了。”有隊員這么說道。
采標是最危險的治療環節,感染風險極高。每每如此,李太生都和科里的專家站在最前面,“我們是‘老兵了,為‘新兵做示范,傳授他們正確的操作技巧,保證人身安全。”
一次查房中,李太生發現患者出現“黑腳丫”現象—手指、腳趾、腳部出現紫紺色。病人體內相關臟器存在血栓,嚴重時可導致臟器衰竭甚至死亡。
李太生認為,新冠肺炎不僅是一種肺炎,更是一種感染綜合征。于是,他提出由被動防守轉為主動出擊的理念—治療前移。本著盡早抗凝的原則,給予低分子肝素的同時,為患者注射一定劑量的免疫球蛋白,提高重癥患者救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
“此方案安全有保障,關鍵是藥價便宜,每家醫院都有儲備,便于大規模推廣!”李太生的聲音里透著興奮和激動。
隨著一系列科學有效的治療方案落地,多位患者先后脫離生命危險,并轉入普通病房。鏖戰81天,完成重癥救治攻堅使命,北京協和醫院援鄂醫療隊“收兵”撤離武漢。
“病人診療高于一切!”
回到北京,屬于李太生的“戰斗”仍在繼續。
近日,記者來到協和醫院老樓,走進一間陳設簡樸、面積不足10平方米的辦公室。書架上,一本鮮紅的“全國先進工作者榮譽證書”,仿佛在訴說著戰疫背后的汗水和擔當。
如今,門診和查房,已經排滿了李太生每周的工作和生活。這位年近六旬的醫生身上,像是安裝了“加速器”:語速快、走路快、腦子轉得更快。
“病人治療高于一切!”這是李太生常掛在嘴邊的話。面對慕名而來的患者,問診時,李太生注重細節、從不馬虎。送走患者,他往往會花上半天時間,認真研究患者病歷,同時,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提出有效的治療方案。
交談中,李太生聊得最多的是他的學生和學術研究。他常常教育學生,“做一名合格的醫生,要懂得理論聯系實際,病人永遠不會按著課本的知識去生病。”
除了擔任感染內科主任一職,李太生還有另一個身份—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候任主任委員兼艾滋病學組組長。
談及下一步工作重點,李太生有著非常清晰的規劃。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新冠病毒、艾滋病依然肆虐,他將目光投向了傳染病的預防和科普工作。
科學傳播健康知識,提高大眾對于傳染病的認知度, 正如李太生工作札記中的一段話:
“用科學的光芒照亮未來的道路,逐步揭開疾病的謎團,我們應銘記,地球本是微生物的世界,要敬畏自然、與微生物和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