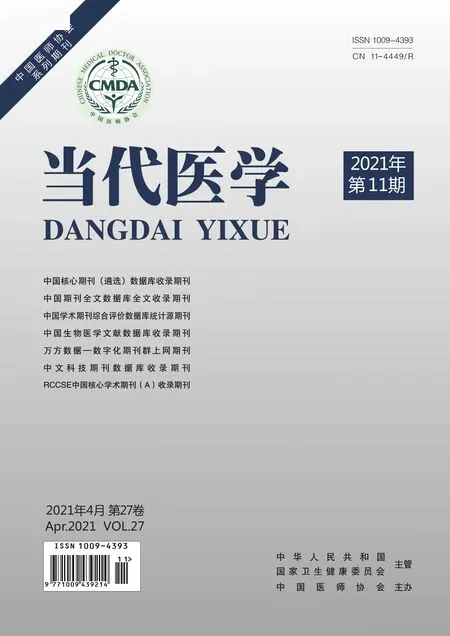腹部手術后應用大承氣湯保留灌腸聯合針刺對患者胃腸功能恢復的影響
方榮臻,林少露
(1.漳州市中醫院外科,福建 漳州 363000;2.漳州市福康醫院精神科男病區,福建 漳州 363000)
腹部手術是外科常見手術類型,術中多采用全麻或硬膜外麻醉,外加手術創傷操作會使機體產生應激反應及局部炎癥刺激等,均會影響術后胃腸功能,臨床表現為腸蠕動速度緩慢、便秘、腹脹、腹痛等癥狀[1]。若胃腸功能抑制時間過長,易損傷應激性腸黏膜,誘發各種腸道并發癥,如腸粘連、腹脹、腸梗阻等[2-3]。因此,臨床需重點解決患者腹部手術后胃腸功能恢復緩慢問題,加快術后康復速度。近年來,我國醫學在胃腸功能中的發展日漸顯著,認為胃腸經絡受損、胃腸道運行受阻,造成胃失和降、脾失健運、脾胃受損,致胃腸并發癥發生[4]。因此,提出通里攻下、行氣散結的治療原則。本研究對本院行腹部手術患者采用大承氣湯保留灌腸聯合針刺治療,旨在為胃腸功能恢復治療措施提出依據,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15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本院行腹部手術患者96例,按術后治療方法不同分為兩組,各48例。對照組男 25 例,女 23 例;年齡 20~65 歲,平均(48.63±8.92)歲;體質量50~85 kg,平均(68.52±5.69)kg;胃腸手術21例,腹部外傷手術11例,肝膽手術12例,腹部腫瘤切除術 4 例。觀察組男 28 例 ,女 20 例 ;年齡 20~66 歲 ,平均(49.24±9.05)歲;體質量50~84 kg,平均(69.12±5.72)kg;胃腸手術25例,腹部外傷手術10例,肝膽手術10例,腹部腫瘤切除術3例。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患者及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獲得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標準。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患者均自愿接受腹部手術;術前無胃腸功能障礙;術前無全身感染、凝血異常者。排除標準:術后重度感染、凝血異常者;伴心、肝、腎等多臟器障礙者;有頑固性便秘、假性腸梗阻、炎性腸病等腸障礙者;合并精神障礙性疾病、認知異常者;研究中退出及死亡者。
1.3 方法 兩組患者術后均以常規西醫處理,行腸內外營養支持、液體補充;密切監測體征變化,維持水電解質、酸堿平衡;術后積極抗感染、在床上翻身、活動四肢。
觀察組在此基礎上行大承氣湯保留灌腸聯合針刺。術后24 h肛門未排氣開始使用,大承氣湯保留灌腸:大黃12 g,芒硝6 g,枳實12 g,厚樸24 g。用600 mL水浸泡30 min,文火煎至200 mL,隨溫度下降至38 ℃~40 ℃備用。左側臥位,適當墊高臀部并潤滑肛門,插入肛管,滴注大承氣湯,于20 min內滴完。隨后取平臥位,休息1 h,每天1次。針刺:術后1 d取雙側足三里穴、上巨虛穴、下巨虛穴、三陰交穴、陰陵泉穴及懸鐘穴,穴位消毒,針刺得氣后,于足三里穴、上巨虛穴連接電極,調整電針頻率為5 Hz,通電25 min,每天1次,連續治療7 d。
1.4 觀察指標 ①比較兩組術后腸鳴音恢復、肛門排氣及飲食恢復時間;②術后炎癥因子:抽取治療前后外周靜脈血3 mL,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腫瘤壞死因子-ɑ(TNF-ɑ)、白細胞介素-6(IL-6)及C 反應蛋白(CRP)水平;③比較兩組術后腸梗阻、便秘、腹脹及感染等并發癥發生率。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3.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n(%)]表示,行χ2檢驗,計量資料以“”表示,行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術后胃腸功能恢復時間比較 術后,觀察組腸鳴音、肛門排氣及飲食恢復時間均短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術后胃腸功能恢復時間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ime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1 兩組術后胃腸功能恢復時間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ime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組別觀察組(n=48)對照組(n=48)t值P值飲食恢復(d)2.16±0.75 4.68±1.27 11.837 0.000腸鳴音恢復(h)21.51±6.14 46.85±12.36 14.227 0.000肛門排氣(h)28.49±4.87 38.12±8.95 14.707 0.000
2.2 兩組患者炎癥因子比較 術前,兩組患者炎癥因子TNF-ɑ、IL-6 及CRP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術后,炎癥水平下降,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2 兩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組別觀察組(n=48)對照組(n=48)t值P值TNF-ɑ(ng/L)治療前352.85±28.63 350.64±30.12 0.370 0.356治療后65.13±10.74 128.49±24.36 16.489 0.000 IL-6(pg/mL)治療前4.01±0.72 3.98±0.70 0.207 0.418治療后1.65±0.36 2.49±0.58 8.525 0.000 CRP(mg/L)治療前21.06±1.58 20.98±1.57 0.249 0.402治療后4.35±0.84 12.37±1.91 26.630 0.000
2.3 兩組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觀察組術后發生腹脹2 例,便秘 1 例,感染 1 例,發生率為 8.33%;對照組術后發生腹脹 5 例,便秘 4 例,感染3 例,發生率為 25.0%;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800,P=0.028)。
3 討論
腹部手術后常見胃腸功能紊亂,多因麻醉藥物、手術組織創傷、手術牽拉等作用,從而抑制認知功能、胃腸道功能。通常術后12~24 h內腸蠕動功能減慢,術后38~96 h內腸蠕動能力逐漸恢復,出現排便、排氣癥狀[5]。但腹部手術過程中通常會牽扯到腸管,腹腔受損,極易誘發腸道功能抑制,腸屏障功能喪失,內毒素移位,極易損害腸道及其他重要器官形態和功能[6]。因此,重視腹部手術患者術后腸胃功能恢復,以積極有效治療措施加快患者康復速度。
我國中醫學認為“六腑以通為用”,腹部手術會使胃腸通降失調、經絡受損、氣血瘀滯,造成脾胃受損、運行受阻,因此,治療應以“通”為主。大承氣湯來源于《傷寒論》,以大黃、芒硝、枳實、厚樸四味中藥組成,并隨癥加味。方中大黃有清熱解毒、通便瀉火、蕩滌腸胃之功;芒硝有清熱瀉火、通便軟堅、潤燥除濕之功;厚樸、枳實有行氣散結、消痞除滿作用,并能推動大黃、芒硝熱結排泄、蕩滌腸胃[7]。同時采用保留灌腸方法可促進直腸藥物吸收,直接作用于患處,減少大黃等藥物對胃腸道功能的損害[8]。而且采用大承氣湯保留灌腸,可促進患者腸胃蠕動及滲液吸收,改善胃腸道血液循環,降低毛細血管通透性及炎性因子的釋放,以此減輕胃腸道組織水腫,恢復腸道組織功能[9]。高佳麗等[10]在剖宮產術后應用大承氣湯保留灌腸,術后首次排便時間、腸鳴音恢復正常時間均明顯縮短,腸粘連治療效果顯著提高,表明大承氣湯保留灌腸對腸粘連有顯著作用。
針刺是中醫重要組成部分,針刺足三里穴、下巨虛穴可促使小腸蠕動功能;針刺上巨虛穴有健脾和胃、通臟導滯的作用;針刺三陰交穴有健脾補肝、和胃益腎、補氣活血作用;陰陵泉穴配以三陰交穴有溫中健脾之功;懸鐘穴針刺可通絡舒筋、補氣益血作用。而且輔以電針穴位,通過氣血經絡、體表局部作用,可促進腸胃蠕動、增強腸道屏障防御能力[11]。因此,對腹部手術患者行針刺治療,能有雙向調節胃腸能力,提高胃腸收縮、輸送能力,增強胃腸道蠕動能力,緩解腹脹、便秘癥狀[12]。
本研究結果表明,術后,觀察組腸鳴音、肛門排氣及飲食恢復時間短于對照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8.33%,低于對照組的25.0%,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提示腹部手術患者術后大承氣湯保留灌腸聯合針刺,可增強患者術后腸胃蠕動能力,預防便秘、腹脹等并發癥發生。原因分析:術后大承氣湯保留灌腸直接作用于患處,經直腸吸收,減少瀉藥對胃腸功能損害的同時起到去除積滯內阻、通便軟堅的作用;輔以針刺調和脾胃,促進腸胃運動、腸道收縮力及腸道腺體分泌,以此充分改善患者胃腸功能,降低術后便秘、腹脹等發生[13]。
腹部手術操作會損傷組織,使胃腸道中性粒細胞活性被激活,不斷釋放大量的炎性因子,造成機體呈高炎癥反應以及腸壁水腫,抑制腸道蠕動能力[14-15]。本研究結果表明,術后,觀察組患者炎癥因子TNF-ɑ、IL-6及CRP水平低于對照組(P<0.05)。提示大承氣湯保留灌腸聯合針刺用于腹部手術患者,能夠抑制機體炎癥反應,對改善腸道水腫、充血及機體高炎癥反應具有積極促進意義。原因分析:大承氣湯保留灌腸能夠相應阻斷內毒素誘發的炎癥因子及細胞因子,緩解術后急性應激反應,減少炎性細胞釋放,緩解機體炎癥反應。
綜上所述,腹部手術患者術后采用大承氣湯保留灌腸聯合針刺治療,能促進患者胃腸功能恢復,降低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緩解機體高炎癥反應,應用價值較高,值得臨床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