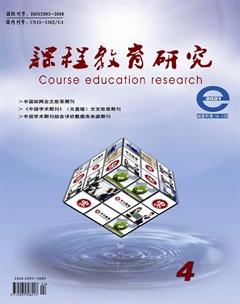于詩歌中回望道不盡的愛情
張錚
【摘要】詩歌中的愛情是不竭的創作源泉,詩人用或精巧或樸拙的修辭來表達自己關于愛情的理解,代入自身關于愛情之路的感嘆。在不同時空的詩人筆下,愛情的呈現和理解各有異同,可以說在愛情的反復無常的外衣之下,詩人們殊途同歸的展現出了愛情永恒纏綿的內核。李商隱和穆旦是不同時期不同經歷下的古典與新派詩歌的代表人物,他們對于典型意象均有超越多數詩人的敏感性,對于語言的序列也有如同密碼一般的重組和演繹。本文試圖由分析《錦瑟》與《春》中語言和意象的不同形式,來探尋兩位詩人的愛情理解。
【關鍵詞】《春》? 《錦瑟》? 意象? 想象? 聯想? 愛情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21)04-0095-03
一、古典詩歌側重典型意象的個人化闡述,現代詩側重意象的個性化。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李商隱 《錦瑟》
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
它渴求著擁抱你,花朵。
一團花朵掙出了土地,
如果你是女郎,把臉仰起,
看你鮮紅的欲望多么美麗。
藍天下,為關緊的世界迷惑著
是一株廿歲的燃燒的肉體,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鳥的歌
——穆旦《春》
《春》中的“泥土”顯而易見的帶有發掘和啟示的功能,被賦予了某種思想和特性。“綠色的火焰”“花朵”都是泥土中來,這是新的希望和春天的生命得以綻放的根基,與此同時,泥土還是那“鳥的歌”,是“誰家新燕啄春泥”中鳥兒的新巢,新的希望。在中國的創世神話中,泥土是女媧造人的來源,是落地即活的肉體。泥土是肉體,在其中生長蔓延的綠色的草、紅色的花,都是新鮮的生命力和蓬勃的欲望。在這濃烈的顏色撞擊中,誕生了一尊廿歲的青年人的肉體。這新鮮的肉體在花草之間,恰如蘇軾所言春天之美是“一朵妖紅翠欲流”,是新鮮奔騰的色彩。年青人的靈與肉不斷對抗和消解,探索著愛的意義,然后陷入長久的迷茫和痛苦。肉體承載了詩人的幻想,與此同時又是禁忌而難以突破的。肉體若沒有承載著愛情,就是貧瘠而蒼白的,是一座荒城,而現如今愛情這一肉體的春天驀然奔襲而來,在天地間所感而開合,恰是“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生命從此有了依托。落地生根,蓬勃不息。
“錦瑟”是開篇之物,這是《漢書·郊祀志》中素女的瑟,是傳說中的瑟。素女用此瑟彈奏哀傷的歌曲,而這種哀傷凡人難以承受。這一傳說在觀念上已經確定了錦瑟的器型和內核:哀傷之物。而弦樂器在古代詩歌意象中一直以來和愛情均有聯系,愛情的落空恰如弦斷無人聽,在中國古人關于婚姻的敘述中,亦有續弦一詞。弦之器物獨有的幽深綿密的聲音被認為觸動心靈之音。由錦瑟發端,顯見敘述之情是哀情。也可見這是蕩滌了歲月后的曲調,深沉縹緲,不似年青人的熾烈和反復,已經停止了追尋,而是靜默的喃喃自語。開篇“無端”二字,無理之問,仿若思念情人至極而百無聊賴的下意識的低吟,似一聲嘆息,但聽不到,為錦瑟的弦音所掩。如同一切無可言證的感情,于縹緲里暗藏濃烈。先秦詩作《越人歌》里唱“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先從山上的樹木起興,也是無端之言,這一如愛的萌發,不知為何而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無法用邏輯來推導說明。然而聽來不覺無理,反而心證其理,理所應當,那山上的木枝在春天也會萌蘗,上古歌謠里,人們已經發現了木枝本身暗含著的生命力,并將其和人相比,人內心關于愛的體悟也如林木不斷滋生發展,呈現多種形態。《錦瑟》中的藍田玉暖,暗合《搜神記》中紫玉與韓重的愛情故事,紫玉由愛而死,無法回應韓重的擁抱,化為了煙塵,愛而不得,無望無著。可以看到,《錦瑟》通篇都用這種極致之美的事物和傳說來展現內心對于愛的理解——這愛是回憶中的愛,隔著茫茫的時空,蒙上了悵然若失的迷離意味。李商隱在他的另一首《馬嵬(其二)》中談到對于楊貴妃和唐明皇之間生死兩隔的愛情的理解,說是“他生未卜此生休”,異曲同工的表達了他對于無望之愛的深刻解讀,或許可以認為李商隱詩中的愛的最高形式就是未完成。《錦瑟》之愛未曾道盡,沒有具象,或許是詩人自身愛的過往,又或者是無數個愛的故事中抽離而出的歲月的歌謠。
二、傳統詩歌重聯想與想象,現代詩歌重直覺與幻想。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李商隱《錦瑟》
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
它渴求著擁抱你,花朵。
一團花朵掙出了土地,
當暖風吹來煩惱,或者歡樂。
如果你是女郎,把臉仰起,
看你鮮紅的欲望多么美麗。
藍天下,為關緊的世界迷惑著
是一株廿歲的燃燒的肉體,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鳥的歌,
你們是火焰卷曲又卷曲。
呵,光、影、聲、色,現在已經赤裸,
痛苦著;等待伸入新的組合。
——穆旦《春》
詩歌主情。傳統詩歌尤忠于此。
李商隱詩歌純為抒情體,全詩整體為一。其中四句似不可讀,也不能解,解讀即是美的毀滅。其意象的神秘和統一使其成為唯美典范。莊周夢蝶,杜宇化鵑,人與物合二為一,我是周遭之物,物也即我,不分彼此,相互融合。古典詩歌含蓄唯美,用山水來托情,用典故來遮蓋未盡之言,留下迷思,催人一讀再讀。讓讀者得以擁有多層欣賞視角,人人皆可通過這一語言密碼來打開內心,比照自身關于愛的理解,若合一契,不能不有所感慨。“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意境擴大,虛實幻境,海天一色,珠玉相合。重的是意境的營造,情已無人訴說,但一如愛情的如泣如訴,珠淚之美,玉煙之暖,讀來從舌尖滲透進骨髓,通體都柔軟起來,進入迷離之境。如一頭扎進太虛幻境的賈寶玉,俗舌眼餳,悠悠蕩蕩。在迷幻和想象里蕩滌身心,忘卻凡俗之事。真真假假,無人追尋意象的一一指應,而是通篇讀來頓感萬千紅塵中柔情萬丈,不禁心碎至此。
穆旦的《春》對于愛情的描繪,更多是依靠直覺的搜索。意象中的象,即為形象與視覺現象中的投射。詩人讓春天的典型意象悉數登場,看似如朱自清的《春》一般熱鬧喧騰,而細究這些意象的刻畫,卻超越平常的認知。他沒有選擇傳統意象中唯美的存在,反而單刀直入,只取春天的景物來描繪。按照常規的閱讀順序,綠色的火焰對應著燃燒的肉體,都在擁抱、搖曳、卷曲;女郎的臉是花朵,是鮮紅的欲望,它們在關緊的世界里赤裸的展現著,又歡樂又痛苦。詩歌用散文化的方式打亂了排列,憑借著幻想讓愛從土里掙扎著冒出來,讓愛情的無望和誘惑沾染到春天的一切事物之中。把意象的封閉靜止完全打破。讓二十歲的青年愛情有了溫度和質地。好比握雪之后的觸感,痛苦而炙熱,這種奇異性在文本中自然的排列鋪陳,用身體的經驗來直接抒寫,新穎奇異,擴大了文本張力。文中點明的:光、影、聲、色,是感官的一次集體釋放,由“火焰”而產生了動態感,大地上生長的一切本來就有動態性,而此時的火焰更是加深了顏色的對比,空間的折疊,人和物在火焰之光中變形,展現出其他的形態。原本一目了然的油畫變得抽象離奇。“光、影、聲、色,現在已經赤裸”直接大膽的表達了青年人在愛欲中的沉淪,年輕的詩人在模糊重疊的意象里鋪陳思想的矛盾,拉著讀者一起進入焦灼而熱烈的心理世界。這一“燃燒的肉體”中有綠草,有紅花,有暖風和鳥鳴,這一身體就是春天,詩人將兩者糅雜一起,不分彼此,眼前之景就是心中之境。
三、作為高度凝練的文學形式,傳統詩歌側重于含蓄寫意,現代詩歌更加直白。
《錦瑟》開篇和結尾直接抒情,傳達對于華年逝去的追思和情感的惘然。由身邊圍繞的天地萬物發端,可心里眼里不見萬物,一個勁的只指內心,這才可見“為情所困”,將抽象之情愛寄寓具象之萬物。讓情感有跡可循,落地尋蹤。但這種“情”不知具體年月,也不能確定深度重量。最妙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可待指向未來,追憶暗合現在,當時又指過去。一句之中,過往如今未來三個時間點紛繁交錯,避無可避,正如《百年孤獨》首句的撰寫“多年以后,奧雷連諾上校站在行刑隊面前,準會想起父親帶他去參觀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由時態的多重復合來擴大空間和時間的邊界,此情的厚度和廣度無邊無際,這才證明情網恢恢,難以消解。張愛玲的散文詩《愛》里,也將這愛形容為“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用時空的廣袤拉長愛的閾值。作者自己對于愛也難以捉摸,這和《錦瑟》的無端之愛,有所照應。
相對于《錦瑟》里無可發端,充盈天地的情愫,穆旦的《春》卻是把情感倏忽拉下,寄托在沉重的肉身之上。這恰是“靈與肉”的分界,《錦瑟》之美在于空中樓閣,半壁海日。《春》中處處都是招搖的情愛,“渴求著擁抱你”“鮮紅的欲望”“燃燒的肉體”,分明是二十歲的青年炙熱的愛,是情欲,是泥土里的原始欲火。這愛不是“傷心橋下春波綠,疑是驚鴻照影來”的哀怨纏綿,而是充滿了初次感受愛的滋味的新奇和苦痛,青年之愛是冒失無理的,缺乏考量,隨心所欲。但這愛讓初嘗滋味的詩人并不好受,“一團花朵掙出了土地”中的“掙出”是肉體的自我覺醒,是生命的力量。而“當暖風吹來煩惱,或者快樂”則暗示著“暖風”作為外因在誘導著詩人的愛的覺醒。作為二十歲的青年,對于世界還是外放型的,他們不停的感受身邊之物,由他物而觀照自我。《春》中的愛并不收斂,但卻單純。它藉由春天的景色而盡情揮發。“女郎”“泥土”“花朵”的組合,并不是穆旦這一新派詩人的獨創,而是糅合了古典美學和新派主義的一次嘗試。中國戲曲史上的杰作《牡丹亭》中杜麗娘第一次踏入家中花園,發出了“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的感嘆,這是生命的感嘆,杜麗娘這一懷春的女郎,游園驚夢,為這春花春情而感動,她眼中所見也即自身之美,那千古一嘆“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不正是“燃燒的肉體”和“鮮紅的欲望”的膠著。在這一刻人和春天之物合二為一,由賞春景中驚覺自己也是春的一部分,在她的身體中原來一直存在著一個未曾展露于世的春天。而我們的詩人穆旦沿襲了古典美學中關于春情的頌揚,但是他大膽的將這一內心中的春天潑灑出來,他不再隱晦,而是直言春天的美,那美便是春情,便是年輕人熊熊燃燒的心火,他直接道出這哪里是滿園的花朵,分明就是滿園的欲望。那“為關緊的世界迷惑著”的肉體也正是為愛蘇醒的蓬勃的欲望的載體。詩人穆旦將古詩歌中隱藏的情感從意象的掩映里解放出來,讓花、草、女郎、鳥等蓬勃的春天之物象悉數出場來佐證這情意,詩人眼中可見之物全是愛情,全是色彩,全都動起來,探索著愛。而意象的選擇甚為巧妙,讓這萬物都在燃燒。愛情一如吻火,光熱太甚,疼痛也甚,卻光芒大盛,無法回避。這是大膽的愛情之火的縱情高歌,待火燒盡,人也老去。暮年的詩人李商隱早已不是需要他物來印證自身的青年,藉由閱歷,他已和世界相融,那洶涌的愛也靜止下來,在愛的灰燼里回望的才是《錦瑟》。
參考文獻:
[1]裂帛:現代詩與思維的野性
[2]《穆旦詩文集》(修訂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
[3]《葉嘉瑩說中晚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2008:148—156.
[4]張丹.重彈《錦瑟》——一種文本中心主義的分析[J].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02):52-54.
[5]吳投文.在生命的限制中對自由的張望——穆旦詩歌《春》導讀及相關問題[J].北方論叢,2016(06):36-41.
[6]《牡丹亭》(明)湯顯祖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
[7]《張愛玲散文》張愛玲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