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與不變
鄧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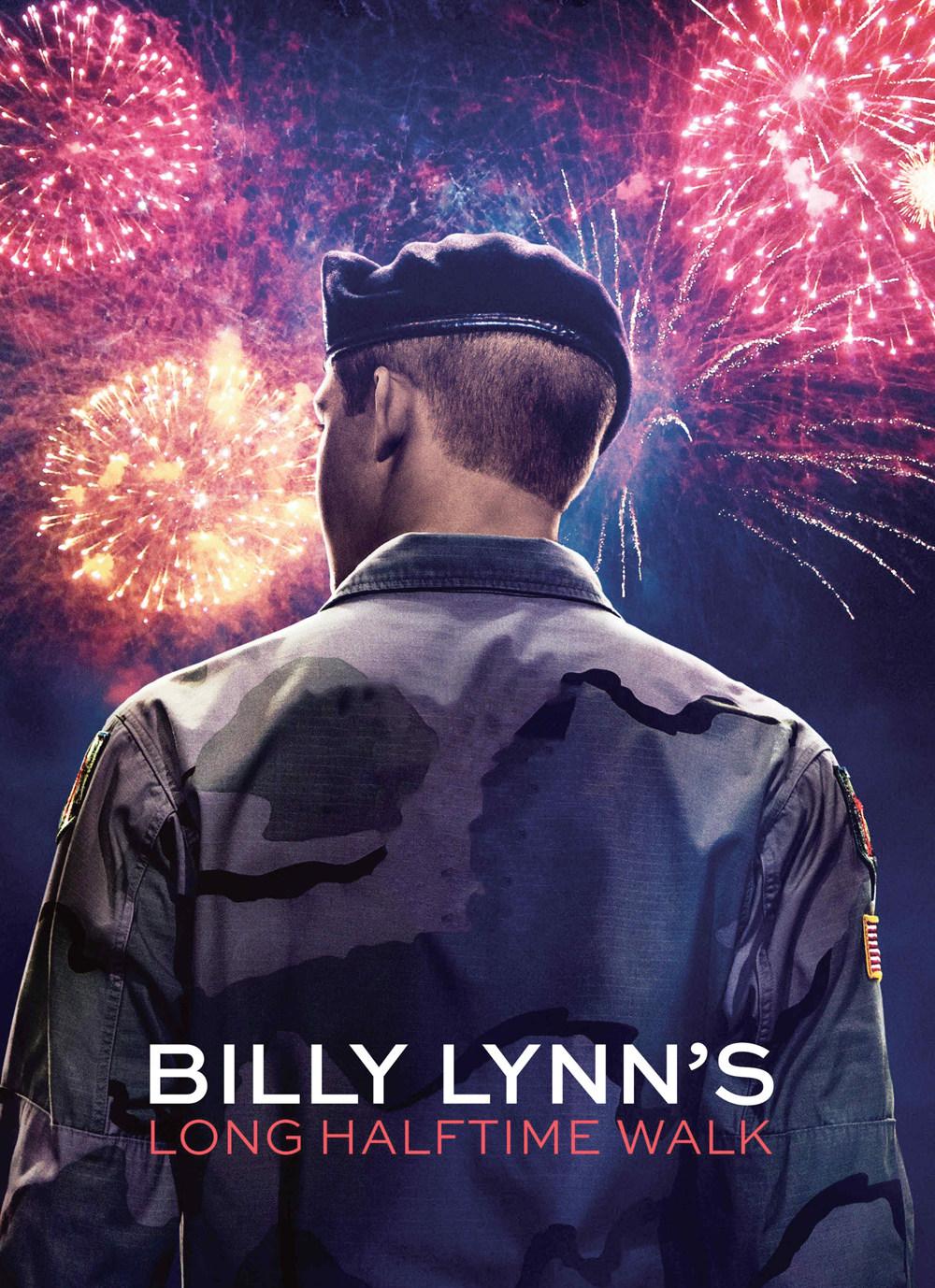
關于“電影是什么”這一問題,60多年前,安德烈·巴贊從“攝影影像的本體論”“電影語言的進化”“其他藝術形式與電影”等方面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并佐以案例進行分析。國內電影理論界對該問題的研究,很長一段時間都聚焦于電影的社會功能,沒有真正涉及“電影本體”的討論,直到1979年,“電影理論開始謹慎地轉向對電影自身規律的摸索”。[1]進入21世紀,國內理論界從美學、技術、產業等諸多方面入手展開涉及“電影本體”問題的討論:由“魔幻影像的思考”[2]到“綜藝電影的反思”[3],從對“影院本體”[4]到對“電影制作放映”[5]的考察,再到“技術沖擊”[6]、“媒介考古”[7]視角下關于電影本體問題的思考,眾多研究者都圍繞“電影是什么”這一問題闡釋了各自的觀點。D.N.羅德維克在《電影的虛擬生命》[8]中將這一問題轉化為對歷史的回望和對未來的前瞻,從承載電影的“物”的維度探討“新”媒介沖擊下電影本體是否存在。理論界關于電影本體的討論從未停止也不會停止,本文從馬歇爾·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出發,探析電影在當今技術革新背景下的變與不變,以期進行一次對電影本質屬性的探尋。
一、突進與改造:電影感官革新的兩種路徑
電影是視聽的藝術,縱觀電影的歷史,一路上都在進行著視聽革新。1895年盧米埃爾兄弟的活動電影機將電影這一新奇事物帶到人們面前,1927年《爵士歌王》的出現(艾倫·克羅斯蘭,1927)標志著聲音正式進入電影。此后,不論是面對其他媒介的沖擊還是自我更新的需要,電影始終在視聽上不斷拓展邊界,尋求新的可能。不論是從黑白到彩色的跨越式發展;還是IMAX放映系統對視聽效果的改良;乃至具體作品對于視覺呈現的形式探索:《快樂結局》(邁克爾·哈內克,2017)中社交媒體豎屏畫面展示,《我不是潘金蓮》(馮小剛,2016)中由方到圓的畫幅轉變,《解除好友》(列萬·加布里亞德茲,2014)、《網絡謎蹤》(阿尼什·查甘蒂,2018)中全片“桌面視點”的嘗試。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電影對感官的革新已不再局限于視覺和聽覺,而是呈現出追求多重感官體驗革新的趨勢,實現這種革新主要有以下兩種路徑。
第一種路徑是突進式的,它以技術變革為支撐,不斷推進觀眾在觀影時的沉浸感與超真實感官體驗。麥克盧漢“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論斷不是簡單地將媒介視為人的“體外器官”,它們在服務人的同時也深刻影響著人類的思維方式并反作用于現實。“西方人從讀書識字的技術中獲得了行動時不必反應的能力……在電力時代,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靠技術得到了延伸。”[9]電影作為媒介,由2D到3D乃至4D的升級,是對身臨其境感官體驗的不斷追求。“3D電影……從電影的本體特征來講,就是將原本在平面上通過傳統透視關系模擬表現三維世界的方法,革新成為了現在讓觀眾能真實感受到三維空間的方法。”[10]4D電影在3D電影的基礎上通過晃動座椅、噴水、噴霧等環境特效增加了觸覺、嗅覺等感官體驗。技術帶來的突進式的對感官的革新,其目的是令觀眾在觀影時達到更深層次的沉浸。3D版《頭號玩家》(史蒂文·斯皮爾伯格,2018)令觀眾與主角一同沉浸于虛擬現實打造的“綠洲”探險;4D版《中國機長》(劉偉強,2019)則讓觀眾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模擬空難。影院之外,流媒體推出的互動敘事電影,也在形式創新中召喚著觀眾的“深度參與”:在Netflix平臺播出的《黑鏡:潘達斯奈基》(大衛·斯雷德,2018),電腦端的觀眾可以通過按鍵來決定主角的命運和劇情走向,雖然這是一種無法逃脫創作者預先設定的“虛假參與”,但其與3D、4D電影一樣,均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觀眾的沉浸感,實現了對電影感官的革新。
每一次技術變革不單為觀眾帶來了更加舒適、新奇的觀影體驗,同時也讓創作者不再滿足于復刻與還原現實,他們開始探索那些觀眾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的體驗。李安通過《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2016)開啟對3D、4K、120幀的影像探索,實現了電影在延伸感官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感官的目的。高清晰度、高幀率下,觀眾可以清晰看到平時不易察覺的人物微表情,現實生活中肉眼無法捕捉到的火花噴濺過程也在電影中得到還原與呈現。電影畫面的特點也在強化感官的技術變革中發生變化:畫面中的細枝末節得到充分展示,傳統電影講求縱深的主次分明變成了毫發畢現的“等量齊觀”。在技術的加持下,電影由復制現實走向了超越現實,更清晰的人物、更豐富的畫面細節,再加上激烈的動作場面,電影對視覺感官的強化,讓觀眾經歷了多重奇觀下的超真實冒險。
第二種路徑是改造式的,以現有技術為基礎,通過對技術運用形式的創新達成對觀眾感官體驗的刷新。正如學者尹鴻在論述電影敘事技法時所言,“世界上沒有被使用過的技巧幾乎沒有了,但藝術的能力就在于我們永遠能讓技巧花樣翻新。”[11]與此類似,跨越式的技術變革不會常常發生,但對現有技術進行花樣翻新的應用同樣也能達到更新觀影體驗的目的。手持鏡頭拍攝并不是一種新的拍攝技術或手法,但婁燁在《風中有朵雨做的云》(2018)中將這種手法運用到極致。電影首映時“嘔吐袋伴手禮”似是噱頭卻也是部分觀眾的必需,大量的手持晃動長鏡頭在灰蒙蒙的城市穿梭,迷幻眩暈,雖是2D電影卻達到了4D電影的觀感。在某種程度上,長鏡頭對普通觀眾來說是一種折磨,而畢贛在《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電影放映時間過半時,以戴3D眼鏡這一動作再次向觀眾強調——要“入夢”了。戴3D眼鏡“入夢”的儀式感不僅是一次指涉“元電影”的嘗試,更召喚著觀眾跌入創作者營造的雙重夢境,經歷感官與情感的浮浮沉沉。再如前文所提到的社交媒體豎屏、由方到圓的畫幅、以及攝像機視點的轉變,都是通過對現有技術進行形式創新帶來的對電影感官體驗的影響。
如果說以技術變革為支撐的感官革新類似于“硬件升級”,那么通過對現有技術進行運用形式上的改造所達成的感官革新便接近于“軟件更新”,但不論是突進還是改造,電影都在技術的支持下實現了多重感官革新,它在召喚觀眾沉浸的征途上又前進了一大步。由此,觀眾從觀看逐漸轉向體驗,電影也逐漸從復制走向生成。
二、“熱”與“冷”:電影媒介屬性的重新劃分
冷媒介與熱媒介,是麥克盧漢橫向比較報紙、電話、廣播、電視、電影等媒介調動受眾感官參與程度的不同提出的理論,雖然曾因論述與劃分的不夠明晰而備受爭議,但關于冷熱媒介劃分的基本原則卻值得我們在審視媒介時借鑒:“熱媒介只延伸一種感覺,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熱媒介要求的參與程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參與程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12]按照這一原則,電影被劃分為熱媒介。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如今的電影較之當年已發生了巨大變化,關于電影是熱媒介的屬性劃分似乎也需要重新界定,我們再也無法籠統地將它直接劃進熱媒介的子集。
沿襲是否需要受眾調動多種感官參與填補信息的原則,電影這一曾經的熱媒介如今需要在內部被劃分為“熱電影”與“冷電影”。從敘事層面來看,“熱電影”的故事往往清晰明了,無需動腦;因此,《人在囧途之泰囧》(徐崢,2012)等歡樂而通俗易懂的喜劇片可劃歸為“熱電影”。從技術層面來看,3D、4D、4K、120幀甚至VR等技術加持下的電影不斷推進“真實感”并給觀眾帶來多重感官刺激,看似調動了觀眾的多種感官,但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多重感官體驗并非是觀眾主動調動并發揮想象參與信息填補的,而只是一種物理意義上的被動刺激。“生理喚醒,嚴格意義上,并不屬于自愿行動。”[13]觀看4D版《中國機長》時顛簸的感覺主要來自座椅的晃動而非視覺觸發的想象;3D、4K、120幀的《雙子殺手》(李安,2019)無需觀眾費力去辨認和思考,畫面充盈到分毫畢現,觀眾再也無需填補任何信息……因此它們屬于熱電影。
“一切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形式,與其最終呈現的形式截然相反,這條原理是一條古老的原理。”[14]好萊塢大片通過賽車美女、超級英雄、視覺奇觀打造出一個個精致刺激的美夢,令“熱電影”的風潮席卷全球。我們縱然可以在“熱電影”中縱情笑淚,感受刺激,也無法否認這些電影所帶來的情感宣泄作用。但需要明確的是,這種感官強化式觀影,看似是“人的延伸”,實則是“人的退化”,借用麥克盧漢的話說便是“人的自我截除”。在這些模擬真實或“超真實”的技術輔助下,觀眾無需調動任何感官與想象,全部的感官刺激由技術與設備操控。正如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所說,“工業社會具有一些工具,可以把形而上的東西轉變成形而下的東西,把內在的東西變成外在的東西,把心靈的探索轉化為技術的探索。”[15]技術加持下的沉浸式與超真實觀影體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觀眾感官的封閉,其本質是技術的增強而非人的增強。技術暴政控制下的“熱電影”,讓觀眾淪為“被動人”。看似驚心動魄的觀影體驗,不過是外在環境與特效作用的結果,主動的情感體驗退回為被動的應激反應。
然而,這樣的批判并非代表“熱電影”一無是處,而是這種“熱”應與放映環境和觀眾能力相匹配,全社會影院系統的更新與完善以及觀眾對于新媒介技術的理解與應用在感知電影之美中同樣重要。只為售出高票價而粗糙轉制的偽3D、4D影片是對電影和觀眾的雙重傷害;而在AR、VR等新奇的交互敘事體驗中,觀眾對視角和敘事機制的理解與把控至關重要。否則,觀眾對電影的信息獲取和美學感知都將大打折扣。
與“熱電影”相對,“冷電影”在敘事層面上往往結構較為復雜,或者令人難以立刻明白故事原委,也即人們常說的有“燒腦感”。因此像《信條》(克里斯托弗·諾蘭,2020)這樣的電影,雖有大量刺激的動作、場面奇觀,卻需要觀眾高度集中注意力、調動感官補充大量信息才能理解,通常可劃歸為“冷電影”。另一方面,“冷電影”脫離了新技術帶來的“超真實”與“強刺激”,它們甚至是悠長、緩慢的。在這類電影中,觀眾對電影氣質、情感的體味再也沒有外界的物質輔助,需要主動調動起全身心才能浸入電影中的世界。《路邊野餐》(畢贛,2015)中慢悠悠的摩托車和夢幻的霧;《山河故人》(賈樟柯,2015)中沈濤在飄雪冬日里的起舞;《無問西東》(李芳芳,2018)中課堂上的靜坐聽雨;《六欲天》(祖峰,2019)中長沙夏日的悶熱潮濕;《地久天長》(王小帥,2019)中劉耀軍與王麗云時常放空的神情……它們均展現出“冷電影”的靜觀之力。“視覺的使用是由過去所看見的形象、個人體驗、記憶和意圖塑造的,如同由我們眼前的物理形式和物質性空間塑造一樣。”[16]在這些靜觀電影或靜觀場景中,聽到雨聲感到的涼,通過天氣所透露出的人物情緒,與電影人物的情感共鳴,均需要觀眾積極調動自身感官并發揮想象來達成。如果說,“熱電影”帶著一份殷勤和事無巨細;那么“冷電影”則多了一分神秘與高深莫測。
就如冷媒介與熱媒介在不同時代和語境下劃分的相對性與可變性,關于“熱電影”和“冷電影”的劃分也并非非此即彼的鐵板一塊,這僅僅是就媒介與電影都急速發展的背景,嘗試提出的一種對電影媒介屬性重新劃分的可能,同時也是我們反思電影的一個切入點。
三、回歸本體:生成“中間空間”的電影
刻印在膠片上的是電影,被數字化存儲在硬盤中的也是電影;在電影院里放映的是電影,在藝術館屏幕、電視、電腦、手機中播放的也是電影;在技術飛速發展、形式千變萬化的時代,我們如何定義電影,電影又如何確立自身?
莫里斯·梅洛-龐蒂和阿蘭·巴迪歐分別從心理學和哲學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梅洛-龐蒂認為“電影不是被思考的,而是被知覺的;”[17]巴迪歐則認為“藝術作品自己在思考,并且生產真理。”[18]他們看似截然相反的觀點,卻共同指明了電影的本質屬性。在梅洛-龐蒂看來,觀影的時刻具有決定性作用,他用“左手觸碰右手”的例子闡明了主客體之間并非截然分明的特質,主客體接觸的時刻,彼此交互的“混沌性”由此生發。電影具有這樣一種特性:它向觀眾訴說的同時又被觀眾感知。電影的訴說與觀眾的感知發生作用之處便是梅洛-龐蒂所言的“之間的世界(intermonde)”,即“中間空間”。它是一個非物質性的空間,在“觀影”這一動作發生的時刻被激活。巴迪歐認為電影與哲學具有某種同構性,都是從斷裂之處建立起新的關系。因此,兩人的觀點共同指向了電影作為媒介的本質屬性,即讓不同的人、事、物產生聯系,產生聯系的瞬間,“中間空間”便生成了。
首先,諸多電影運用“中間空間”架構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無敵破壞王》(瑞奇·摩爾,2012)中的游戲世界讓來自不同游戲的角色碰面;《無敵破壞王2:大鬧互聯網》(菲爾·約翰斯頓/瑞奇·摩爾,2018)讓來自游戲機時代的游戲角色闖入當下的互聯網世界;《勇敢者游戲:決戰叢林》(杰克·卡斯丹,2017)和《勇敢者游戲:再戰巔峰》(杰克·卡斯丹,2019)將來自不同時代的玩家集合到同一游戲中;《頭號玩家》則用虛擬現實技術開辟出一個幾乎平行于現實世界的游戲世界。這些電影不僅將歸屬于不同世界的人物聚合到一起,碰撞出新奇好玩的故事;同時,那些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無法親身進入的世界全部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現,非物質的“中間空間”通過電影獲得了“虛擬肉身”。
其次,觀眾在觀影時所激活的“中間空間”,是電影與觀眾進行對話并完善自身的場域。電影從被觀看的那一刻起,才算實現了自身的完整性。“人的經驗賦予了性質某種情感意味,所以一旦我們把一個性質放回人的經驗之中,那么這個性質何以能夠和其他那些原本與之毫無關系的性質發生關聯也就變得開始能夠理解了。”[19]雖然這是通過知覺探尋“物”與“我”之間的關系,但知覺具有破除外在干擾認識事物本質的恒常性,可破除技術帶來的迷幻與狂熱,從而抵達電影隱藏的本質屬性——生成“中間空間”,由此可以反觀電影訴說與觀眾感知之間的關系。電影訴說與觀眾感知的結合處所激活出的“中間空間”的大小,不在于電影所展現的故事與觀眾經驗或經歷重合度的高低,而在于電影的情感內核獲得觀眾的共情與共鳴的多少。2021年春節檔上映的《你好,李煥英》(賈玲,2021)采用了不尋常經歷加普遍情感的組合,收獲了高票房和好評。“母親車禍去世”屬于與觀眾重合度較低的經歷,但電影中所蘊含的母愛與母女情卻是令多數人都會產生共鳴的情感。因此,電影訴說與觀眾感知激活的“中間空間”幾乎取得了所有解中的“最大公約數”。反觀一些國產青春片飽受詬病的原因,是電影中的經歷與情感均未引起觀眾的共鳴。夸張的情節、失實的造型、矯揉造作的臺詞不僅與大部分觀眾的經歷無法對接,邏輯不嚴謹的敘事也令本就懸浮的愛情主線難以引起觀眾的共鳴。經歷與情感的雙重陷落勢必壓縮電影與觀眾對話的“中間空間”。
“熱電影”往往通過技術的突進不斷強化觀眾的感官體驗來拓寬“中間空間”;“冷電影”也通過手法與技巧的創新在兼顧藝術表達的同時試圖在“中間空間”與觀眾有更深層次的共鳴。雖然技術突進帶來感覺的無所不包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觀眾知覺的不信任,并存在令觀眾走向“惰性”的風險,但不論是技術的突進還是對其創新性的應用,都是對“中間空間”的守衛與維護。
需要明確的是,“中間空間”并非一體化的“大集合”,而是具有個體差異性的“小子集”,它對接不同的感知與體驗。不同的觀眾被同一部電影感動,但每位觀眾所動情的點各不相同;不同觀眾對同一部電影的理解也千差萬別。電影在向不同人訴說的同時,也通過“中間空間”獲得了不計其數的“分身”,這些分身是構成電影本質的靈魂。因此,不論未來電影的形式如何變化,因為“中間空間”的存在,電影擁有了突破物質載體實現永生的可能。
結語
從媒介視域對技術革新背景下的電影本體問題進行考察,突進與改造是其革新感官的兩種路徑;在對電影媒介屬性的重新劃分中,也完成了一次對電影與觀眾關系的反思;而不論技術如何變革、電影形式如何變化,電影作為媒介最本質的屬性是生成“中間空間”,這一本質屬性不僅是催生新穎故事的錦囊妙計,更是電影與觀眾獲得聯結并完善自身乃至超越物質載體獲得永生的關鍵。就如“熱電影”需要配套設施與觀眾對新技術的了解,“冷電影”需要觀眾全方位調動自身感官,在技術不斷革新、技巧和手法被不斷翻新的今天,“中間空間”的拓展與維護也需要創作者與觀眾雙方的努力。電影作為媒介,聚合了不同維度的人、事、物;電影作為“綜合”的藝術,令萬事萬物互聯。
參考文獻:
[1]胡克.中國電影理論史評[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219.
[2]王宜文.來自魔幻影像的思考:電影是什么?[ J ].中國圖書評論,2008(6):16-21.
[3]趙正陽.本體論視域下的綜藝電影[ 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5(07):86-90.
[4]尹鴻,袁宏舟.影院性:多屏時代的電影本體[ J ].電影藝術,2015(03):14-18.
[5]陳晨.數字時代電影的再認識:論電影制作與放映的改變對觀眾感知的影響[ J ].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6):6-13.
[6][10]付宇.3D電影:本體美學的改變與視聽語言的變革[ J ].電影藝術,2012(05):54-58.
[7]繆貝.“電影是什么”——一次電影媒介觀的歷史考察[ 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0(09):13-22.
[8][美]D.N.羅德維克.電影的虛擬生命[M].華明,華倫,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1.
[9][12][14][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21,51-52,66.
[11]尹鴻.當代電影藝術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11.
[13][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M].周娜,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41.
[15][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M].李小兵,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89.
[16][英]凱·安德森等主編.文化地理學手冊[M].李蕾蕾,張景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361.
[17][19][法]莫里斯·梅洛-龐蒂.電影與新心理學[M].方爾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25,30.
[18][法]阿蘭·巴迪歐.論電影[M].李洋,徐珍,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