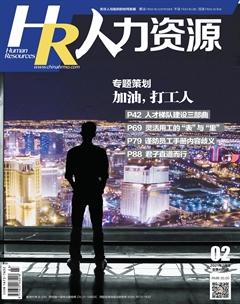互聯網打工人的職業之重
周琪

“要去最新的領域就業。”依稀記得幾年前,一位資深的HR針對年輕人的就業方向,這樣說道。不可否認,年輕人想要有更好的歷練、更廣闊的晉升空間,新興行業是最佳的選擇。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年輕人涌入,在繁華的寫字樓里,每天都有各種公司誕生。它們在一群奮斗者的打拼下做大做強。無數個凌晨兩三點鐘,快車司機長龍似的排在寫字樓下,將這些疲憊的打工人護送回家。我們沒有辦法統計,到底有多少年輕人幾乎每天都是后半夜才回到出租屋。不過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有同樣的感覺——自己就像是一顆螺絲釘,已然職業倦怠,想要擺脫現狀。
漲工資后裸辭了
在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工作的張華是朋友眼里的工作狂。大學畢業后,張華就選擇到互聯網公司工作,他當時的想法是,互聯網公司的工作節奏快,交流氛圍自由,有想法就可以去做。可是,在互聯網公司工作了三年多后,他正式裸辭了。
可怕的工作時間是選擇裸辭的首要原因。從每日工作8個小時延長到了10個小時,然后是12個小時,后來是14個小時……同事勸他:“租的房子千萬不要距離公司太近,不然你會更晚下班。”而伴隨這樣的工作狀態,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鮮花都枯掉了;金魚換了一茬又一茬。他錯過了長輩的九十歲壽宴,錯過了中秋團圓之日,錯過了七夕情人節約會,甚至外婆去世時,他也未能回去看最后一眼。母親傷心地說:“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嗎?”
其實,工作真的很重要。對于多數成年人來說,只有有了工作,才配擁有很多東西,比如房子、車子、穩定的生活。但同時,很多人也因為工作失去了很多東西。趕路不忘看風景,可許多人的步子邁得太快太猛,從而錯過了太多的風景。
慢跑一直是張華緩解壓力的一種方式,但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即便在休息日,張華連慢跑的力氣也沒有了,只想在床上躺一整天,可是一直睡覺也無法恢復精氣神。后來他發現喝紅酒能讓自己的睡眠好一些,于是他變本加厲地喝紅酒。由于長時間加班導致免疫力下降,一年后,張華竟患了輕度糖尿病。身邊的朋友問他:“你不要命了嗎?你拼命工作賺的錢夠支付你治病嗎?”張華無言以對。
與同一座城市的朋友相聚的機會越來越少,即便是那些經常靠微信聯系的朋友,有時也被工作的信息淹沒了。沒有娛樂、沒有朋友、沒有健康,離開工作,張華竟不知道該做什么。張華開始質疑:這樣下去,三年之后我會是什么樣子?一定很糟糕吧。一次張華陪客戶吃飯,竟喝得不省人事,倒在路邊后半夜才醒過來。躺在霓虹閃爍的路邊上,張華大哭起來,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問自己:這樣的生活到底為什么?
可是互聯網公司的節奏就是這樣快。流量就是一切,你錯過了一波風口,就意味著失敗甚至死亡。他與領導溝通多次,領導也很無奈。因為每一個人都背負著沉重的業務壓力。想要改變現在的工作狀態,最好的選擇就是離開。
對于是否能夠接受加班這個問題,多數職場人的答案一直都是可以接受因工作需要的必要加班,不接受無意義的加班。可是,對于互聯網公司尤其是規模較大的互聯網公司來說,員工每天在公司工作12個小時以上似乎是一種常態。
長時間的過度消耗,必然會帶來身體素質的急速下降,無法維持正常的可持續發展。如果要靠員工長時間在公司的消耗來維持公司的高速發展,即使給予看上去令人羨慕的工資,恐怕也只是鼓勵員工用自己的身體掙錢。反過來,掙得的錢能否支付因透支身體而患上的職業病,答案是否定的。
互聯網行業的朝氣蓬勃對年輕人有莫大的吸引力,可是這個行業的職業年齡又是多久?年輕人可以憑借年輕這個本錢,拼命加班,可是過了30歲、35歲、40歲后,又該怎么辦?一旦在這個年齡無法繼續透支身體,那么未來幾十年的職業通道又在哪里?雖然張華在年底之前就晉升為項目總監,工資也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他還是選擇了裸辭。
如今,遠離互聯網公司沉重壓力的張華,終于獲得了久違的平靜與舒適。他會看一些專業書籍來提升自己,到了周末,會有計劃地進行一次短途旅行。即便因為疫情不能出行,張華還能在家里看看電影、種種花、做做飯,經常與久不聯系的朋友視頻交流。他還選擇用文字記錄這些生活的細節,這不是為了給誰看,而是要給自己留下一些記憶,同時不斷提醒自己:生活就在這里。至于下一步的工作計劃,張華還是打算放空一段自我,再重新出發。
焦慮的年輕打工人
張華輕輕地裸辭了,不帶走一片云彩,然而,卻無法改變互聯網行業的工作節奏。在互聯網公司的打工人們依然在不停地忙碌、加班、沖業績。充斥在互聯網行業的焦慮感一刻也未能停止。在龐大的人事系統里,打工人只能靠跳槽實現升職加薪,靠“論資排輩”在用人單位“升級”的規則,在人才流動頻繁的互聯網企業并不奏效。更何況,在一些互聯網公司還存在殘酷的“35歲定律”,如果你35歲還沒有成為足夠高層的管理人員,那么面臨的下場就可能是被淘汰。
很多企業會通過塑造校園化環境來構建起自己的公司文化——內部擁有品質不錯的食堂,同事之間互稱“同學”“兄弟姐妹”,公司還會通過組織豐富多彩的集體活動來建設團隊,讓員工們對企業有一種歸屬感。這些做法自然有其值得褒揚之處。從校園到公司,人際關系依然簡單,年輕的畢業生不會感到太多不適,可以像完成一份作業一樣來完成工作任務。
但是,完全依靠這種類似校園的組織框架來實行管理是不現實的。一個人在學校里,唯一的身份就是學生,一切行為都要遵循學生的身份特征。而進入社會以后,他就必須接受自己的多元身份——于公司而言是雇員,于戀人而言是未來的依靠,于房東而言是繳納租金的房客。那種試圖以類校園環境框住員工,而缺乏對員工其他身份角色考慮的企業,本質上也是對人才的不尊重。
最近,“深圳女孩”的段子火了。兩個深圳的女生到外地朋友處做客,主人問她們在深圳的生活怎么樣,女孩說:搞錢。有人批評這樣的段子是地域性的人設販賣,但在年輕人的眼中,“深圳”就是一個為理想而打拼的精神坐標。“搞錢”不是拜金,它也是對創造價值的一種直白描述。
因此,讓年輕人看到上升的空間,看到打工人的前景,才能有效釋放他們奮斗的焦慮。相比父輩們細水長流的財富積累,這代年輕人的財富觀也需要被傾聽。住房問題、子女教育問題和未來贍養老人的問題,都對年輕人積累財富的能力提出要求。但年輕人并不愿意被數字上的財富約束。比如,如果租房能夠滿足居住需求就未必要買房,教育“內卷”也愈發成為社會深刻反思的現象。年輕人更希望把財富使用到他們真正認同的領域,而這就要求企業能為他們消除引發不安全感的后顧之憂。
上班時拼命工作,下班時徹底放松,節假日完全與工作切斷,這也是年輕人所期待的生活模式。這也本該成為一種被充分認可的價值坐標。因此,在處處是焦慮的工作氛圍中,“搞錢”對于年輕人來說并不可恥,只有搞到了足夠的財富,才有資格談詩和遠方,這才是一個正常社會應該有的樣子。
工作的意義在何方
曾幾何時,工作似乎是一件不需要懷疑的事情,每天上班,不管做什么,數十年如一日,一直到退休。隨著時代的變遷,生活方式更為多元,生活節奏逐漸加快,互聯網沖擊著勞動的分工與合作,人事流動不斷加劇。工作對于個體的意義,亦不再像從前。如果對于前幾代的人來說,工作是一趟長途火車,那么,對于現代的年輕人而言,工作或許更像是地鐵,坐幾站都可隨時下車。
這樣的轉變,是年輕人自我意識越來越凸顯的一種表現。其一,大家不愿讓自己淪為一個機器人,每天在規定的條條框框中按部就班地工作;其二,年輕人希望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價值,能夠體會到成就感;其三,大家期待自己的價值觀能夠被尊重,不被領導強迫做事,不做一些無用功,尤其是形式主義的事務。
這些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凡事過猶不及,自我意識越來越凸顯,也可能導致“入一行恨一行”。盲目跳槽后,仍然會陷入迷茫,甚至最終懷疑自我。那么,怎樣去理性分析工作中涉及的各類因素?如何面對工作中的困惑?如何更好地平衡自己對于工作的心態呢?
做一件事情,有兩個最基本的維度,那就是“快樂+意義”。有些事情可以為自己帶來快樂,比如打游戲、品嘗美食、旅游、購物、看電影等;有些則可以為自己帶來意義,比如看書、寫文章、練琴、跑步等。當然,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每個人的標準會有不同,對某些人來說快樂的事情,對他人而言可能是痛苦的;對部分人來說有意義的事,于其他人而言可能毫無價值。
工作中的快樂可以來源于多方面,最常見的有:自己真心喜愛,對行業真正感興趣;“錢景”光明,報酬豐富;工作內容清閑,不費力;社會大眾認可度高。同樣,工作也能帶來多重意義,包括有價值感和成就感,可以積累經驗、不斷成長,自己具有主動權、能夠被尊重,可以幫助他人等。
快樂和意義可以把工作分為四類:快樂且有意義的事情;快樂但沒有意義的事情;不快樂但是有意義的事情;不快樂且沒有意義的事情。我們會發現,魚和熊掌難以兼得,所謂“錢多活少離家近”的工作幾乎沒有。就算有,長期這樣下去,在意義方面也可能受到很大影響。
因此,大部分工作,實際上是在后三種情況間做出選擇。快樂但沒有意義的事情,往往只能給人帶來短期的愉悅感。長遠來看,這樣的工作只能讓年輕人虛耗時光,無法累積行業知識、提升職業技能,必然會影響未來的職業發展。
日常工作中,也不乏不快樂但是有意義的事情,比如讀一本枯燥的專業書、熬夜做PPT、寫一份產品報告等。這類事情雖然做起來比較難,不太容易堅持,但恰恰是在專業層面的打磨與深耕,為自己打下堅實的發展基礎。不快樂且沒有意義的工作,可能是每天忙于應付領導和同事不合理的工作要求。即便自己不喜歡、不贊同,也只能一味地忍讓和迎合。
如果某項工作對于自己確實是不快樂且沒有意義的,那就應當及時止損,早點離開。否則,不僅會讓自己的事業停滯不前,還容易引發抑郁狀態等。如果一份工作做起來不快樂但還是有意義的,那可以不著急跳槽。快樂與否并非恒定不變的狀態,有時候,人會因對某一領域了解更多而進一步產生興趣。因此,不妨給自己多一些探索時間,積累經驗、培養興趣,為未來更好的發展奠定扎實的物質基礎和心理基礎。
當然,利用這一標準衡量工作選擇的前提是對自我偏好有著清晰的認知。若是不清楚自我特點與目標定位,不知道自己應該承擔何種責任,就很難從工作中體會到真正的快樂,也不能感受到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因此,年輕人應當在工作中多體驗、多進行自我探索,明確自身的優劣勢和熱情所在,避免在不停地換工作之后陷入迷茫狀態,隨波逐流地工作。
互聯網公司員工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讓許多996、007的打工人忽覺一驚。年輕人的猝然離世,觸動了某些深層次的焦慮與不安。前幾年一首《感覺身體被掏空》的歌曲,以一種海派幽默的氣質,描述了都市奮斗青年的身心疲憊感。近段時間,網友通過比較幾座城市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流調情況,又將觀察視野引向追求安逸還是“多打一份工”的討論。
可以說,這代年輕人不排斥奮斗,甚至主動擁抱奮斗。相比他們逐步接觸市場經濟的父輩,這一代年輕人更熟悉市場規則,也深刻地領悟到付出換取回報的樸素經濟學常識。不幸去世的互聯網公司女員工,最后的朋友圈簽名是為公司“守邊疆”,令人唏噓感慨之余,也不得不承認新興互聯網產業對年輕人充滿吸引力。多數年輕人并非懼怕奮斗,而是擔心自己的奮斗被“工具化”。只有讓奮斗者看到遠方的愿景,他才能踏實篤定地邁出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