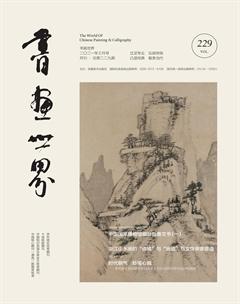我筆下的眾生相



馬凌燕
馬凌燕,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先后獲學士、碩士學位,專業方向為中國花鳥畫創作與研究,師從吳冰教授。
我喜歡動植物,它們真實、純粹、天然,但更多的時候我覺得它們可憐,因為人們很少能理解它們的訴求。相較于植物,動物更容易得到我的關注。尤其是常見的小動物,你可以很容易地和它們互動,雖然有時被它們誤傷,但那又有什么關系呢?和動物們互動的美好心情可以持續很久,有時甚至能撫慰受傷的心,讓人變得柔和細膩。自然地,我的很多創作跟動物相關。
《和平頌》是我第一幅關于動物的創作,對我來說意義不尋常。《和平頌》這幅作品,從構思、收集素材、起稿、設色等直至正式展出歷時半年。上半場的構思極盡心思,反復推敲,下半場的體能考驗讓我疲憊且快樂。無悔半年多的努力,無悔為動物們發聲,因為想到立意、使命、擔當。
徐悲鴻有詩曰:“天地何時毀,悵然歷古今。平生飛意動,對此一沉吟。”藝術家面對天地蒼生,感懷傷情,為萬物寫照。我本孱弱之軀,學業未竟,初涉藝途,豈敢效前輩大師妄談大愛?然每觀動物們被監禁、戲耍以取樂,或被剔骨、鑿牙以買賣,或被剝皮、取膽以牟利,此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是喪盡天良、慘絕人寰的罪惡交易!每慮及此,便心如錐剜不能自已,以作品《和平頌》為眾生呼號鳴冤,我之愿也!
《和平頌》立意保護動物,眾生平等。出于情感和信仰的考慮,保護動物,倡導生命平等、和諧,是我迫切想要表達的。畫面中動物們正在合力演奏反對殺戮,渴望和平與愛,倡導眾生平等的、“真正”和諧的曲子。畫面物種的選取主要是普遍受到人類殺戮迫害的幾種,如貂、大象、熊、穿山甲、海豚、猴子等。所選取的動物形象全部進行擬人化,進行大量的重復,用演奏時動作表情的一致象征它們渴求平等愿望的一致。動物們姿態統一,表情一致,以此烘托嚴肅的氛圍。
作品為豎構圖,分為上、中、下三部分,分別為飛禽、走獸、水族。我希望盡量多地表現出不同類型的動物,將天上陸地海洋集結在一幅畫面上,視覺中心集中在中層陸地上的動物代表們。它們之間的安排相對疏松,中間一個指揮,四周選取體形稍大些動物,如大象、犀牛等。之后一排排的動物按體形依次排列,形成勢眾的感覺,靠前的有貂、兔、狐、猴,依次為羊、鹿、牛、熊等。它們神情專注,或演奏或吟唱。畫面整體色彩基調選用暖紅色調,動物身上的顏色統一在整個大的色調里。從中間到上下會有一個顏色上的漸變,中間對比最強烈,繼而從顏色上突出主題。在造型上采用了傳統的勾線,高古游絲描如春蠶吐絲。色彩的染法是高染、低染結合,技法豐富。基于朦朧意境的需要,其中傳統大型動物的輪廓線加以虛染,使之看上去虛幻而朦朧,如月光之韻,整體來說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的工筆畫。其中大象借用了敦煌壁畫中的剝落效果,使畫面看上去更加豐富。
2020年的疫情讓人們措手不及,停工停產或許能讓平時忙碌的人們放慢腳步來反思這場疫情的諸多原因。記得在疫情的初期,各種關于蝙蝠的文章或報道鋪天蓋地,很多人憤憤不平,恨不得消滅地球上所有的蝙蝠。我心想:這難道不該是那些過度侵害蝙蝠的人類之錯嗎?蝙蝠何其委屈啊!所以我創作了《我們》這個系列的作品來延續保護動物的立意。在《我們》這個系列作品里,不同動物的形象各不相同,人們可以輕松識別其形象。我試圖將它們的形象表現得俏皮可愛,比如在一些動物臉頰加上腮紅,就像鄰家萌寵般毫無兇煞之氣。每個形象的重復、排列,為畫面帶來一種強烈的形式感。在整個創作過程中,關于繪畫本體形式語言的運用也圍繞立意而展開,在保留了傳統以線造型的基礎上,減弱了線條在傳統程式中提、按、頓、挫的特征,用色更加主觀,色調浪漫柔和。
從《和平頌》到《我們》,從以人的視角為眾生吶喊到打破人與動物的界限,表達出強烈的眾生平等的愿望。“我們”既以被迫害的動物們的口吻表達弱者的訴求,同時又表達了作者與動物們以及其他一切生靈站在一起的立場。
藝術創作中所呈現的無論是崇高還是優美,都難以脫離藝術家對周遭的現實關懷,這現實關懷歸根結底來自對生命的愛。這生命是眾生,這愛是博愛。
約稿、責編:徐琳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