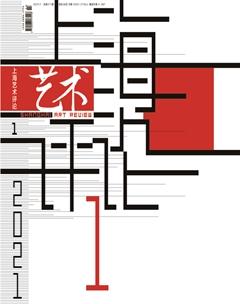尋找扶貧題材戲曲創作的內生力量
秋實
對于戲曲創作者而言,扶貧題材是熱點,也是難點。從近年涌現的扶貧題材劇目數量來看,它的熱度有增無減,且涉及的劇團之多、覆蓋的劇種之廣,遠在同期其他題材之上,然而這一炙手可熱的題材卻讓不少劇作家望而卻步。究其原因,多在于面對短時間內大量涌現的“同題”創作,要實現扶貧題材的“內化”,尋找到獨特的切入視角,使之從眾多同類題材作品中脫穎而出,即使于那些成熟的劇作家而言,也并非輕而易舉的事。
“內化”題材,是扶貧題材戲曲創作的必經之路
扶貧,首先是個社會學層面的概念,其次才是戲曲創作的一個題材類型。作為社會學概念的“扶貧”,其內涵和外延無疑是復雜而開闊的,它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倫理等多個方面,是國家政策層面大力推動并致力解決的宏大的社會命題。作為戲曲題材類型的“扶貧”,同樣具有廣闊的能指空間,但戲曲舞臺的特殊性,要求劇作家必須把這種廣闊的“能指”轉換為具體的“所指”,換言之,劇作家要用明確的“所指”將觀眾引向扶貧題材深層的能指空間,通過作品主旨內涵的建構,引導觀眾對社會、時代及人生進行更為深刻的思考,讓他們在收獲審美享受的同時,得到心靈的啟迪和升華。而這個過程,即是劇作家將作為社會學概念的“扶貧”轉化為戲曲題材的過程,是劇作家對社會現象或生活素材進行“內化”后的再表達,它是扶貧題材戲曲創作的必經環節。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反思近年來涌現的扶貧題材戲曲創作出現“模式化”癥結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一些劇作者忽視了對扶貧題材的“內化”,沒有把“好的”材料轉化為“我的”材料,不能透過生活的表象去探索生活的本質,難以形成自己對扶貧攻堅這一社會現象的獨到判斷及認識,更不用說以此為標準指導自己對扶貧素材的發掘、鑒別和提煉,使得“扶貧”這一本應開闊的社會學概念在戲曲舞臺上呈現出“路徑相同、人物相似、結果一致、缺少懸念”的整體面貌。
在越劇《山海情深》中,我們是可以看出劇作者對扶貧問題的獨到見解的。首先,編劇提煉出“山”與“海”兩個重要意象,一邊是代表鄉土文明的“山”,一邊是代表城市文明的“海”,試圖打破“扶貧者”與“被扶貧者”的二元矛盾結構,將“扶貧”的內涵提升到兩種文明之間的碰撞與融合,展現了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由“舊”入“新”的必然歷程,以及這種歷史必然性下人們心靈的陣痛;其次,編劇試圖挖掘兩種文明之間及其內部的深層矛盾,超越“經濟扶貧”的單一向度,引導人們關注“經濟扶貧”背后“被扶貧者”精神與情感世界之“貧”與“困”,拓展了扶貧題材的內涵與外延。以上兩個方面,無疑是對扶貧題材進行“內化”的結果,劇作者不僅關注到生產方式落后、男性勞動力匱乏給山區經濟發展帶來惡性循環的表象,更敏感地捕捉到這種表象背后隱匿的沉重的情感及人倫危機,以蔣大海、蔣蔚等為代表的扶貧工作者,他們面對的不僅僅是山區經濟的復蘇、產業的振興,更是對當地傳統文化的搶救和道德體系的重構。可以說,劇中的“扶貧”,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一般“扶貧戲”片面追求經濟效應的模式,它對社會轉型時期鄉土文化撕裂與陣痛的觸及,是敏銳而深刻的。劇作家將自己對“為什么扶貧”“如何扶貧”的思考,集中表現在人們追求富足生活與渴望家庭圓滿這一對本不該成為矛盾的矛盾之上,它的產生、發展和解決,能夠折射出深刻的社會命題,體現了作為社會學概念的“扶貧”的廣闊能指空間。這樣的矛盾設置,無疑是充滿戲劇性且能夠以小見大的。頗為遺憾的是,雖然劇作者通過題材的“內化”,揭示出“扶貧”表象之下的深層矛盾,但從《山海情深》的首演本來看,這對矛盾常常淹沒在蔣大海、蔣蔚的父女積怨以及龍阿婆、應花的婆媳誤會等次要矛盾之中;或者說,劇中的次要矛盾沒有緊緊圍繞主要矛盾來鋪陳,導致主題表達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散和沖淡。因而,在劇本下一步的修改提升中,劇作者不妨對這些次要矛盾作適當的刪改,使全劇的核心沖突能夠更加集中、敘事節奏更加緊湊,讓觀眾能夠隨著“山”與“海”由碰撞走向融合的過程,深刻地體味城鎮化進程中的世道人心和時代陣痛。
寫活人物,是扶貧題材戲曲創作深入人心的關鍵
任何一部戲劇作品都包含了題材、主旨、人物、語言等諸多要素,觀眾自然希望其中每一項都能在作品中得以完美的呈現。然而,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一部具體的作品,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通常情況下,觀眾對于這些瑕疵具有一定的包容度,但這種包容建立在一個重要的前提之上,即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必須是鮮活且可信的。倘若人物形象樹立不起來,這個作品就很難說服觀眾而獲得成功。同樣地,“扶貧戲”要打動觀眾、深入人心,必須依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們是劇作的靈魂,反映時代特征、記錄歷史進程必須依靠他們,傳遞情感、感染觀眾也必須依靠他們。當下許多“扶貧戲”之所以吸引不了觀眾,與這些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模式化、套路化有很大關系。沒有立體的人物作為載體,不管劇作者對扶貧問題的思考多么深刻,也只能成為一句空談。借用威廉·阿契爾的觀點:“有生命的劇本和沒有生命的劇本的差別,就在于前者是人物支配著情節,而后者是情節支配著人物。”在扶貧題材的戲曲創作中,要把人物寫活,其關鍵并不在于編寫的情節是多么的曲折和傳奇,而在于透過戲劇性的事件,挖掘歷史車輪之下人性深層的沖突,并將這種沖突融入具體的人物行動邏輯,在人與自我、與他人、與時代的多重關系中,賦予扶貧主題以深刻的內涵。
越劇《山海情深》的人物形象可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是以蔣大海、蔣蔚等為代表的扶貧工作者;第二類是以應花、滕媧、龍阿婆等為代表的山區留守女性;第三類是以根強、梁寶等為代表的外出務工的山區男性。這三類人物的命運都與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因“扶貧”而聚合,也因“扶貧”而彰顯出不同的個性;即使在同一類型的人物內部,不同人物之間也因“扶貧”而存在迥然的差異。劇作家對不同類型或同一類型人物個性差異的描寫力求客觀,沒有對人物進行褒貶評價,而是試圖以“扶貧”為背景,去描摹不同人物在時代浪潮中的心路歷程,聚焦他們在這種不可阻擋的歷史進程中的較量與和解。比如,劇作家對蔣氏父女兩代人的刻畫,他們一個是深扎基層的扶貧干部,一個是年輕有為的竹編技術人員,二人在矛盾重重的表象之下,懷揣著帶領山區群眾脫貧致富的共同理想,而這個理想逐步實現的過程,也是父女二人由對抗走向和解的過程。劇作家對苗寨女性群像的刻畫,同樣采用了這種矛盾分析法。她們樂觀開朗的表象之下,都藏著思念外出務工親人的苦澀,但她們對待扶貧的不同態度,又讓她們彼此產生分歧,隨著竹編產業在一次次挫折中逐漸壯大,她們也走上了同心協力壯大竹編合作社的道路。而以根強、梁寶為代表的苗寨外出務工眾男子,在劇中更像是一個具有象征意味的符號,他們在前四場戲中是存在于苗寨女子期冀中的“未出場”人物,寄托了留守女人們對美好愛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脫貧之日,亦即他們的回歸之日。在這三個人物類型中,劇作者對代表“扶貧者”的蔣氏父女以及代表“被扶貧者”的苗寨留守女性進行了重點刻畫,尤其著重構建了蔣大海、蔣蔚父女以及龍阿婆、應花婆媳兩組人物關系。蔣大海、蔣蔚這對父女人物關系的設置很巧妙,它既象征著扶貧責任在兩代人肩上的延續,也為父女二人在扶貧觀念上的分歧作好了鋪墊。然而,劇作者沒有將父女二人矛盾的根源歸結于扶貧觀念的不同,而是過多地著墨于父女二人因母親去世而產生的個人積怨,這樣的矛盾是游離于脫貧主題之外的,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人物行動的必然性。同樣地,應花、龍阿婆象征了苗寨兩代人對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態度,龍阿婆是長者、智者也是保守者,應花年輕、聰慧又有一顆開放包容的心,這樣的人物關系設置本應很有戲,但劇作者過多地渲染婆媳之間的苦情、悲情,尤其是龍阿婆這樣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不惜違背自己做人原則,佯裝惡毒逼走兒媳婦,其行為動機于情于理都不符合現實邏輯,不僅貶損了這位本應出彩的人物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作品的理性思考。此外,應花這個人物應該是全劇的“戲眼”,她生長于苗寨,卻對蔣氏父女的竹編產業項目最為理解和包容;她經歷苦難,卻依然堅信幸福可以靠自己雙手得來。可以說,她的身上集中了“山”的質樸與“海”的開闊,最能體現時代陣痛之下人的復雜性,也最能代表扶貧過程中“被扶貧者”之中的內生力量,她值得也應該被劇作者作為重點人物來刻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