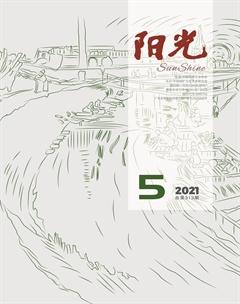用平凡寫下生命的質樸(創作談)
情緒帶動語言,流暢、自然、真實地表達,還是語言表達情緒,思索、安排、組合,巧妙布局而抵達深井或云層?
常常在兩者之間猶豫徘徊。既喜歡自然流暢的抒情,又想要語句精煉、超前、創新。當然,自然的抒發也可表達深邃,達到詩意的厚度。而有意識的講究語言、布局、技藝,可能會失去自然流暢真實的第一感應,但錘煉的語言或許可能更精確的表達深廣,且也是治學的態度使然。
在探索與實踐、比較與舍棄中,我無法放下一方成全另一方。而要達到自然之情緒和語言之精煉的結合,做到下筆之流暢和技藝之純熟的統一,這是一種修煉得道后的境界,是能不能達成的一種冒險。
但這方向是對的,是詩學通往頂峰的恒途。
而實際上,又何處才是頂峰呢?漢語詩或西方語言詩歌發展幾百上千年來,有過波浪式的低谷與頂峰(專指表達形式、語言等方面),總是在摸索中前進,在一種語境成熟后,人們又開辟另一種語境,或在一種語境行不通半路被廢后,人們又卷土重來。所以創造和爭論從未停歇。
而恒途是有的。恒途便是詩歌的內核。是詩歌傳遞的愛與真。這是詩歌的終極信仰,與人的心靈信仰一致。而要抵達這樣的頂峰又是很難的。
作為一個社會人,無法脫離還在進程中的人類標簽,使得愛與真都有著隔膜的氣息。比如愛,親情的、友情的、陌生人的、男女的愛情等大愛或個體之愛,都抵達純凈之境了嗎?或許抵達時,眺望過,在途上跋涉過,但終在路途或在終途被現實的灰塵蒙蔽,沒有人可以在這樣的純凈里全身而退,退回現實中生存得很好。除非那一刻,死亡才能幫你抵達永恒。
真,又何嘗不是。人們總是小心翼翼把真理呵護在謊言里,把真理掩藏在庸俗的日常行為里。以使這來之不易的僅有一次的生命能不受到無謂的摧殘。
所以詩歌是很難的。詩歌就像一種愛的護膜或俗的事務,通過曲折幽婉的語境和手法,不露聲色地抵達,或需要坐下刮骨般地剖析,方可窺見其中的愛與真。
這既是難點,也是詩歌的妙處。若不是這樣的霧蒙云迷營造出的純凈山嵐與空氣,也不能稱之為詩歌了。
但有時我們也會像種下白菜、蘿卜一樣,用平凡的結構和語言,寫下生命里最質樸的東西。
王馨梓:本名王友愛,土家族,張家界人,現居長沙。作品見于《詩刊》《星星》《芙蓉》等期刊,入選《中國當代文學選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