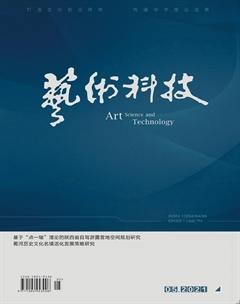從電影《無名之輩》中反思教育
王楠 駱瑋
摘要:電影《無名之輩》作為一部小成本影片,在上映之初憑借跌宕起伏的劇情設計以及精準的人物刻畫,引起了觀眾的熱烈反響。該片用喜劇的表演形式訴盡悲情,實際上是一部探討尊嚴與生存、直擊人的靈魂深處、引人深思的電影。本文從情節、語言、角色、細節4個方面對《無名之輩》進行藝術賞析,從中反思教育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電影;情節;語言;角色;細節;教育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5-00-02
《無名之輩》是一部影戲十分濃郁的影片,它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人物形象的刻畫,片中不管是主角還是配角,角色的調性達到了高度統一,使原本處在城市邊緣的個體,隨著影片的劇情發展,表層被逐漸剝離,使觀眾能真切地體會到生活在城市底層人民的悲哀以及被命運戲弄的人們的真情實感。劇中所有人亦活潑亦慘烈的命運,都被擰成了一股繩,使觀眾極具代入感,感受這些城市人群中“無名之輩”的痛苦境遇。
1 荒誕幽默的故事情節
電影《無名之輩》講述了一對缺乏教育的“低配版”劫匪,一個潑皮而又落魄、“四五年沒考上公務員”的保安,一個全身癱瘓、性格彪悍且稍有文化的“毒舌女”,陰差陽錯糾纏在一起引發的一樁烏龍劫案。所有故事的爆發點都在缺乏教育的小人物身上。
電影的前半段,兩個佩戴頭盔的劫匪攜帶獵槍去搶掠有保安看管的銀行旁邊的手機店,在逃竄的過程中,誤入了一個經歷車禍、全身殘疾、待在家中不見天日且性格彪悍、一心求死的“毒舌女”的家中,她想要通過激起兩個“悍匪”的怒火,完成她一直以來的心愿——死。到這里發生的故事好像一場平淡的喜劇,導演用喜劇的表演形式為后面的悲劇情節做足鋪墊,“上藥”“做飯”等生活的場景使兩個缺乏教育、被人瞧不起的劫匪狀況百出,再到后來新聞的報道,手機變成了手機模型,想要出人頭地的“悍匪”變成了報道中“鬼畜”視頻里的“憨匪”,這讓他們再次感受到了社會對他們的羞辱,導演用巧妙的手法慢慢把觀眾從喜劇的情感拉向悲劇的深淵[1]。
而“悲劇凸顯的永遠是不幸的性質,是人類在追逐物質和精神征途中的苦難象征”[2]。兩個缺乏教育、從農村出來的劫匪,有著在人們看來非常荒誕的“頭盔俠”計劃,農村帶來的桎梏是他們永遠無法逃避的,正是他們對法律的一無所知和對城市生活與前途的迷茫,引發了烏龍案。
從另一條線索出發,保安馬先勇教育程度低,因醉酒肇事而失去本擁有的一切,他想要重拾尊嚴,重新“活著”,就產生了“當英雄”的念頭,來獲得當回協警的機會。于是他開始牽頭尋找丟失的獵槍,卻誤入賣淫場所,引出兩位劫匪和影片開頭交代的跑路的開發商,從而導致一場混戰,影片的最后馬先勇用玩具槍“對戰”劫匪手中的獵槍,當這個城市的禮炮響起,“悍匪”再次被戲弄,而馬先勇也中槍當了“英雄”,影片末了那句“你們能夠把我抓起來,能夠槍斃我,可你們為何要惡搞我?恥辱我?”,使影片再次達到高潮,更有質感,這種質感亦是情感。這種情感的爆發是底層人民最真實的反抗,他們接受的是整個社會的冷眼與嘲笑,在最后卻依舊只有無聲的反擊。
魯迅說過,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是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3]。這就是導演的高級表達,無論是喜劇的表演方式,還是悲劇的宣泄出口,它不同于《您好瘋子》,也區別于《瘋狂的石頭》,在節奏的把控上非常巧妙,那種沒有炫技的簡單,少了很多“精妙”,卻使人物更加立體,實現情感的宣泄,使觀眾與角色情感共振。該片是一部黑色幽默性質的喜劇,也是一場教育缺失的社會悲劇。這場社會的悲劇值得所有人反思,情節荒誕,卻也是生活最真實的寫照,應使這種荒誕的悲劇停止上演[4]。
2 獨特的語言風格
《無名之輩》的導演饒曉志在采訪的初期就提到過《無名之輩》的創作背景,是一次在飛機上聽了堯十三的歌曲《瞎子》而產生了思鄉之愁,并通過話劇《蠢蛋》帶來的靈感創作了此部影片。該片的語言風格成了影片的亮點,同樣也是笑點,直擊觀眾的笑穴。幽默、形象、生動的方言俗語使觀眾潛移默化地融入電影情境,同時突出人物的形象,側面表示人物的生活背景及生存狀態,不僅可以發揮語言風格的獨特性,也可以很好地切合影片的主題[5]。
任素汐扮演的馬嘉祺直接使用貴州山城的地方方言,與“悍匪”眼鏡說的重慶話互通互融,這類方言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大量的罵人詞匯,這源于西南人民獨特的交流方式,臟話似乎是他們的語氣點綴,并不存在任何意義,這也是在現代文明社會下,大量罵人詞匯被保存下來并得到廣泛使用的原因[6]。“憨皮”“瓜娃子”“瘋婆娘”等大量民間話語為影片增添了詼諧、俏皮的色彩,將方言“野蠻生長”的狀態展現得淋漓盡致[5]。電影利用平民化的語言來拉近觀眾與角色的距離,潑辣倔強的“毒舌女”馬嘉祺,處處咄咄逼人,不斷試圖激怒“悍匪”對他開槍,而從馬嘉祺所生活的環境、墻上的字畫、房屋的裝飾,不難看出她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但命運的不公卻使她成了“潑辣的瓜婆娘”。因為在她看來,沒有尊嚴,沒有價值地活著,不如走向死亡。“悍匪”胡廣生和李海根是飽含市井氣息的具有倔勁的小人物,是“鄉下進城”“具有抱負”的“無名之輩”,市井化的語言交流更貼合人物本身的形象,帶動了人物的情感,一個想要賺足錢歸鄉娶妻的大頭,卻被一心想要有所成卻被戲耍的“悍匪”眼鏡譏諷“你真的覺得她會跟你回去嗎”,他想要點醒的不僅是癡情的大頭,更是他自己,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被命運戲弄,被人看不起,“無名之輩”真的能在這里立足嗎[7]?鄉音的處理,不僅塑造了角色人物,更貼合了主題的情感變化,甚至每一個新流行詞的運用,如“鬼畜”“盤他”等,都在不斷交代角色本身的生存背景,在這個社會中,他們一直都是不受人待見、被人羞辱的小人物。沒有任何教育背景的他們難以融入這個社會,只有他們的“俠氣”能為他們找到僅有的存在感[8]。
《無名之輩》中角色對平民化語言的運用,不僅為該片增添了幽默感,更貼合了角色的固有形象。無論是受過一些教育卻被命運戲弄的“毒舌女”,還是未受過教育、被社會羞辱、無法生存、想要做一番大事的“悍匪”,一個文明的社會需要給予他們一點包容,對這類人的法律和心理方面的教育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
3 極具張力的角色演繹
“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這是當下演藝圈流行的一碗“雞湯”,在《無名之輩》中得到了很好的驗證。比如妓女真真,雖然在影片中并沒有直觀表現出她是嫌棄大頭窮而分手,但從眼鏡與大頭的爭執中不難看出,她是一個不甘在農村鄉下貧苦生活進城打工的女子,不論她的職業有多么的不堪,大頭卻始終相信她,是生存使兩個持有愛意的人面臨分別、經歷苦難。她雖然對大頭也有愛意,但要為了生存去過活。但她甘愿為大頭撒謊,這種愛在她保護大頭的時候體現得淋漓盡致。而這種愛由于教育的問題變得十分滑稽,在片頭警員審訊過程中“驗證指紋”的劇情,使后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落網成為必然。教育的缺失使他們天真地以為自己可以瞞天過海,可以靠個人的力量保護心愛的人。她的天真承載了荒誕和現實的支點,渴望愛情,想要生存,卻往往適得其反。這一點在馬嘉祺身上也得到了體現。
馬嘉祺原本彩色的人生,卻因為哥哥的意外車禍變得灰暗。她雖然是劇中最具文化的角色,卻被展示得最悲情,因為哥哥的過失高位截癱,在這樣不見天日的日子里,她從沒有喪失對“光”的渴望。劇中她與哥哥的告別,也是她的一種釋懷,是她對哥哥的原諒。教育使她原本的人生充滿希望,而經歷一場災難之后的她卻變得失魂落魄、毫無希望。“沒有一個人在最苦情的狀態下能夠自救。”馬嘉祺在灰暗的時光中,并沒有出現一道“光”使她走出陰霾,這在一定意義上應歸因于教育的缺失,這種教育不再是啟蒙的教育,而是意外后的心理教育。意外帶走了太多人的生命,而活下來的人有的卻失去了希望,相較之下,關心與愛護比啟蒙教育更加有意義。只有心里的光才能照亮整個人生[9]。
影片之初,馬嘉祺和眼鏡兩個人的角色沖突最強烈,眼鏡卻成了那個陪馬嘉祺過“橋”的人。眼鏡是教育程度很低的小人物,但是他有一股子傲氣,他在社會上受盡屈辱,想通過“悍匪成長計劃”獲得人們的關注,在他走之前,在黑板上畫的那幅畫,成了他和馬嘉祺一起走下去的勇氣,也是他們人生階段要邁過的“橋”。
雖然文化教育的缺失、法律知識的匱乏,使兩個角色就像平行線,但在眼鏡遇見馬嘉祺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得到了改變,漸漸走向正軌。因為愛和包容可以彌補他之前缺失的部分。教育和愛在這一刻互通互融。這告訴我們,在現階段,值得我們關注的點不再只是學前教育,還有心理和法律方面的教育。這些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也是對社會環境影響較大的部分,掃盲和普法同樣重要。
4 惟妙惟肖的細節刻畫
“即便是最好的例證,也只不過具有某種曖昧模糊的存在,不是作為完成的藝術作品,而是因為某些可圈可點的局部。”一部好的電影離不開細節的刻畫,《無名之輩》中的多處細節都讓人印象深刻。保安馬先勇生活十分貧困,在水果攤上賒賬消費,日常生活中像潑皮無賴,但在女兒的學習教育方面,他祈求老師寬限時間,又顯得十分卑微,這表現出他對女兒教育的重視,也表現出他對良好教育的尊重與渴望。露臺那一場戲中,劫匪答應給馬嘉祺做一個了斷,問到她最后的心愿是什么的時候,她說是拍一組賞心悅目的照片,而她的真實愿望就是重新站起來,感知雙腿的力量,回歸正常的生活。在這一段拍攝中,演員任素汐達到了忘我境界,最后才發現身上被繩子勒出血痕。在眼鏡看《水滸傳》的地方也有很多的細節,首先是書的本身就是拼音版本,暗示眼鏡的受教育水平不高,可能連拼音都不認識,另外,這本書是馬先勇在出車禍之后照顧馬嘉祺時為她閱讀的故事,從側面暗示了馬先勇的文化水平也不高,這就是導演在細節上為之后的情節做出的鋪墊,“四五年沒考上公務員”。警察為了捉住搶劫犯,執行任務,不管下面開槍打架,直到大批學生涌入,立即呼叫外圍協助,高喊“保護學生”,這給了觀眾心靈的震撼,在當下,保護學生、保護教育成了整部影片的中心。包括最后依依為了告訴爸爸她并沒有改姓,拿出了帶有簽名的高中教育課本。無論在怎樣的環境下,人們首先想要保護的是學生,而馬先勇的實際狀態是保護教育。
電影的這些細節無一不在為角色服務,為影片的主體服務。正因為主配角受教育程度的低下,才發生了這樁無厘頭的劫案,從而導致了最終的結果,所有人都“得到了”他們想要的,也因為無知而付出了代價,教育知識的匱乏導致的魯莽行為,也會使人“失去”他們擁有的[10]。
5 結語
影片用喜劇的表演形式,卻充斥悲情,影片的收場是一場奪目的煙花演出,仿佛在告訴我們:生活不僅有羞辱,還有祝賀。祝賀你重新找到出處,重新走向生活的正軌,眼鏡有馬嘉祺,馬先勇有依依,大頭有真真,每個人又有了“光”。給人重新開始的勇氣,或許這就是教育最初的意義。在現階段的教育文化中,我們應重視教育的實施問題,關注小人物所在的生活環境狀態,重視教育匱乏導致的后果,將其減少到最小化。
參考文獻:
[1] 方蘇涵,黃瀅.泥泥狗的藝術特色分析及其在當代景觀設計中的運用[J].藝術科技,2020(15):18-21.
[2] 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M].楊燕迪,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167-187.
[3] 蔣榕.《無名之輩》鏡頭語言分析和受眾共鳴[J].戲劇之家,2019(22):146-148.
[4] 梁良.淺論電影《瘋狂的石頭》中鏡頭語言的運用[J].文史藝術,2013(9)112-115.
[5] 張寧,李蕙廷.《綠皮書》主題內涵之解讀[J].大眾文藝,2019(24):182-183.
[6] 賀靖婷.“生命不該承受之重”《活著》悲劇性新探[D].長沙:中南大學,2010:66-68.
[7] 陶皓淼,耿植榮.淺析文化思想的繁榮對美術作品的影響[J].藝術科技,2020(21):125-126.
[8] 張寧,顏瑩露.解讀現代攝影的人文關懷[J].大眾文藝,2019(22):172-173.
[9] 葉煜哲.從精神分析學說論《三體》的人物形象[J].大眾文藝,2019(18):16-19.
[10] 王納納,華陽.新媒體環境下非遺文化媒介傳播與文化傳承[J].藝術科技,2020(20):84-85.
作者簡介:王楠(2000—),女,江蘇宿遷人,本科在讀,系本文通訊作者,研究方向:數字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