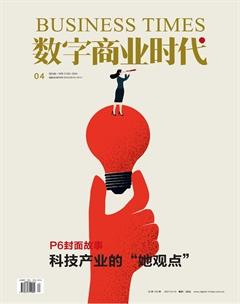中國科技和中國互聯網,誰拖累了誰
蟲二
5年前,特斯拉已成為豐田、大眾眼中釘時,資本市場仍然不知道如何給一家“軟硬不分”的公司定性。
按照彼得·蒂爾“從0到1”的理論,虛擬產品復制幾乎沒有邊際成本,但制造業并不享受這份紅利。
不管特斯拉的技術多牛X,作為硬件的汽車本身似乎拼不過豐田、大眾的成本優勢。
所以有人覺得,特斯拉不如讓生產環節回歸傳統制造模式,這有點諷刺了,創新的夙命就是變成它想要顛覆的對象?
但不是沒道理,老牌車企不怕PPT狂魔。也不在乎馬斯克的光環,怕的是能把逼格變成出貨量的Model 3和Model Y。
這么說來,未來的超級公司必然是一個綜合體。
硬件學傳統制造業的大規模低成本生產,產品學互聯網的快速迭代,研發要耐得住寂寞,創新要快速應用。
一個軀體住著四個靈魂,關鍵是哪個起主導作用。
至少目前,中國還未出現這樣的超級公司。
互聯網擅長模式創新,最喜歡把所有賺錢的場景塞進流量池,哪怕“與民爭利”。科技制造關注規模和成本,生態既強大又脆弱,從中興到華為莫不如此。
這兩類公司都是中國創新的頂梁柱,但社會聲望卻在反轉。
號稱“移動互聯網元年”的2012年,手機取代PC成為主要的流量、用戶和業務入口,線上巨頭全面滲透線下,2014年春晚紅包大戰激活了移動支付,網約車、共享單車等大量O2O創新紅遍全球,頂峰是2017年的“新四大發明”。
獵豹傅盛甚至說“中國是灰犀牛,美國在抄中國的作業”,這讓中文媒體有了“學生變老師”的優越感。
另一個變化卻被忽視了,移動互聯網公司開始搶走聯想、華為等硬件公司的光環。
最典型的2018年小米上市。
盡管證監會反饋了2萬多字的84個問題,盡管營收大部分來自手機,仍然無法阻擋小米將自己定義為一家互聯網而不是硬件公司。
明明是“硬”公司,非讓自己“軟”下來,說明商業生態的價值取向變了。
同年中興事件發生。
馬化騰率先反思,他在“未來論壇X深圳峰會”表示,移動支付只是表面輝煌,“不能再抱有僥幸心理,一定要投入更多資源在基礎科學方面”。
“新四大發明”的金字招牌隨之褪色。
中國創業圈向來尊敬任正非,但華為對互聯網新貴并不感冒,去年8月的“中國信息化百人峰會”,余承東帶頭嗆聲。
彼時的華為麻煩纏身,自主設計的麒麟芯片遭遇精準鎖喉,谷歌停止GMS授權更新,海外手機市場有坍塌的風險。
但余承東的炮口指向出人意料。
他既沒有指責臺積電和asml的“背信棄義”,也沒有把谷歌當出氣筒,而是分享了另外兩個觀察,傷害不大,侮辱性很強。
首先,余承東把中國終端產業的“困境”,歸因于美國主導軟件生態。

言外之意,如果windows和android屬于中國,華為就無所畏懼,甚至可以讓低端的榮耀手機打價格戰,再把鴻蒙包裝成另一個IOS,去攻擊蘋果、三星把持的高端市場。
其次,余承東認為中國app很多,全球化的不多,這是實話。
早年主打海外的都是工具型應用,象久邦數碼、獵豹清掃大師等等,但很快被打回原形,目前除了Tiktok,幾乎沒有殺手級產品。
在華為看來,就算谷歌、臺積電、asml再搗亂,只要我們手里有國民級APP(用戶無法戒斷的那種),生態慣性就能頂住行政壓力。
所以華為等中國“硬公司”希望“軟公司”做好兩件事。
第一,不計成本的開發全球通用的底層源生系統,堅決不要給android當美工,這樣即便遭遇外部脅迫,用戶轉移也有極高切換成本,道理一如蘋果IOS。
這就能看出,華為發力鴻蒙,實在是迫不得已。
第二,堅定不移的做全球用戶離不開的殺手級產品,tiktok不夠,必須深度嵌入生活和工作場景。
但華為也知道這兩件事希望不大。
首先,谷歌為什么能把android做起來,因為抑制了硬件野心,親兒子pixel與其說是商業化利器,不如說是技術探索的炮灰。
商業利益上也相對克制,Android的“過路費”與“蘋果稅”都是三七開,愿意讓開發者拿大頭,中國應用商店就是五五開。
只要涉及利益分配,誰肯妥協,華為自己也單挑過騰訊。
其次,殺手級產品拼的是耐力和定力,基因里多少要有一些反商業的成分,張小龍說喬布斯給后人的啟示,就是“純粹也能成功”,說明到了這個層面,格局決定一切,真不是產品力說話了。
所以,余承東的本意還是希望建立美國CHIP那樣的聯盟。
CHIP是蘋果、谷歌、亞馬遜牽頭的開放物聯生態,基于領英創始人reid hoffman的“聯盟”理念,即每個成員都克制本能的商業沖動,只做自己最擅長的事。
前提是大家愿意妥協,放棄贏者通吃。
舉個例子,亞馬遜alexa、谷歌assistant都很強勢,卻愿意在CHIP框架下共享市場,換成小愛同學,愿意跟小度同學二人世界嗎?
更別說,大物聯生態還有很多關鍵的技術節點,芯片,底層通訊協議,云端服務等等。
中國公司執行最徹底,貫徹最堅決,維持最長久,最不受外界干擾的產品策略,就是對友商的排斥。
就算軟公司們達成了一致,硬公司會一起愉快玩耍嗎?
CHIP吸引了宜家、霍尼韋爾、恩智浦、施奈德等企業加入,美的、格力、海爾愿意加入米家還是華為生態呢?
這種“聯盟生態”也未必有多少開放基因,大家口頭上情懷滿溢,動起手來,誰都不會放棄陽光下的地盤。
至少現階段,互聯網公司仍然迷戀軟經濟的溢價變現。
幾年前任宇昕被問及騰訊為什么不做智能硬件?
他講了個故事,大意是某位男同事習慣飯后溜彎,但回家時間不固定,老婆心存疑惑,原來這位老兄必須刷到微信前10名才肯回家。
在老華為任宇昕看來,內容和社交才是智能硬件的核心競爭力,至于硬件本身何時做以及誰來做都不重要。
同理,中國新造車勢力也認為不必自行建廠,找缺錢的車企代工就好,甚至都不必研發,只要顏值唬人,交互加點料,足矣。
在內心深處,他們并不相信基礎研究有“點石成金”的魔力。
經常被拿來說事的就是波士頓動力,這家公司經常搞出嚇人的新玩意,但命運多舛,一直被轉賣,韓國現代收購80%股權只花了11億美元,阿里蔡崇信寧可花同樣的價錢收購NBA籃網隊,也沒考慮過這家逼格滿滿的公司。
在典型的互聯網邏輯中,為春節紅包一擲萬金勝過押寶失敗的硬核科技,這不是沒有遠見,而是避免不確定的風險。
當年谷歌賣掉波士頓動力,理由之一就是公司不能把30%的資源浪費在十年方能小有所成的項目。
大多數互聯網公司相信場景而不是技術的力量。
過去十年,從最早的千團大戰到最近的社區團購,每次戰斗都是資本戰、規模戰,從不是技術戰。
2011年的千團大戰,美團幸存是得到了阿里的輸血。
2014年的網約車大戰,滴滴贏在社交用戶的導入效率。
2016年的共享單車,更是純粹的燒錢游戲。
“軟公司”還相信快速商業化的威力。
扎克伯克為什么忌憚Tiktok?因為中國移動互聯網有兩項超能力。
其一是產品冷啟動的快速拉動力。
期望值和容忍度成反比,任何不能快速取勝的產品,都會被無情拋棄,像小米為米聊續命2年太罕見了。
美國雜志《好萊塢報道》用“boom”形容tiktok的爆炸力,因為精準短內容不需要人脈支撐,反而能給普通人提供社交貨幣。
何況市場推廣舍得砸錢,快手主導的zynn,從注冊到邀請再到發視頻,都有現金可拿,燒錢速度甚至宿華都無法容忍了。
美國“佛系”app顯然并不適應這種玩法。
其二是產品路徑的商業化遠超預估。
中國app的迭代從不停歇,有流量就會做游戲,有用戶就會做社交,有場景就做消費金融,幾乎沒有不可觸碰的領域,而在成熟市場,所有東西都是有邊界的。
余承東指責中國式創新過度商業化,真不算無的放矢。
但華為自己也是局中人。
華為封神那幾年,被看做是腳踏實地做科研的典范,但2019年5月之后的一系列變化證明,華為其實也缺乏核心技術。
公眾期待的理想狀態是:要么中國的軟公司和硬公司攜起手來,打造獨立自主的創新體系。要么干脆出個馬斯克,從一個點狀創新發展出一整套創新宇宙。
其實都不太可能。
首先,大公司彼此有路徑依賴,并不意味著必然抱團,更可能的關系是誰忽悠誰,誰拖累誰,誰拯救誰。
其次,純粹比做生意的話,不用馬云,黃崢就把馬斯克爆出翔了,但真正宏大的使命恰恰是反商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