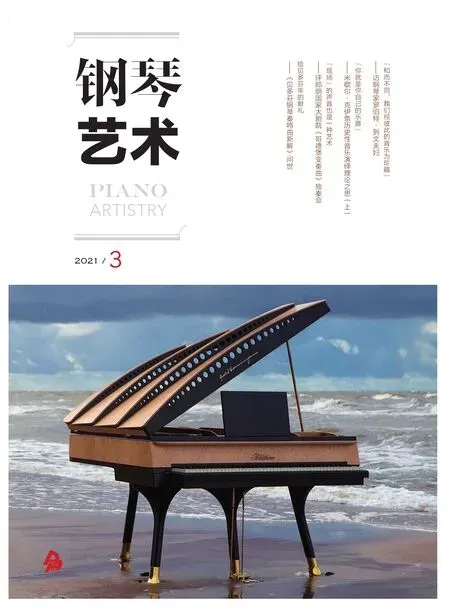古典重讀之四
——連線的奏法
文/ 汪月含

The Articulation of Slurs
記譜法和演奏法
英國音樂學者克萊夫·布朗(Clive Brown)在著作《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時期演奏法:1750至1900》中寫道:“雖然過去的音樂一直在被人演奏……但好像,只有有限的符合史實的演奏技巧受到關注。代代傳承著的音樂人們,習慣性地將他們自己所處時代的風格,運用在所有的曲目里。”
正如布朗所描述的那樣,在演奏風格發展延續的過程中,一代又一代音樂人口傳心授。盡管代際內部的審美取向也是豐富多元的,但這種差別,確實比不上代際之間的差異。作為演奏者,我們沒有辦法不受限于自己所處時代的審美導向;同時作為個體,也必然會在每一次演奏音樂作品時,嵌入自己的審美偏好。一邊是強烈的個人與當代風格,另一邊是歷史上作曲家原本的風格,二者之間的平衡與度量,始終是演奏者的取舍難題。在此,我們拋開所有個人與當代的風格不論,只談歷史上的作曲家與他們同時代的文獻記載,哪怕歷史上的選擇與我們今天的喜好不一致。讓我們忘掉今天的“習以為常”,站在時間之外去看演奏風格。
對比歷史長河里的不同時期,也會發現明顯的音樂風格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創作習慣和演奏習慣兩個方面,且二者關系的緊密程度也是在發展變化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分別打開任意一份巴洛克時期、古典主義時期、浪漫主義時期的樂譜,三者的譜面差別顯而易見—從最“干凈”到最“繁復”。這背后體現的不僅是記譜法的細致程度越來越高,而且反映了創作者對演奏者的“控制”越來越多。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就是對演奏者的自主能力要求越來越低了。越干凈的樂譜,越要求演奏者僅憑少量的信息(只有音高與節奏)便可判斷出樂曲的特質,比如哪種舞蹈、哪里分句、哪里分段、如何分配力度變化和時間變化。越復雜的樂譜,反而為演奏者做出了更多的演奏提示。而這種作曲者沒有明示,需要靠演奏者自行判斷的演奏方法,通常也是當年已經廣泛流傳、約定俗成的演奏習慣。這些習慣不需要被特意記載在譜面上。就好像我們走進中餐館會使用筷子、西餐館會使用刀叉一樣,是已經約定俗成的習慣,沒有必要專門標記在餐廳門口。
對當年的演奏者來講,這種省略沒有任何問題;可是對后人來說,卻是個大麻煩。如果不了解當年的這些規矩,我們怎么知道譜面背后暗藏的真實意圖呢?我們怎么能準確地判斷出符合當時音樂風格的處理方法呢?這些知識的缺失,或者說是判斷的偏差,的的確確也不是我們的錯。因為正如前文所寫的,我們作為歷史的一個點,接受的是一代一代的傳承,沿襲的是與我們最近的上一輩人的習慣,影響的是下一輩人。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需要意識到這其中的差異。
在接下來的若干篇連載中,筆者會依次列舉,在古典主義時期的鍵盤作品譜面上,那些區別于其他時期的、約定俗成的讀譜習慣和演奏習慣。比如,連線如何演奏,斷音如何演奏,什么標記都沒有的音如何演奏。這些資料同樣直接來自當年的文獻作品。
連線的目的
連線(slur,不是同音連線tie),恐怕是運用得最多的記譜符號和演奏指示了。古典主義時期鍵盤作品的連線,多為短連線,在兩個音到四個音,或者多至八個音的上方,用半圓弧線圍起來。它們需要區別于浪漫主義時期,或者是古典主義晚期,那種連跨幾個小節的、用于劃分樂句的超長連線。這種超長連線在古典主義早期和中期的鍵盤作品中非常少見。所以單是連線這種標記,在古典主義時期內部,就已經發生了意義上的變化。如果說,后來的長連線是為了分句,那么,早前的這種較短的連線,則是為了提示articulation的。
關于articulation這個詞(曾譯為“運音法”),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對應中文詞可以囊括其全部意思,尤其在針對不同的樂器和聲樂時,具體的含義也不太一樣。在鍵盤樂器上,articulation包含但不限于指示極細微的連、斷、跳變化,也就是從何時與如何下鍵,到何時與如何離鍵的一系列最細枝末節的觸鍵問題。要想弄清楚連線的真正含義,完成連線的真正作用,也就需要弄明白連線中的每個音需要怎么樣下鍵與離鍵。
古典主義時期的短連線,筆者認為,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提示分詞的作用(或者分字,對應長連線的分句作用)。該時期的大量文獻,都將音樂結構與語言結構放在一起分析。那個時代的音樂語匯與語言藝術,聯系實在是太緊密了。這也促成了該時期語言風格(speaking style)的形成,區別于其他年代的歌唱風格(singing style)。顯然,用連線組在一起的兩三個音,很難構成一個完整的樂句,但是可以用來代表一個詞語或者字。這里其實體現了不同語種之間的差別。中文里,一個音節一個字,兩個音節就是一個詞語;西方語言中,一個單詞可以是單音節,也可以是多音節的。連線將音和音分在不同組里,每組便是一個單詞,詞和詞最終排列在一起,就成了一句話。例如,莫扎特《降B大調奏鳴曲》(K570)第二樂章的主題(第1至2小節),高音聲部中,第一個“詞”有兩拍半,第二個“詞”有兩拍,第三個“詞”有一拍半,第四個“詞”有一拍,第五個“詞”有一拍。這些就是靠連線體現出來的。如果不是作曲家這樣畫連線,像這種不太規則的片段,演奏者恐怕未必會這么劃分。
例1 莫扎特《降B 大調奏鳴曲》(K570),第二樂章,第1 至2 小節

連線的基本奏法
首先,連線下的音,肯定要用連奏,即音和音之間沒有斷開的縫隙。卡爾·菲利普·埃曼努埃爾·巴赫(以下簡稱卡爾·菲利普)寫道:“需要用連奏去彈的音,必須要留滿書寫的全部時值。連線會放在這些音的上方。”
其次,也是古典主義時期關于連線最重要的一點:對連線下第一個音的強調。就是說,只要是畫了短連線的地方,連線開始的第一個音一定需要被強調。具體該如何操作?下方將依次列舉出歷史上的重要文獻作品,對該問題的描述。
1. 卡爾·菲利普,1753年
“兩個和四個音的連線,其中第一個和第三個音需要被彈奏成輕微的、幾乎不被注意的加重。三個音一組中的第一個音也是如此。在其他數量的情況下,連線中的第一個音也要這樣做。”
例2 卡爾·菲利普

2. 約翰·約阿希姆·匡茨,1752年
“兩個音中的第一個音,必須始終要比后方跟著的音更厚重,不管是時值上還是力度上。”
例3 約翰·約阿希姆·匡茨

3. 利奧波德·莫扎特,1756年
“對于兩個音的連線,重音要落在第一個音上,不僅僅只是演奏得響一點,還要演奏得長一些。而第二個音要和前一個音平滑地連起來,并且更輕和稍晚一些彈。”
“如果當兩個、三個、四個,甚至更多的音被連線連在一起時,我們由此可以得知作曲家希望音符不被分開,而是如歌唱般連奏,且第一個音必須要加重強調,剩下的音則是平滑且越來越輕。”緊接著不遠的段落中,他又寫道,“第一個音不僅要重一點,還需要保留得長一些”。他同時強調這種時值上的變化,不能影響整個小節的總長度。
4. 丹尼爾·戈特洛布·蒂爾克,1789年
連線的奏法,“需要始于柔和的幾乎不被察覺的重音”。 在蒂爾克的譜例中,有兩個音、三個音、四個音和八個音的連線。
上述是四份來自18世紀下半葉的文獻描述。四位作者的四本書,是古典主義時期涵蓋鍵盤、弦樂、管樂的四部極為重要的學術著作,深深地反映且影響了整個古典主義時期。
總結一下四位作者的演奏方法:第一,連線下使用連奏。第二,第一個音需要被強調,強調方法有差異。卡爾·菲利普和蒂爾克寫給鍵盤的文獻中,方法是加重。匡茨和利奧波德認為,除了力度上,第一個音的時值也要稍微拉長一點。所以,盡管書寫時值是均分,但實際演奏并不是平均的。第三,剩下的音相對更輕,利奧波德還專門提出需要漸弱。
這種用連線指向力度與時間變化的習慣,不僅出現在18世紀,19世紀依舊如此。在筆者看來,19世紀初的文獻甚至強化了音和音的區別。18世紀的文獻多是對第一個音的演奏方法的討論,沒有專門提到連線的最后一個音。但19世紀的文獻中,多次提到了對最后一個音的處理方法。
就像1804年,讓·路易·亞當(Jean Louis Adam)所寫的:“當只有兩個音連在一起,且兩個音的時值相同,或者第二個音只有第一個音的一半時值時,為了更好地體現連線,無論整體音量是強還是弱,都必須要更用力地彈第一個音,然后在第二個音時抬起,第二個音不僅要比第一個音彈得更柔和,還要減少第二個音的一半時值。”
例4 讓·路易·亞當,第1 小節是記譜,第2小節是演奏法

總結起來,就是在兩音時值相同或第二個音只有一半時值的情況下,第一個音更響,第二個音更輕,且只保留第二個音的一半時值。這種減少第二個音時值的做法,不只是亞當一個人提出的。后來的胡梅爾、車爾尼、莫舍萊斯等人,認為甚至是在更長的連線之下,也需要把最后一個音的時值變短。勃拉姆斯也堅定地認為,兩個音的連線中,第二個音是必須要變短的,無論這個音上有沒有寫斷音或者休止記號;對于長一點的連線則是可選擇的。
對于第二個音,或者說連線中的最后一個音,是否該變短,歷史上也存在討論。雖然18世紀的文獻里沒有專門說這件事,19世紀初的文獻倒是討論得較多。這里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關于大環境的問題。進入19世紀以后,用于指示分句的長連線越來越多,而且無論是創作方面還是演奏方面,對于歌唱性連奏的偏好愈盛,已經和18世紀的音樂審美不一樣了。就像克萊夫·布朗在書里寫的那樣,門德爾松在1845年特意指明,兩個音的連線在亨德爾的時代代表著漸弱處理。所以作者認為,這其實暗指了在門德爾松自己的時代,已經沒有了自動做出漸弱的習慣。因此,閱讀文獻時,對于作者的語言描述方式,也要放到時代背景中全盤考慮。
在旋律聲部,分詞的短連線和跨小節分句的長連線是容易區分的,但是介于二者之間的連線比較難以判斷。蒂爾克對此給出了例子:
例5 丹尼爾·戈特洛布·蒂爾克

蒂爾克特意指出,像類似例5(a)中這樣的半小節或一小節的連線,不能彈成例5(b)中的樣子。
對于19世紀初用于分句的長連線,比如貝多芬的作品里,長連線不意味著除了第一個音之外的其他音都不能出現重音或者力度變化。筆者認為,還是要分清連線是為了體現articulation,還是為了劃分句子(phrasing)。目的不同,演奏法也就不一樣了。
連線末尾的斷音
上文寫過,即便沒有任何斷音符號,連線末尾的音也是要變短的。那么,如果音符本身帶有一個斷音記號呢?二者的演奏是否有不同?
卡爾·菲利普的書中,把兩種狀況分別列出。但他確實沒有清楚地區分長度上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差別。下面是卡爾·菲利普的譜例和原文:
例6 卡爾·菲利普

“Figure171(與Figure170)彈起來相似,除了每個連線的最后一個音是斷開的。手指必須要在觸鍵后馬上離鍵。”
相對于時值長度的疑慮來講,更重要的其實是力度的問題。是否需要把標記了斷音的末尾音彈得更重呢?
蒂爾克在書中專門對此作了詳細說明:
例7 丹尼爾·戈特洛布·蒂爾克

“在連線末尾抬起手指是必須的,但是在抬起的時候加上重音的演奏方法是不對的,就像例7(a)那樣[例7(b)是正確的]。當用常見的斷奏標記來區分樂句的時候,就像例7(c)中那樣,我們便常常聽到這種錯誤的彈奏。很多演奏者都認為斷奏(detached tone)必須要帶著重音彈短,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從蒂爾克的表述中可以得知,這里的斷音記號是起區分樂句的作用,不是表示強調的。不只是蒂爾克這么說,舒爾茨(J. A. P. Schulz)同樣提到過用這種豎線式斷音記號放在句尾來表示分句。這種做法在那個時代非常常見。
連線改變節拍重音
短連線除了分詞的作用之外,由于其重音特征,連線還是用于改變節拍重音的一種非常便捷的方式。在古典主義時期,要想把小節中原本的強位弱位對調,只需要小連線即可。
卡爾·菲利普(見例6)和蒂爾克對此都有專門的譜例。
例8 丹尼爾·戈特洛布·蒂爾克

例8中的(g)(h)(i),都是將原本弱位上的音通過連線變成了重音。例8(g)中,十字符標記的音需要彈重。
另外,例8(k)的情況較為特殊,因為有兩層連線。蒂爾克表示這種狀況下,需要將所有音都連奏,不能斷開,但是第一、三、五、七個音需要略加重音。
例9 海頓,《C 大調奏鳴曲》,第一樂章,第1至8 小節

海頓這首《C大調奏鳴曲》(Hob. XVI:50)的第一樂章,是個非常典型的巧妙運用連線的例子。在第3至6小節里,左手的重音始終放在原本的弱位上。第2至3小節里,右手重音在弱位,但到了第4至6小節,右手重音挪回了原本的強位。主題第一句里,除了第6小節的fz外,沒有任何重音記號,但卻用連線表達了非常豐富的重音變化。下例同樂章的第26至27小節也是如此。
例10 海頓《C 大調奏鳴曲》,第一樂章,第25 至27 小節

連線的特殊用法
1. 用于分解和弦
卡爾·菲利普解釋道:“如果在分解和弦上加連線,則需要把音全都保留住。”
例11 卡爾·菲利普,第1 小節是記譜法,第2小節是演奏法

蒂爾克同樣也提到了這種記譜方法,盡管他推薦更精準的記譜。
2. 法國風格
在18世紀的法國或者法國風格作品里,依舊會使用不均勻演奏(Notes Inégales),但加了長連線之后,則不使用這種處理方式。(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