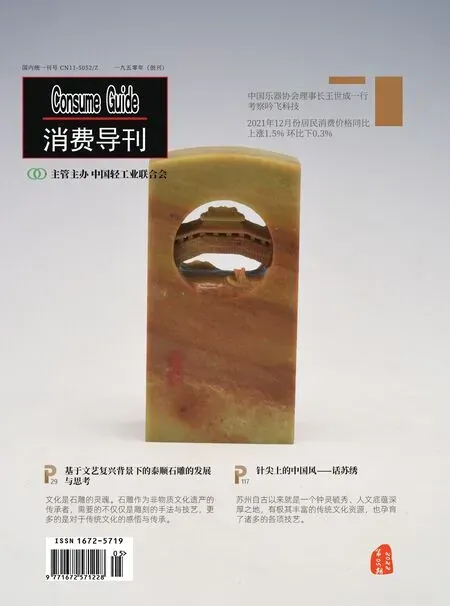青春電影《少女哪吒》的福柯式閱讀特征
夏華錦
江西傳媒職業學院
臺灣的青春電影發展已經有三十多年,它以獨具特色的表征個性演繹臺灣本土文化,以青春為表現主體、以人物的成長經歷為敘事的框架,在特定的歷史框架下表現焦躁的人物形象,試圖通過用社會潮流中的愛情、成長中的沖突、個體身份的認同和找尋來揭示臺灣在社會文化變遷中的縮影。《少女哪吒》作為一部人物個性鮮明的青春影片,將少女叛逆和壓抑的青春表現出來,它是導演個性的自我張揚,更是青春期少女個性的真實寫照。
一、福柯式特征概述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在一生中成績顯著,尤其是他的“微觀權力”理論將現實的生活以微觀視角呈現出來,在臺灣青春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人生軌跡,表現為將微觀權力理論滲透到電影影像中,從而將現實空間和理論空間進行深層次地匹配,讓影片與觀眾產生共鳴。規訓權力是微觀權力中重要的理論依據,它能夠將創作者的個人思想植根于電影的視聽語言中,而創作者的主觀意圖和影片中人物的形象又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微觀權力的介入可以有效地分析影響中的話語權力,而臺灣青春電影中特殊的話語體系也正需要這種微觀權力的介入。
(一)福柯式的微觀權力
在福柯的概念中,微觀權力是所有權力中最終形成的一種高級形式,它既不是一種結構,也不是一種特定的制度,而是在一個社會中人們被賦予的特殊的戰略形勢。而權力是一個單獨的有機體,它內部之間的各個要素相互影響,在外力的作用下改變自身的狀態。福柯的微觀權力和以往的各種權力有所不同,它所被運用的客觀現實是一種相對的意識性的存在,在影視作品中,角色的選定、故事情節的發生以及視聽效果都可以運用微觀權力來加以說明。
理論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實踐,福柯的微觀權力隨著時代的發展也被人們廣泛知曉,尤其是在中國,福柯的微觀權力被當做研究封閉式的監控體系,例如學校、監獄、醫院等,因為在它們內部存在著復雜交錯的利益關系,處處體現著權力的實施和接受。在這些封閉系統中,利益關系的此消彼長會促使體系內部發生本質上的變化,從而推動社會的發展。在影視作品中,現實中的監控體系被濃縮在一個視聽空間中,電影中的監獄、學校、醫院都被賦予現實的意義,而微觀權力正是現實中權力在影片中的縮影,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二)微觀權力的特點
福柯的微觀權力最大的特點就是權力之間的關系。在他的理論中,人與人的關系并不是不對等的,而應該將這種關系置于大環境中,以一個視角斜街另一個視角,構成一個空間關系而不是平面關系。微觀權力和宏觀權力是相對立的,所以,微觀權力關注的是人物或事件的內在而不是外表,它解釋的是現實社會中復雜的關系網絡,闡述這一關系網絡中的關系,而微觀權力又是最終形成的一種權利,最終會排擠其他權力,并繼續推動事件發展。即使是微觀的權力也離不開整體的社會,任何權力只有在社會這一大環境中才能成立,所以,人們在分析微觀權力時要以社會環境為研究藍本,而不是根據自己的意向來改變微觀權力。正所謂“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抵抗”,權力具有控制的作用,而反抗與它的合力才能實現事件的平衡。
二、《少女哪吒》中的微觀權力表述
在臺灣青春電影中,學校是一個產生巨大矛盾的地方,它的內部有著嚴格的一套管理制度,包括上課、放學時間的限定、學生禮儀規范的遵守以及一系列的規章制度,而處在青春期的學生大都是懵懂的,對世界的認識是模糊而新奇的,所以家長、老師以及學校管理者與學生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矛盾。學校是一個富有微觀權力的場所,隱秘的微觀權力處處存在,影響著學生的成長。在《少女哪吒》中,根據學校的學生規范來考慮,王曉冰就是一個成績好、尊師重道守規矩的好學生,而李小路則是成績差、不遵守紀律、目無尊長的壞學生,這種好學生與壞學生的區別就是一本成文的“學生守則”或是世俗的眼光。而李小路轉學后和王曉冰成為同桌、好朋友之后,王曉冰內心中的叛逆被激發出來,但青春就是青春,王曉冰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在抽煙、輟學、自殺、離家出走等一系列行為之后,她的不合乎微觀權力的部分最終會被打壓下去回歸正常。
(一)“他者”集體權力的解讀
在青春電影中,問題少年是主要的人物角色,在青春期,他們表現出與大多數同齡人的不同,所以,集體的“他者”就是實施微觀權力的不二人選。在《少女哪吒》中,“他者”的權力的實施者是小冰的整個家庭、工作單位,小冰和小路的學校和社會,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受著這些成年人的“監視”,王小冰在認識李小路之后敢于和老師頂嘴,為愛的人私奔、自殺,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觀眾展示了殘酷而血腥的青春,他的無處安放的青春是“權力”者母親和學校的犧牲品,她痛恨母親渾渾噩噩的生活,她不理解母親所持有的愛情觀,所以她選擇反抗,但是,母親的“規訓”卻是她自身情感缺失的體現,她并沒有從小冰的立場去考慮,而是遵循一套約定俗成的管教方式,這種規訓習慣就是福柯的微觀權力的具體體現,正是這種習慣使得青春期的孩子糾結掙扎,不斷陷入苦痛之中,迷失自我。
(二)“主體”自我權力的建構
在一部影片中,每個人物都有其特殊的性格特征,而“自我”的主體性則是臺灣青春電影中的爆發點。影片中人物“主體”的自我構建需要通過人物關系來實現,從空間的連接和延續中可以讓觀眾看到充滿個性和自我意識的“主體”。在《少女哪吒》中,王曉冰和李小路是兩個具有典型性格的“主體”,一個本是眾人喜歡的好學生,一個是老師同學都討厭的壞學生,知道兩人相遇,她們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由此拉開,王曉冰的人物性格變化是影片中的重點,她的形象是叛逆期青少年的典型形象,而性格的轉變是經過一個不斷的自我肯定、否定的過程,其實,這種性格并不是在李曉路強加給她的,而是她內心深處藏著的本身性格,正是李曉路的出現才讓她有了真正實現自我“主體”的機會。但是,從李曉路轉變后的性格可以看出,她的“主體”仍然逃脫不了矛盾的個性,她看似成熟卻做著孩子做的事情,然而她給李曉路留下的一盒煙頭又是寂寥無助的,所以,臺灣青春電影更是當代年輕人生活的真實寫照,每個人在尋求“主體”的過程中的各種表現才能更加吸引觀眾,實現共鳴。
(三)權力關系的融合與消解
在青春電影中,主人公始終處于抗爭這個社會的過程中,他們在追尋“自我”實現中不斷抗爭、妥協、再抗爭,最終讓權力的實施者妥協。在《少女哪吒》中,由于家庭環境的因素,兩位女主人公有著不同的青春期經歷,李曉路的爸爸是工人,管教她的方式是寬容的,任其生長,而王曉冰生在一個離異的知識分子家庭中,母親因為父親的背叛始終處于一種精神質的狀態,表面看似平和,內心卻是極度脆弱敏感的,所以,李曉路本身就很自由,她沒有經歷叛逆期這一過程,因為她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而王曉冰卻時刻被母親監視,為別人而活。在遇到李曉路后,她開始發現真實的自己,而這種發現卻顯得過于倉促,沒有方向,這種壓抑已久的叛逆比李曉路的更決裂些,她在課堂上公然頂撞老師、向心愛的教官告白、當著全家人的面割腕到最后離家出走,這些極端的方式是他在和微觀權力的持有者進行的抗爭,而整個過程卻是慘烈的以犧牲自我為代價的,最終,這種權力關系達到了消解和融合,影片的結尾,李曉路去了王曉冰家里,曉冰的媽媽也做回了自己,也理解了自己的女兒,但是,整個權力融合的過程卻是讓觀眾更為難忘的,也許那就是自己的青春。
三、臺灣青春電影的文化內涵
(一)混亂與缺失的價值觀
在臺灣青春電影中,我們看到的是迷失的青少年,他們在青春期不斷地向外界對抗,而在對抗的過程中卻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他們在混亂的現實中找尋著自己的理想。在《少女哪吒》中,好學生王曉冰在青春年華找尋自由、理解、愛情和友情,而對于處在青春期的她來說,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愛情她卻沒有去考慮,只是一味地對阻礙自己的人進行沒有節制的反抗,在價值觀剛開始形成的過程中她卻不知道正確的價值觀是什么,在她的世界里,只有黑與白,沒有過渡地帶,所以,李曉路和男同學一起上學就是對她的背叛,教官的拒絕就是失戀,她只會選擇逃跑或死亡。這種混亂和缺失的價值觀是他們叛逆的原因,也是結果,而這也正是青春期的真實寫照。
(二)社會和“自我”的脫節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疏離,人在社會中迷失了自我,逐漸失去個性,越來越多的人走向“人格分裂”的極端,而青春期的少年則是這種“分裂”的典型。
在《少女哪吒》中,家庭之間的疏離是導致王曉冰叛逆的最大根源,她本來生活在一個幸福溫暖的知識分子家庭中,但是由于父親的出軌使得家庭破碎,母親終日神經兮兮地監視著自己,母女倆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但是卻形同陌路,王曉冰在疏離的家庭中缺乏親情,在心智成熟的最重要時期卻沒有父母的關愛,而她內心的真實想法又無處訴說,影片中,王曉冰與母親的交流只言片語,每次都能擦出火花,誰都看誰不順眼,更不要說談心里話,所以,李曉路的出現打開了她塵封已久的心門。
這種青春期的“失語”狀況是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結果,它讓人們之間變得冷漠、讓社會變得復雜,人與人之間也缺乏信任,青少年在叛逆期所付出的代價是社會的悲哀,而這種代價警醒了社會,卻是極其慘痛的。
(三)異化的道德觀
在經濟社會高度發達的社會里,人們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但是仍然滿足不了他們日益膨脹的欲望,所以在競爭激烈的社會里,道德觀念卻逐漸走向異化,在青少年的眼中,他們腦中的社會道德是純凈的,但是他們看到了成年人世界中的骯臟,所以自身也在選擇的過程中也產生了嚴重的困頓,最終在叛逆的過程中異化了道德觀念。
在《少女哪吒》中,王曉冰從小就生活在破碎的家庭中,在她眼中,寧愿相信父親是去世了,也不承認父親和別的女人好了,而這種第三者之間的感情是她這個年紀的孩子不應該接觸的,在她回家看到母親和自己的語文老師勾勾搭搭時,她就覺得自己的母親不要臉,這些成年人世界里的東西被過多地灌輸到她的腦子中,她身邊沒有人告訴她該怎么做,遇到這種事該如何處理,所以她只是將與自己傳統道德觀念上不同的事都當做是壞事,她只能自己去接觸,去尋找真正的道德觀念。
四、結語
臺灣青春電影是臺灣民眾的歷史淵源、生存環境、文化氛圍的一個縮影,本文運用福柯的微觀權力理論將《少女哪吒》中的青春“主體”,青少年的思想、行為特征以及特定時期的價值觀及成人后的命運進行了解讀,對在青少年期間出現的擁有微觀權力的“他者”及所反映的文化內涵進行深刻剖析,讓觀眾與創作者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