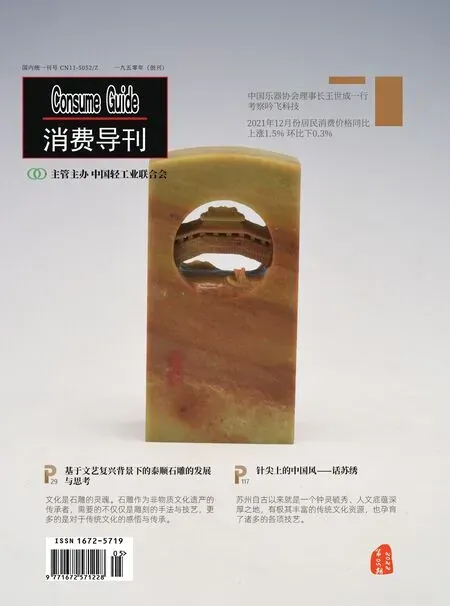淺析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稅改革進程
王震川
河南日報報業集團
2020年10月份,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習總書記來到了我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城市深圳,并再次釋放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時代強音。改革開放40周年,砥礪奮進的40年,亦是我國從建國時期一無所有的處境逐步成長為國家綜合實力位于世界強林之中。我國從改革開放到2013年基本上搭建起來和我國市場經濟相符合的財稅管理制度,這也是我國財稅改革的一個重要時期。改革開放40年的成效顯著、舉世矚目,在我國大力建設財政制度的大環境下,對我國制度變革和財稅體制進行中長期發展的分析。
一、回首40年來我國財稅制度改革主要歷程
改革開放初期,全國處于適應階段,為了使地方政府財稅經濟該給融入國家大的經濟發展環境中,并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經濟建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的目的。我國開始實行以“讓利放權”為主要手段的財政體制改革,之后我過得財政體制進行了三次重要的調整,分別在1980年開展并實施的“分級包干、劃分收支”的財政政策、在1985年實行了“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財稅政策,并在1994年又中央開始調整為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在分稅制制度實行以前,我國財政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五年一微調,這種調整既不是政治化和規范化的現代財政制度體系,又不能與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這種頻繁的調整不利于各級政府間形成穩定且長期的管理預期。自從1993年起,我國才結束實行“分灶吃飯”的中央和地方財稅管理模式,此時中央財稅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才下降到了22%的左右,在極個別的月份,中央財政甚至要向地方財政借債以維持正常運轉。這樣就產生了兩個弊端,第一是使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大大降低,第二是形成了“分封制經濟”,地方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加緊了各項保護措施。所以在強化法治治理的模式下,從1994年中央開始實行了以“三分一轉一返還”為要的分稅制改革。第一次引入“因素法”的概念,這種形式使中央對地方返還的財稅收入,以及支付轉移方式更加完善和清晰,這樣使中央和地方在分配制度上更加明確和合理,在各級政府財政分配上形成了較為長期穩定的模式。2014年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社會的經濟的飛速發展,前期實行的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稅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規范、不協調、不適應等問題也在不斷地暴露出來,由國家本應該對為民眾提供基本民生服務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力。但“分稅制”實行20周年后的今天,以“管理上浮、征稅下沉”為基調的發展下,國家著手對各級管理機構間財稅關系開始調整。2014年國家審議并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2016年中央發布了《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央和地方財政事權分工才去得明顯的區分。從收入方面,在保持收入局勢總體不變的情況下,尤其是在“營業稅改增值稅”施行后,頒布收入劃分的過渡性制度,開始劃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權比例。從支出側這方面看,確定支出責任和財政事權區分的原則,加強有關領域的協同變革,從側面推進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的進一步劃分,建立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相輔相成的制度體系。與此同時,優化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加大一般性轉移措施,爭取到2022年底,逐步建立起標準合理,權責清晰,保障有力,財力協調的公共服務的保證機制和體系。
二、總括中國財稅改革40年的歷程
(一)如何樹立市場和政府的關系
如何樹立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始終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必須解決的問題,是財稅制度改革必須直面的問題,也是市場和政府如何劃分權限,明確分工的事宜,直接影響了公共財政的支出范圍和納入程度,未解決財政資金的分配不均提供一個概念支持。隨著社會主義的不斷深化發展,歸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企業規模實力的飛升,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再把握全局的框架下,進一步深化改革。
(二)財稅改革需要與我國的基本國情相匹配,不能采取急功近利式的改革道路
我國的制度改革只能是循序漸進溫和進行的,應該處理好增量和存量的銜接問題,在平穩中進行改革。在黨“十四大”的確定了市場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中流砥柱的基礎,并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化與過渡;在黨的“十八”以后我國確定了市場在資源調配中的起到決定和和核心性的作用,明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大門繼續大開;在黨的“十九”以后,伴隨轉變政府職能政策和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實施,我國的財政體制改革更加需要根據國家的實際國情,由表及里、由簡到難的繼續推進。
(三)財稅改革進程中需加強中央政府的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職能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際,中央人民政府是國家治理和社會各項責任的最后負責人。所以,當前我國的財稅改革已經進入底層環節,剩下部分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加強宏觀調控面臨的是巨大的阻力和困難,改革過程充滿了復雜性和曲折性。在財稅改革中要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系,積極調動兩個層級的動力,最終實現國家總體治理效能的提升。
(四)財稅改革進程中處理好協調推進和頂層設計關系
2013年開啟的我國新的財稅深化改革中,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它需要規范著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中央和地方關系的一系列財政制度。在建立現代財政制度三大任務的關系來說,一是稅如何收,收入如何分配,以及經濟的周期調節,屬于籌集國家財政收入的職責;二是明確地方各級政府該承擔什么樣的支出責任和財政事權,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形成相互制約和激勵,才能把政府和人民的事辦好。
(五)財稅改革過程中要學會牽“牛鼻子”
從1994年國家開始實施分稅制改革后,抓住了上一次財稅改革的的核心問題,國家的財政收入大幅增加。2013年國家提出全面深化體制改革,這是一場拉開關乎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大幕的事件,既要從國家層面考慮,增強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規范性、協調性;還要精細政策規范,準確把握各項改革措施頒布的實效。財稅改革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是以2014年國家頒發《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方案》為標志的,也為之后修訂的《預算法》具有了經濟憲法的作用,為財稅體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據。
三、我國今后財稅改革的發展方向
(一)財稅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相適應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標桿,把財政事權放到了國家核心要務的層面上,所以現代財政事權制度要堅持法治思維。財政資金的預算安排和收入支出情況必須納入發路框架內,合規合法,之后還應該逐步完善預算的制作,實行,監管和考核等方面的法律規范,強化預算紅線,防止行政權力對財政權力的干涉。實施稅收法定原則,培養知法懂法,依法納稅的意識,做到無論新稅舊稅一律由法律作為規范;循序漸進將現行行政法規規范的稅收上升為法律規范。
(二)繼續推進預算管理方面改革,培養預算即法的理念
1.編制長期科學的預算編制的。中長期涵蓋了兩年或者兩年以上的收支需求的預算情況,能對中長期的財政進行約束和管理。不再片面以一年為期限為預算編制設限,為政府全方位掌握財政未來的發展走勢提供了基本的支撐,為財政政策的連續性有效性提供了保障。之后還要持續推進中央部門預算三年滾動規劃工作,提前對各個部門的研究政策進行審議,提前對支出項目做好計劃,強化事前規劃對年度預算的控制力。
2.實施全績效管理,優化資源配置。首先是在監督部門做好項目績效自評的同時,進一步擴大重點績效的外延,建立健全惠及民生政策和重大專項支出和的績效管理機制,其次是鞏固績效目標監管無死角的成果,完善績效的事后評估和審計,健全各類績效評價指標,并及時和反饋,形成閉環管理模式。
3.依法依規推進預算公開。第一按照法律規定和結合自身情況,逐步規范門路、渠道和方式,突破各級政府預算公開內容不一致、口徑不合規、監管不到位的困境。第二是持續擴大政府預算范圍,簡化公開內容、細化預算層級,把本單位預算向社會公布作為主要任務去落實,讓預算的管理更加透明和清楚。第三是健全預算責任追究和考核制度,加強各級政府的經濟責任,在做好好本級政府和本層級的預算公開事宜,并依照法律規定及時全部的向廣大民眾公開。
(三)繼續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地方稅體系
1.繼續完善增值稅改革力度。隨著國家“營改增”范圍的不斷擴大,,實現增值稅對一切服務、不動產和貨物的全涵蓋。我國增值稅改革取得的另一項主要成果是把不動產和服務納入進項稅抵扣范圍之內。當前處于疫情常態化防控期間,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為了實現所有行業稅賦只減不增,試點過程中并未對原來增值稅存在的制度性問題進行優化,繼續使用原營業稅各項優惠措施,對一些特殊行業還采取了一系列過渡性的稅收優惠制度,導致我國實行的增值稅和改革后的稅制還有很大的后勁,同樣也是這是我國后來財稅改革重點努力的地方。
2.研究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進步、民眾的收入不斷增加,開始推進分類和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就需要提到以后工作的重點中。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需要中央總體設計、企業事業單位和個人實施分步到位相結合,逐步建立起適合現階段發展國情的個稅制度,讓個人所得稅發揮其平衡收入水平、區域水平的調節作用。
3.建立健全各級政府地方財稅體制。針對營改增后,各級地政府稅稅收流失,納稅主體稅種缺失的問題,實施推進將房地產、改革土地使用稅納入到新的改革措施中。在現行國家開展的“六穩六保、房住不炒的”大環境下,清理不合理的稅收優惠和不正當的稅收競爭,發揮稅收隱形手的作用,抑制房地產泡沫,使各地政府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促進經濟的轉型升級,努力增強人民的幸福感、獲得感。
(四)進一步推動各級政府間財政關系
1.持續推進各級政府間,公共服務領域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的權責劃分。在分配專項轉移支付、一般轉移支付、各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以及涉及民生保障資金時,充分考慮我國實際國情,在不同人口因素、區域情況、發展均衡等問題基礎上,充分考慮增加轉移支付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相結合情況的因素。
2.改革完善各級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和分配的措施。目前在我國轉移支付制度改革“提高財力性轉移支付比重,整合專項轉移支付,發揮各級政府能動性”的政策指引下,建立專項轉移支付的清理、評審和退出機制。國家在改革專項支付管理制度,應該調動轉移支付的靈活性和主動性,減少中央的負擔,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