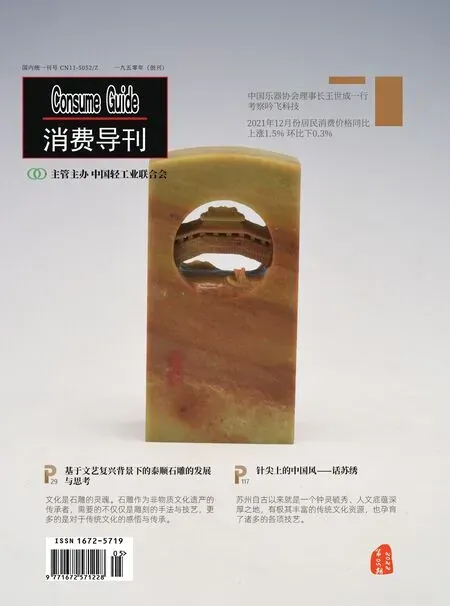中國海洋文化話語權(quán)建構(gòu)的三重邏輯
郭萬敏
廣東海洋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
隨著國際海洋競爭由單領(lǐng)域轉(zhuǎn)向多領(lǐng)域,海洋文化話語權(quán)等“軟實力”在競爭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顯。然而,以西方海洋文化為中心的示范效應(yīng)不斷擴大,表現(xiàn)為表面的多元海洋文化交流與對話,實則為呈單向度態(tài)勢,世界海洋文化話語權(quán)仍由西方發(fā)達國家主導(dǎo),中國處于弱勢地位。隨著中國“海洋強國”戰(zhàn)略及海洋崛起進程的推進,建構(gòu)能提升中國在世界海洋文化交流中的話語權(quán)的海洋文化已十分迫切。
根據(jù)話話權(quán)理論可知,海洋文化話語權(quán)的實現(xiàn)依賴于主體與客體(或“他者”,本文特指其他國家與民族。下文兩種提法交替使用——筆者注。)雙向互動。是主體通過海洋文化話語的表達、傳播在實現(xiàn)自身影響力的同時增強客體對其所表達的海洋文化話語的認同。認同程度的高低決定了海洋文化話語權(quán)的“力量”,這種“力量”能將國家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動員力變現(xiàn)為“他國”的自覺認同與自愿追隨[1]。因此,應(yīng)基于獲得這種“力量”的考量,要求所建構(gòu)的海洋文化話語應(yīng)該是能使客體愿意聽、聽得到、聽得明、愿回應(yīng)和愿參與的話語體系。這意味著海洋文化話語需具備能有被客體愿意聽的價值邏輯,有能夠被客體聽得到、聽得明的話語邏輯和有產(chǎn)生設(shè)置議題并得到客體回應(yīng)和參與的實踐邏輯。
一、重構(gòu)中國海洋文化的價值邏輯
海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只有與客體產(chǎn)生“共鳴”才會被客體愿意聽聞,話語才有轉(zhuǎn)化為“文化力”的可能。因此,中國所重構(gòu)的海洋文化話語在價值邏輯上應(yīng)注重中國“特殊性”的價值取向的同時,融合進“他者”的具有“普遍性”價值偏好。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所強調(diào)的“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dāng)代,關(guān)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讓“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fēng)格、中國氣派”[2]那樣,在新時代重構(gòu)中國海洋文化應(yīng)繼承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海洋文化,立足新時代中國海洋強國戰(zhàn)略實踐,借鑒“他者”海洋文化所長;要在挖掘中國海洋文化的歷史中把握當(dāng)代海洋文化旨歸,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中國優(yōu)秀的海洋文化歷史資源;要在“關(guān)懷人類、面向未來”的宏大視野中,與世界多元海洋文化交流與借鑒;要在綜合創(chuàng)新中體現(xiàn)海洋文化建構(gòu)中的中國特色、中國風(fēng)格和中國氣派[3]。
第一,中國海洋文化命運多舛,但從未消亡,其優(yōu)秀的海洋文化價值理念理應(yīng)在當(dāng)代被發(fā)揚。在新時代重構(gòu)中國海洋文化時應(yīng)摒棄陸主海從的傳統(tǒng)文化觀,正視中國文化乃是復(fù)合型文化,客觀的重拾和補綴傳統(tǒng)海洋文化的優(yōu)秀價值理念,結(jié)合于新時代海洋文化的發(fā)展,回應(yīng)當(dāng)代世界海洋文化交流與發(fā)展,推動中國海洋文化價值理念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向,在面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與時俱進,延續(xù)生生不息的海洋文化生命。
第二,立足當(dāng)代、面向未來,創(chuàng)新中國海洋文化價值理念。“當(dāng)前,中國正處于由陸向海、由大向強轉(zhuǎn)變的重要歷史階段”[4],走向海洋已然成為中國崛起的必由之路。與此同時,國際海洋競爭已從單領(lǐng)域轉(zhuǎn)向多領(lǐng)域,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制定本國的海洋發(fā)展戰(zhàn)略,參與到世界海洋發(fā)展的“藍色爭鋒”中,其中海洋文化話語權(quán)等“軟實力”在爭鋒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這是區(qū)別于大航海時代的“武力爭鋒”下的,“慎用武力”的海洋合作與發(fā)展的價值偏好的體現(xiàn)。而中國海洋文化所具備的“對外和平的開放性”特質(zhì)正好契合了這一價值偏好。故此,中國海洋文化重構(gòu)應(yīng)從價值取向維度的視角,繼續(xù)伸張中國海洋文化所具有和平開放性,立足于建設(shè)“21世紀(jì)海上絲綢之路”的當(dāng)代,面向構(gòu)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未來,將這一世界“慎用武力”“合作與發(fā)展”的價值融進新時代中國海洋文化重構(gòu)中,凝練出“親、誠、惠、容”[5]為核心價值的“和諧海洋文化”。
第三,吸收“他者”海洋文化所長,開創(chuàng)包容互鑒的海洋文化格局。中國海洋文化具有開放與包容的特質(zhì),在世界多元海洋文化交流中,能以開放包容的姿態(tài)吸收和借鑒“他者”海洋文化所長,開創(chuàng)“既包容西方又超越西方,為人類海洋文明開創(chuàng)新的時代”[6]的,面向世界的包容互鑒的海洋文化格局。當(dāng)然,基于主體性的維度,新時代中國海洋文化的重構(gòu)必須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干擾,將更多的研究集中于中華民族自身的海洋文化價值邏輯上,“他者”海洋文化只能是吸收和借鑒的對象。如此方可保證所重構(gòu)的海洋文化的價值邏輯是中國本土的,同時又因有“他者”的價值融合,而易于為“他者”所認同和接受。
二、重構(gòu)中國海洋文化的話語邏輯
海洋文化價值邏輯解決的是客體愿意聽的問題,而充分、嚴(yán)謹(jǐn)?shù)脑捳Z體系能將海洋文化的思想內(nèi)容傳遞給客體,解決的是客體能聽聞和聽得明的問題。包括話語內(nèi)容建構(gòu)和話語內(nèi)容傳播兩部分。話語內(nèi)容建構(gòu)的充分與嚴(yán)謹(jǐn)決定了話語的“質(zhì)量”,話語內(nèi)容傳播渠道的寬與窄決定了話語的“音量”。
第一,話語內(nèi)容建構(gòu)。充分、嚴(yán)謹(jǐn)?shù)脑捳Z內(nèi)容建構(gòu)是必要的,否則核心價值理念再好的海洋文化亦不能被充分表達,不能被客體所聽聞、所理解,更無從談起認同。且話語內(nèi)容建構(gòu)的邏輯體系越完整、越充分,所起議題設(shè)置能力越強,話語權(quán)也就越強。在海洋文化話語內(nèi)容的建構(gòu)上要做到:一方面要充分發(fā)揮學(xué)界專家主力軍的作用。學(xué)界專家有著高深的理論功底,經(jīng)過他/她們的專業(yè)性研究后能解構(gòu)“西方中心論”,建構(gòu)起完整的中國海洋文化話語體系,并打破西方學(xué)術(shù)話語的壟斷;能提升海洋文化話語的質(zhì)量,保證話語的邏輯性和創(chuàng)新性;能充分運用翻譯技巧,讓海洋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能有效傳播。另一方面,要注重政府在海洋文化話語內(nèi)容建構(gòu)中的主導(dǎo)性功能。有政府的參與,話語建構(gòu)能借助于政府權(quán)力的力量將其作為一項國家工程來推動,如此可保證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nèi)完成建構(gòu)任務(wù)。因為政府能為其提供制度供給和財政支持,能有效調(diào)動各方資源形成合力推動建構(gòu)任務(wù)的完成,也能在涉外交流中的聲明、講話、談話及發(fā)文中為中國海洋文化話語內(nèi)容建構(gòu)指明方向,尤其是對海洋文化的核心理念起著導(dǎo)向性的功能。
第二,話語的傳播。話語傳播的有效性,是話語能被聽聞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在中國海洋文化話語的傳播上應(yīng)建構(gòu)包括國家政府層面、學(xué)者、企業(yè)、媒體、公眾等參與的全方位的有效的傳播路徑。應(yīng)在國家的引導(dǎo)下,建立起有效的傳播機制,打造出多樣的、先進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話語載體,如媒體、大師級的專家、高質(zhì)量的海洋文化產(chǎn)品等,形成強大的傳播合力,達至話語的有效傳播。
當(dāng)然,政府作為傳播的一個重要渠道,在話語傳播上應(yīng)少些“硬”,多些“柔”。即淡化官方的宣傳,多些如“和諧”、“和平”、“合作”、“共贏”、“誠信”等具有“柔”性的詞;在一些海洋文化的專業(yè)新聞報道中應(yīng)多采取“暖”的報道的方式,增加人文、世界環(huán)境、海洋治理等合作議題的內(nèi)容。例如在與東南亞國家的海洋文化交流中,可將歷史上形成的“東漢海洋文化圈”作為共同的“文化情感”,與這些國家形成海洋文化話語的“共情”,讓其易于接受和認同當(dāng)代中國海洋文化。
三、重構(gòu)中國海洋文化話語的實踐邏輯
根據(jù)實踐理論可知,話語可以促進實踐,實踐又會強化或弱化話語,話語與實踐一起促進形成話語議題設(shè)置的實踐共同體[7],影響話語權(quán)的強與弱。中國海洋文化要在世界海洋文化的交流中贏得話語權(quán),則需加強海洋文化話語的實踐邏輯建構(gòu),實現(xiàn)能“行事”,能“成事”。即需將中國海洋文化所承載的價值理念改造為海洋文化議題設(shè)置,并積極實踐,同時以“共同利益”為目標(biāo)指向,以“合作開發(fā)”為形式吸引“他者”參與。可見,中國海洋文化話語權(quán)的提升絕不是走“文化殖民擴張”與“文化霸權(quán)”的道路,而是以言行一致的實際行動來向世界展示中國“和合”的海洋文化價值理念,表達中國愿意同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們的合作誠意。
第一,言行一致的實踐中國海洋文化議題設(shè)置。在世界海洋文化的交流中,中國作為海洋文化議題設(shè)置者與實踐者,應(yīng)將中國海洋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融入議題設(shè)置中,并在行動上保持一致,做到言行一致。議題設(shè)置應(yīng)盡可能的體現(xiàn)“合作”“和平”“共同”“和諧”“誠信”“開放”“包容”等價值偏好,且在實踐中始終做到誠信、負責(zé)、有擔(dān)當(dāng)、不搞霸權(quán)、不“以大欺小”,將中國愿意與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的真誠合作的姿態(tài)以實際行動在世界海洋文化的交流平臺上呈現(xiàn)。當(dāng)然,在涉及國家主權(quán)等原則性的問題,中國海洋文化的“硬氣”仍需繼續(xù)保持,絕不能因為“柔”而放棄該有的“硬”。
第二,吸引“他者”的參與與認同。在世界海洋文化的交流與實踐中,中國一直秉持尊重多元文化主體最大化的價值取向,使多元文化主體能在海洋文化利益博弈中相互理解、彼此尊重、求同存異,實現(xiàn)包容性發(fā)展,完成利益共享。從價值邏輯到話語邏輯,再到實踐邏輯,讓每個海洋文化主體作為“海洋命運共同體”中的利益相關(guān)者,讓其能主動作為,發(fā)揮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力,致力于促進主體之間的利益均衡,找到利益共同點和合作點,以促進利益共同體的形成,并統(tǒng)一于一個宏觀的人類海洋命運共同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