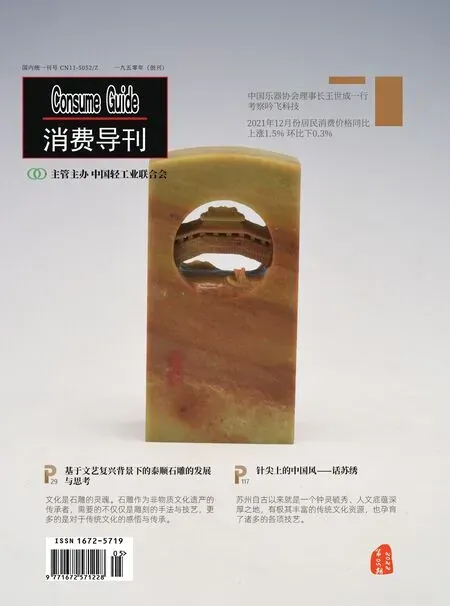新準則下企業金融資產管理的挑戰和建議
馬曉男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商學院在職人員高級課程研修班學員
引言:我國經濟正處在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制造業等實體產業面臨著經營環境趨緊、運營成本剛性上漲、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等發展困境,一些非金融企業紛紛開始配置金融資產。據Wind數據統計,2017年共有1221家上市企業購買了金融產品,同比增加59.2%,購買金額同比增加84.9%,其中,有1099家企業配置金融資產的總額過億元。
一、新舊準則分類概述
金融資產的分類依據從按照多維的判斷標準和識別特征到只以業務模式和合同現金流特征劃分,從原來的四分類: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貸款和應收款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和持有至到期,到現在的三分類:以攤余成本計量,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和以公允價值的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二、背景
當前,中國企業正面臨國內經濟下行及國際貿易萎縮的雙重壓力。同時,由于房價上漲、人口老齡化、環保加強等原因,使得企業的土地、人力、環境等成本不斷上升,利潤空間受到不斷擠壓。然而,與實體經濟利潤下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金融業利潤率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為應對主營業務回報不確定性,分享金融業利潤,改善企業盈利狀況,非金融類企業通過各種方式進入金融業,其中最常見的方式就是配置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配置雖然有利于改善企業盈利狀況,分散企業經營風險,但也擠占了企業用于主業發展的資源,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當前,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已成為現代企業的管理方向,越來越多的企業注重企業價值管理,將企業價值最大化作為企業經營管理的最終目標。因此,研究金融資產配置是否有利于企業價值以及如何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金融資產配置、生命周期與企業價值
處于成長期的企業內部都存在大量投資機會,主營業務收益高,也需要大量企業資源,配置金融資產對企業經營構成嚴重負面影響,不利于企業價值。同時,處于成長期的企業缺乏發展資金,急需從外部融資,配置金融資產可以緩解融資約束,有利于企業經營活動,對企業價值產生正面影響。因此,處于成長期的企業配置金融資產會產生正、負兩種效應,兩種效應相當,產生了中和反應,相互抵消,使得金融資產配置對處于成長期企業的企業價值影響不顯著。處于成熟期的企業,產品和服務在市場中已經享有較高的品牌知名度,市場占有度較高,產品銷量和企業盈利較為穩定。同時,產品市場趨于飽和,企業已經過了快速增長期進入平穩發展期,增長速度放緩。因此,處于成熟期的企業,將主業經營獲取的閑置資金投資于金融資產,能夠提高企業經營效益,有利于企業價值的提升。雖然配置金融資產對企業的主營業務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負面影響效應較小,因而最終表現為正效應,即金融資產配置提升了成熟期企業的企業價值。
四、融資約束與企業資產金融化
與“蓄水池”理論和“投資替代”理論不同,“實體中介”理論并不是從金融資產的屬性出發,而是從企業的融資約束角度來解釋新興市場國家企業資產金融化現象。事實上,“實體中介”理論是基于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來更加廣泛地識別企業金融化的行為,其理論基礎源于融資優序理論,即企業進行投資時會優先采用內部資金,其次是外部資金。利用這一思路來識別企業金融化,并提出了“實體中介”理論,該理論認為由于銀行融資歧視的存在,一些企業容易從銀行獲得資金,但是其生產效率不高,因此這些企業便將從銀行獲得的低成本資金轉貸給其他不易獲得銀行貸款的企業。因而這類企業的行為在學術界被稱為“為貸而借”,而這類企業也被稱為“實體中介”。在十大產業政策出臺以后,為了擴大內需,刺激消費需求所實施的政府補貼、減免稅收、出口退稅、鼓勵金融機構提供貸款以及支持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等措施,都直接為企業獲得資金提供了便利,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企業的外部融資約束。根據“實體中介”理論,十大產業政策的實施實質上是帶來了政策融資歧視,相比產業外的企業,產業內企業更容易獲得資金,因此十大產業內的企業可能會由于融資約束的緩解而成為“實體中介”,將資金通過金融市場轉貸給需要資金的企業,導致產業內企業資產金融化水平上升。
五、企業面臨的挑戰
權益工具投資分類的困難,因為新準則下以攤余成本法計量的和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需要滿足持有目的和合同現金流量測試,使得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將接受更多未滿足條件的金融資產。例如,可供出售金融工具、衍生工具、權益工具因為不能通過現金流量測試,只能進入以公允價值計量的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或者計入以公允價值計量的且其變動計入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中去,且一經選擇不得改變,使得權益工具的分類存在選擇困難。
六、研究假設
第一,從企業內部金融投資決策者角度來看,使用內源融資投資金融資產給自己留有較大的選擇余地,因而主觀上更傾向于使用內源融資進行金融投資。內源融資具有低風險的特點。使用內源融資投資金融資產過程中,如果金融資產價格短期內發生向下波動,可以選擇繼續持有以等待價格反彈。而如果使用外部融資金投資金融資產,標的資產價格下跌往往疊加外部融資成本上升,資產縮水疊加融資困難,尤其是多家企業同時出現這種情形時,將不得不降價拋售相應資產,造成實際損失。第二,從企業經營所處的制度環境來看,法律法規限制和懲罰企業使用募集資金投資金融資產。《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辦法》《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細則》等均對非金融企業募集資金(包括IPO募集資金和再融資募集資金)做出限制性規定,要求募集資金使用項目原則上應服務于主營業務,不得為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借予他人、委托理財等財務性投資,不得直接或者間接投資于以買賣有價證券為主要業務的公司。綜上可知,盡管企業可以一定程度上規避對募集資金和信貸資金用途的監管,私自變更資金投向、進行金融投資,但使用外部資金畢竟會受到來自外部投資者和監管部門的監督,導致上市公司對于使用外部資金進行金融投資有所顧忌。相比之下,企業使用內源融資進行金融投資受到的限制更少,這將導致企業更傾向于使用內源融資進行金融投資。在研究美國上市公司金融投資資金來源時也發現,外部投資者不會為企業的金融投資行為融資,企業只能依賴內部融資進行金融投資。
七、對企業管理的建議
(一)引入信息系統,量化風險
引入信息系統,量化企業信用風險。如風險參數、違約損失率、風險敞口,債項回收率等優化減值模型使新減值政策更好地運行。新減值模型:第一階段——當風險未顯著增加,計提12個月內的減值,第二階段——風險顯著增加,計提整個存續期間的減值損失。通過量化風險并根據風險大小更準確地區分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以及對減值損失的量化,尤其處于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對整個存續期間的減值進行估計,主觀性和不準確性更強。信息系統的運用有助于減少對會計人員專業判斷的依賴和主觀色彩,也有助于企業更好地運行新準則。
(二)合理配置資產,符合戰略需求
新政策仍保留有盈余管理的空間,企業可以通過金融資產的減值及轉回、公允價值的變動、金融資產的重分類以及關聯方交易等對報表進行操縱,從而模糊企業的風險管理意識。對投資主導性和經營和投資并重性的企業,由于金融資產的配置占比較大,資金管理更為重要。企業需要提高資產配置水平,配置不同風險的金融資產,使得風險錯配,避免相同風險源引起的風險水平變動對資產價值的沖擊。同時資產配置的規模和比例需滿足企業的戰略需求,同時也要考慮資金的占用期和機會成本,和企業戰略目的的吻合程度。
結束語:進一步研究表明,與國有、低環境不確定性和低市場化水平的企業相比,配置金融資產對非國有、高環境不確定性和高市場化水平的企業而言,投融資期限錯配的加劇效應更加明顯。最后的作用機制研究證實,銀行可以有效識別企業配置金融資產的機會主義行為,并通過增強對企業的融資約束加劇企業投融資期限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