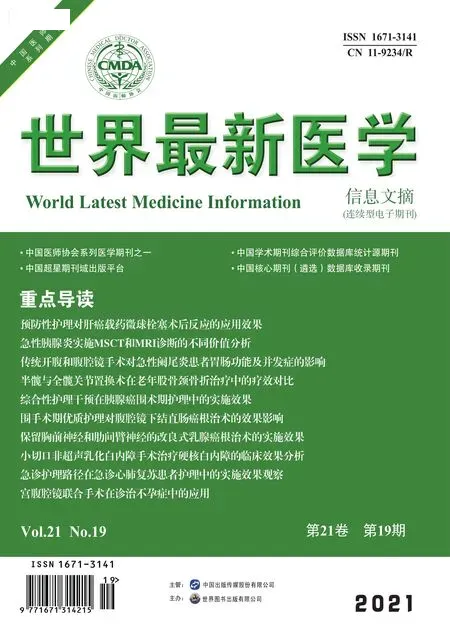Caprini 風險評估量表在神經外科重癥患者下肢深靜脈血栓風險評估中的應用
李超,郭修紅,胡安強
(清鎮市第一人民醫院 重癥醫學科,貴州 貴陽 551400)
0 引言
下肢深靜脈血栓(DVT)是神經外科患者術后常見的并發癥,其發生率為19%~50%[1],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很可能會誘發遠期下肢靜脈功能障礙或致命性肺栓塞[2]。本研究使用Caprini風險評估量表分析神經外科重癥患者發生下肢深靜脈血栓(DVT)的風險,為臨床預防提供一定的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我院ICU收治的神經外科重癥患者58例。,其中男50例,女8例,年齡(52.09±14.96)歲,入院GCS評分(5.66±3.45)分。住院期間經下肢血管B超共檢出DVT 7例,發生率12.07%。
1.1.1 納入標準:經病史、體查及頭顱CT檢查證實為自發性腦出血或重型顱腦損傷患者,前者包括基底節區腦出血、丘腦出血、腦葉出血、腦干出血;后者包含腦挫裂傷、原發性腦干損傷、顱內血腫、彌漫性軸索損傷等復合病變者,格拉斯哥評分(GCS)<8分,均需入住ICU行機械通氣等監護治療。
1.1.2 排出標準:入院不足72小時、輕中型顱腦損傷、GCS評分大于8分者、已知腫瘤或血液系統疾病等。
1.2 方法。本研究采用2009年修訂的Caprini風險評估模型對患者進行VTE風險評估。該模型由Caprini等人于2005年研制[3],并于2009年進行修訂,國外已有大樣本研究證實該模型可有效地預測住院患者VTE發生風險。Caprini評估量表包括年齡、既往VTE史、臥床、手術方式、中央靜脈通路、合并心力衰竭、肺炎、外傷骨折、腦卒中、凝血物質異常等37個危險因素,按危險系數分為1分項-5分項,每項相加累計得分即為患者的VTE風險總分,按總分將患者分為低危(0~2分)、中危(3~4分)、高危(≥5分)3個等級。分別于入ICU及住院1周時進行VTE風險評分并檢測患者血小板、纖維蛋白原,于住院2周時行下肢血管B超檢查。所有患者住院期間均使用間歇氣壓裝置預防DVT。
1.3 統計學處理。使用SPSS 19.0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VTE風險評分、血小板(PLT)、纖維蛋白原(Fg)。入ICU時,患者VTE風險評分為(8.12±3.14)分,住院1周時VTE風險評分為(9.84±3.11)分,與入ICU時比較,住院1周時患者VTE風險評分、PLT、Fg均明顯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VTE風險評分、PLT、Fg
2.3 VTE風險分級及危險因素。與入ICU時比較,住院1周時VTE低、中、高危患者構成比無明顯差異(P>0.05),但VTE危險因素呈上升趨勢,其中以臥床>7 2小時、發生肺炎、中央靜脈通路明顯增加(P<0.05),見表2。
3 討論
神經外科患者由于創傷、長期臥床、合并肢體癱瘓、甘露醇或其他高滲液體及止血藥的使用等因素,易并發下肢深靜脈血栓(DVT),DVT形成不僅影響患者肢體功能及預后,嚴重者可因血栓脫落導致急性肺栓塞而猝死,是神經外科嚴重并發癥之一[4]。已有大樣本研究證實Caprini風險評估模型可有效地預測住院患者VTE發生風險[5-6],中華醫學會骨科學會明確推薦應用Caprini風險評估模型對骨科大手術患者進行VTE風險評估[7]。本研究中,神經外科重癥患者入ICU時VTE風險評分(8.12±3.14),高危患者占比達86.21%(50例),隨著臥床時間延長、并發肺炎、中央靜脈通路等因素的影響,VTE風險評分逐步增加,住院1周時VTE風險評分升高至(9.84±3.11)分,高危患者占比高達96.55%(56例),表明神經外科重癥患者入院早期及住院期間具有VTE高危風險,與學者胡智洪等[8]研究相一致。

表2 VTE風險分級及危險因素
血液高凝狀態是血栓形成的三大基礎之一。顱腦損傷患者由于嚴重的腦組織挫傷、顱內出血、腦水腫、合并缺氧、酸中毒、休克等多種因素,機體容易出現高凝狀態,導致局部和(或)全身血栓形成。本研究觀察到神經外科重癥患者,隨著住院時間的延長,血小板計數及纖維蛋白原水平均較入院時明顯增加,提示患者血液逐步呈現一種高凝狀態,這可能是神經外科重癥患者DVT發生的機制之一。目前臨床上多采用機械方法如間歇氣壓療法(IPC)等措施早期預防神經外科重癥DVT,本研究患者均使用了IPC,但經下肢血管B超仍檢出DVT 7例(發生率12.07%),說明對于神經外科重癥患者機械預防措施效果有限,與前期我們的研究[9]結果相符合。肺血栓栓塞癥診治與預防指南[10]推薦Caprini風險評估為高危患者使用藥物或藥物聯合機械預防DVT,但這是否適用于神經外科重癥患者,尚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總之,神經外科重癥患者住院期間具有較高VTE 發生風險,臨床應加以重視并采取積極的早期預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