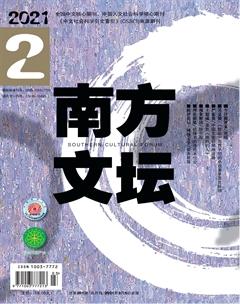在文本內(nèi)外
2017年,我寫(xiě)過(guò)一篇題目類(lèi)似的文章,談王安憶早期作品與她插隊(duì)經(jīng)歷的關(guān)系。所謂“內(nèi)”,是指她插隊(duì)的人生波折;所謂“外”,是指她的知青題材小說(shuō)。我以為,僅從作品層面,是很難進(jìn)入王安憶的文學(xué)世界的,而只有深入細(xì)致地挖掘其人生經(jīng)驗(yàn)的復(fù)雜成分,才弄得清楚她“為什么寫(xiě)”的問(wèn)題。
我這里所說(shuō)“在文本內(nèi)外”,可能與上述稍有不同。所謂“內(nèi)”,是指批評(píng)家與作家的關(guān)系;所謂“外”,則是批評(píng)家怎樣來(lái)看作家的作品。在文學(xué)批評(píng)活動(dòng)中,或隱或現(xiàn)地反映著批評(píng)家與作家的關(guān)系,但這不是他們生活中的關(guān)系,而是批評(píng)家與作家的關(guān)系。
確實(shí),批評(píng)家與作家是兩種不同的角色。批評(píng)家在從事對(duì)作家作品的批評(píng)活動(dòng)時(shí),既是一位讀者,也好像是對(duì)作家個(gè)人的情況比較熟悉的朋友。正因他是一位讀者,才知道讀者在閱讀文學(xué)作品時(shí)的心理期待;他又不能只是讀者,而是一位比讀者更了解作家生活觀念和生活態(tài)度的朋友。他不是冷淡地站在作家的世界之外,而是設(shè)身處地進(jìn)入其心靈活動(dòng)之中,體貼地觸摸和猜想這些隱秘的心理活動(dòng)。我把這種“設(shè)身處地”和“觸摸”,稱(chēng)之為“入其內(nèi)”的批評(píng)經(jīng)驗(yàn),沒(méi)有這種經(jīng)驗(yàn)做底子,他的批評(píng)文章就會(huì)與作家的真實(shí)一面很“隔”。
盧卡奇有一篇題為《〈農(nóng)民〉》的批評(píng)文章,分析巴爾扎克一部不那么引人關(guān)注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要講,盧卡奇與巴爾扎克不是同時(shí)代人,然而,這篇文章為什么那么了解巴爾扎克“這個(gè)人”呢?我認(rèn)為就是他“入其內(nèi)”了,真正進(jìn)入批評(píng)對(duì)象的個(gè)人世界中去了,而且是非常了解的那種“熟悉”。他說(shuō),在很年輕的時(shí)候,巴爾扎克就寫(xiě)過(guò)一本小冊(cè)子,主張?jiān)谵r(nóng)業(yè)社會(huì)向工業(yè)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過(guò)程中,反對(duì)拆散大莊園,主張維持長(zhǎng)子繼承權(quán),像英國(guó)那樣,即使經(jīng)歷工業(yè)革命那樣激烈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也依然完整地把貴族莊園和文化傳統(tǒng)保留了下來(lái)。也就是說(shuō),在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的過(guò)渡之間,需要有一個(gè)英國(guó)1648年“光榮革命”那樣的妥協(xié)方案。他的意思是,英國(guó)成功地在巨大轉(zhuǎn)型活動(dòng)中,讓大莊園發(fā)揮了它的社會(huì)作用和社會(huì)義務(wù),即是在社會(huì)變遷中的壓艙石的作用。從巴爾扎克的個(gè)人矛盾,到他對(duì)《農(nóng)民》這部小說(shuō)的批評(píng),盧卡奇敏銳抓住了作者擔(dān)心文化毀滅的歷史心情。他說(shuō),正是這種矛盾,體現(xiàn)了巴爾扎克作品的“偉大性”。
其實(shí),每個(gè)作家的創(chuàng)作史中,都有一個(gè)這樣那樣的“歷史心情”。這是認(rèn)識(shí)一個(gè)作家內(nèi)心世界的最關(guān)鍵的一點(diǎn),即我所謂“入其內(nèi)”的說(shuō)法。
但是,對(duì)一個(gè)批評(píng)家來(lái)說(shuō),僅僅“入其內(nèi)”也不夠,還應(yīng)該“出其外”。所謂“出其外”,就是一定不能被作家這個(gè)人束縛住,而需要從這個(gè)漩渦中走出來(lái),站得比作品更高一點(diǎn),去體諒作家內(nèi)心世界的想法,也就是“歷史的心情”,是在他具體的作品中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實(shí)現(xiàn)。一般說(shuō)來(lái),作家的這個(gè)“內(nèi)”,和他的“外”結(jié)合得好不好的問(wèn)題,是決定這些作品哪些是他的“代表作”,而哪些只是他的“一般性作品”的一個(gè)取舍標(biāo)準(zhǔn)。
作家對(duì)自己的文學(xué)作品,有一套“好作品”和“壞作品”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但那只是作家本人的看法。批評(píng)家評(píng)價(jià)作家作品,因角色差異,以及他工作方式的不同,往往與作家不一樣。對(duì)比較高明的批評(píng)家來(lái)說(shuō),他對(duì)作家作品的取舍和評(píng)價(jià),經(jīng)常會(huì)是出乎意料,同時(shí)又是入情入理和富有啟發(fā)性的。這種評(píng)價(jià),會(huì)不同程度地修正作家的看法,影響讀者的閱讀,對(duì)文學(xué)史的構(gòu)成發(fā)揮長(zhǎng)時(shí)期的影響。
因此在我看來(lái),好的批評(píng)家和他較好的作家作品評(píng)價(jià)文章的出現(xiàn),恰好是批評(píng)家在批評(píng)活動(dòng)中,“內(nèi)與外”的關(guān)系協(xié)調(diào)得比較好的時(shí)候。
程旸,生于1985年,北京海淀區(qū)人,原籍江西婺源。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館第八屆客座研究員,現(xiàn)為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室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研究,兼及文學(xué)批評(píng)。近年來(lái)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領(lǐng)域是王安憶和路遙研究。在國(guó)內(nèi)核心學(xué)術(shù)雜志《文學(xué)評(píng)論》《文藝研究》《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文藝爭(zhēng)鳴》《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南方文壇》《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當(dāng)代文壇》《江漢論壇》發(fā)表多篇論文,為《文藝報(bào)》《光明日?qǐng)?bào)》《人民日?qǐng)?bào)》《文匯報(bào)》《讀者》撰稿多篇。不少文章被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復(fù)印資料全文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