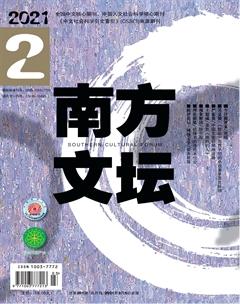史料學(xué)的文學(xué)史視野
一
最近幾年,一批優(yōu)秀的85后青年批評家和研究者開始進入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和批評的領(lǐng)域,成為一股新生的力量,程旸是他們中有代表性的一位。程旸在南開大學(xué)師從著名學(xué)者喬以鋼教授讀博,畢業(yè)后入職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室。我最初對他的印象,來自他幾次參加我主持的聯(lián)合文學(xué)課堂,程旸的幾次發(fā)言,條理清晰,要點得當(dāng),頗有見解。我還注意到他每次都準(zhǔn)備了相應(yīng)的文稿,打印在A4紙上。這讓我想起當(dāng)年讀書的時候,我的導(dǎo)師程光煒先生諄諄教導(dǎo)我們要認真治學(xué),不可虛言而逞口舌之快。那時候我直覺程旸如果從事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和研究,一定會做出一番成績。果然,在短短的數(shù)年之內(nèi),他寫出了一批高質(zhì)量的論文,發(fā)表在很多重要的雜志上,成為現(xiàn)代文學(xué)館的客座研究員,我也時常從身邊的朋友那里聽到對他為人為文的肯定和贊許。這樣看來,程旸選擇了一條適合他個性和興趣的道路,雖然這條路才開始,卻已經(jīng)嶄露出“不一樣”的頭角。
程旸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王安憶,從目前發(fā)表的文章來看,主要圍繞王安憶、莫言、路遙、王朔等作家,其中尤其以王安憶和路遙的文章為最。也就是說,程旸關(guān)注的是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的“50后作家群體”。就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來說,“50后作家”一直是一個特有的富礦,這不僅僅是指這些作家大都已經(jīng)獲得相應(yīng)的文學(xué)史位置,擁有大量豐富的前期研究成果,更重要的還是因為這一批作家與其他代際作家相比,其寫作實踐具有不可替代的長度和寬度。就長度來說,這一批作家從1970年代后期開始從事寫作,大部分人如王安憶、賈平凹、莫言等都是“長跑能手”,其寫作時間甚至超過了很多現(xiàn)代作家的生命長度。更重要的是,這種長度不是一種均質(zhì)性的展開,而同時是在斷裂和延續(xù)的多種層面上螺旋遞進,比如柳青和路遙,在蔡翔看來,柳青和路遙的關(guān)系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影響與被影響的關(guān)系,同時也是當(dāng)代文學(xué)中兩個文學(xué)傳統(tǒng)——“十七年文學(xué)”與80年代文學(xué)——之間互動生成的關(guān)系,柳青和路遙由此在內(nèi)在性上統(tǒng)一于“當(dāng)代中國”的“情感結(jié)構(gòu)”中。從寬度上看,50后這一批作家由于歷史的機緣,使得其文學(xué)實踐與社會實踐密切關(guān)聯(lián),王安憶與知青文學(xué)、韓少功與尋根文學(xué)、莫言和余華與先鋒文學(xué)、路遙與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等,無不從不同的層面立體式地展示著文學(xué)社會學(xué)的視野,即使一度以“敘事圈套”、解構(gòu)著稱的馬原、王朔等,也帶有明顯的社會歷史指向。“50后作家群”這個富礦由此擁有了豐富的礦脈,在不同的層面上產(chǎn)生了一種如韋勒克所謂的文學(xué)的“結(jié)構(gòu)性”,在這個意義上,確實是文學(xué)史研究的絕佳樣本。眾所周知,因為當(dāng)代文學(xué)的“進行時”屬性,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一直有“研究”與“批評”之爭,很多研究者尤其是年輕的研究者,往往容易被當(dāng)代文學(xué)生動鮮活同時不可避免的“魚龍混雜”弄得眼花繚亂,甚至是茫然無措,因為找不到方向而浪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程旸的高精準(zhǔn)定位使得其一開始就占有了先機,很顯然,他無意做一個批評家,他更愿意做一個研究者,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思路、方法和行文方式。
二
在《路遙在延安大學(xué)》這篇文章中,程旸開篇就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相對于路遙的《山花》時期,延安大學(xué)才是路遙真正的起點……是一次真正的質(zhì)變”①。這篇文章是一篇典型的作家“前史”和“生活史”的研究,文章從路遙的考試、錄取說起,通過不同資料的征用詳細敘述了路遙當(dāng)年一波三折的入學(xué)經(jīng)歷,由此不但可以看出路遙那一代人求學(xué)的艱難,也部分還原了1970年代中國高校招生錄取的特殊機制。然后文章又從“生活、讀書和寫作”的角度進一步展開對路遙大學(xué)時代的詳細考察,其中尤其對路遙閱讀的敘述最為充分,通過對不同傳記材料的仔細梳理,全面勾勒了路遙大學(xué)時代的閱讀地圖:基本上是外國文學(xué)名著,尤其以法俄兩國作家的作品為主。在方法上“泛讀”和“精讀”結(jié)合,尤其以“精讀”為主,以至于留給大學(xué)同學(xué)最深的印象是翻爛書——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翻爛了三本!通過這樣詳盡可信的敘述,一個生動逼真的文學(xué)青年的形象如在眼前,由此得出“延安大學(xué)時期是一個質(zhì)變,是真正的起點”②也就順理成章了。
另外一篇文章《路遙〈人生〉中巧珍的原型》繞開了《人生》的男一號高加林,而將目光聚集到女一號劉巧珍身上,這種聚集,又不是以批評的方式對這一形象進行再建構(gòu),而是試圖從文本之外去為之尋找發(fā)生學(xué)意義上的原型。這是這篇文章視角的新穎之處,我手頭正好有一本路遙的研究資料,隨手一翻,發(fā)現(xiàn)解讀劉巧珍形象的文章相對較少,而從原型這一角度去分析劉巧珍的研究文章幾乎沒有,在這個意義上,這篇文章有了填缺補漏的價值。我自己也寫過幾篇解讀路遙作品的文章,但幾乎每次的視角都集中在高加林身上,劉巧珍成了附屬般的存在,這暴露了我研究的盲點,因為太過熱衷于建構(gòu)高加林的形象和價值,而忽略了小說文本作為一個結(jié)構(gòu)性的整體,其中的任何一個人物都有其不可代替的結(jié)構(gòu)性功能。舉個例子,《人生》中的德順老漢,以前我一直覺得只是一個更加附屬性的人物,但這兩年我反復(fù)重讀作品,發(fā)現(xiàn)德順老漢的聲音其實構(gòu)成了一個“執(zhí)拗的低音部”,這一低音部代表著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和倫理道德,并對高加林所代表的現(xiàn)代美學(xué)和現(xiàn)代性道德進行勸誡和召喚,從而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種對話和制衡的關(guān)系③。在程旸的這篇文章看來,劉巧珍不僅有原型,而且是多個現(xiàn)實人物在文本中的美學(xué)投射,她并不和現(xiàn)實中的人物構(gòu)成一一對應(yīng)關(guān)系,但也不是完全的無本之木、無水之源。由此程旸提出一個更加文學(xué)史化的問題,“作者與人物難以避免地在人生道路某一階段出現(xiàn)相互疊合和移情的現(xiàn)象”,而且“作品與人物原型處于有明顯落差的不均衡狀態(tài)。不均衡讓路遙飽嘗愛情和婚姻生活的痛苦,一直到他生命的終結(jié)。然而不均衡又是典型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正是這種不均衡,才使得路遙的文學(xué)生活極具傳奇色彩。人們愿意對巧珍人物原型進行窮盡式考證,正因為對路遙大起大伏的人生經(jīng)歷懷揣著好奇心。不均衡還會不斷延長作家作品的生命,不斷為它們的傳播添柴加火”④。
程旸非常善于使用作者的傳記材料與作品進行對讀,發(fā)現(xiàn)作品中的蛛絲馬跡,從而一次次揭穿作品虛構(gòu)背后的歷史實存。另外一篇研究王安憶的文章《王安憶作品中的素材來源》集中體現(xiàn)了這種學(xué)術(shù)思路。這篇文章從王安憶2019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成長初始革命中》發(fā)現(xiàn)了王安憶數(shù)篇小說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和細節(jié)的痕跡,“王安憶說小說和現(xiàn)實不同,當(dāng)現(xiàn)實變成小說,就會脫離原型而發(fā)生變化。其實也不盡然。這篇回憶文章里,就散落著作者幾篇作品人物原型、故事和細節(jié)的痕跡,也有個別作品只稍微改換,把‘現(xiàn)實直接搬入……作家作品影射的是社會現(xiàn)實,有時也可以當(dāng)作作者的傳記材料來讀”⑤。文章從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是尋找虛構(gòu)作品中的素材來源,尤其對《富萍》中的保姆形象進行了鉤沉索隱,這一塊重在史料。另外一個方面則是追問素材如何變身為小說,這里面涉及創(chuàng)作的具體過程,有理論的色彩,程旸對此有很精準(zhǔn)的論述:“然而必須看到,‘素材跟‘作品的關(guān)系,并非只是削減或增容,對于作家極富創(chuàng)造力的大腦來說,對一部具體作品的誕生過程來說,它會比事先估計得周折復(fù)雜。”⑥在此我可以稍微補充一點例證材料,王安憶在20世紀(jì)90年代曾經(jīng)根據(jù)在上海與安徽交界處的白茅嶺女子監(jiān)獄的采訪寫成了一部紀(jì)實作品《白茅嶺紀(jì)事》,如果將這部作品與王安憶90年代的幾部小說《我愛比爾》《米尼》對讀,也會發(fā)現(xiàn)程旸所關(guān)注的這個問題,即《白茅嶺紀(jì)事》中的大量素材被挪用到了小說作品中,并在一定意義上能夠為王安憶1990年代的寫作美學(xué)提供更深層的解釋。⑦
程旸的另外兩篇文章《王安憶與徐州》和《寫在陜北》也值得注意。這兩篇文章都從文學(xué)地理學(xué)的角度去探討作家的生活經(jīng)驗與作品的隱秘關(guān)聯(lián)。前者集中于王安憶關(guān)于徐州題材的作品,借此勾勒出王安憶在1970年代的個人生活,由此豐富了王安憶的作家形象,其中有很多小細節(jié)很有文學(xué)史價值,比如,為了讓女兒王安憶能夠順利調(diào)回上海,著名作家茹志鵑想了很多辦法:“她于是寫了一篇散文,內(nèi)容是‘四人幫打倒了,大家很開心,在一列火車上旅客們說啊笑啊之類。媽媽感覺不錯,把散文重寫一遍,拿到《新華日報》發(fā)表了。后來,她又寫了篇一兩千的東西,又被媽媽送到了《光明日報》。”⑧這些細節(jié)為學(xué)理性的文學(xué)史書寫補充了人情味。《寫在陜北》則是要“研究當(dāng)代小說創(chuàng)作地點和題目的變更,有利于探尋作家創(chuàng)作、自然環(huán)境、文化認同和社會癥候相互交換的隱秘”⑨。通過對《人生》這部作品名字修改過程的詳細敘述,程旸試圖說明:“不少作品的題目與作者人生經(jīng)歷掛鉤,還受社會思潮刺激,它牽連作者對歷史進程的總認識,一定程度也內(nèi)含著文學(xué)修養(yǎng)、性格特征、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包括對文壇氛圍的敏感捕捉。”⑩這一觀點總體上是讓人信服的。
三
通過對程旸幾篇文章的簡單梳理,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色。第一,占有大量豐富的史料并能夠得當(dāng)?shù)厥褂煤图舨檬妨稀o論是路遙的研究還是王安憶的研究,程旸都使用了大量的史料尤其是傳記資料,程旸對作家的生活經(jīng)驗、生命歷程、作品與社會、作家與地理的關(guān)系有更大的學(xué)術(shù)興趣,這一傾向于“外部研究”的學(xué)術(shù)志趣對史料的要求極高。程旸對史料的使用可以說有一種窮盡的努力,往往一個觀點都有數(shù)個史料予以互證,這使得他的文章非常扎實、緊密,沒有什么空話。我們知道,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歷史化”和“史料化”是這些年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界的一個新潮流,雖然學(xué)術(shù)界對此有不同的態(tài)度,但都會承認一個基本的事實,在程光煒教授“80年代文學(xué)研究”范式的引領(lǐng)下,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得到了有效的加強。程旸顯然受益于這一潮流的觀念并分享了其積極的成果。
第二,雖然史料是程旸文章的基礎(chǔ),但是將這一基礎(chǔ)激活,并產(chǎn)生富有活力的問題意識,卻需要敏銳的作品感受力和理論想象力,這一點同樣能夠在程旸的文章中看到。比如在討論巧珍人物原型的那篇文章中,他就使用了美國政治學(xué)家戴維·比克奈爾·杜魯門的“不均衡理論”:“任何社會中,某一社會集團模式如果想保持相對的穩(wěn)定性、一致性、形式化以及普遍性,一個關(guān)鍵秘訣,就是如何保持集團內(nèi)部的均衡。”他由此出發(fā)將均衡理論轉(zhuǎn)化為對文學(xué)史結(jié)構(gòu)的考察,并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對任何一個當(dāng)代作家,也包括路遙,如何保持他們在文學(xué)史上的影響力,均衡理論將會發(fā)揮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在作家作品這個‘制度化集團內(nèi)部,有作家、作品、批評家、出版商、讀者等傳播管道,以及人物原型研究、作家史料文獻整理、作品當(dāng)時影響以及多年后的再發(fā)力等諸多復(fù)雜的組織化、形式化環(huán)節(jié)。就本文研究的作品與人物原型關(guān)系而言,會發(fā)現(xiàn)由于《人生》《平凡的世界》在社會和讀者的巨大影響,在當(dāng)時是不依賴于人物原型這個均衡因素的。”11這種通過跨學(xué)科理論的征用,發(fā)現(xiàn)問題的可能性,是程旸這一代青年學(xué)者的優(yōu)勢和長處。
第三,對歷史的同情理解。過于歷史化的研究往往會導(dǎo)致文學(xué)研究的社會學(xué)化,從而喪失文學(xué)研究的靈動以及與歷史之間的審美關(guān)系,因此,如何在歷史化和審美化之間找到一個平衡,是很關(guān)鍵的一點。程旸的文章總是在學(xué)理和史料中抱有一種歷史的同情之心,比如“由此可知,荒蕪動蕩的七十年代,年輕人的顛沛流離,像當(dāng)年的王安憶一樣乘坐夜行列車、輪渡,奔波于各個城市文工團考場的知識青年,一定有很多旅途苦澀的經(jīng)歷”12。又比如“其實兩人心里都明白,《人生》的巧珍就是林紅和林達。她們都曾經(jīng)把最純潔的愛情無私地獻給了路遙,雖然結(jié)局未必稱心如意。這是路遙感情生活中最吃重的部分”13。這是他審美的一面,他由此更深切地擁抱了作家作品,不僅僅是將他們作為客觀的研究對象,同時也是在投射自我,尋找理解和對話。有如此認真嚴謹?shù)膽B(tài)度,又有自覺的自我意識和同理之心,相信程旸會在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好。
【注釋】
①②程旸:《路遙在延安大學(xué)》,《文藝爭鳴》2020年第6期。
③楊慶祥:《路遙的多元美學(xué)譜系——以〈人生〉為原點》,《文學(xué)評論》2020年第5期。
④13程旸:《路遙〈人生〉中巧珍的原型》,《文藝研究》2019年第10期。
⑤⑥程旸:《王安憶作品的素材來源關(guān)于回憶文章〈成長初始革命年〉的故事和人物原型》,《文藝爭鳴》2020年第12期。
⑦楊慶祥:《阿三考——由〈我愛比爾〉兼及王安憶的寫作癥候》,《文藝研究》2015年第4期。
⑧12程旸:《王安憶與徐州》,《文藝爭鳴》2019年第8期。
⑨⑩程旸:《寫在陜北》,《文藝研究》2018年第7期。
11程旸:《路遙人生人物巧珍的原型》,《文藝研究》2019年第10期。
(楊慶祥,中國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