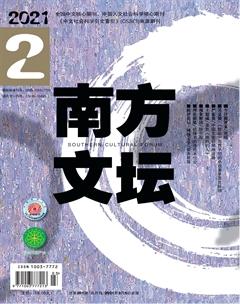那束誠摯而專注的目光
2014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南開大學范孫樓章閣廳,博士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面試。當叫到報考喬以鋼先生的考生時,一位高高大大的男同學走到我們對面,微微頷首后慢慢坐下,自我介紹到,他叫程旸,本科就讀于武漢大學,碩士階段在英國利物浦大學度過,學的都是法律。他的話一下子引發了我的興致,一則武漢大學是我的母校,二則是他完全跨專業。我琢磨,報考喬老師的學生那么多,他需要經歷怎樣艱難的博弈,才能脫穎而出;本碩都是名校,又是炙手可熱的法律專業,為什么偏偏轉向相對冷清的文學研究?面對導師組的提問,他很沉穩,應答自如,回答的什么具體內容已經模糊了,但記住了他回答我同時那束誠摯而專注的目光。
當年9月,程旸如期入學。開始,我在心里還是隱隱地替他捏一把汗,他的專業基礎是否牢靠,能不能順利地完成專業轉換?畢竟“隔行如隔山”啊!何況他碩士畢業已經五年,還能坐得住冷板凳嗎?半年下來,結果證明我的擔心是多余的。他們那級的博士生有十來個,能坐幾十人的教室略顯空曠,我發現他每次上課都坐在最后一排,幾乎不喝水,筆記也很少記,只是偶爾在筆記本上寫幾個字。更多的時候都在斂心傾聽,不時點點頭,目光始終看著你,誠摯而專注,容不得你不努力把課程講得深入、生動、精彩。每次見他,他都少有許多博士生那種焦慮之態,而是不溫不火、不急不躁、云淡風輕的樣子,說話也不緊不慢、有條不紊的;但在討論課和博士論文開題過程中,年紀輕輕的他卻是很有主見,思想的銳氣和沖擊力十足,像他平素的閱讀、思考、寫作一樣,在“慢”中透著一種“快”的風度。
博一時,程旸的科研優勢即有所展露,先聲奪人,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等名刊上發表有關莫言、王朔和當代小說家文學閱讀方面的文章;到了博士二年級,更是一發而不可收,更上層樓,將自己有關王安憶小說、夏志清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等視域的思考成果,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雜志刊布出來,和讀者分享,并因之在2016年獲得教育部特等獎學金,這種研究層次和高度在博士生中是少見的。至于畢業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后,陸續在《文藝研究》《當代文壇》《文藝爭鳴》等一系列刊物上,推出路遙《人生》中巧珍的原型、路遙小說創作地點及題目、路遙在延川與延安的兩份書單、王安憶與徐州等問題的考察成果,引起評論界的廣泛注意,自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系列成果的出籠表明,程旸已找到王安憶、路遙等相對穩定的學術陣地和研究視域,研究方法與個性也日漸成熟。他同樣立足于文學本體研究,畢業論文《地域視角與王安憶小說創作》在“文學尋根”、九十年代上海重新崛起和文化思潮等外部影響和作家內部轉型沖動的關系網絡中,探討王安憶20世紀90年代創作轉型問題,并結合王安憶及其作品文本,提出“軍轉二代身份”“弄堂人物檔案”等新穎的理論概念,刷新了王安憶研究的已有高度。但與文本研究并行不悖,他更注意史料意識,愿意也善于發掘文本現象背后的“本事”因素,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作家生活、地域文化、作品原型、書名變遷等因素中,找尋它們和作品之間關系的蛛絲馬跡。如果說程旸最早的“閱讀研究”,是想通過“閱讀”討論“創作”,完成從“閱讀史”到“創作史”的考察與再研究,那么后來對路遙、王安憶等個人經歷、作品發生環境、人物來源的某些發掘和考察,就更自覺地延續了這條路線。
實話說,那種“本事”以及和“本事”相關的研究,以往多在古代文學、現代文學領域被運用,而程旸大膽地將之移入到當代文學研究中來,非但不別扭,反倒比較奏效。如他對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劉巧珍等形象也感興趣,只是沒有僅僅在文本層面打轉轉,而是多方考證路遙和延安大學的關系、路遙的書單,特別是以層層剝筍的方式寫下《路遙〈人生〉中巧珍的原型》。在程旸看來,人物原型是現實主義小說研究的必要課題,路遙小說又具“自傳色彩”;所以對《人生》中巧珍的人物原型“窮追不舍地探究”。他承認說別人提出的巧珍是三姐的外形,與劉鳳梅有關,乃至是陜北女孩子的縮影,都不無道理;可他繼續發掘后卻斷定巧珍人物原型也“還有其他一些來源線索,例如路遙的初戀女友林紅及妻子林達”,甚至“巧珍軟弱自卑的影子”也有路遙的成分,“眾多女孩子被幻化成巧珍的原型,這是路遙對自我世界的錯位式的認知”。再有,程旸就作家王安憶已經在臺灣推出一本研究專著,但因為他對文本內外的“本事”留心,自然有比別人更多的發現,他閱讀王安憶的回憶文章《成長初始革命中》時,意外捕捉到作者寫保姆的《鳩雀一戰》《鄉關處處》《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保姆們》和《富萍》等幾篇小說的原始素材,最終順藤摸瓜,發掘出幾篇作品的故事和人物原型,寫下《王安憶作品的素材來源》一文。還有,《王安憶與徐州》圍繞作者做文章,兼顧文本的內外視角,闡釋、建立王安憶2009年前一百三十篇(部)作品中與徐州有關的《命運》《荒山之戀》《小城之戀》《文工團》等十六篇小說里,作品和下過八年鄉的安徽蚌埠地區五河縣、徐州地區文工團之間的聯系,其中有作家生活的若干面影,更外化了王安憶“個人意義上的地方志寫法”內涵。
說到程旸的研究方法和特點,華東師范大學的黃平教授在2020年4期的《當代作家評論》上著文《文學批評的實證之維》,稱程旸的研究“展現出以實證之維建構文學經典的學術抱負,顯現出青年批評家沉穩扎實、持論有據的學術氣度”,可謂說到了點子上,堪稱知音之談。巧珍原型考既和以往的研究成果間構成了一種潛在的對話結構,又可加深理解路遙隱秘的創作心理和潛意識;王安憶和下鄉地的關系建立,也因視角別致,多有新意,這種實證研究無疑提高了文學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程旸坦承對巧珍的人物原型是“窮追不舍地探究”,一個“窮追不舍”,道出了他性格中“刨根問底”的“執拗”勁兒,做感興趣的事情決不蜻蜓點水、淺嘗輒止,而是認準理兒不服輸,這股“深挖”“追問”勁兒,是不是和程旸本碩階段培養起來的邏輯嚴謹、注重證據、判斷冷靜的法律思維互為表里呢?它恐怕正是學術研究最需要而年輕人中又最為匱乏的。
我常想,文學創作有天分一說,這并非唯心論,文學研究也存在不少有天分者。程旸是有一定天分的,但這種天分在浩瀚的學問面前遠遠不夠,他的成績取得還應歸功于導師精心到位的學術指導,還有自身的熱愛、工夫和毅力。對程旸學術成長個案的透視,也讓我對大學的文學教育產生了困惑:為什么有些非漢語言文學專業出身的研究者一出手就氣象非凡,其學術水準和沖擊力甚至令一些純專業的研究者汗顏?是不是多年的專業訓練限制、遮蔽了學生的學術創造力,規范但也受到了許多條條框框的約束,反倒不如外專業和文學專業兩個相關或陌生領域的撞擊,會產生人們意想不到的思維或思想?最重要的是它讓人們思考,優秀研究成果的標準到底是什么,精致圓熟但無沖擊力的文章,和雖不無缺陷卻生氣四溢的文章哪個更值得褒揚?
由程旸學術成長,聯想到幾年前秋天回母校武漢大學,一個中午和於可訓先生散步,他說自己有出息的幾個博士原本都不是文學專業出身,有學歷史的,有學工商管理的,還有學熱處理的。這倒讓我腦海中盤桓幾年的追問有了著落,以后招生時也該重新考慮骨子里曾經排斥的“跨學科”的背景了。
行文至此,眼前又浮現出程旸那一束誠摯而專注的目光,仿佛在悄聲問詢:“羅老師,您在寫什么?”我微微一笑,印象記趕緊打住。
(羅振亞,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