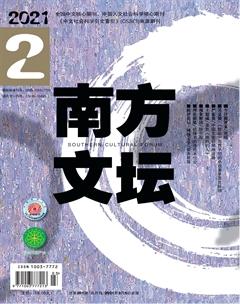網(wǎng)絡玄幻小說進化的敘事與復歸的傳統(tǒng)
于經(jīng)緯 張學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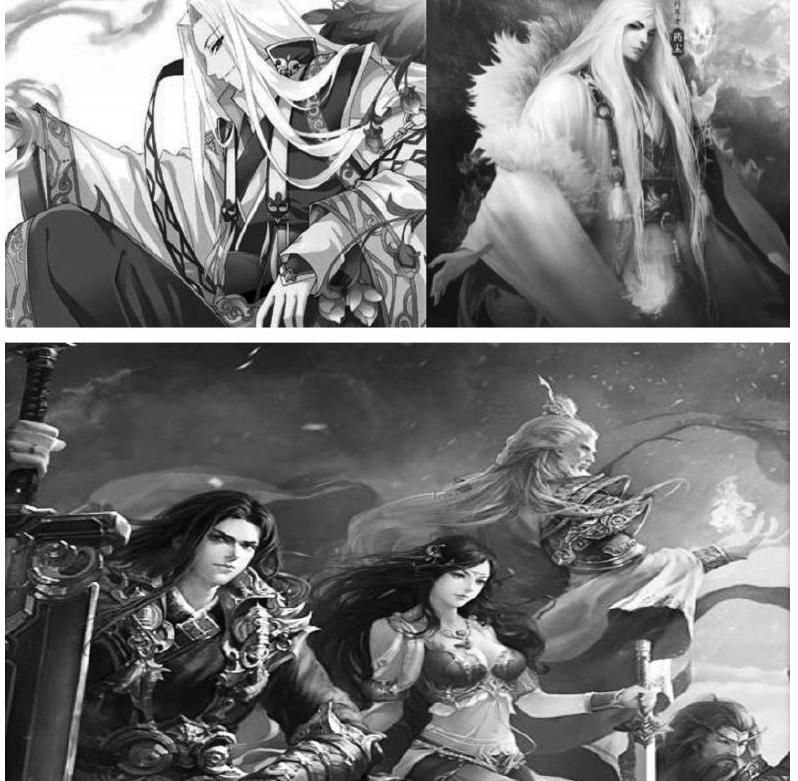
2009年4月,經(jīng)歷了處女作《魔獸劍圣異界縱橫》的業(yè)績慘敗之后,天蠶土豆(李虎)開始在起點中文網(wǎng)創(chuàng)作他的第二部玄幻小說《斗破蒼穹》。令天蠶土豆自己都沒有想到的是,這部小說迅速成為當年起點玄幻小說各種排行的榜首,并且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雄踞起點月票榜的前十。或許這種成功對于十年前的李虎來說多少有些偶然,但是從《斗破蒼穹》文本本身來說,這種成功又有著某種必然。可以說,《斗破蒼穹》的出現(xiàn)本身就是中國網(wǎng)絡玄幻文學發(fā)展的一個拐點,它的成功是當代網(wǎng)絡玄幻文學在敘事言語上的一次進化與定型,也是當代網(wǎng)絡玄幻文學在“內(nèi)面”對于通俗小說的某種復歸。更重要的是,這種進化與復歸憑借著《斗破蒼穹》的爆紅與持續(xù)發(fā)酵,實際影響了當代中國網(wǎng)絡玄幻小說的創(chuàng)作途徑與書寫模式。
一、進化:標準敘事言語的形成
2003年,《誅仙》在幻劍書盟網(wǎng)站開始連載并迅速躥紅起來。這無疑是沉潛了四十余年的仙俠小說在中國內(nèi)地的復興。隨后的幾年,仙俠類小說占據(jù)了中國網(wǎng)絡文學創(chuàng)作的半壁江山。然而真正令人猶疑不決的問題是自《誅仙》以來的仙俠小說,比如《搜神記》《凡人修仙傳》《縹緲之旅》《星辰變》等其分類是在仙俠與玄幻之間來回擺動。換句話說,歐美的魔幻/奇幻文學(la literature fantastique①)在2000年前后開始大量譯介,導致了中國本土的仙俠文學開始出現(xiàn)了所謂“玄幻”的傾向性,但是這種傾向性在2009年之前有影響力的作品上卻又難以做出明確的判斷。實際上,在中國網(wǎng)絡文學的發(fā)展中,直到2009年《斗破蒼穹》出現(xiàn),才意味著中國本土網(wǎng)絡小說中玄幻類型的誕生,使玄幻文學能夠在概念上徹底與仙俠文學進行區(qū)分。②
李虎的《斗破蒼穹》能夠?qū)崿F(xiàn)玄幻與仙俠之間的徹底分區(qū),其實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下三點:一是敘事類型的復合化;二是描述言語的圖像化;三是去象征化的言語系統(tǒng)。
不論是明清通俗白話小說,民國通俗文學,還是網(wǎng)絡文學,往往都會根據(jù)小說敘述的核心內(nèi)容劃分為不同的類型。不同的類型都具有相對明顯的特征,一如《封神演義》屬于魔神小說,《七俠五義》屬于俠義公案小說,《江湖奇?zhèn)b傳》屬于武俠小說等。即便是網(wǎng)絡文學,其本身也有較為清晰的類型劃分,以《誅仙》為代表的修真系的仙俠小說,以《步步驚心》為代表的宮斗言情小說等。不過,與2009年之前的火熱的仙俠小說相比較,《斗破蒼穹》的故事本身很難說屬于特定的某種類型,除非用“玄幻”來描述它。總而言之,《斗破蒼穹》作為網(wǎng)絡玄幻小說,它最大的特征在于敘事類型的復合化。
與較為傳統(tǒng)的修真仙俠小說《誅仙》《凡人修仙傳》《縹緲之旅》相比較,《斗破蒼穹》并沒有在中國傳統(tǒng)的魔神、仙俠、宗教等話語體系中尋找表達詞匯,而是使用完全獨創(chuàng)的方式來設立自己的世界觀③。用小說自己的話說就是:“這里是屬于斗氣的世界,沒有花哨艷麗的魔法,有的,僅僅是繁衍到巔峰的斗氣。”④姑且不論小說“內(nèi)面”性質(zhì)的問題,僅從概念本身來講,這種設計已經(jīng)完成了對仙俠類型,抑或說對中國傳統(tǒng)仙俠文化,至少是概念層面上的脫離。這種脫離就導致了小說在敘事層面擺脫了典型仙俠類型的桎梏——以修真為終極目的敘事言語——轉(zhuǎn)而開始依靠李虎本人獨特的想象力開始對各類型的小說進行混合。
單就《斗破蒼穹》故事而言,除了包含有貫穿整部小說的“斗氣”話語系統(tǒng)下的修真體驗,在其具體的敘事中顯然可見長篇章“偵探”類故事、“俠義”類故事,甚至于某種程度上的“言情”類故事。貫穿故事“斗氣”修真很大程度上只是推動不同模式間故事敘述轉(zhuǎn)型的工具,而非像《縹緲之旅》《凡人修仙傳》等小說一樣是作為小說的終極目標存在。因此,可以說《斗破蒼穹》的敘事是對2009年之前大多數(shù)主流仙俠小說敘事模式的逆轉(zhuǎn),故事不再為目的服務,而衍生出系統(tǒng)下的故事模式復合化。正是這種小說的復合化,使得《斗破蒼穹》作為典型的網(wǎng)絡“玄幻”小說在閱讀體驗方面與《誅仙》等小說產(chǎn)生明顯的異樣感。
除了敘事類型的復合化,《斗破蒼穹》另一個重要的敘事特征在于文本言語的圖像化。圖像化不同于形象化。一般而言,在經(jīng)典文本中的人物角色的形象化意味著作者力圖向讀者傳達一種特定人物外在或者內(nèi)面的獨特特征,從而使其文本角色與其他人物作出區(qū)分。盡管有著“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說法來意指經(jīng)典文學人物形象的豐富性,但是哈姆雷特作為一個獨特且與眾不同的文學形象存在卻是毋庸置疑的。不管刻意為之還是無意之舉,《斗破蒼穹》圖像化的描述語言恰恰放棄了經(jīng)典文學中的這種追求,或者說他用另外一種形式言語替代經(jīng)典的形象化。
最典型的圖像化言語,就是在《斗破蒼穹》中對于藥塵的描述。實際上,小說根本缺乏對藥塵這個主要角色的描述性言語,在相當長的篇章內(nèi),唯一具有描述性特征的詞匯只有蕭炎對藥塵的稱呼——“老者”。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這個“老者”絕非是一般意義上的老人,尤其是對于《斗破蒼穹》此類玄幻小說的真正讀者而言。實際上,在絕大多數(shù)的對《斗破蒼穹》二次創(chuàng)作中——漫畫、游戲等——都沒有將藥塵視為我們在經(jīng)典文學所理解的“老者”形象。
上面三幅圖分別是藥塵的漫畫形象以及游戲形象。如果依照經(jīng)典文學對于人物形象的理解,這三幅圖像所繪制的藥塵可以說完全是三個不同的人物,如果僅僅從圖像來說甚至于三個人物差異不僅存在于外貌上,而且存在于人物內(nèi)面之中⑤。然而,不論圖像之間的反差多么劇烈,對于小說而言,對于讀者而言這些都是藥塵。實際上,在《斗破蒼穹》中李虎對于各種人物的描述言語都是相對匱乏的,這是小說中真實存在的問題。不過,對于具有故事復合化性質(zhì)的小說而言,這種描述語音的匱乏恰好實現(xiàn)了小說人物的圖像化。這種圖像化并不依靠文本描述性言語引導讀者,而是在一個一個不同類型故事中,通過人物的差異性行為表現(xiàn)促使讀者完成對于人物圖像的獨立想象。換句話說,不同的讀者在不同類型的故事獲得某種情感共鳴后,便獨立地產(chǎn)生具有個體經(jīng)驗偏好的獨特想象。比如對于小說“言情”類型故事有偏好的女性讀者,往往對于藥塵想象更接近圖一;而喜歡蕭炎、蕭薰兒、藥塵三人征戰(zhàn)四方的“魔神”類型故事的讀者則可能更偏愛圖三的藥塵。
與2009年之前同樣具有影響力的仙俠小說相比,無論是《誅仙》《搜神記》之類都還延續(xù)著經(jīng)典文學對于人物塑造的基本要求,努力地使用描述性言語,比如《誅仙》中對碧瑤的頗具特征性的描述幾乎使碧瑤的形象完全定型。以敘述性情節(jié)替代描述性言語的人物圖像化雖然未必是《斗破蒼穹》的首創(chuàng),但是這種文本言語形式卻借由《斗破蒼穹》的影響力,獲得爆發(fā)性的推廣,很多網(wǎng)絡小說,尤其是采取復合型敘事的玄幻小說都采用這種言語策略。實際上后來唐家三少在《斗羅大陸》中也幾乎全部繼承了李虎的這種言語類型。
進一步說,在敘事類型復合化與描述言語圖像化的基礎之上,《斗破蒼穹》完成了當下作為類型的網(wǎng)絡玄幻小說言語特征的塑造——去象征化的言語系統(tǒng)。
這里的“象征”是對波德里亞的符號理論概念的借用。在波氏的理論中,象征意味著符號與意義具有對應性,也就是符號能夠產(chǎn)生特定的意義⑥。對于文學作品而言,尤其是經(jīng)典文學作品,其言語本身作為符號系統(tǒng),意在傳達人生中呈現(xiàn)的“不可言詮和交流之事”,“顯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⑦。換句話說,在經(jīng)典文本言語中,可以去追尋其言語作為符號而具備的象征意義。實際上,這種言語的象征不僅存在于經(jīng)典文本之中,嚴格來說,大多數(shù)現(xiàn)代小說的寫作都理應具有這種象征意義。即使如典型的奇幻小說《魔戒》《納尼亞傳奇》與《地海傳奇》等,其言語符號都有著深刻的象征意旨。同樣,早期的仙俠小說,作者們也盡力地想要在文本中為言語符號與象征意義搭上一條橋梁,典型如《誅仙》中文本始終面對并討論著善惡正邪之間的辯證意義。當然,中國網(wǎng)絡仙俠文學由于多種原因使得言語符號的象征意義一直持續(xù)減弱,直到《斗破蒼穹》出現(xiàn),終于得以徹底完成文本言語的去象征化。簡單而言,讀者不必再去向文本要任何可能存在的微言大義,文本言語的直接意義就是文本的意義。
實際上,在描述言語圖像化的特征中,這種去象征化呈現(xiàn)得最為明顯。人物不再由描述言語所構(gòu)建,也不是被作者創(chuàng)造的、與其他文本人物形象有著差異的獨特性存在,而是隨著描述性言語的消失,變成在故事講述過程中任由讀者想象的一種圖景。這一過程顯然顛覆了經(jīng)典文本對于人物形象描述言語的象征意旨,顯而易見,在言語符號的缺失處境中,象征是不存在的。然而,這種去象征化的言語并不意味著文本對于讀者而言缺乏吸引力,或者缺乏意義。去象征化的言語系統(tǒng)是將經(jīng)典文本中對于獨特人物或者事件的描述意義直接轉(zhuǎn)化為故事,只有在言語符號直接意義等同于文本意義的情況下,故事敘述上才能完成不同類型隨意轉(zhuǎn)換而不至于發(fā)生內(nèi)面上的矛盾。試想一下,如果一套有著復雜象征意義的言情言語系統(tǒng)在寥寥數(shù)行之間迅速轉(zhuǎn)換為激昂熱血仙魔斗法,其人物的內(nèi)面上會出現(xiàn)不可避免的——前面還在憂郁惆悵情緒悲悲戚戚,突然間就揮手斬妖除魔英姿颯爽——矛盾感。正是基于去象征化的言語,使《斗破蒼穹》在各個類型故事之間隨意切換而并無矛盾,更重要的是,去象征化的言語為另外一種復歸提供了可能。
《斗破蒼穹》在2009年的迅速爆紅,其實是中國網(wǎng)絡仙俠小說發(fā)展進化的集成表現(xiàn)。在幾年的仙俠小說寫作努力的基礎之上,由李虎將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敘事系統(tǒng)最終穩(wěn)定下來。這既是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在敘事形態(tài)上的進化,同時也標志著在這種進化之下的某種傳統(tǒng)的復歸。
二、復歸:玄幻網(wǎng)絡小說的“通俗”傳統(tǒng)
《斗破蒼穹》一方面奠定了當下網(wǎng)絡玄幻小說敘事形式的基礎,另一方面則展示出網(wǎng)絡玄幻小說在某些內(nèi)面特征上的向傳統(tǒng)通俗小說的創(chuàng)造性繼承與復歸。
《斗破蒼穹》所使用的敘事類型復合化寫作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章回體小說《儒林外史》。如果說《儒林外史》與《斗破蒼穹》在不同故事類型、人物圖景之間相互轉(zhuǎn)化在形式上的重要差異在于“惟全書無主干,僅驅(qū)使各種人物”⑧的話,那么在晚清出現(xiàn)的章回體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中用主角“九死一生”連綴眾多類型差異的故事則可以說是標準的敘事類型復合化的寫作策略。進一步說,學者對于章回體小說研究也提出了“故事集綴”的構(gòu)型⑨。可以說,《斗破蒼穹》敘事的復合化,是對傳統(tǒng)通俗小說中慣用“故事集綴”構(gòu)型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它在傳統(tǒng)“集綴”基礎上,添加了能夠貫穿故事始終的主干系統(tǒng)。正是由于《斗破蒼穹》突破了繁雜而缺乏連綴性的傳統(tǒng)文化詞匯術(shù)語,轉(zhuǎn)而使用自己設計的更為嚴格的且成體系的當代玄幻系統(tǒng),才促使小說在連綴多類型故事的同時克服了傳統(tǒng)章回體的裁斷感,保持了連載故事的完整性與情節(jié)的集中性。
實際上,在《斗破蒼穹》之前,很多網(wǎng)絡仙俠小說本身都對采用復合化敘事存在一定程度的抵觸。中國網(wǎng)絡仙俠小說的興起與歐美奇幻小說之間有著復雜的聯(lián)系。廣義上歐美奇幻小說是一種通過“吞噬整個文本世界,連同讀者在內(nèi)”,進而形成的一種“包含了真實與虛構(gòu)的對立”的文學存在⑩。《魔戒》《納尼亞傳奇》等經(jīng)典模式的歐美奇幻本身就包含著歷史與文化隱喻因素,文本本身也作為一個整體的故事存在,無論是在中洲大地上對抗邪惡,還是在納尼亞的土地傳頌基督神圣。歐美玄幻小說這種整體性直接地影響了中國網(wǎng)絡仙俠類小說創(chuàng)作,不只是《誅仙》《九州》,即使追溯更早的小說比如《悟空站》《輕功是怎樣煉成的》等諸多具有仙俠或者玄幻性質(zhì)的小說,其在文本敘事中追求的整體性與隱喻性甚至不會亞于一般意義上的經(jīng)典文學作品。可以說正是《斗破蒼穹》的出現(xiàn)將過去所追求的整體性文本徹底轉(zhuǎn)化為多類型故事綴合的復合型文本。
當然,《斗破蒼穹》敘事復合化并非一蹴而就的,也不能稱作第一獨創(chuàng)。這種轉(zhuǎn)變是經(jīng)過近乎十年中國網(wǎng)絡文學的發(fā)展逐步形成的,也是中國網(wǎng)絡玄幻小說逐步脫離歐美奇幻文學影響,重新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發(fā)現(xiàn)并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自身文化資源的過程。
如果說敘事復合化是對通俗小說章回體的某種創(chuàng)化的話,那么《斗破蒼穹》在文本言語上去象征則是多少意味著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在言語趣味上向傳統(tǒng)通俗文學言語的復歸。
在傳統(tǒng)通俗文學的文本言語中,往往包含著煽情、說教等特征,而且這種特征又與通俗文學文本言語的“時尚趨向”“都市心態(tài)”息息相關(guān)11。簡而言之,傳統(tǒng)通俗文學的文本言語是大眾能夠通過直接的方式理解其意義的語言,并且在這種文本言語中又包含了作者對于大眾倫理行為的某種非前沿性的傾向。比如張恨水在《春明外史》中敘述了陸無涯與學生陳國英之間、趙鈿與陶英臣之間以及胡曉梅和時文彥之間自由戀愛的故事,而張恨水對由新文化運動而起的自由戀愛在小說中加了不少暗諷的言語,以此希望讀者確認他的傾向性。易而言之,通俗文學的文本語言具有意義上的直白性與倫理上的保守性。
如此看來,結(jié)合前文中關(guān)于《斗破蒼穹》去象征化的言語特征,即文本言語的直接意義就是文本的意義,顯然是通俗文學文本言語的特質(zhì)在當代網(wǎng)絡媒介下的復歸。盡管這看上去并不是一個值得稱道的優(yōu)點,但是正是這種文本言語的特質(zhì)才能在更廣泛的程度去接納城市讀者,尤其是當代網(wǎng)絡社會中的都市讀者。“一代人現(xiàn)在佇立于荒郊野地,頭頂上蒼茫的天穹早已物換星移,唯獨白云依舊。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場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軀體。”12這是本雅明所預言的深陷于現(xiàn)代媒介體驗的個體之處境。在這種處境之中的個體“住在大城市中心”,“已經(jīng)退化到野蠻狀態(tài)去了——就是說:他們都是孤零零的。那種由于生存需要保存著的依賴他人的感覺逐漸被社會機制磨平了”13。當代網(wǎng)絡小說的閱讀主體與本雅明的預言相比,有著更為孤獨與破碎的處境。被“社會機制磨平”的大眾既無力亦無暇在繁復的言語背后去尋找意義的隱喻,只有去象征化的言語才能告訴他們,怎樣的做法才是更為有效,也才更適應日趨零散化的都市生活。
實際上,對傳統(tǒng)通俗文學文本言語而言,《斗破蒼穹》去象征化言語的創(chuàng)化之處在于它的內(nèi)質(zhì)并非傳統(tǒng)通俗文學的“敦厚婉諷”,而是建立在當代都市主體的去象征化白描上。比如,主角蕭炎雖然不斷給人一種所謂“莫欺少年窮”的剛直氣概,但同時也是一個隨時轉(zhuǎn)化,可以看風使舵、見機而行的人物。這種本質(zhì)上的矛盾無論是在通俗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經(jīng)典文學作品中,都應力圖避免。但是去象征化的言語,卻成功地將這兩種來回變遷的態(tài)度變得渾然一體,這種渾然性使當代都市主體自認為的生活處境,代表人的曲折是生活的純?nèi)还莻惱恚虼水斝≌f以最直接的形式將這種當代主體矛盾呈現(xiàn)出來之后,主體反而獲得直接認同。換句話說,蕭炎的矛盾其實就是閱讀主體的內(nèi)在矛盾。
因此,可以說《斗破蒼穹》去象征化的言語是當代處境中對傳統(tǒng)通俗文學文本言語那種煽情說教的再生,也是當代都市社會和網(wǎng)絡社會生活中重新發(fā)現(xiàn)人的日常生活狀態(tài)與倫理情趣的重要途徑,在這一點上兩者可謂殊途同歸。
三、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的
“通俗化”與“化通俗”
《斗破蒼穹》通過敘事類型的復合化、描述言語的圖像化、去象征化的言語系統(tǒng)等三條途徑,完成了對傳統(tǒng)通俗文學的“敘事進化”和“傳統(tǒng)復歸”。在這一過程中,《斗破蒼穹》所展示出來的與傳統(tǒng)通俗文學文本特征的異同,實際指向的是二者之間一種更為復雜的關(guān)系,即“繼承—延伸”的關(guān)系。換而言之,以《斗破蒼穹》為代表的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一方面繼承了現(xiàn)當代通俗小說的內(nèi)核,是“通俗化”的;另一方面,它又對現(xiàn)當代通俗小說加以發(fā)展和延伸,有著獨特的“化通俗”的審美取向。
要廓清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與現(xiàn)當代通俗文學之間的“繼承”關(guān)系,首先要考慮“通俗化”的問題。即何為“通俗”,它又有什么樣的特點。進而,再通過將“通俗化”的特點與當代網(wǎng)絡小說的特點進行對比,發(fā)現(xiàn)二者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繼承關(guān)系。
一般而言,現(xiàn)當代通俗文學被認為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延續(xù),依托于大眾媒體和市場運作,主要呈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類型化的世俗化閱讀14。其特點主要有五個,分別是大眾文化的文字表述,具有強烈的媒體意識,具有商業(yè)性質(zhì)和市場運作過程,具有程式化特征并有傳承性,是當代社會的世俗閱讀。換而言之,這五大特征即為“通俗性”,而滿足上述定義的小說則可被稱為“通俗化”的小說。
大眾文化的文字表述指的是通俗文學具有大眾文化的全部特征。《斗破蒼穹》通過描述語言的圖像化和去象征化的言語系統(tǒng),將語言的象征性意味加以消解,使其能夠以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傳遞給大眾,實現(xiàn)了文本意義與直接意義的重合,成為大眾文化最直觀的文字表達。同時,在這種去象征化的言語系統(tǒng)的影響下,《斗破蒼穹》在大眾倫理層面,也展現(xiàn)出了以約定俗成的價值判斷來作為文本中是非衡量標準的取向。
具體而言,中國現(xiàn)當代通俗文學的最深處是以社會公允倫理作為其文化核心,這一文化特征在《斗破蒼穹》里也有明顯的體現(xiàn)。小說開頭時,云嵐宗弟子納蘭嫣然來到蕭家,憑借著強大的門派背景強行要求與蕭炎退婚。而“被退婚”刺激的正是根治于中國社會的家族意識的“羞恥意識”層面,所以后來蕭炎才會不擇手段地修煉,為的就是能在三年之約后憑借實力“一雪前恥”。這種知恥后勇的價值判斷,正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通俗文學約定俗成的大眾文化內(nèi)核。用范伯群的話來說,也可稱之為是一種“符合民族欣賞習慣”15的表達方式。
作為網(wǎng)絡玄幻小說,《斗破蒼穹》的媒體意識無須多言,其本身的存在就是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發(fā)達的產(chǎn)物。而李虎作為起點中文網(wǎng)的寫手,在文學創(chuàng)作平臺上進行簽約連載的行為也十分清晰地昭示了其商業(yè)性質(zhì)和市場運作。
在“世俗化的閱讀”方面,《斗破蒼穹》面向的是全體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無論學生、白領(lǐng)還是其他社會階層。這一點與傳統(tǒng)通俗文學類似,同樣是追求閱讀的最大化,力圖覆蓋所有讀者階層。對于“程式化特征和傳承性”而言,《斗破蒼穹》亦表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通俗小說一樣的類型化特征,其在起點中文網(wǎng)的分類標簽中被定義為玄幻類小說。但值得注意的是,《斗破蒼穹》的玄幻是敘事類型復合化后形成的新的種類。它摒棄了從中國傳統(tǒng)的魔神、志怪、仙俠、武俠等話語體系中尋找表達詞匯,企圖用一種全新的“世界觀”來建構(gòu)文本世界,這無疑是對傳統(tǒng)通俗文學程式化在某種程度上的突破,因而可以看作是在“通俗化”基礎上的一種“化通俗”的表現(xiàn)。
“化通俗”指的是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在“通俗化”的同時,又在某些審美特征上展示出與傳統(tǒng)通俗文學的不同。即在和傳統(tǒng)通俗文學“通俗化”內(nèi)核保持一致的基礎上,網(wǎng)絡玄幻小說將新的“時代元素”滲入其中,從而形成自身獨特的審美特點,并最終在“繼承—延伸”的關(guān)系中,將“通俗化”發(fā)展成為“化通俗”。
如上所述,從程式化和傳承性的角度來說,《斗破蒼穹》的玄幻敘事也屬于類型小說的一種,符合現(xiàn)當代通俗文學的通俗化特征之一。然而由于玄幻類型本身對傳統(tǒng)類型有所突破,玄幻就在“通俗化”的基礎上變成了“化通俗”。同樣,在大眾文化的文字表述層面上,《斗破蒼穹》所展現(xiàn)出來的道德價值判斷,除了以傳統(tǒng)文化作為核心外,還夾雜著西方式的個人英雄主義。以主角蕭炎在迦南學院中所成立的學生組織“磐門”為代表,每當磐門有難時,幾乎都是蕭炎憑著個人強橫的實力將危機迎刃化解。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情節(jié),無疑是伴隨著大量美國影視作品的流入而漸漸滲透在大眾文化之中,并最終通過網(wǎng)絡小說進行了文字化的表達。因此,借由將大眾文化的融合與變遷進行文字表達,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在傳統(tǒng)的“通俗化”基礎上,完成了一次“化通俗”的蛻變。
就媒體意識和商業(yè)運作而言,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在保留原“通俗化”的基礎上,發(fā)展出一套涉及產(chǎn)業(yè)更加復雜,運行鏈條更加周密的商業(yè)系統(tǒng)。依托輻射更加廣泛的媒體(互聯(lián)網(wǎng)),網(wǎng)絡玄幻小說不但顛覆了傳統(tǒng)紙質(zhì)閱讀的范式,完成了屏幕閱讀和移動端閱讀的構(gòu)建,還在傳統(tǒng)通俗小說“文本—電視劇—電影”的商業(yè)運作外,發(fā)展出ACGN16產(chǎn)業(yè)鏈。單就《斗破蒼穹》一部作品所旁涉的商業(yè)產(chǎn)物就有電視劇、動畫、漫畫、游戲等數(shù)種之多。此外,近年來更有逐漸火熱的“IP”17產(chǎn)業(yè)興起(例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慶余年》等影視劇的改編及相關(guān)商業(yè)衍生物的出現(xiàn)),使網(wǎng)絡玄幻小說的商業(yè)運作得到進一步的拓展和深化。總而言之,當代網(wǎng)絡小說的全新媒體性和商業(yè)運作模式為現(xiàn)當代通俗文學的“通俗化”開辟出了新的可能性,展示出了“化通俗”的獨特商業(yè)潛力。
最后,在讀者層面,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和傳統(tǒng)現(xiàn)當代通俗小說間也有一個明顯的“繼承—延伸”關(guān)系。一方面,網(wǎng)絡玄幻小說繼承了傳統(tǒng)通俗小說追求讀者最大化的訴求,將受眾層面定為所有社會閱讀主體;另一方面,它又對傳統(tǒng)通俗文學中閱讀主體作為“探索者”18的功能進行了超越,將當代閱讀主體的經(jīng)驗感受融入文本之中,使得小說本身充滿著“當代情緒”。《斗破蒼穹》中,無論是蕭炎不斷重復的那句“莫欺少年窮”,還是他對絕對力量的不斷追求,為了修煉不惜見風使舵,甚至不擇手段,這其中所滲透的情緒無疑都與當代都市主體自認為的生活處境有所暗合,既揭示了閱讀主體的“內(nèi)在矛盾”,又戳中了閱讀主體的“痛點”,在某種程度上實現(xiàn)了他們對現(xiàn)實生活的預期和幻想。而這種創(chuàng)作方式,無論是在張恨水還是金庸這些最出色的傳統(tǒng)通俗小說作者的筆下都是從未出現(xiàn)過的。也正因此,當代網(wǎng)絡小說在“世俗化閱讀”層面上表現(xiàn)出比傳統(tǒng)通俗文學更強的即時性情感交互能力,也是在“通俗化”基礎上延伸出“化通俗”特性的一種體現(xiàn)。
《斗破蒼穹》借由“通俗化”和“化通俗”的雙重特性,與傳統(tǒng)通俗文學間產(chǎn)生了“繼承—延伸”的關(guān)系。同時,由于《斗破蒼穹》的巨大影響力,使得其他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在創(chuàng)作和書寫過程中也紛紛效仿,在有意無意中加深了“通俗化”和“化通俗”的交織融合。可以說,正是因為“通俗化”和“化通俗”雙重特征的并置存在,當代網(wǎng)絡玄幻小說才成為現(xiàn)當代通俗小說在網(wǎng)絡時代的發(fā)展和延續(xù)。用湯哲聲的話說,網(wǎng)絡小說實際上就是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的延伸。它把當下的一些世界文化放進來,把現(xiàn)代都市生活中的一些人物的心情和感情放進來,進行一些重新的組合,就變成了網(wǎng)絡小說。因此網(wǎng)絡小說既有傳統(tǒng)性又有獨特性。
【注釋】
①對于奇幻小說概念范疇、類型與言語的研究,以法國的托多羅夫為先驅(qū),故使用他在《奇幻文學導論》中所用的概念詞語。奇幻文學最初被譯介到中國大陸時,有譯為“魔幻”的翻譯。
②需要說明的這并非意指《斗破蒼穹》是第一部真正意義的玄幻小說,而是說由于《斗破蒼穹》強大的影響力,最終使“玄幻”這一文學類型與仙俠類型作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區(qū)分,并且影響到了后續(xù)十余年的同類型網(wǎng)絡文學創(chuàng)作的走向與類型劃分。
③不應否認的是《誅仙》等小說的世界觀也是原創(chuàng)世界觀,但是不難發(fā)現(xiàn)對于世界觀的表達無論是在概念的范疇,還是在小說內(nèi)部設定上都使用的是中國傳統(tǒng)魔神、仙俠、宗教等文化領(lǐng)域所具有的概念。這是與《斗破蒼穹》之間十分重要的不同。
④起點中文網(wǎng):https://book.qidian.com/info/1209977。
⑤圖三藥塵長者式的道骨仙風與正氣凌然,與圖二邪魅的藥塵有著明顯的不同。圖一則又以少女漫畫的男主人物形象出現(xiàn),亦與圖二、三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
⑥讓·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譯林出版社,2006,第68頁。
⑦12本雅明:《啟迪》,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第99、96頁。
⑧魯迅:《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221頁。
⑨張蕾:《“故事集綴”型章回體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⑩茲維坦·托多羅夫:《奇幻文學導論》,方芳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第130、131頁。
11陳建華:《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第413頁。
13本雅明:《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魏文生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第151頁。
14湯哲聲:《何謂通俗:“中國現(xiàn)當代通俗文學”概念的解構(gòu)與辨析》,《學術(shù)月刊》2018年第?期。
15范伯群:《〈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總序》,載《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南京出版社,1994,第1頁。
16ACGN是Animation(動畫)、Comic(漫畫)、Game(游戲)、Novel(小說)的縮寫。
17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縮寫,即知識產(chǎn)權(quán)。
18瑪麗-勞爾·瑞安在《故事的變身》一書中認為,“探索”是主體作為旁觀者的身份與作品進行交流的模式,其對作品本身不會產(chǎn)生影響。
(于經(jīng)緯、張學謙,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