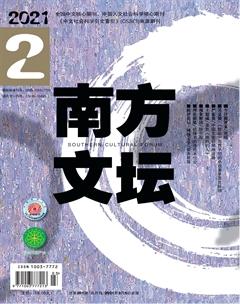釋“能文”:錢鍾書的詩性本位論
錢鍾書詩學與學術史正名
大抵尊錢鍾書(1910—1998,以下簡稱“錢”)為“文化昆侖”的海內外學者,皆愿稱錢是20世紀讀書最多、最具博識的“大學問家”。比如王元化(1920—2008)感嘆“錢鍾書這個本領很厲害,博聞強記啊”,“我說他一走了,沒有人比他讀書更多了”①;余英時則“鄭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國古典文化在20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國古典文化和20世紀同時終結”②。
錢作為飲譽世界的現代學術傳奇,當不限于古典學的淵默精妙,還在其平生(從青年到晚境)始終閃耀歌德式的曠世智慧,百科全書般的遼闊視野。論出身,他是民國大學名宿錢基博之子;論學籍,他是國立清華暨英倫牛津的雙料本科學霸;論職稱,他28歲聘為西南聯大的清華教授(1938年);論小說,長篇處女作《圍城》一問世便洛陽紙貴,連印三版,轉眼告罄,堪稱雅俗共賞的現代敘事經典(1946—1948);論舊詩,《槐聚詩存》輯集大半輩子的獨吟唱酬,計173題281首,有識者可從中探詢一代泰斗的幽邃心路(1934—1991);更無須說三大名著《談藝錄》(1948年初版)、《宋詩選注》(1958年初版)、《管錐篇》(1979年初版四卷,1994年增補為五卷),均是標志現代中國學界在相應時段所抵達的歷史深厚度與崇高度,恐令時賢及后世難望其項背。瞻仰如此浩瀚、峻拔的人文學思峰巔,后學拙于詞窮,不知如何命名才穩當,只能模擬古人浩嘆“大哉孔子”一般說“無所成名”——因為錢的博學淵源也已遠遠溢出知識學范疇,不宜用某學科的單一尺度來測定其非凡存在。這借古人毛奇齡《論語稽求篇》的話,即“所謂不成一名者,非一技之可名也”③。
但這無礙學界更宜珍惜錢的詩學瑰寶。錢在20世紀末留下的學思遺產遠非詩學(學科)所能涵蓋,然詩學確是錢生前傾注心力最沉潛、耗時最久遠的專業,此亦史實。錢在80年代末曾撰《作為美學家的自述》,他說:“研究美學的人也許可分兩類。第一類人主要對理論有興趣,也發生了對理論的興趣。我的原始興趣所在是文學作品;具體作品引起了一些問題,導使我去探討文藝理論和文藝史。”④這無疑表白錢以詩學角色來分擔美學家的名分,不僅無甚隔閡,并也是他頗情愿,當之無愧的。也因此,當后學期盼學術史終將明確地為其“正名”,追認錢才是真正無愧于20世紀中國詩學桂冠的第一人,也就未必無正當性。
詩,自古是中國文學皇冠上的明珠。“詩學”作為司職于詩的學問,在現代學界則按“技、藝、道”被劃出“詩技”“詩藝”“詩意”三塊。若曰王國維(1877—1927)以“境界”為元概念的《人間詞話》,是旨在標舉詩詞所蘊結的、關涉個體存在的終極關懷,這頗近荷爾德林的“詩意”⑤;那么,朱光潛(1897—1986)重在對“音律”作中西比較的《詩論》(全書13章,除末章論“陶淵明”屬附驥之尾,其余12章有8章或直接或間接地論及音律,占此書三分之二⑥),只能說它偏重“詩技”。這就是說,在20世紀真正鍥而不舍于“詩藝之學”(或“詩性之學”)幾近縱貫一生的,唯錢鍾書一人。這只須細讀錢1933年撰《中國文學小史序論》,再讀1948年版《談藝錄》、1958年版《宋詩選注》序、1979年版《舊文四篇》及1994年增訂版《管錐篇》五卷,理當能若明若暗、時斷時續地掘出一條錢在西學東漸語境,兢兢于“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的潛在理路。此即錢憑借“打通”古今中外之思辨原則、所不懈構建的閃爍闡釋學光輝的中國詩學系統:從“能文”(詩性本位論)→“修詞”(詩語分子學)→“才、學、識”(詩人修養論)→“神韻”(詩貴清遠說)→“格調”(詩分唐宋說)→“探本”(詩評倫理學),前后做了整整60年。相比較,王國維在1907—1908年撰《人間詞話》,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金盆洗手,不再涉及包括詩學在內的文哲之學了。無獨有偶,朱光潛1931年寫出《詩論》初稿,1943年初版,1948年出增訂本,嗣后也無暇再為詩學下工夫。此歷時17年,全屬1949年前的事,這與錢跟詩學相忘于風云、相濡以血淚的60年,差距甚殊。姑且不計彼此學思含金量之孰輕孰重。
述史至此,一個繞不過的疑點是:為何王著《人間詞話》、朱著《詩論》在傳播史上的影響因子,明顯高于錢的詩學?根因之一,擬是錢的述學方式不適宜絕大多數受眾的胃口。按理說,愿談論錢、愿解囊收藏錢著且擇而披閱的讀者大多意趣高雅,其中不乏能直覺錢著的傳世分量的學者頗想走近其性靈。但問題是,錢著作為國學的現代峰值,又酷似高聳于雪線之上的凜凜冰峰,你真敢爬么?你真能像挑戰生命的登山家一般,先寫遺書,再一步一個雪坑地攀緣么?不得不說,不少學者的當下心態大體講“現實”,像做小生意,太算計如何節縮成本,又如何收益最大化。于是,他們也就傾心于王著、朱著的述學方式,盡管逐字逐句地通讀甚至讀通也不太易,然畢竟王著、朱著已將其詩學,或條分縷析或篇章儼然地安置在各自篇幅不厚的集子里了。這便暗示讀者,不論你讀得深入、周延與否,王著、朱著至少已將其詩學悉數擱置你掌心了。這會令讀者放心,因為王著、朱著確乎能讓讀者不太費神,即可大致俯瞰其詩學版圖或輪廓。這就頗像顧客目睹“老廟黃金”的玻璃展柜,你心儀的金銀飾品極透明、全方位、貨真價實地“狀溢目前”(劉勰),你只消從錢包抽出銀聯卡刷一下,也就一切搞定。
但讀錢著(小說除外),卻難得如此放松。因為其詩學之著述,雖也有取專論式(如《中國文學小史序論》《舊文四篇》),但更多地卻訴諸文言札記,談片式(如《談藝錄》),融注、疏、釋、評、論于一爐,交織得密不透氣,稍一走神,即令你一頭霧水,茫然不知所向,仿佛是在亙古荒蠻的原始森林沒了路徑,更像是跌落雪崖冰窟憋得慌,含氧量甚低,瀕臨窒息。更要命的還在于,你最想發掘、淘洗的詩學珍寶,并不盡像王著、朱著那般已輯集一書,相反,錢著(《管錐篇》尤甚)是近乎惡作劇一般,將其宋瓷般珍稀的詩學國寶擊成碎片屑末,隨機地散落在洋洋百萬言的古奧縫隙里。這就很難不讓那群更愿從教科書吸吮學識的人望而卻步。因為,這意味著他想從錢著汲得詩學,肯定要比他讀王著、朱著預支更多代價,且還無計保障他未來定然收支平衡。這誠然不像去“老廟黃金”選奢侈品那樣瀟灑了,這分明是在冒險去昆侖峽谷的荒灘野澗撿和田子玉,極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這也就解釋了如下現象:為何頗有人早在1979年《管錐篇》初版時便興沖沖地把四卷本抱回書齋,然延宕到40年后的2019年,此書仍完璧若初(雖然書頁發黃)?無非是難讀,讀不進去,也就懸置。
由此,另個繞不過的疑點是:錢著為何舍棄當代人所習慣的述學語式(白話+專論),偏用令多數人頭暈的文言來寫詩學呢?對此,須先還原兩個史實。
史實一,錢40歲前撰詩學大多取學界流行語式。1933年正式宣示其“文學觀念”⑦的《中國文學小史序論》,還有同時段寫的《論不隔》《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讀中國詩》《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英譯千家詩》《旁觀者》《落日頌》《論復古》諸文,大多是很規矩的“白話+專論”(時23歲)。錢1942年脫稿,1948年初版的《談藝錄》雖未用白話,但并不因此而變得隱晦枯澀(時32—38歲)。相比較,文言版《談藝錄》所呈示的文辭、文脈,其實要比錢1958年版《宋詩選注》序論更鑒澄明,至少未像后者那樣被刻意寫成“模糊的銅鏡”(“它既沒有鮮明地反映當時學術界的‘正確指導思想,也不爽朗地顯露我個人在詩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許這個晦昧朦朧的狀態本身正是某種外境的清楚不過的表現”)⑧。盡管此序論是用白話寫的(時47歲)。
這表明錢40歲縱然用“白話+專論”的流行語式,也難免因故而寫得捉迷藏似的曲里拐彎,或耍魔術似的拍案驚奇⑨。這屬無奈之舉,是錢被逼得無路可走時的另辟蹊徑。否則,要么是《宋詩選注》因錢的直行其道而不準面世;要么是為了出書,曲學阿世,若如此,錢也就不是那位極自尊、極狂狷、又極聰慧的錢了。錢1988年曾這般表白此事:“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⑩(未透露操作細節)錢1957年自述“別出心裁”時的七絕倒吐露了其內心甚惶恐:“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11很是為當年自己的“敢違流俗別蹊行”12玩了一把心跳。
錢1955—1957年撰《宋詩選注》尚且警覺如此,當不難體恤錢1972—1975年(“文革”晚期,62—65歲)寫《管錐編》又怎能不仰賴文言,而把自己那顆既想有尊嚴地言說、又想有安全感的詩哲之心,裹得嚴嚴實實呢?須知錢撰《管錐編》時尚屬“戴罪之身”,頭上還壓著“反動學術權威”的黑帽,當需謹防那群熱血沖昏大腦的紅衛兵會破門而入,來嚴查錢是否仍在炮制“封、資、修”毒草。幸虧錢能嫻熟地讓古文與多種西語詞匯斑駁交集,混沌雜居,而讓其最想傳世的那些學思遺產(含詩學)得以幸存13。因為滿腦子“斗爭哲學”的造反派,憑其當年智商,還長不出一個博學靈敏的鼻子,能真正嗅出錢的用心。這在客觀上似表明,現實再嚴酷,也不會嚴酷到不留任何縫隙。錢就在此縫隙大智大仁大勇地隱居三年,皓首窮經,以日撰千字文言之速率,累積出《管錐編》四卷達百萬言。這以錢1974年的七律為證,即“耐可避人行別徑,不成輕命倚危欄”14。
史實二,類似嚴酷語境,對仍想有尊嚴且安全言說的錢來講(哪怕是撰詩學),究竟該怎樣慎用“白話+專論”的述學方式,也就不得不深思。與此同時,錢對40歲后所目睹的大陸學界盛行蘇聯教科書式、動輒硬拗“體系”“重視廢話一噸,輕視微言一克”15的輕浮語式,也甚厭惡。誠然,錢當年是指桑罵槐,借古諷今。錢先微詞古代典籍也不乏“假、大、空”——
葉燮論詩文選本,曾慨嘆說:“名為‘文選,實則‘人選。”(《己畦集》卷三《選家說》)一般“名為”文藝評論史也,“實則”是《歷代文藝界名人發言紀要》,人物個個有名氣,言論常無實質。倒是詩、詞、隨筆里,小說、戲曲里,乃至謠諺和訓詁里,往往無意中三言兩語,說出了精辟的見解,益人神智;把它們演繹出來,對文藝理論很有貢獻。也許有人說,這些雞零狗碎的東西不成氣候,不值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發的偶見,夠不上系統的、自覺的理論。不過,正因為零星瑣屑的東西易被忽視和遺忘,就愈需要收拾和愛惜;自發的孤單見解是自覺的周密理論的根苗。再說,我們孜孜閱讀的詩話、文論之類,未必都說得上有什么理論系統。更不妨回顧一下思想史罷。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時效。好比龐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壞,住不得人、也唬不住人了,而構成它的一些木石磚瓦仍然不失為可資利用的好材料。16
時隔半個多世紀,再細思錢1962年寫的這段話,不啻預言暨寓言。所謂預言,是說當年曾大紫大紅、師承蘇聯模式所編纂的巴人《文學論稿》17、以群《文學的基本原理》18等權威教材,而今確像整體垮塌的老房子既“住不得人、也唬不住人了”。所謂寓言,則指此話實已蘊含錢當年對述學語式(文體)的價值裁決:與其掛出理論“體系”的牌子去兜售“陳言加空話”19,毋寧用文言去注釋且闡釋古籍遺贈后世的那些尚存現代活力的珍稀啟示。這么做,是否會將頗多不想花大力氣來求知的讀者拒之門外?錢無所謂了。
錢在詩學語式(文體)上的“拒絕媚俗”,作為思想史的“博弈”,不能不付代價,甚至昂貴。錢1932年(時22歲)就探討“不朽”命題,確認“‘不朽是依靠著他人的,是被動的,因為我們通常所謂‘不朽,只是被后世知道,被后世所記得之謂”“我們不僅要‘好,并且要人家知道我們的‘好,才算‘不朽”。簡言之,“‘實雖在于自己,‘名有賴乎他人”20,此謂真諦。年表轉眼翻到1962年乃至撰《管錐編》時的1972—1975年,錢或許沒料到,他22歲寫的話,酷似孫悟空頭上的金咒箍,竟將62—65歲的自己也罩得難以脫身。是的,錢可以不屑在詩學語式(文體)上取悅于大多數人(含后世),但作為報應,大多數人(含后世)也將不自覺地會因錢的卓絕(決絕)而疏離乃至冷落錢。這落到學術史上,即錢明明已崛起為堪與王著、朱著比高的詩學頂峰,但因為其語式(文體)難以被輕易駕馭,故大多數人也就測不出錢著究竟比王著、朱著高多少?高在哪里?這在實質上,也就形同讓錢著這片世紀性詩學屋脊,被無聲地湮沒在公眾的學術史視野之外。
這一切,對29歲時便以兼備“異量美”的“豪杰”21自期的錢來說,很難不生“隱痛”。不妨說,此“隱痛”已從《管錐編》注釋《全漢文》淮海小山《招隱士》一文時,沛然流出: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云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按“我”,山之“英靈”自謂,即“誘我松桂,欺我云壑”“慨游子之我欺”之“我”。蓋人去山空,景色無以玩賞者而滋生棄遇寂寞之怨嗟也;詞旨殊妙。22
誠然,錢何等人物,“隱痛”縱然令其郁悶,但相信其胸襟浩蕩如海,自有巨大的心靈凈化功能,而使自己安魂。比如信手拈來一句西哲名言以自慰:“何苦于無人處浪拋善物乎。”23但后學作為學術史研究者,卻會油然而生一夙愿:將錢的詩學系統從公眾的微茫忘川中打撈出來,再巍然呈現于學術史,以祈百年公論即“正名”——此當后學義不容辭的責任。
“能文”含義的詩性三維
與朱著《詩論》相比,錢的詩學與其說是把“詩”視作“文體”符號,用來區分“詩”“小說”“散文”“戲劇”之間的差別;毋寧說更愿把“詩”視作“文類”標識,以期甄別“文學”與“非文學”的邏輯界限何在。否則,朱著就不會在“音律”上耗大功夫,錢著也不宜對中國詩特有的“音律”幾無眷顧。正相反,錢是由衷地將國史幾千年前就誕生的抒情詩(“純粹的抒情,詩的精髓和峰極”)尊作祖國文學“崇高的境界”24;據說這與美國“愛倫·坡的詩法所產生的純粹詩(poesie pure)”無甚區別,都隸屬“文學”范疇;且憑這點,錢強調中國詩就“它該是詩”而言,“比它是‘中國的更重要”25。
這就坐實了錢為何1933年就將其詩學觀徑直稱作“文學觀”的原因。說白了,錢屢屢就詩“談藝”,根子就在他愛在詩學平臺做文藝理論,這叫“詩學搭臺,文論唱戲”。故也可說錢的詩學是“廣義詩學”(就內涵而言),又是“狹義文論”(就體裁而言)。這很像醫院里有些臨床“小手術”,乍看切口小,然縱深度可觀。以王著、朱著為參照系,錢的詩學當得起“廣義詩學”這個名號,因為當錢事實上已在“能文”(詩性本位論),“修詞”(詩語分子學),“才、學、德”(詩人修養論),“神韻”(詩貴清遠說),“格調”(詩分唐宋說)與“探本”(詩評倫理學)之間,埋下有待后世厘清的總體暗線時,它其實已是用詩學文言來聯綴的現代文論系統了。故稱為“狹義文論”亦可。
本章重在解析“能文”。“能文”作為錢氏詩學的核心關鍵詞,這不僅因為它在詩學系統排位第一,更因為它是此詩學的理論源頭即“邏輯起點”,宛如全息胚一般蘊含著這株詩學大樹日后得以參天遮地的全部思辨基因。這就是說,欲想真躋身錢的詩學邸府,首先得叩響錢“釋能文”這扇前門。因為錢從“能文”(源自蕭統《文選序》)這一古詞所闡發的、“能文”之“能”所涵蓋的“審美大欲”“夸飾自足”“引誘之魅”這詩性三維,實際上是從“動力、本體、效應”諸方面展示了錢賴以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的三條原則。
詩性維度一,“審美大欲”是“能文”之動力。
國人自古講究日常人倫之大用,從孔子悠悠萬事唯“克己復禮”為大,到歷代書生奉“久雨甘霖”“洞房花燭”“金榜題名”為人生至樂,可堪明鑒。魯迅晚年漢譯普列漢諾夫《沒有地址的信》,也采信原始土著之陶紋等“史前藝術”,當是“實用價值”在先,“審美價值”殿后。總之,與社會經濟、政治、倫理、日用相比,一個詩人的歌哭耽吟之審美需求,總難免被低估。錢的詩學頗不以此為然。他明言,“且以藝術寫心樂志,亦人生大欲所存(kunstwollen)”;“譬如野人穴居巖宿,而容膝之處,壁作圖畫;茹毛飲血,而割鮮之刀,柄雕花紋。斯皆娛目恣手,初無裨于蔽風雨、救饑渴也。詩歌之初,何獨不然。……初民勿僅記事,而增飾其事以求生動;即此題外之文,已是詩原。論者乃曰:‘有史無詩,是食筍連竹,而非披沙揀金”26。
錢又以古代“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轉藉文詞之末節,得以不廢,如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鞹,狐貉之裘,皮之得完,反賴于毛”為喻,說“古人屋宇、器物、碑貼之類,流傳供觀賞摩挲,原皆自具功能,非徒鑒賞之資。人事代謝,制作遞更,厥初因用而施藝,后遂用失而藝存”——說到這兒,錢又口鋒一轉,稱“文學亦然”,即以酈道元《水經注》為例:說“酈書刻畫景物佳處”,足以媲美柳宗元游記,然鑒于酈書本系學識性“輿地之書,模山范水是其余事,主旨大用絕不在此”;但也大可不必像某些人將言及酈書有文學性者訶為“直不解文,非但不解《水經注》”歟?錢以為這撥呵責者“恐似仰空而唾、逆風而溺,還汙著于己身耳!”27
這里要點有兩。
其一,蕭統《文選序》既然倡導“以能文為本”,不當“以立意為宗”,故此“文”指歸在考量行文之美,諸如“綜輯詞采”“錯比文萃”“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之類,實謂“文學性”。于是,那些標舉“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的姬公之籍、孔父之書,也就抱歉了,只能偏從闕略;另些“老莊之作、管孟之詩,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文選序》)28。
其二,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蕭統《文選序》之“文”,與陸機《文賦》之“文”近義,而與劉勰《文心雕龍》之“文”(“文章學”非“文藝學”)異義。然歷代論及魏晉六朝批評史者卻又大“多以蕭統《文選序》與劉勰《文心雕龍》并舉,而不知二者之相鑿枘,斯真皮相耳食,大惑不解者也!”29同時,錢又認為這撥輕言“經、史、子不得為‘文”者之毛病,是出在“蓋皆未省‘詩與‘文”均可由指稱體制之名進而為形容性能之名(considerare la poesia piuttsto come aggettivo che come sostaneivo)”30,這就是說,老拘泥于世襲“體制之名”(體裁、體類),“‘文之一字,多指‘散文‘古文而言,斷不可以‘文學詁之”31,即“文以載道”之“文”與“詩以言志”之“詩”走的不是一路。但若放眼“純粹詩”固然是文學瑰寶,但有些經、史、子、集也不乏甚至相當高的文學性,為何就不能在“形容性能之名”層面,打通文學史在“詩”與“文”之間設置的屏障,而將其化為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詩學共名呢?錢將此叫作“觀乎跡,雖復殊途,究乎其理,則又同歸”,簡稱“溝通綜合”32。錢所以將其“詩學觀”等同于“文學觀”,理由歸一。
詩性維度二,“夸飾自足”是“能文”之本體。
想要真正領悟錢關于“夸飾自足”才是“能文”本體之卓見,須在面對“詩史之辨”時去“世眼”33。
所謂“世眼”,是指世間自古流行、習焉不察的那種凡物皆講“信實有征”的知性眼光。以此尺度來衡量史家,甚正當。以此尺度來苛求詩家,則強人所難。為何?答案很簡明:“史必征實,詩可鑿空。”34然并非古賢皆信此說,漢代寫《論衡》的王充就不信,且撰“《語增》《儒增》《藝增》三篇,蓋記事、載道之文,以及言志之《詩》皆不許‘增。‘增者,修辭所謂夸飾(hyperbole),亦《史通》所謂‘施之文章則可,用于簡策則否者”35。看來,寫《史通》的劉知幾眼界要比王充開闊且開明,他畢竟能把“文章”與“簡策”(政事)分開,而給“詩”宜“夸飾”騰出地盤。
錢主張“夸飾”,也是認定“詩”之迥異于“史”,是因為“史”當視知性為命,故原則上不寫“不可能的事”,不準無中生有;然“詩”正相反,“蓋明知事之不然,而反詞質詰,以證其然,此正詩人妙用”——此即“夸飾”:“夸飾”以不可能為能,比喻以不同類為類,“理無二致”36。錢旋即以漢代《鐃歌·上邪》為例,說“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一詩,無非是用大自然的一串“不可能”(從山“不可能”無陵到天地“不可能”彌合)來“夸飾”,實則祈愿詩人與愛人“彼此恩情與天同長而地同久,綿綿真無盡期,以斯喻情,情可知已”37。誰能忍心粗暴地逐一責之于實呢?否則,這與其說是“知性”,不如說“無人性”。這也就是說,在“詩”宜“夸飾”一案,若無趣地遷就王充式似是而非的知性規訓,“則文藝所言,什九則世眼所謂虛妄”38,人世間也就沒文藝了。
錢從“夸飾”引出的“虛—偽”“真—誠”之辨也甚別致。坊間往往將“虛—偽”“真—誠”非思辨地讀作“虛偽”“真誠”。錢則提醒讀者:“蓋文詞有虛而非偽,誠而不實者。語之虛實與語之誠偽,相連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無害,夸或非誣。《禮記·表記》:‘子曰‘情欲信,詞欲巧;亦見‘巧不妨‘信。誠偽系乎旨,征夫言者之心意,孟子所謂‘志也;虛實系乎指,驗乎所言之事物,墨《經》所謂‘合也。所指失真,故不‘信;其旨非欺,故無‘害。”39
錢又由此推演到文學“夸飾”:“高文何綺,好句如珠,現夢里之悲歡,幻空中之樓閣,鏡內映花,燈邊生影,言之虛者也,非言者之偽者也,叩之物而不實者也,非本心之不誠者也。《紅樓夢》第一回大書特書曰‘假語村言,豈可同之于‘逛語村言哉?《史記·商君列傳》商君答趙良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設以‘貌言‘華言代‘虛信‘假言,或稍減誤會”——至于大腦簡單讀者讀書不開竅,誤“以華語為實語而‘盡信之,即以辭害意,或出于不學,而多出于不思。”40這就怪不得文學“夸飾”有錯。錢為此開的方子頗辯證:“顧盡信書,固不如無書,而盡不信書,則又如無書,各墮一邊;不盡信書,斯為中道爾。”41
進而,后學還想說,若欲細深體悟錢“夸飾自足”中“自足”一詞之微妙,尚須校正學界對“緣情”說的單向度粗讀,即粗糙地界定陸機“緣情”之“情”純屬詩人之“情”,而不是被“夸飾”(“能文”本體)所設定的藝術結晶。這用錢青年時的話來說,即“夸飾自足”所以“自足”,其“要旨,不在題材為抒作者之情,而在效用能感讀者之情”42。
這就是說,錢所定義的詩“情”,并非是像作者心頭滴下的血一般注入題材的;相反,已被編織為題材,且通過題材而把讀者感染得走心淚目的那個“詩情”,其實是被“夸飾”所巧妙假定、精致構成且整體氤氳所彌散的、能在給定語境重復的審美氛圍或效用。也因此,錢不茍同“文生于情”;相反,錢強調“情非文”:“性情可以為詩,而非詩也。詩者,藝也。藝之成敗,系乎才也。”43此才即“夸飾”之才。當文學能獨立地不簡單地依附詩人之情,而更講自由地揮灑詩性之才,“夸飾自足”之“自足”要義,也就自明。
這當然不是說,秉持“夸飾自足”,錢即不在乎文學中有否“情”了;而是說錢更計較詩“情”是怎樣被煉成。錢甚至注意到《史記》所以比一般通史多“迥出之篇,有聲有色,或多本于馬遷之增飾渲染,未必信實有征。寫相如‘持璧卻立倚柱,怒發上沖冠,是何意態雄且杰!后世小說刻畫精能處無以過之”44。但鑒于史著畢竟是史著,不論其文學性“夸飾”有否讓后世小說自愧不如,終究壓不倒史著本色仍在“信實有征”,而不宜讓野馬跑得太遠。錢譏諷后世史著也確有讓野馬跑得野豁豁的,比如“《晉書·王遜傳》:‘怒發沖冠,冠為之裂,直類《史通》外篇《暗惑》所譏‘文鴦侍講,殿瓦皆飛,拴牙慧而復欲出頭地,反成笑柄”45。究其質,也是因為“史”不是“詩”:“史”即使有些文學性“夸飾”,它更終仍受制于出處、本事,太過了,過猶不及,即錯;相反,“詩”激勵自己上天入地,即使無甚出處、本事,也能讓悟空一個筋斗云翻十萬八千里,且將此視為真“本事”。
寫到這兒,再回頭來咀嚼錢青年時對“無病呻吟”一語的別解,也就不得不嘆為絕妙。錢明察學界慣于把“修詞立誠”定格為“不作無病呻吟”。錢偏作驚人語:“竊以為唯其能無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讀者信以為有病,方為文藝之佳作耳。”46其解釋是:“作者之真有病與否,讀者無從知也,亦取決于呻吟之似有病與否而已。故文藝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無病也,實由其不善于呻吟;非必‘誠而后能使人信也,能使人信,則為‘誠矣。”47如此妙解當醍醐灌頂,遂認同錢對“立誠為因”“修詞為果”之因果律顛倒,也確鑿顛倒得精當絕倫。錢說:“蓋必精于修詞,方足‘立誠,非謂誠立之后,修詞遂精,舍修詞而外,何由窺作者之誠偽乎?且自文藝鑒賞之觀點論之,言之于物,融合不分;言即是物,表即是里,舍言求物,物非故物。”故亦可說“一切文藝,莫不有物,以其莫不有言;‘有物之說,以之評論思想則可,以之興賞文藝,則不相干,如刪除其世眼之所謂言者,而簡擇世眼之所謂物,物固可得,而文之所以為文(quiddity),亦隨言而共去矣”48。當你無歧義地確信如上“言即是物”的那個“言”,即錢所謂“夸飾”,則“夸飾”焉有不“自足”之理?
詩性維度三,“引誘之魅”是“能文”之效應。
為了說清作為“能文”效應的“引誘之魅”到底是什么,錢分別用了“白話”“文言”兩套語式。白話版“引誘之魅”宛若三部曲:一是詩篇宜有“珠璣似的耀眼的字句”;二是詩句當能“喚起你腔子里潛伏著的回響的音樂”;三是它實際上已在“搔你心頭的癢處”,或已“熨帖你靈魂上的瘡痛”49。如此三部曲被錢轉述為文言版,它又依次被壓縮為“不隔”“直尋”及“耐讀”。
稍知《人間詞話》者對“不隔”不會陌生,它在王國維那兒是指某種鑒賞(閱讀)狀態,它首先取決于詩人的藝術傳達能否使讀者從中“得到一個清晰的、正確的、不含糊的印象,像水中印月,不同霧里看花”50——這用王國維的話即“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這就呼應了錢所謂“珠璣似的耀眼的字句”,也無非是清詞麗句,歷歷在目的意思。這是檢測詩作有否“引誘之魅”的第一指標。也因此,錢原則上認同王國維忌諱寫詩用“替代詞”,且把“替代詞”界定為“空洞的詞藻”,“因為空洞的詞藻是用來隔絕和遮掩的,仿佛亞當和夏娃的樹葉,又像照相館中的衣服,是人人可穿用的,沒有特殊的個性,沒有顯明的輪廓(confour)”51。這也就“隔了”,把讀者鑒賞時應有的“一種透明洞澈的狀態——‘純潔的空明”,亦即將“作者所寫的事物和境界得以無遮蔽地暴露在讀者的眼前”那種狀態,阻隔了。這也就沒了“引誘之魅”。
錢將“引誘之魅”的第二指標定為“直尋”。學界恪守鐘嶸《詩品·序》本義,大體把詩人吟詠情性不必貴于用事(類“替代詞”)界定為“直尋”,比如“‘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這純然經典。錢的別具慧眼,是從接受美學角度來新探“直尋”。他說讀者固然可先假設有一類似供翻譯的原著,以此為標準來核對譯本對原著是否忠誠(忠誠即“不隔”);然在文藝鑒賞時,讀者該“向何處去找標準”來核對作品之描寫是“隔”或“不隔”呢?錢發現“這標準其實是從讀者們自身產生出的”:“只要作者的描寫能跟我們親身的觀察、經驗、想象相吻合,相調和,有同樣的清楚或生動(Hume所謂liveliness),像我們自己親身經歷過一般,這便是‘不隔”52;亦即“直尋”。大凡治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名家名著言涉鐘嶸“直尋”說,幾乎皆從作者角度切入;能從讀者角度切入,錢大概是唯一。
青年錢鍾書的了不起,當不限于他24歲時即能對鐘嶸“直尋”發時賢之未發(時1934年,燕京教授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剛問世);其了不起,還在22歲就能頗專業(絕不生搬硬套)地引用西方行為主義理論來探幽讀者“直尋”的審美心理機制。這很像是馮友蘭說人須同時讀兩本書:“有字人書”與“無字天書”。“有字人書”是指一切輯錄人類文字的印刷物或手抄本。“無字天書”是指人類個體(首先是自身)內心所幽閉的,因其經歷、閱歷所持續沉積的那些不曾敞亮或無可名狀的私己經驗,諸如夢幻、恐懼、暗戀、怯懦、戰栗……這部宇宙星云狀微茫且沉睡的“無字天書”,時而碰上能感應的“有字人書”,很可能會被局部地喚醒或激活。這用錢所譯介的行為主義理論來說,即“我們對于事物既有反應,我們對于語言文字便有定性反應(conditionedresponse)。所以,從行為主義的立足點看起來,文藝的欣賞不過是conditionedreflex”53。
其實,這一通過閱讀而“把已消滅的定性反應重新喚起”54的鑒賞心理現象,若用現代文論術語來表述,即“再造想象”。“再造想象”,是指在讀者內心喚起與給定語符相契的藝術圖景,而此藝術圖景所賴以完形的諸多構成元素,則往往是在讀者心底幽閉甚久、幾近被忘卻(近似消逝)的私己經驗。完全可以說,一部作品被閱讀,若能激活讀者的私己經驗愈多、愈鮮活(“直尋”)、愈幽邃、愈具心靈品位,則表明此作品愈具鑒賞性或“引誘之魅”。這也就形同錢所描繪的“喚起你腔子里潛伏著的回響的音樂”。
錢還把“引誘之魅”的第三指標定為“耐讀”。錢說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的邊界是在:非文學作品只求“能讀”(readable),文學作品須求“耐讀”(re-readable)且謂“‘咿唔不厭巡檐讀,屈曲還憑臥被思這是耐讀的最好的定義”55。那么,怎樣的作品才經得起讀者如此手不釋卷、擁被沉思呢?錢說要能“搔你心頭的癢處”或“熨帖你靈魂上的瘡痛”。這無異于是期盼作品若夠經典,須能寫出人之所以為人、又令天下讀者痛感“字字為我心中所欲言,又非我之所能自言”56的那份既日常又遙深的“終極關懷”。“終極關懷”是指這么一種旨在安魂的身心聚焦,它能為每位在乎自我存在質量的主體敞亮或雅潤意義,且從心靈最深處驅動每位覺識者能為此意義而無怨無悔地抵押一生。這當然只有大詩人方能擔當。王國維說“境界有二:有詩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詩人之境界,唯詩人能感之而能寫之,故讀其詩者,亦高舉遠慕,有遺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淺焉。若夫悲歡離合、羈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唯詩人能寫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廣57”。這也足稱是“引誘之魅”最高級了。
“引誘之魅”最高級,也不啻是“夸飾自足”之最高級,這兩者“強強聯手”,決定了高品質鑒賞也確能做到“足恃于內,無求于外”的。錢亦由此覓得如下甄別作品優劣之詩學標尺:
鄙見則以為佳作者,能呼起(stimulate)讀者之嗜欲情感而復能滿足之者也,能搖蕩讀者之精神魂魄,而復能撫之使靜,安之使定者也。蓋一書之中,呼應起訖,自為一周(a complete cireuit),讀者不必于書外別求宣泄嗜欲情感之具焉。劣作則不然,放而不能收。動而不能止,讀者心煩意亂,必于書外求安心定意之方,甚且見諸行事,以為陶寫。故夫誨淫誨盜之藉,教忠教孝之書,宗尚不同,胥歸劣作。何者?以書中引起之欲愿,必求償于書外也。58
“能文”從古典向現代轉換
稍具學術史視野的人,不難認同發源于“西學東漸”背景的20世紀中國文論版圖實有兩大流脈。流脈一,是致力于系統譯介、研究或灌輸域外之學,來深刻影響乃至宰制大陸學術之演化。這又可分“藍色西學”(歐美)與“赤色西學”(俄蘇)兩條支流:前者以朱光潛為卓越大師;后者則曾蔚然而成大勢,從瞿秋白、魯迅、周揚到巴人、蔡儀、以群等。流脈二,是傾心于中國詩學的現代轉換,此轉換當酌情滲入西學元素,但目標乃指向中華文論的自我完善暨學思復興,以期融入世界學林也不失東方神韻,而絕不盲目地、無尊嚴地崇洋媚外,以致為了迷信西學(作為方法)的天然英明,而不吝有損中國經驗(作為對象)的獨特性暨豐富性。毋庸說,學界在這方面做得最具里程碑意義的,是王國維與錢鍾書。
這就意味著,“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作為呼吁雖是新世紀初轉為瀏亮,然若作為一種鑿鑿“可觸”的實績,它是在20世紀初的王國維及30年代后的錢鍾書那兒已甚可觀。同時,王、錢的學思遺產又默默地提醒后學,“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既是一條值得抉擇的創新路徑,怕更是某種亟待學賢用生命去擔當的學科史大任。話說得這般重,無非是與浩如煙海的千年文論典籍相比,一個學者的專業壽命即使高于60年(如郭紹虞、錢鍾書),也只是滄海一粟,且還難免遭累于歷史曲折而致蹉跎。
不妨讓史實來說話。“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作為學術工程擬分兩塊:“照著說”與“接著說”。郭紹虞(1893—1984)撰《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下卷,其要務就是對古典文論(從孔、墨、莊、荀到明、清)作編年史細讀,考鏡源流,此即“照著說”。“照著說”欲做到位,其前提是在對給定文獻(對象)作專業鉤沉、輯錄、注疏的基礎上,再給予整體邏輯還原,繼而為歷代名家名篇的學術地位逐一下經得起證偽的判斷。郭撰此史著,若從1927年算起,1934年出版上卷,1948年下卷問世,歷時20年。如此長時段勞作不免煩苦,然又誠屬“自討苦吃”,誰讓你夙愿當學術史家呢?當學術史家命定得老老實實地“照著說”,且以此為尊、為榮,雖苦猶樂。這是責任,也是權利。因為曾幾何時,學術史家連“照著說”的權利也被讓渡,而被規訓須“順著說”。1959年版《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卷,作為郭紹虞對其民國版史著的修訂版,其特點即按“文學史是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史”這一蘇聯模式,把批評史涂改得面目全非。這當然不是在做“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分明是被迫參與“古典文論的現代變異”59。直到粉碎“四人幫”后的1979年重版郭著,才基本(并非全部)恢復其民國版之本真,然著者已垂垂老矣。
與郭相比,錢鍾書做“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特征有兩:一是錢詩學研究雖也綿延60年(從民國到共和國),然其文化立場暨學術方法并未因語境變遷而呈質的異化(近乎戴震“為學不作媚時語”);二是其詩學研究在文獻學層面雖也恪守“照著說”,但錢顯然比郭更情愿,亦更有能耐對古典詩學作“接著說”。
這“接著說”落到“能文”一案,也就不得不令人驚訝:“能文”本是蕭統530年撰《文選序》所拈的一枚邊界欠明、有待定義的術語,傳到1400年后錢鍾書的筆下,竟華麗轉身為一個足以撐起“詩性本位”這套現代詩學架構的“范疇”命名。事情所以變得這樣,用錢的話說,即“古人立言,往往于言中應有之義,蘊而不發,發而不盡”60,而錢恰恰能將蕭埋在“能文”中的那些“蘊而不發,發而不盡”的“應有之義”,不僅發掘,且發揚至廣大。故可謂“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第一義,是宜將古人訴諸印象式評點、只靠上下文關系去含混猜測的文言術語,置于現代思辨的顯微鏡下去“鉤玄抉微”,其結果是導致錢對“能文”含義的“參稽會通”61比蕭統所領悟到的要幽深豐厚。或曰,“能文”在批評史上雖系蕭統首倡,然“自知不透”;錢在千百年后卻借現代思辨透視,“知之勝其自知”62。
這就意味著,經過現代思辨洗禮后的“能文”,它已脫去含糊其辭的古典語式,而轉換為含義明晰的現代“概念”,足以用來指稱“文學”與“非文學”之間確有一條異質邊界。不僅如此,“能文”在錢的詩學視域里,還升格為一個能統轄“能文”之動力、本體、效應諸維度的現代“范疇”。這更是蕭統始料不及的。打個比方:蕭當年鑿在批評史上的“能文”二字若像歷經滄桑的石匾,錢則破天荒地將它高懸門楣,讓它去標識門墻后的那幢號稱“詩性本位說”的三進庭院,依次為“審美大欲”(“能文”之能力)、“夸飾自足”(“能文”之本體)、“引誘之魅”(“能文”之效應)——且不說“引誘”庭院還別具雅致地錯落著“不隔”“直尋”“耐讀”三處亭閣。整個“詩性本位說”布局渾然一體,生氣流貫,又層層遞進,步移景換,間而未隔。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王國維以下簡稱“王”撰《人間詞話》時,將“境界”這一古老的佛學詞語轉換為現代詩學“概念”“范疇”的事。當王用“境界”去指稱詩詞所蘊藉的、作者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詩意穎悟時,“境界”也就轉為王的詩學“概念”。當王用“境界”去涵蓋“造境”與“寫境”、“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人生三境”以及“詩人之境”與“常人之境”時,“境界”也就升華為王的詩學“范疇”。王在1907—1908年所做的,與錢在1933年后所做的,大致皆歸為“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但錢針對“能文”所下的“現代轉換”功夫,比較王在“境界”所下功夫,顯得厚重,恐亦史實。原因至少有二。原因一,王在“三十自序”曾坦呈其現代思辨構建能力欠強,故而對他最想做的哲學、美學、倫理學體系原創時,他嘆喟“可愛而不可信”63。“可愛”,是指他當初愿傾其全力來做的事;“不可信”,則指他“三十而立”時已痛感做不了一流哲學家(理論家),因其系統思辨功力有限,駕馭不了康德、黑格爾式的體系建構。錢鍾書從青年到晚年從未質疑自己理論構建之能力,倒是常常因厭煩當世“體系”之“假、大、空”,而不屑寫那類通編教材式的高頭講章。原因二,是王用在“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上的時間欠少,縱然自1904年撰《紅樓夢評論》算起到1908年《人間詞話》問世,充其量才五年。這與錢相比,無可比性。因為錢的學思生涯有多長,其“古典文論現代轉換”之路也就有多長。不涉其他,只舉“能文”一例,便可鑒錢將“能文”從古典轉換到現代的全部軌跡,其源頭固然在1933年《中國文學小史序論》,然嗣后其思路卻屢屢波及1948年版《談藝錄》、1958年版《宋詩選注》、1979年版《舊文四篇》以及1994年版《管錐編》5卷。何謂學術史的“源遠流長”?此亦范例(微觀)。
錢釋“能文”,為何能釋成“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之范例?擬有三條,很值得后學深思,依次為“選擇”“重構”與“打通”。因篇幅有限,本章無法逐一具體展示其內涵,只好先在此簡述各自意向,此即“選擇”源自錢的詩學創新動機,“重構”出于錢創新詩學所須有的理論訴求,“打通”作為錢的詩學方法旨在敞亮人類藝文通義。
己亥冬月于滬上學僧西渡軒
【注釋】
①吳琦幸:《王元化談話錄》(1986—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445頁。
②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載《文化昆侖——錢鍾書其人其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第197頁。
③參閱王元化:《釋“無所成名”》,載《思辨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68-269頁。
④錢鍾書:《作為美學家的自述》,原載《中國當代美學家》,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第641年。
⑤參閱夏中義:《境界說》,載《王國維:世紀苦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30-45頁。
⑥參閱夏中義:《朱光潛詩學的“中西匯通”——〈詩論〉的方法論細讀》,載《朱光潛美學十辨》,商務印書館,2011,第142-165頁。
⑦錢鍾書:《論復古》注釋1,載《寫在人生的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第327頁。
⑧⑨錢鍾書:《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1988年),載《宋詩選注》附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第477-478、479頁。
⑩參閱夏中義:《反映論與錢鍾書〈宋詩選注〉——辭別蘇聯理論模式的第三種方式》,《文藝研究》2016年第11期,第41-50頁。
11錢鍾書:《赴鄂道中》之五(1957年),載《槐聚詩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第119頁。
12錢鍾書:《龍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絕句即追和其去年秋夕見懷韻》(1959年),載《槐聚詩存》,第121頁。
13參閱夏中義:《論錢鍾書學案的“暗思想”——打通〈宋詩選注〉與〈管錐編〉的價值親緣》,《清華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14錢鍾書:《老至》(1979年),載《槐聚詩存》,第132頁。
151619錢鍾書:《讀〈拉奧孔〉》(1962年),第34、33-34、33頁。
17巴人:《文學論稿》上下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50。
18以群:《文學的基本原理》,初稿完成于1961年底,上海文藝出版社于1963—1964年分上、下冊出版。
20錢鍾書:《鬼話連篇》(1932年),載《寫在人生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第260頁。
21錢鍾書:《游雪竇山》(1939年),載《槐聚詩存》,第42頁。
2223錢鍾書:《管錐編》卷四,中華書局,1994,第1347、1350頁。
2425錢鍾書:《談中國詩》(1945年),載《寫在人生的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第162、167頁。
26343543錢鍾書:《談藝錄》(1948年),中華書局,第39、38、38、39-40頁。
2730錢鍾書:《管錐編》卷二,中華書局,1994,第539、539頁。
2829313233384246474858錢鍾書:《中國文學小史序論》(1933年),載《寫在人生的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第101、100、96、96、104、104、102、105、105、105-106、107頁。
36373940414445錢鍾書:《管錐編》卷一,第74、74-75、96、96-97、98、319、319頁。
4955錢鍾書:《落日頌》(1932年),載《寫在人生的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第310、310頁。
505152錢鍾書:《論不隔》(1934年),載《寫在人生的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第112、112、113頁。
5354錢鍾書:《〈美的生理學〉》(1932年),載《寫在人生的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第269、269頁。
5657王國維:《人間詞話》附錄之五,載滕惠咸校注:《人間詞話新注》,齊魯書社,1981,第110、110-111頁。
59參閱夏中義:《蘇聯模式與郭紹虞“學科變異”——對1959年版“中國文學批評史”作思想史解碼》,《社會科學輯刊》2016年第6期,第122-130頁。
606162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第325、325、325頁。
63王國維:《自序二》(1907年),載《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周錫山編校,北岳文藝出版社,1987,第244頁。
(夏中義,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