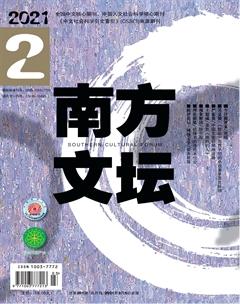文學(xué)闡釋學(xué)發(fā)凡
文學(xué)闡釋學(xué)有一種內(nèi)在的文化互動(dòng)功能,它包含了觀念重構(gòu),重構(gòu)的資源來(lái)自于表現(xiàn)為文本的他人的生活經(jīng)驗(yàn)、表達(dá)方式、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和審美取向。為了拓展自己的經(jīng)驗(yàn)視界,通過(guò)對(duì)某個(gè)文本進(jìn)行闡釋,打開(kāi)視野,在他人經(jīng)驗(yàn)之上豐富經(jīng)歷,提升智慧,獲得愉悅、美和善的陶冶,在獲得心靈自由的同時(shí)也認(rèn)識(shí)到自身的局限。由于每個(gè)個(gè)體判斷力的差異,即使面對(duì)同一個(gè)對(duì)象也會(huì)產(chǎn)生各自不同的見(jiàn)解(獨(dú)識(shí))。要把個(gè)人的經(jīng)驗(yàn)視界拓展到普遍性層次需要?jiǎng)?chuàng)作者與闡釋者共建。由于闡釋主體間存在著不懂和誤解,以及交往理性的不對(duì)稱性,闡釋者希望達(dá)成一種不同主體間可交流、溝通的愿望,這種強(qiáng)烈的行為沖動(dòng)產(chǎn)生某種共識(shí),即由于各闡釋主體與對(duì)象之間大相徑庭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和知識(shí)背景而產(chǎn)生陌生化體驗(yàn),并促成一種“行為共識(shí)”;反之,由于各闡釋主體與對(duì)象之間大致相近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和知識(shí)背景而產(chǎn)生的憧憬,形成一種“目標(biāo)共識(shí)”。這一認(rèn)識(shí)論基礎(chǔ)使得文學(xué)闡釋具有可實(shí)現(xiàn)性。
一、交往理性與共識(shí)
按照康德對(duì)人類情感類型的劃分,人類內(nèi)心全部能力有3種類型,即認(rèn)識(shí)能力、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欲求能力。認(rèn)識(shí)能力在諸能力中屬于知性能力,它是合規(guī)律的,主要應(yīng)用于自然;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則屬于判斷力,屬于合目的性的行為,廣泛應(yīng)用于文學(xué)藝術(shù);欲求能力是一種理性的認(rèn)識(shí)能力,人類為了達(dá)到自由,在先天原則中被視為終極目的。文學(xué)闡釋活動(dòng)需要運(yùn)用內(nèi)心的全部能力,但最核心的是判斷力。康德對(duì)判斷力即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做了進(jìn)一步細(xì)分,分為快適、美、善三種情感類型。對(duì)于這三種情感的定義,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說(shuō)得很明白:“快適對(duì)某個(gè)人來(lái)說(shuō)就是使他快樂(lè)的東西;美則是使他喜歡的東西;善則是被尊敬的、被贊成的東西,也就是在里面被他認(rèn)可了一種客觀價(jià)值的東西。快意對(duì)于無(wú)理性的動(dòng)物也適用;美只適用于人類,即適用于動(dòng)物性的但卻有理性的存在物,但這存在物又不單是作為有理性的(例如精靈),而是同時(shí)又作為動(dòng)物性的存在物,但善則是一般地對(duì)任何一個(gè)有理性的存在物都適用的。”①按照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文學(xué)闡釋就不單單是判斷力的問(wèn)題了,因?yàn)槲膶W(xué)文本綜合地包含了快適、美和善三種要素,接受者往往分不清自己被感動(dòng)是動(dòng)用了哪一種情感,或者三種情感天然地混合在一起。作品中的某種情節(jié)使他快樂(lè)(快適)、喜歡(美),并且由衷的尊敬和贊成(善),這當(dāng)然是由于作品達(dá)到了極高的層次才會(huì)使人產(chǎn)生如此豐富高級(jí)的情感。然而大多數(shù)情況下,接受者是容易混淆的。
有些寫作和閱讀就是為了獲得心靈的自由,在達(dá)到善的同時(shí)也獲得了快適和美的享受。這里頭只有美是無(wú)利害的一種情感,“對(duì)美的鑒賞的愉悅才是一種無(wú)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悅;因?yàn)闆](méi)有任何利害、既沒(méi)有感官的利害也沒(méi)有理性的利害對(duì)贊許加以強(qiáng)迫”②。人們常說(shuō)“產(chǎn)生閱讀快感”是一種籠統(tǒng)的說(shuō)法,作為接受者,哪種是快適、哪種是美、哪種是善,讀者感受對(duì)象的存在時(shí)可以不加區(qū)分,但如果要把它闡釋清楚,就有必要說(shuō)得更明白一些。那么,要對(duì)它們進(jìn)行區(qū)別就必須運(yùn)用理性,這與康德所說(shuō)的前兩個(gè)環(huán)節(jié)不需要理性又是矛盾的。
理性的運(yùn)用是實(shí)現(xiàn)文學(xué)由混沌到澄明的必要環(huán)節(jié)。理性并不是一個(gè)獨(dú)立存在物,理性的可信任之處其實(shí)是在一種實(shí)存狀態(tài),即理性總是在意見(jiàn)之中寄托自身,通過(guò)意見(jiàn)顯現(xiàn)出來(lái)并具身化。也就是說(shuō)闡釋行為本身即包含了理性,不存在一種脫離闡釋行為的絕對(duì)理性。理性可能在闡釋過(guò)程中某個(gè)任意時(shí)空節(jié)點(diǎn)上顯現(xiàn),如果把這個(gè)節(jié)點(diǎn)的密植增加并無(wú)限擴(kuò)大,它可以充盈整個(gè)闡釋過(guò)程。把理性實(shí)現(xiàn)過(guò)程上升到概念,理性就是存在,就是一切事物本身。闡釋主體這個(gè)自我也不是通俗意義上的“自己”,它打破自己的界限,把自己對(duì)象化,形成“自我意識(shí)”,是自我意識(shí)與事物(闡釋對(duì)象)共同作用形成的理性。正如黑格爾所說(shuō):“理性的自我意識(shí)通過(guò)其自身的活動(dòng)而實(shí)現(xiàn),自我意識(shí)發(fā)現(xiàn)事物即是它,它即是事物:這就是說(shuō)它明確意識(shí)到它自身即是客觀事實(shí)這一事實(shí)了。”③但我們也不能忽視高蹈于實(shí)踐理性之上的“純粹理性”。但純粹理性總是寄身于其不純粹之中。意識(shí)形態(tài)、文化戰(zhàn)略也是從日常生活實(shí)踐中提煉出來(lái)的,純粹理性也包含“不純粹行為”。包括哈貝馬斯和謝林共同認(rèn)可的一個(gè)觀點(diǎn),即失誤、犯罪和欺騙不是沒(méi)有理性,而是被顛倒的理性的外觀形式。黑格爾在論及“心的規(guī)律與自大狂”時(shí),認(rèn)為個(gè)體性的自大狂也是一種被顛倒的形式,或者被顛倒的世界真相。理性是不承認(rèn)幸運(yùn)的,它只承認(rèn)必然性。它有自己的原則。哈貝馬斯所說(shuō)的理性想成為可信托的理性不能還原到純粹理性,而是要引入其他理性。從實(shí)踐理性到純粹理性的提升,必須經(jīng)過(guò)自我意識(shí)的反向運(yùn)動(dòng)。要讓各路闡釋相互言說(shuō)、傾聽(tīng),并理解對(duì)方的理解,最終達(dá)成某種共識(shí)。也就是說(shuō)在闡釋活動(dòng)中理性的最低要求要做到眾口喧嘩、各路言說(shuō)。非理性在這種交往中被理性的力量所淘汰。因此“交往理性”是在“主體間性”和“他性”的制約之下,其結(jié)果則是可見(jiàn)、可實(shí)行和可結(jié)出豐碩果實(shí)的。理性是交往的前提,如果說(shuō)真理、真誠(chéng)、正當(dāng)、可理解是“交往理性”得以順利實(shí)現(xiàn)的四項(xiàng)基本條件,并且也可以把這四項(xiàng)條件看成公共理性應(yīng)當(dāng)遵從的原則。那么就像金惠敏所說(shuō)的那樣,“共識(shí)在交往理性中形成”④。
二、行為共識(shí)與目標(biāo)共識(shí)
共識(shí)是在交往理性中形成,交往理性以及理性的公共闡釋強(qiáng)調(diào)共識(shí),其意義不言自明。如何理解交往理性以及理性在文學(xué)闡釋中的“共識(shí)”?其總體性原則應(yīng)該有以下幾點(diǎn):其一,共識(shí)是各個(gè)個(gè)體性闡釋觀點(diǎn)的集合,可交換、可通融。其二,共識(shí)必須照顧到各方利益訴求,最大可能納入不同意見(jiàn)。其三,共識(shí)是在現(xiàn)實(shí)性基礎(chǔ)上的虛構(gòu)性想象,往下可以作為行動(dòng)準(zhǔn)則,往上可以升華為集體理想。并不是所有行為動(dòng)機(jī)有趨向共識(shí)的意向,鑒于這個(gè)共識(shí)過(guò)于籠統(tǒng),在闡釋實(shí)踐中,有必要對(duì)共識(shí)做進(jìn)一步區(qū)分,或可分為“行為共識(shí)”和“目標(biāo)共識(shí)”。行為共識(shí)即闡釋者受思想支配和情感沖動(dòng)做出的闡釋行為與其他闡釋者有某種一致性,在闡釋過(guò)程中有一些共享的行業(yè)規(guī)則、共同的生命體驗(yàn)、類似的行為沖動(dòng),并遵循總體的歷史前提、客觀事實(shí)、方式方法等。目標(biāo)共識(shí)即闡釋者的闡釋活動(dòng)通過(guò)闡釋的不同的路徑達(dá)到某個(gè)預(yù)期的目標(biāo),闡釋主體以期達(dá)到某種目標(biāo),在闡釋過(guò)程中通過(guò)主體間性制約,理性介入程度比較高,在減少損耗節(jié)約能量的前提下,形成某種共識(shí),如文化權(quán)力、話語(yǔ)體系、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倫理規(guī)范、利益訴求等。
(一)行為共識(shí)
文學(xué)闡釋似乎從來(lái)就要標(biāo)新立異,要“獨(dú)識(shí)”。每個(gè)人的“獨(dú)識(shí)”意識(shí)即獨(dú)立表達(dá)意見(jiàn)的意愿,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行為共識(shí)”。在以文本為對(duì)象的闡釋中,某種觀點(diǎn)一旦被人闡釋出來(lái)(盡管絕對(duì)正確,并產(chǎn)生英雄所見(jiàn)略同之感),其他闡釋者卻只好另辟蹊徑,換一種說(shuō)法。只有理解出現(xiàn)障礙后才會(huì)附和另一種與自己一致的意見(jiàn)。在文學(xué)闡釋中,因?yàn)槲膶W(xué)文本留給闡釋者的途徑山重水復(fù),闡釋者打開(kāi)的方式有無(wú)數(shù)種可能,任何一種闡釋實(shí)踐由于闡釋者的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生命歷程、知識(shí)背景的不同,可能產(chǎn)生與眾不同的結(jié)論。他的這種具有個(gè)性化的“別有洞天”的闡釋結(jié)果,才是文學(xué)闡釋的“真理”。不同闡釋者所依據(jù)的原點(diǎn),產(chǎn)生出無(wú)數(shù)的輻射區(qū),其交叉和重疊部分,形成一種共同可接受的東西。但這并不是無(wú)意識(shí)間達(dá)到的共識(shí),而是由于闡釋者生活閱歷、情感需求、文化基礎(chǔ)某種一致性促成的。闡釋者追尋的目標(biāo)也各不一樣,從文本中尋找諸如理性精神、情感慰藉、知識(shí)見(jiàn)聞、倫理原則、政治謀略、文化滋養(yǎng)等,闡釋者通過(guò)某種可以不斷打開(kāi)長(zhǎng)期被遮蔽的自性,讓它始終處于一種認(rèn)知的開(kāi)放狀態(tài)。因此他們實(shí)際上處于行為共識(shí)之中,而不是目標(biāo)的共識(shí)。
需要說(shuō)明的是在“個(gè)體闡釋”階段,不參照他人觀點(diǎn)的前提下,依據(jù)自己對(duì)文本的理解,一般會(huì)產(chǎn)生不同于他人的獨(dú)特闡釋。當(dāng)個(gè)體闡釋進(jìn)入“公共闡釋”⑤領(lǐng)域,同類型闡釋觀點(diǎn)聚合,形成“達(dá)成共識(shí)”的假象。闡釋的實(shí)踐環(huán)節(jié)包含了文學(xué)理論與社會(huì)學(xué)的跨學(xué)科行為。英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約翰·湯普森就提出過(guò)“社會(huì)闡釋”,他認(rèn)為:“從社會(huì)闡釋學(xué)的觀點(diǎn)來(lái)看,我們有闡釋相互沖突的空間,而這個(gè)空間里沒(méi)人能夠確切知道沖突會(huì)怎么展開(kāi)。”⑥社會(huì)空間充滿了彼此不同、相互沖突的闡釋,每一種闡釋都有它自己的利益訴求,審美需要和情感表達(dá)也是一種利益。社會(huì)闡釋可能并不追求共識(shí)(或者有一個(gè)隱性的模糊的共識(shí))。公共闡釋的確隱含了“共識(shí)”的假定,或者對(duì)“共識(shí)”有著某種期待。正如湯普森所說(shuō),共識(shí)是讓我感到不安的一個(gè)術(shù)語(yǔ)。與社會(huì)闡釋不同的是,文學(xué)闡釋并不假定也不期待每個(gè)人都同意,因?yàn)檫@個(gè)假定的存在就是對(duì)文學(xué)豐富性和復(fù)雜性的否定。分歧似乎是文學(xué)闡釋的宿命,而不是“必須被動(dòng)接受”。在文學(xué)闡釋中,文學(xué)批評(píng)家避免與他人見(jiàn)解雷同,并不是說(shuō)他必須無(wú)中生有開(kāi)發(fā)出一套見(jiàn)解來(lái),而是文學(xué)本身就包含了無(wú)窮的可能性,這里指的是經(jīng)典文本或者普遍的文學(xué)現(xiàn)象。
(二)目標(biāo)共識(shí)
在文學(xué)闡釋中,也存在著某種信念,追求快適、美、善的“目標(biāo)共識(shí)”。自由、和諧、圓滿的共識(shí)可能是最終想要達(dá)到的效果之一,但行為共識(shí)這個(gè)環(huán)節(jié)恰恰不能省略掉。共識(shí)的前提和基礎(chǔ)必須是無(wú)數(shù)的“獨(dú)識(shí)”,由“有著類似的行為沖動(dòng)”的闡釋者表達(dá)意愿促成。人首先要解決闡釋的生理訴求。大約在7萬(wàn)年前人類的“認(rèn)知革命”⑦啟動(dòng)以來(lái),“說(shuō)話”就是成了人的基本的生理屬性和社會(huì)屬性。文學(xué)闡釋的終極關(guān)懷是存在的,但目標(biāo)共識(shí)卻要極力避免“一言以蔽之”“總的來(lái)說(shuō)”這樣的結(jié)論。面對(duì)一個(gè)文本,可能一開(kāi)始就達(dá)成的共識(shí)是“總的來(lái)說(shuō)這是一部好作品”,或者“毫無(wú)疑問(wèn)這是一個(gè)平庸的作品”。這種結(jié)論性的話語(yǔ)會(huì)掩蓋很多事實(shí)。因?yàn)樗枰f(wàn)萬(wàn)個(gè)“獨(dú)識(shí)”來(lái)解釋這個(gè)“好”或者“不好”的原因。文學(xué)闡釋“何以可能”可以看成目標(biāo)共識(shí)的動(dòng)機(jī)。它被公共理性所推動(dòng)。也就是伽達(dá)默爾所說(shuō)的“公理的極端自明性”以及康德的“善良意志”⑧。在文學(xué)闡釋中,公共闡釋的最末端,涉及公理的極端自明性。這個(gè)自明性靠什么來(lái)達(dá)到?在“德法之爭(zhēng)”(伽達(dá)默爾與德里達(dá)的辯論)中德里達(dá)曾經(jīng)對(duì)此表示疑慮。“善良意志”是否在相互理解方面有絕對(duì)的約束力。事實(shí)上,人們都有意愿認(rèn)可這個(gè)公共闡釋的極端自明性。它其實(shí)不僅僅是一個(gè)倫理問(wèn)題,它應(yīng)該成為言說(shuō)的共同體的有效倫理起點(diǎn)。德里達(dá)提出一個(gè)非常根本性的問(wèn)題,這個(gè)無(wú)條件的公理性是否還預(yù)設(shè)著一個(gè)隱形的條件,即意志作為最高的規(guī)定性?“如果像康德所說(shuō)的那樣,在善良意志之外沒(méi)有任何無(wú)條件的善,那么,意志到底是什么呢?難道這種規(guī)定——作為最終機(jī)關(guān)——不會(huì)屬于海德格爾完全合理地稱之為意志或者意愿主體性的存在者之存在的規(guī)定?難道這樣一種講法——包括它的必然性——并不屬于一個(gè)過(guò)去的時(shí)代,即那個(gè)意志形而上學(xué)的時(shí)代嗎?”⑨在公共闡釋中,這種由善良意志為基礎(chǔ)的理性闡釋即包含了“公理的極端自明性”的闡釋,對(duì)于眾聲喧嘩的文學(xué)闡釋,可以視為理性和人性的雙重標(biāo)尺。尤其是對(duì)“準(zhǔn)經(jīng)典”的闡釋。“共識(shí)以共同的信念為基礎(chǔ)”(哈貝馬斯)。經(jīng)由信念達(dá)到的共識(shí)是非強(qiáng)制性的、彼此心悅誠(chéng)服的。行為共識(shí)的主觀能動(dòng)促成目標(biāo)共識(shí)的自在自為,可能有“無(wú)心插柳柳成蔭”的效果,客觀上形成了文化權(quán)力的統(tǒng)一、話語(yǔ)體系的構(gòu)建、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的形成、倫理規(guī)范的養(yǎng)成,各利益訴求者也因此得到一定回報(bào)。在一般性的公共闡釋里,這個(gè)邏輯是圓滿的。
(三)兩種共識(shí)的交互力量
哈貝馬斯與湯普森一樣對(duì)“共識(shí)”感到緊張,甚至有“專制的壓力和恐怖”,這種恐怖和緊張是所有理性闡釋都想要設(shè)法消除的。比較極端的是文學(xué)藝術(shù)為了抵制這種“共識(shí)”,不惜以違背真相和真理原則為代價(jià)。文學(xué)闡釋有一個(gè)本能的沖動(dòng),即拒絕獨(dú)斷、總體化。但并不是說(shuō)文學(xué)闡釋的公共性就是眾聲喧嘩、各說(shuō)各話,文學(xué)闡釋要回避的是“被規(guī)定的目標(biāo)共識(shí)”,防止情感認(rèn)知與精神靈動(dòng)方面的固化、板結(jié),防止走向文學(xué)闡釋的開(kāi)放性、多樣性的反面。文學(xué)作品尤其是經(jīng)典作品,它的本質(zhì)是活性的有生長(zhǎng)力的一個(gè)“生命體”。文學(xué)闡釋在闡釋行為上普遍存在一種不可名狀的“闡釋沖動(dòng)”。由于公共性闡釋最初的沖動(dòng)并不一定是理性的闡釋。個(gè)人體驗(yàn)訴諸語(yǔ)言、行動(dòng),便成為一種公共闡釋,當(dāng)闡釋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就包含了交往理性,其行為共識(shí)和目標(biāo)共識(shí)互相交織在一起。承認(rèn)文學(xué)類的公共闡釋存在某種共識(shí),是在文學(xué)闡釋中達(dá)成對(duì)某一文本的經(jīng)典認(rèn)知,可以算作一種總體上的共識(shí),它是“行為共識(shí)”和“目標(biāo)共識(shí)”通力合作的結(jié)果。兩種共識(shí)的更高層面,應(yīng)該是在公共闡釋中每個(gè)闡釋主體都無(wú)法保持原來(lái)的樣子,由交往、對(duì)話、影響而升級(jí)到一種更高的普遍性。在理解中達(dá)到的這個(gè)新層次,實(shí)際上使兩種特殊都得到了克服,即自身的特殊性和他者的特殊性。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個(gè)人學(xué)會(huì)超越自己狹隘視域,站在更高層面審視自我、他者以及整個(gè)世界。
區(qū)分行為共識(shí)與目標(biāo)共識(shí),有利于走出長(zhǎng)期以來(lái)我們所認(rèn)為的共識(shí)的誤區(qū)。因?yàn)殛U釋者總是從自身有限的視域出發(fā),對(duì)千姿百態(tài)的文學(xué)文本進(jìn)行解釋的時(shí)候,將“他者”看成“同一”,形成一種無(wú)差別的共識(shí)。行為共識(shí)可能會(huì)將自己的見(jiàn)解預(yù)設(shè)為高于其他人的見(jiàn)解,因?yàn)殛U釋行為僅僅表現(xiàn)為闡釋者對(duì)闡釋的需要。個(gè)體都有一種愿望,希望從差異中得到學(xué)習(xí)和提升,體驗(yàn)?zāi)切┎煌谧约侯A(yù)判的陌生的“他者性”和“差異性”。分享他者的不同之處,以作為一個(gè)參與者為目標(biāo)。鑒于這種原因,目標(biāo)共識(shí)就更為明朗了,為了理解和認(rèn)識(shí)某物,探索更好的表達(dá)或者創(chuàng)建一種共同的愿景,伽達(dá)默爾在這個(gè)理論上向前發(fā)展一步,他在《真理與方法》中強(qiáng)調(diào)視界拓展的最終落腳點(diǎn)為“視界融合”。
三、“獨(dú)識(shí)”與更高程度的普遍性
由于人類經(jīng)驗(yàn)的有限性——人類總是生存在一種特定的空間與時(shí)間里,約斯·德·穆?tīng)柗Q之為“視界”。他的視界理論由三部分組成,即視界拓展、視界融合和視界播撒。并認(rèn)為這三段同時(shí)也是闡釋學(xué)的三個(gè)階段。個(gè)人與文化、文學(xué)與隱喻都有一種視界。因此,穆?tīng)栒J(rèn)為有些文本因?yàn)橛兄厝徊煌臍v史視界或迥異的思想、習(xí)慣和傳統(tǒng),讀者感到解釋與溝通的需要。在闡釋學(xué)實(shí)踐中體驗(yàn)到困惑和誤解,反思就非常有必要。每個(gè)闡釋主體獨(dú)有的視界和經(jīng)驗(yàn),經(jīng)由反思而產(chǎn)生獨(dú)特見(jiàn)解。
做到與眾不同還只是“獨(dú)”,在闡釋學(xué)中重點(diǎn)是“識(shí)”。闡釋者對(duì)某一文本的本質(zhì)特征在發(fā)現(xiàn)和解釋的基礎(chǔ)上而產(chǎn)生真知灼見(jiàn)。從自身生命體驗(yàn)出發(fā),通過(guò)一種知識(shí)化形式揭示文本的秘密,發(fā)現(xiàn)非同尋常的意義。知識(shí)化不等于科學(xué)化。文學(xué)理論家設(shè)計(jì)出層出不窮的公理性、框架性的理論,目的是讓闡釋者不費(fèi)力氣地讀懂盡可能多的文本內(nèi)容,這一策略帶來(lái)的嚴(yán)重后果是:它遮蔽了讀者對(duì)文學(xué)的想象力和感悟能力。這里的知識(shí)化應(yīng)該傾向于感知、認(rèn)識(shí)和反思。文學(xué)文本展現(xiàn)的是活性的、流動(dòng)的、充滿想象的空間和世界,它可能設(shè)置了某種難以達(dá)到的理想標(biāo)桿,但這個(gè)標(biāo)桿設(shè)置恰好是人性向上的動(dòng)力。它可能揭示了人性的某些黑暗和不堪,此種狀態(tài)恰好是警示人性有向背黑暗和光明的選擇。文學(xué)指向有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恰好是對(duì)固化闡釋的一種拒絕。模式化闡釋觸摸不到文學(xué)的敏感區(qū)域,其價(jià)值也難以呈現(xiàn)。文學(xué)的真理在認(rèn)知領(lǐng)域,它不像科學(xué)真理可以驗(yàn)證。闡釋者面對(duì)文學(xué)文本,需要與其他學(xué)科文本進(jìn)行區(qū)別性對(duì)待:1.對(duì)“文學(xué)是什么”這個(gè)最基本的問(wèn)題是清晰的。2.不為文學(xué)有用與無(wú)用而困惑。3.承認(rèn)文學(xué)闡釋客觀上有去蔽與加魅的效果。去蔽即公共闡釋論中所說(shuō)的“澄明性闡釋”⑩。闡釋者應(yīng)該對(duì)難以理解的晦暗文本、不易接受的疏異性文本加以觀照、解釋和說(shuō)明,使文本向公眾漸次敞開(kāi),釋放其固有的自在性。加魅類似于“光暈現(xiàn)象”,本雅明認(rèn)為“早期的照片,表現(xiàn)在人的轉(zhuǎn)瞬即逝的面部表情中,我們看到了最后一縷光暈,就是這光暈給了他們憂郁、無(wú)與倫比的美”11。在闡釋過(guò)程中對(duì)文本意義的升華也存在一種照相原理中的光暈現(xiàn)象。4.了解作為語(yǔ)言藝術(shù)的文學(xué)的特性。看起來(lái)是一個(gè)最低要求,但在實(shí)際操作過(guò)程過(guò),闡釋者往往忘記了這一基礎(chǔ)性原則,轉(zhuǎn)而用科學(xué)手段分析文學(xué)。文學(xué)闡釋的獨(dú)識(shí)并不拒絕諸如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生態(tài)批評(píng)等外在的文化批評(píng)。文化批評(píng)可以打開(kāi)認(rèn)識(shí)路徑,但如果要從中獲得某種體驗(yàn),則需要拋開(kāi)主義、方法和規(guī)則,帶著感知進(jìn)入文本內(nèi)部。傾聽(tīng)人物的歡欣和悲苦,真切感受煙塵、汗水、血淚后面顫抖的靈魂,既有洞穿宏大歷史敘事的眼光,也有把握微觀世界細(xì)小脈動(dòng)的能力。把流動(dòng)的、轉(zhuǎn)瞬即逝的感覺(jué)固定下來(lái),認(rèn)識(shí)其價(jià)值,通過(guò)知識(shí)化表達(dá),上升為更高程度的普遍性。
文學(xué)闡釋的獨(dú)識(shí)不被重視,文學(xué)評(píng)論容易陷入“機(jī)械主義”誤區(qū)。文學(xué)闡釋既有它自身的本體性法則,同時(shí)還要警惕如何避免法則本身可能導(dǎo)致的僵死。那么,一種活性的,排除自身陷入死循環(huán)的法則是否存在?如果把闡釋者看作一個(gè)中立的認(rèn)知主體,闡釋者自身有限的經(jīng)驗(yàn)視界不被考慮在內(nèi)的話,“偏見(jiàn)”總是被圍剿和抵制。為什么會(huì)造成對(duì)“偏見(jiàn)”的偏見(jiàn)?絕對(duì)中立的闡釋者是不存在的。按照伽達(dá)默爾的說(shuō)法,偏見(jiàn)恰是理解之可能性的前提條件,因?yàn)槔斫馐窃凇扒耙?jiàn)”“前理解”的基礎(chǔ)之上達(dá)成的。海德格爾所說(shuō)的“前見(jiàn)”或者“前判斷”(Vorurteil,prejudice),迦達(dá)默爾把它擴(kuò)展到知識(shí)層面的成見(jiàn)。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gè)方面考察文學(xué)闡釋實(shí)踐中獨(dú)特見(jiàn)解。首先是藝術(shù)感知力,包括審美感知力、共情能力、藝術(shù)表現(xiàn)感知力。人類內(nèi)心深處的情感,能夠敏銳地把握藝術(shù)特性,通過(guò)對(duì)人物命運(yùn)、情境鋪排、事物細(xì)節(jié)、文字表現(xiàn)性等方面的感知,綜合起來(lái)形成一種感受。藝術(shù)感知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天賦異稟”的能力,感知力弱的人經(jīng)過(guò)訓(xùn)練也能得到相應(yīng)提高。藝術(shù)感知力強(qiáng)的人對(duì)于藝術(shù)表現(xiàn)力所給予的刺激反應(yīng)比常人激烈,能夠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情感力量和價(jià)值導(dǎo)向。其次是生活與教養(yǎng)。人文藝術(shù)感染力能夠?qū)θ水a(chǎn)生深刻的精神轉(zhuǎn)變。現(xiàn)代文化批評(píng)將文本內(nèi)部藝術(shù)價(jià)值和思想價(jià)值排在次要位置,重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闡釋行為本身,集中精力關(guān)注某一特定群體和對(duì)象,并為這些對(duì)象所遭受的不公而辯護(hù),提出批評(píng)和反思。將從特定對(duì)象反射出來(lái)的現(xiàn)象上升為普遍的價(jià)值意識(shí)和權(quán)利意識(shí)。闡釋者擁有特定領(lǐng)域深刻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和文化背景,能夠提出獨(dú)特見(jiàn)解。最后是闡釋能力。藝術(shù)感知力、生活與教養(yǎng)大都停留在知性層面,闡釋能力需要有邏輯和理性能力。笛卡兒確定了理性的原則,認(rèn)為有了理性的清楚明白,就可以把握一切真理。對(duì)規(guī)律的觀察已經(jīng)進(jìn)入本質(zhì)論階段,但還不是本質(zhì)。在觀察理性中存在或然性。或然性有大有小,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九十九在真理性面前是一樣的。沒(méi)有區(qū)別就不好斷言。精神科學(xué)不同于自然科學(xué),因此,文學(xué)闡釋中的理性和邏輯并不是要追求絕對(duì)真理,而是采取一種類比的方法。我們所說(shuō)的闡釋能力表現(xiàn)為歷史性邏輯和價(jià)值性邏輯。
四、沖突性闡釋
闡釋的多樣性決定了闡釋不僅是公共的,同時(shí)也是沖突性的,闡釋者的觀點(diǎn)彼此之間的沖突、對(duì)抗構(gòu)成了闡釋的總體性行為。每一種闡釋在反對(duì)者看來(lái)都是“強(qiáng)制闡釋”或者“反面闡釋”,這種沖突性闡釋正是文學(xué)闡釋的活力。按照康德的審美判斷力批判對(duì)“美的理想”的看法,認(rèn)為審美的理想的規(guī)定根據(jù)是主體情感而不是客體的概念。鑒賞判斷只以一個(gè)對(duì)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為根據(jù),“使一個(gè)對(duì)象在某個(gè)確定概念的條件下被宣稱為美的那個(gè)鑒賞判斷是不純粹的。”12他認(rèn)為有兩種不同的美,即自由美,或只是依附的美。花朵是自由的自然美,它不歸于任何按照概念在其目的上被規(guī)定了的對(duì)象,它自由地憑著自身使人喜歡。而一個(gè)人的美,或者一座建筑的美,則是以一個(gè)目的概念為前提的,這概念規(guī)定著此物應(yīng)當(dāng)是什么,附加其上的善與美同樣造成對(duì)鑒賞判斷的純粹性傷害。因此,“這種判斷就不再是一個(gè)純粹的鑒賞判斷了。”13文學(xué)作為以概念為前提的依附的美(即第二種美),其闡釋行為預(yù)設(shè)了雜多的目的、雜多的愉悅。其鑒賞判斷的先天根據(jù)以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作為一個(gè)結(jié)果,或者普遍的道德概念先天性地推導(dǎo)出來(lái)。純粹鑒賞判斷是不依賴于刺激和激動(dòng)的,而文學(xué)闡釋,可以套用康德的原話——“這種鑒賞當(dāng)它為了愉悅而需要混有刺激和激動(dòng)時(shí),甚至將這作為自己贊賞的尺度時(shí),它就永遠(yuǎn)還是野蠻的。”14那么,沖突性闡釋就成為文學(xué)闡釋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文學(xué)闡釋的沖突性大致有以下特征:1.沖突性闡釋是以文本為基礎(chǔ)的沖突,每一種闡釋的意義本體都能從文本中實(shí)現(xiàn)對(duì)應(yīng)(包括實(shí)物和情感)。2.沖突性闡釋雖然是以公共理性為前提的,但混雜著因個(gè)體愉悅目的而產(chǎn)生的刺激和激動(dòng)等非理性因素。3.沖突性闡釋是否定和揚(yáng)棄的過(guò)程,最終表現(xiàn)為一種合目的的形式。4.沖突性闡釋匯合各種意見(jiàn),保證文本的每一種意義都最大限度地彰顯,能夠?qū)崿F(xiàn)從混沌到澄明。每一種獨(dú)特的見(jiàn)解與其他獨(dú)特見(jiàn)解相遇,充分表明了闡釋主體的存在價(jià)值,以及闡釋對(duì)象意義的多樣性。政治闡釋、宗教闡釋的總體性有強(qiáng)制性特征,既保持其本身的合法性,同時(shí)也以此方式維持其闡釋行為的合法性。一旦這合法性被解構(gòu),對(duì)政治或者宗教內(nèi)部來(lái)說(shuō)都是一場(chǎng)革命。文學(xué)的闡釋權(quán)是開(kāi)放的、公開(kāi)的,而且大多數(shù)時(shí)候是平等的。與政治闡釋、宗教闡釋不同,不用爭(zhēng)奪闡釋權(quán)。它的所有闡釋動(dòng)機(jī)是為文本、為闡釋者自身爭(zhēng)取生存空間。對(duì)文本來(lái)說(shuō),不論是否定性闡釋,還是肯定性闡釋,經(jīng)過(guò)沖突、協(xié)商,對(duì)于被闡釋對(duì)象來(lái)說(shuō),客觀上實(shí)現(xiàn)了空間的拓展和時(shí)間的廣延。對(duì)闡釋主體來(lái)說(shuō),通過(guò)這種闡釋行為,進(jìn)一步確立自我與世界的關(guān)系,可視為生命價(jià)值的延展,具有存在論意義。由此可以推斷:1.闡釋是一種生存權(quán),這一權(quán)利將最大限度地符合自己的利益訴求。2.在實(shí)現(xiàn)這個(gè)權(quán)利的過(guò)程中,闡釋者以自我生命體驗(yàn)作為立法依據(jù),對(duì)社會(huì)整體的價(jià)值尺度、審美標(biāo)準(zhǔn)既有服從也有挑戰(zhàn),以創(chuàng)新性體驗(yàn)探索生命自由。這一過(guò)程會(huì)形成激烈的沖突。3.在互相沖突的闡釋中,引入反思闡釋與建構(gòu)闡釋,不斷調(diào)整自身,超越個(gè)體闡釋的狹隘局面,從而獲得一種總體上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闡釋。其行為動(dòng)機(jī)符合人的“類本質(zhì)”。4.個(gè)體闡釋匯入公共闡釋之后,即成為一種具有公共理性的闡釋。那么,文學(xué)闡釋的目標(biāo)也變得明確起來(lái),在個(gè)體進(jìn)入公共這一集體性行為中,達(dá)到說(shuō)服別人(觀點(diǎn)搖擺的人),將其他邊緣群體一同納入這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之中。這種意愿不像政治和宗教那么強(qiáng)烈。
從社會(huì)學(xué)的角度考察,造成沖突性闡釋的原因,是與搶占資源、爭(zhēng)奪權(quán)力、自我利益最大化相關(guān)。每一種闡釋背后都有一個(gè)強(qiáng)大的利益共同體,闡釋者為這個(gè)共同體代言,集中所有成員的訴求,以某種現(xiàn)實(shí)為依據(jù),虛構(gòu)一種觀念性的東西,有現(xiàn)實(shí)性但不一定有真理性。文學(xué)闡釋的沖突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有些可能集中了某一利益共同體的集體意愿,達(dá)到某種訴求。有些純粹是個(gè)人見(jiàn)解。各種同類型沖突性闡釋合并的同時(shí)也是沖突性被消失的過(guò)程。為了保證在沖突性闡釋中獲勝,占據(jù)某一領(lǐng)域制高點(diǎn)是沖突的最終形式。以屈原的作品為例。最終形成三種制高點(diǎn),以愛(ài)國(guó)情懷為核心的道德制高點(diǎn),以浪漫主義為核心的情感制高點(diǎn),以詩(shī)歌創(chuàng)新手法為核心的知識(shí)制高點(diǎn)。最后各種制高點(diǎn)并不是完全排斥對(duì)方。
五、余論
其他學(xué)科的闡釋可能只需要闡釋者做一個(gè)冷靜旁觀者,便可做出理解和判斷。文學(xué)闡釋需要闡釋者既是旁觀者同時(shí)也是參與者,尤其是情感參與。前者的判斷和理解是知識(shí)認(rèn)知的結(jié)果,后者是知識(shí)認(rèn)知+情感認(rèn)知,兩種認(rèn)知都是困難的,文學(xué)闡釋是兩種困難的結(jié)合。文學(xué)闡釋學(xué)是闡釋學(xué)的分支學(xué)科,作為一門新興學(xué)科,目前在文論界還處于“開(kāi)路破題”的階段。要把文學(xué)闡釋學(xué)說(shuō)清楚是艱難的,盡管文學(xué)本質(zhì)上屬于感性事物,如果嘗試把這門學(xué)科知識(shí)形態(tài)化,它仍然需要形式邏輯和先驗(yàn)邏輯兩種邏輯思維的介入,形式邏輯判斷雖然不用考慮對(duì)象,但它要考慮概念與概念相符合,需要一個(gè)靠得住的整體框架;先驗(yàn)邏輯直接與對(duì)象打交道,它同時(shí)考慮實(shí)踐部分和理論部分,需要以大量生動(dòng)活潑的文學(xué)文本為對(duì)象的不那么純粹的實(shí)踐理性。文學(xué)闡釋學(xué)作為精神學(xué)科,還要解決方法上難題和存在論難題。在學(xué)科建構(gòu)上,既要構(gòu)建適合解決中國(guó)文藝現(xiàn)實(shí)的文學(xué)理論,同時(shí)它作為一種從實(shí)踐中提煉而來(lái)的一般理論,應(yīng)該是普遍意義上的文學(xué)理論,某種意義上它應(yīng)該超越“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文學(xué)闡釋學(xué)的真理性問(wèn)題,在以上方法工具達(dá)不到的情況下,其不確定性或許可以通過(guò)“提問(wèn)研究”的方式獲得進(jìn)一步確認(rèn)。
【注釋】
①②121314[德]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9,第255、255、273、275、267頁(yè)。
③[德]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上),賀麟、王玖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294頁(yè)。
④金惠敏:《闡釋的政治學(xué)——從“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談起》,《學(xué)術(shù)研究》2019年第1期。
⑤“公共闡釋”概念由張江提出,見(jiàn)《公共闡釋論綱》,《學(xué)術(shù)研究》2017年第6期。
⑥張江、[英]約翰·湯普森:《公共闡釋還是社會(huì)闡釋——張江與約翰·湯普森的對(duì)話》,《學(xué)術(shù)研究》2017年第11期。
⑦Yuval Noah Harari: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Penguin Randorn House UK,Vintage 20 Vauxhall Bridge Road,London SWIV 2SA.p.3。
⑧“善良意志”是康德的道德哲學(xué)的核心概念,以此為中軸展開(kāi)的義務(wù)論對(duì)西方道德哲學(xué)的現(xiàn)代發(fā)展影響深遠(yuǎn)。他在《道德形而上學(xué)基礎(chǔ)》開(kāi)篇就表明觀點(diǎn),認(rèn)為在世界之內(nèi),甚至根本在它之外,除一個(gè)善的意志之外,我們不能設(shè)想任何事物,它能無(wú)限制地被視為善的。
⑨[德]伽達(dá)默爾、[法]德里達(dá):《德法之爭(zhēng)——伽達(dá)默爾與德里達(dá)的對(duì)話》,孫周興、孫善春編譯,商務(wù)印書館,2005,第51頁(yè)。
⑩張江在《公共闡釋論綱》中認(rèn)為公共闡釋具有六個(gè)特征,即理性闡釋、澄明性闡釋、公度性闡釋、建構(gòu)性闡釋、超越性闡釋、反思性闡釋。
11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Penguin books Ltd,80 strand,London WC2R,ORL England,2008. p14。
(卓今,湖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