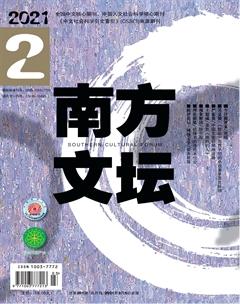欲望超克與精神救贖
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提出,故事講述者最為明顯的人為技法之一,就是那種深入情節表面底下,去求得確實可信的人物思想情感畫面的手段。無論我們關于講述故事的自然技法的概念是怎樣的,每當作者把所謂真實生活中沒人知道的東西講述給我們時,人為性就會清楚地出現。①小說是作者依靠著虛構的角色,通過在虛構空間中設定的人物的活動來表達主題的。在小說中,作者與人物是孿生兄弟,作者所創造的角色實質就是其“代言人”。研究小說主題的表達方式,其實就是研究作家與小說角色之間的關系,這一關系往往體現出極為濃烈的人為性特征。人為性的不同體現方式,正是每部小說的美學差異所在。
在小說中,處在第一地位的講述者是人們所能接觸到的唯一切實的存在。那么,講述者如何引導就至關重要了。好的引導雖是簡單但并非無趣,充滿吸引力又遵循本能。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傳統的獨白型小說之中,作者那如同導游一般的身影,無論是主人公以第一人稱“我”,還是第三人稱的“堂吉訶德騎士”,都很難拋開導游的身份。
在研究楊映川小說主題的表達方式過程中,我們能清楚地感知到人為性的特征,即她對于小說角色有著極強的“控制感”——為每個角色都規劃好了適合他們的情節——每一個角色的發展軌跡都映射著敘述者的心跡。或者說,在楊映川小說中,經過作者精心設計的每一個角色,他們的行動軌跡都遵循著作者所設置的他們各自的個性。《不能掉頭》的主角黃羊自卑且謹慎,所以他臆想中的那場逃亡冒險在現實中有了實實在在的投射,他的逃離一定是小心翼翼而又漫長的,不會像堂吉訶德那樣荒誕;《狩獵場》的主角李綠聰明又固執,所以她一定會不停地反抗,就算失去一切也不會接受她不愿意接受的境地。我們可以說,她筆下角色們的聲音就是經過了各種轉喻與“化妝”的楊映川的聲音,因而將重點放在其小說的人物角色與倫理設定上便顯得饒有興味。
一、從“救贖”出發
救贖是楊映川小說的重要主題。她早期小說中的人物往往在一種“被拖入”的情境中成長,但她筆下的人物并沒有因為自己被動進入情境,而放棄對自我的控制權,他們在竭力嘗試,甚至犧牲自我的過程中完成了自我救贖。在小說《我困了,我醒了》中,主角張釘是一個慣于逃避責任的男人,從小到大一有難事就一睡了之,而這種逃避最集中體現在張釘“守財奴”性格設定上。他承諾了要幫女朋友盧蘭訂一輛車,但當到取車的時候,他睡著了,睡了整整27天;他處心積慮不借錢給前女友,為此他睡了一天,是盧蘭把自己的錢取出來給了張釘的前女友。小說的結尾,張釘被綁架勒索,盧蘭冒著性命的危險幫他擋了一刀,在張釘血流不止又將昏睡過去時,盧蘭用牙齒狠狠地咬住了他,盧蘭的堅持似乎讓張釘找回了那個真實的自己,讓他完成了“被動”救贖,盧蘭在不放棄的執念中也完成了一場自我主動的救贖儀式。《當花瓣離開花朵》的主人公莫云因為自己的出身沒有身邊的人顯赫,或者說自己過于平凡,甚至有些窮困潦倒而質疑自己。困境并沒有給莫云帶來奮斗的斗志,而是帶來了厭世的情緒。她并不仇富,而是希望自己無須付出,便能擁有像身邊那些有錢人一樣的生活。物質的相對匱乏讓她更想擁有這些自己得不到的,莫云在嘗試驗證自己身份失敗后,開始賭氣并埋怨父母。她其實明白,自己的出身是無法改變的,但是她也無力把此作為生活的動力。直到母親生了一場重病,她發現父親為了能快速掙錢而出賣自己的身體,此刻莫云發覺自己對于家庭還是有著認同與眷戀,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認罷了。同時,現實也給她上了一課:自己的好友與自己崇拜的人格完美的偶像發生了一夜情并懷孕。她嘗試在互聯網上出售自己的初夜來試探,看自己的初夜到底值多少錢,結果卻令她大跌眼鏡。她開始接受了世界和自己的不完美,在奔赴遙遠大學的那一刻,在成人禮中開始了自己主動救贖之路。
這一階段,楊映川筆下的角色都有著豐富復雜卻難以填充的欲求,這些欲求占據了她所創設角色的生活的全部,甚至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受制于強烈的欲求,這些人物往往被遮蔽,從而在尋求救贖與自我救贖的過程中徘徊。中篇小說《不能掉頭》講述了主人公黃羊把自己殺人的夢當成了現實,而為了這個夢不斷逃亡的荒誕故事。黃羊的欲求是“活著”,他為了求生,在不同的城市間躲藏,為了生存或者說自由而愿意付出一切的努力,他的欲求強烈到讓他無法脫離自己的夢境世界,一方面源于對胡金水一直以來嘲笑和捉弄自己的仇恨,一方面則是源于自己對自己過失的怨恨,這種恨又是由愛而生的,愛恨交織、善惡交織,他一直都在救贖的道路上,只因欲望太重,交織太密,無法完成個體的自我確認,也就無法完成自我救贖。在《失魂臺》中,主人公李廣度曾經在生活上放縱無度,在一場車禍中因為自己的過失失去了自己的女兒,妻子精神崩潰并離他而去,他的欲求從原來生活上無節制的自由,變成了渴望以自殺來贖罪。而李廣度在失魂臺上又遇到了同樣像他一樣來求死的人,卻共同在文姨以及村里人真情感化下頓悟,自我的身份得到了確認,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屬于他們的救贖。
不管是救贖進行到何種程度,用何種方式,結果又如何,楊映川小說中的角色對于救贖的渴求都是極度強烈的,或者說他們時常陷于自身的處境而試圖掙脫之。《不能掉頭》與《失魂臺》可以說是兩種代表著最極端與最基礎的需求。《不能掉頭》是個求生的故事。主人公黃羊有著強烈的活下去的需求,本來求生也是所有動物的本能,但黃羊貪生到了極致,甚至來不及去核實自己究竟有沒有殺人,僅僅因為錯誤的夢魘就開始一生逃亡,這才有了他一路的悲歌。《失魂臺》本來是一個求死的故事,主人公李廣度因為自己的錯誤造成了悲劇,其中包括害死自己的女兒,從而陷入無窮的懺悔。站在他的角度,如此罪孽深重的懺悔只有死亡這一個方式可以選擇。這兩部小說體現的是角色們生死這兩種最極端的欲求,是角色們在楊映川的設定之中必須做出的反應。而楊映川作為角色的孿生體,角色的反應其實也是她自身的反應的鏡像。她將自身對人的本能與需求的思考分解到筆下的人物中。此時楊映川小說的創作是屬于生活的,直接反映著生活的日常和瑣碎,主角的設定集中在掙脫生活的嘗試,救贖的原因也主要由生活而發生。她的這種應激反應不光是她的小說美學,也可以說是楊映川內心情感與思維方式的集中表達。
二、欲求的消退與主題的轉向
楊映川2015年的作品《馬拉松》可以看作是她創作主題轉向的一個風向標,欲望的誘惑依然存在,但個體對于欲求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受外界的影響逐漸轉向了對內,特別是人內心的思考和沉淀。《馬拉松》中,開餛飩店的范寶盛是一個精明的人,曾有著強烈的欲求與功利心。但兒子的丟失,讓范寶盛認為這是上天給他的懲罰,于是,他開始學會感恩生活,從粗暴不羈轉向了隱忍慈悲,堅持讀了十多年的《金剛經》,向所有曾惡意相對或粗暴對待的人道歉;他為了讓孩子能找到回來的路,放棄了可以擴張的事業,沒有搬離住處,他的餛飩店在他性格轉變之后越開越紅火。在小說中,人的私欲不斷被消解,因為孩子的失蹤,父親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而把原來與鄰居的矛盾甚至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歸咎于自身,把所有的“罪”都聚焦到自身,他的贖罪雖然仍舊是為了找到自己的孩子,但心靈已經有了向善的超越,慢慢地,這種“善”成為范寶盛的生活態度,這種富有禪意的“善”讓激烈的矛盾軟化,讓他脫離了簡單的愛恨情仇,對比其他市井小民的斤斤計較,他的形象尤為凸顯,尤為震撼。小說結尾,范寶盛“看到年輕時候的自己”,暗示了他與兒子的重逢。范寶盛主動的“退”不僅讓他的過錯得到了挽救,也讓他得到了圓滿的人生,楊映川由是完成了對人的本能與需求的救贖,這也意味著對理想生活態度的一種詮釋,即消釋欲望,不再強求,便能收獲心靈的平靜與祥和,并在這份禪意中靜靜體悟生活的圓滿。
這種轉向,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人物主體“需求”的減弱。食欲是人甚至說是動物最本能、最重要也最原始的需求。在楊映川的小說中,食物或者說食欲往往是一個特色“環節”,對于“吃”的描寫在小說的細節中隨處可見。《做只鳥吧》的開篇便介紹了一桌剩菜:看得出昨晚“喝的是魚頭豆腐湯,吃的是素炒西蘭花、蔥花炒蛋、板栗燜排骨”;《狩獵季》中周啟釀制的晶瑩透明的芒果酒、百香果酒沁人心脾,隆重的野味全鳥宴讓人嘆為觀止。我們可以看到之前的楊映川對于美食的需求是相當強烈的,無論情節怎樣推進,對食物詳細而生動的描寫從來都沒有缺席,而在2019年發表的《無腸》之中,楊映川卻對這種最原始的本能需求發起了拷問。
《無腸》通篇圍繞著“吃”這個話題來講述,相濾息來自于海奧華星球,他的使命是拯救星球命運,在地球上與人類的相處中,他忘卻了自己的身份,沉迷于以“吃”為代表的物質生活不能自拔。當圭族的相合第一眼發現相濾息的時候,就感受到他身體強大的磁場能量,在相合苦口婆心的勸導下,相濾息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于是開始絕食。慢慢地,他發現其實絕食并沒有那么痛苦,他并不需要吃東西,呼吸空氣便可以有飽足感。他的功能恢復得異常之快,最終達到了身體內部的平衡,他與相合拉著手說,天長地久,與地球同在,預示著他們又將共同完成拯救地球的使命。《無腸》從“吃”這個角度出發,對人類無節制、無度、無法克制的追求物質欲望進行某種斥責,而這種貪婪的追求會破壞人自身的平衡,這種平衡是物質和精神的平衡,人只有在物質和精神需求合一的基礎上才能達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無腸》預示著一種毀滅,但同時也給人類以希望,雖然相濾息和相合都是“外族”人,但他們都含有地球人的血統,當人沖破了物質的束縛,而追求精神的極致的時候,是可以實現自我最真實的蛻變的。這便是楊映川對于欲望的拷問。她的拷問聚焦到如何把握合理需求與無休止的欲望之間的度,她關注到個體刻意放大需求,以需求為借口掩飾自身對于貪婪欲望追求的行為。楊映川對于“吃”的拷問可以延伸成她對于自己過去沉溺的欲望與需求的拷問,這象征著她的懷疑與轉變。
在2019年發表的《九尾貓》中,束靜生收養了一只弱小無助的小黑貓——黑寶,從此,黑寶(貓)的生命與靜生(人)的生命交織在了一起。靜生與黑寶形影不離,互相陪伴。靜生得了瘧疾,黑寶救了他的命。不料意外接踵,靜生父親母親相繼離開人世,妻子轉頭回了娘家,靜生把黑寶寄存在寺廟里,自己不知所蹤。黑寶并沒有放棄掙扎自我解脫,而是朝著那六道輪回而去,通過修煉“九尾功”報答靜生。一次次幫助靜生后代實現愿望的過程,仿佛是欲望的陳列,把人性貪婪、無節制的一面展露無遺。直到黑寶找到那個孤單的殘疾女孩。女孩拿來了祖傳的刻有黑寶的木梳,他們找到了心靈的契合點。當黑寶要為女孩實現一個愿望的時候,女孩說“謝謝你為我們家做了那么多事情,我沒有什么愿望”。當感恩和回報本身變成一種愿望或者欲望的時候,這種欲望的功利性便被摧毀。欲望在我們看來似乎總與功利相關,總帶有復雜的利益的關系,然而女孩的欲望來源于其對生活的正面思考與其帶來的知足的禪宗心境。女孩的達觀和善良消解了欲望中的灰暗的成分,成為一面心靈的鏡子。女孩幫助黑寶實現了愿望,它的第九條尾巴冉冉生長。靜生與女孩形成了一個輪回,而黑寶還是黑寶,只是從貓變成了人。黑寶回到了靜生童年,這次她主動放棄了全能和完美,成為和靜生一樣的人,與靜生互相陪伴成長,體驗生活的真實與缺憾。《九尾貓》相較《馬拉松》《無腸》創設了一個更為完整的輪回,更為明顯地釋放了一種無欲無求的大愛,當個體真正能放棄全能與完美,放棄所追求的一切,活在當下,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凈化與洗滌,才能實現“得”之道。
楊映川2020年發表的《有人睡著就好》是一部關于生死的嚴肅主題的小說,但是角色的應激反應是明顯與《不能掉頭》和《失魂臺》所不同的。嚴諾最好的朋友云海身患絕癥,云海面臨著與《不能掉頭》中的黃羊一樣的求生問題,同樣的絕境,黃羊選擇不顧一切地活下去,而云海甚至不做選擇。云海這個行為是區別于之前楊映川的寫作模式的,過去的角色或者說楊映川本人對于生死有著十分明確的態度,但現在這個態度變得曖昧了。而嚴諾本應該作為一個救贖者的角色,他卻踟躕了,他很愛自己的朋友,但明顯不像《我困了,我醒了》中的盧蘭一樣為了愛人變得堅定,嚴諾懷疑自己,但卻也沒有試圖擺脫困境,這也是明顯區別于楊映川之前小說中的救贖者的,消極的救贖意味著角色的自我需求的驟降,也意味著楊映川小說新的轉化。人物主體對環境的應激反應大為減弱,這對應著的就是角色們需求的減弱。于是他們有的選擇生活在一個新的社會邏輯之中,有的則放棄選擇。既然楊映川的作品之中角色即為作者本人的孿生體,角色的無感也就是楊映川本人的無感,角色們不再想方設法去控制與改造自身所處,而是追求自身心靈的感悟并運用這份感悟來解決問題,在自我感悟與解決問題之間來回自證,就像對全能和完美的主動舍棄,但所謂有舍就有得,楊映川筆下的人物在舍棄與自證中獲得心靈寧靜與心境圓滿,得到充滿禪意的人生。或許也可以大膽預設楊映川也是如此,這也許是她棲息沉溺于現實生活太久導致的,也許是對一種新的領悟的渴望,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她仍然需要尋找一個答案,一個更加的廣闊、區別于救贖與被救贖的創作范式。
三、新的范式與創作的實驗
從2018年開始,楊映川開始嘗試科幻或者說是魔幻現實主義寫作。科幻小說與現實主義小說的重要區別在于環境的設定,科幻小說在設定上具有與現實生活不同的邏輯,這種改變意味著某種程度上對熟悉的現實生活的放棄,也可以說是現實生活能給予小說角色以及作者的刺激越來越小,作者和角色們都需要一個新的邏輯體系來支撐自己。
角色不知道該對環境做出怎樣的反應,而這個問題也對應著作者不知道該怎樣對現實生活做出反應,或者陷入明知如何反應卻無法實現的怪圈。她無法界定自己設定的救贖是否正確,也無法確定她的角色們在她的設定下做出的反應是否自然而真實。這樣看來,只有創造一個新的邏輯的社會——也就是科幻的社會,才可能讓角色與作者做出“真實”的反應。在楊映川201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知微門》中,設計了主角與狄仁杰、胡夫對話的場景。與名人對話其實有尋求幫助之意,在對話中尋求歷史與現實的連接點,再將這種連接延伸至未來。她2018年發表的《失憶之城——心識愿者M11汪有識實驗檔案》《耳洞——心識愿者S4騰護實驗檔案》,2019年發表的《交界——心識愿者L21藍樘實驗檔案》《第三只眼——心識愿者T1何西實驗檔案》,通過系列的科幻小說構筑了一個新的有別于現實世界的心靈世界。在她2018年發表的《取經》中有這樣的一段描述:“栩栩說,每個作者不都是在自己的故事中行進的嗎?以前我們在作品中反映出來的一切心思意念行為動機,完全都是長久以來被灌輸的知識的外化,該到打破這種形式的時候了,隨機,無意,天成。”②栩栩在現實的列車上無法找到想要的,或者根本不知道要尋找什么,于是在“他人”的引導下,走上了通往新世界的列車,打破和改變成為主角設定的方向,實現由外向內的尋找和改變,在找到《宇宙之問》后,栩栩獲得了先驗的力量,得到了生命的超脫。楊映川完成了從現實主義到科幻-邏輯體系的轉向。
作為女作家,楊映川筆下的女性人物在不同時期也有著顯著的變化。角色是作者的化妝,作為楊映川的“代言人們”,她們都是楊映川在不同時期的鏡像,我們對角色的解讀也作用于楊映川本人,因此也能清晰地感受到,楊映川自身女性主義的變化。
楊映川早期的作品中,女性通常是一個救贖者的角色,比如《不能掉頭》中的何甜與宋春衣、《我困了,我醒了》中的盧蘭,她們都有著善良熱情到極致的特點,為拯救自己所愛的人而奮不顧身就是這種特點的具象化。而在2019年發表的《硬核女主》《住在香若樟》之中,顧若初和俞順順的個性上就完全是另一種形象。《硬核女主》中的顧若初可以說是一個比較理想型的少女形象,她對于愛情對于婚姻有著自己的主見,她的第一任男友叫余自在,她在與余自在的戀愛中一直是主動的,余自在家境不好,顧若初愿意拼命掙錢也不覺得累,他們都曾真心愛過對方,但他們兩人因為經常性的爭吵并沒有成為夫妻,但余自在一直在她的朋友圈里沒有遠去。某天,余自在電話顧若初要送她張學友演唱會的門票,顧若初也意識到捕獲她芳心的不是余自在,而是余自在的那首《三生有幸》。如果說這些都是被標記著青春印記的懵懂而單純的愛戀,那么顧若初的第二任男友韓囑似乎是在向青春敲響警鐘,在鄉間小路上,顧若初和韓囑在自行車騎行的過程中說著笑著親吻著,在一個陡坡處車子意外翻車,顧若初便收獲了一個傷疤。在韓囑甜蜜的承諾中,他們的感情似乎達到了一個高潮。而伴隨著承諾的是猝不及防的分手,韓囑留下了車和房子,消失不見,顧若初在異常的平靜中接受了現實。六年沒談戀愛的顧若初小心翼翼地開始了與胡恒文的交往。顧若初對胡恒文是有好感的,胡恒文也并沒讓她失望。但顧若初都沒有主動出擊,她在遵從自己的內心,她在等待那一個臨界點。在搬遷時的一個意外讓顧若初主動說出了“你愿不愿意養我”這句話,胡恒文自然而然地把戒指放到她的手中,她的心被擊中,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剛剛好。在這里,顧若初沒有一味地去為了愛情抗爭,或者作為一個拯救前任的形象出現,她在理性的后退中完成了“硬核女主”身份的轉變,實現了對自身的和解。
《住在香若樟》中的俞順順面臨家里的逼婚,為了解除家庭包辦婚姻對她的捆綁,與王超凡結婚,她下定決心低價買了一套房子,因為在這房子里曾發生了一場兇殺案。入住兇宅的俞順順逐漸發現自己并不是那么堅強與無所畏懼的,她本能地對自己兇宅帶有的心理暗示,晚上睡覺不關客廳的燈,一個人在家的時候盡可能地越過客廳……打開陽臺,陰風習習,這些都令俞順順不安,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但這種自我懷疑產生了與其對立的與性格的對抗,她蓄積著的同事對她的排擠和冷嘲熱諷的情緒終于爆發,在慶功宴上,她咄咄逼人,一改往常任由大家涮得賠笑的常態,“懷著從未有過的氣急敗壞破罐破摔同歸于盡”,把自己買兇宅的事情托盤而出。這樣一種反常的表現,使得同事們被她的氣場所震懾,這件事也讓他們(被迫)改變了對俞順順的態度。部門同事開始給她送禮、辦公室的空間變大、安排下屬做事無人拒絕、年底的獎金位列最高一檔……俞順順接受了恐懼和自己的不完滿,只因為她的這種改變,這些略顯荒唐的轉變都到來了。
近年來,女性主義呈極端化趨勢,部分女性主義者過于強調女性權力,主張追求完全的獨立自由,極易受到其他思潮影響,偏離原本的女性主義邏輯。③楊映川筆下的女性要么不再主動追求愛情,要么接受恐懼,更不用提為了改變自身拯救他人而奮不顧身。女性不再渴求拯救他人,不再占主動地位,這是女性主義傾向減弱的一種體現。楊映川作為受過較高教育的女性,本應該是為女性主義發聲的主力,而她確實在早期也一直在作品之中賦予女性角色更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相比現在的“急速剎車”,楊映川顯然察覺到了目前女性主義的泛濫,于是才有了顧若初和俞順順這樣看似弱小實則真正睿智獨立的女性形象,楊映川對于女性主義發展趨勢顯然有著相當敏銳的嗅覺。
一個作家寫作主題的轉向,既是本身美學思維的轉向,也是生命哲學的轉向。在信息技術爆炸的當今社會,技術的飛速增長帶來生產力的飛速提升,但是生產關系的解放有其滯后性,因此帶來的諸如貧富差距、社會競爭等矛盾加劇。在現代性場域下,由于故意和非故意的任性導致了風險社會的來臨。技術的解蔽、祛魅功效,使一切神秘的東西都無所遁其身。對人之外和人自身的自然的過度“開發”導致人與自然秩序失衡。④加劇的矛盾是一種失衡,這種失衡使得人們不僅焦慮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還有心理恐慌和精神迷茫,最終,這些情感雜糅到一起,形成了整體的社會焦慮。低欲望與低需求是他們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社會焦慮的應激反應。這種焦慮與楊映川小說的人物處境以及楊映川本人是對應的。
不管是貫穿于楊映川小說始終的救贖主題,還是魔幻現實主義的探索、更為清淡的欲望描寫的主題轉向、女性主義的實驗,都是楊映川的對于生活、對于世界、對于創作的某種選擇,而這種選擇是隨著時間與心境不斷變化的。對于小說角色和主題的實驗性創作,楊映川注入了更多的心血,實驗不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減法,楊映川逐漸傾向用質樸的角色、簡單的情節,喚醒讀者內心深藏的那份純真,同時也讓自己的心靈得到某種程度的凈化。“有舍才有得”,楊映川似乎深悟此理,當然人的心靈變得博大寬厚,便能如煩惱倒空的杯子,走向平靜平和。楊映川以淡然的態度面對外界的物欲橫流,以自省自證探求自己的內心。她的小說實現了時空的超越,從救贖出發,從人的欲望出發,從強烈的欲望書寫到清淡的生活反思,無形的力量直指當代人的內心焦慮迷茫的那一面,在不斷的超克中試圖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價值形態。
【注釋】
①[美]韋恩·布斯著:《小說修辭學》,華明等譯,北京聯合出版社,2017,第4頁。
②楊映川:《取經》,《作品》2018年第9期。
③黃楚新:《女性主義的覺醒與濫觴》,《人民論壇》2019年第2期。
④晏輝:《 現代性場域下生存焦慮的生成邏輯》,《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3期。
(李遜,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