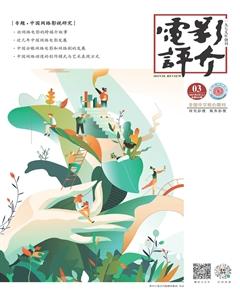媒介融合視域下電影形態(tài)的重構(gòu)
李大偉 王歡歡
自電影誕生一百多年來,其定義一直被反復(fù)探討:喬托·卡努杜的《第七藝術(shù)宣言》賦予電影第七藝術(shù)的身份;安德烈·巴贊的“攝影影像本體論”定義了電影是活動的影像;克里斯蒂安·麥茨援引索緒爾的符號學(xué)原理,認(rèn)定了電影是同語言一樣具有約定性的符號系統(tǒng);麥克盧漢則認(rèn)為電影是可以和書本相媲美的重要媒介,其形態(tài)在未來有著無限的演進可能。但無盡的追問與界定最終也未能達(dá)成一個公認(rèn)的概念,只留下了一條關(guān)于電影概念建構(gòu)的“漸近線”。[1]
當(dāng)前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打破了不同媒體間的壁壘,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新媒體對傳統(tǒng)媒體在形式、內(nèi)容和結(jié)構(gòu)上進行合并重組,媒介融合時代的到來讓信息的傳播方式、社會的生產(chǎn)方式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亨利·詹金斯所說:“融合這一術(shù)語用來描述媒體傳播方面技術(shù)、產(chǎn)業(yè)、文化和社會領(lǐng)域的變遷。它所涉及的一些共同理念包括橫跨多種媒體平臺的內(nèi)容交流、多種媒體產(chǎn)業(yè)之間的密切合作、尋求新舊媒體縫隙間的媒體融資新框架以及那些四處尋求各種娛樂體驗的媒體受眾的遷移行為等。”[2]
媒介融合就其表現(xiàn)形式而言分為兩種。其一是在傳媒業(yè)界跨領(lǐng)域的整合與并購,并借此組建大型的跨媒介傳媒集團,打造核心競爭力,應(yīng)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其二則是媒介技術(shù)的融合,將新的媒介技術(shù)與舊的媒介技術(shù)聯(lián)合起來形成新的傳播手段,甚至是全新的媒介形態(tài)。[3]即文字、聲音、圖片、活動影像等媒介形式全盤數(shù)字化后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重新排列組合的過程。傳統(tǒng)的媒介產(chǎn)業(yè)融合是縱向整合,往往指通過產(chǎn)業(yè)并購的方式完善內(nèi)容制作、發(fā)行以及放映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鏈,例如阿里巴巴成立阿里影業(yè)投資制作電影,收購流媒體放映平臺作為分發(fā)渠道,打造線上購票平臺等。如今的媒介產(chǎn)業(yè)融合則更傾向于橫向擴張,媒體公司不斷納入新的媒介領(lǐng)域,比如騰訊互娛“泛娛樂”推出騰訊游戲、騰訊動漫、騰訊文學(xué)、騰訊影業(yè)、騰訊電競五大業(yè)務(wù)平臺,構(gòu)建了一個打通游戲、文學(xué)、動漫、影視、戲劇等多種文創(chuàng)業(yè)務(wù)領(lǐng)域的互動娛樂新生態(tài)。
媒介融合已經(jīng)在本體論層面改變了電影的存在方式,具體表現(xiàn)在媒介形態(tài)、營銷形態(tài)、消費形態(tài)和生產(chǎn)形態(tài)幾方面,對電影形態(tài)的研究也是重新思考電影本體性所在的關(guān)鍵切入點。
一、電影的外在形式——媒介形態(tài)的變化
“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其形式的不斷變遷,使其從固定性的媒介結(jié)構(gòu)變成一種過程性的框架,電影動態(tài)性的變革使得其媒介屬性更加顯性化。”[4]原來的黑白、無聲、膠片電影逐漸發(fā)展為現(xiàn)在的彩色、有聲、數(shù)字電影,從2D到3D、從單向到互動,電影作為一種“富媒體”不斷地吸納更多的資金與先進技術(shù),它的誕生本身就是媒介聯(lián)動的產(chǎn)物,而歷史也證明電影仰仗著高昂的制作成本,往往可以率先嘗試最先進的影像技術(shù)。與不斷變革的影像技術(shù)不同,電影院為觀眾提供的觀影儀式感一直留存至今,也成為電影與其他影視作品有所區(qū)別的標(biāo)志。但電視劇、網(wǎng)絡(luò)電影、綜藝、短視頻等影視產(chǎn)品的增加使電影的獨特性逐漸減弱,線上流媒體的蓬勃發(fā)展也讓“堅守影院”與“投奔網(wǎng)絡(luò)”變成了一個兩難的選擇,2020年突發(fā)的疫情更是讓“電影的終結(jié)”“后電影狀態(tài)”等言論再次浮出水面,電影需要在新的媒介融合環(huán)境中重新定位。
“好萊塢的百年盛衰以及電影進入第二個百年之后的創(chuàng)作流向,除了藝術(shù)層面上的堅守,更多引向關(guān)于科技、媒介、工業(yè)等層面的關(guān)注。”[5]大量新興的視聽媒介與電影融合,催生了《爸爸去哪兒》《極限挑戰(zhàn)》這類“綜藝電影”,《魔獸世界》《怪物獵人》《刺客信條》等“游戲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xiāng)》等短片拼湊的“集錦電影”,《網(wǎng)絡(luò)迷蹤》等全程只展現(xiàn)電腦桌面的“桌面電影”,《真相捕捉》等用監(jiān)控畫面剪輯的“監(jiān)控電影”等新的電影形態(tài)。在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形態(tài)中,“交互電影”“VR電影”憑借資本的加持成為未來電影發(fā)展的新方向。早在2017年,網(wǎng)飛就陸續(xù)推出《穿靴子的貓:魔法書中逃》《黑鏡:潘達(dá)斯奈基》《你的荒野求生》等成功的互動電影;2018年騰訊也推出了互動電影《畫師》,并在2019年7月發(fā)布了互動視頻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觀眾可以在觀影過程中作為故事主角選擇不同的故事情節(jié),以此增強觀影的沉浸感。VR技術(shù)作為近年來最熱門的領(lǐng)域,也早已引起了電影巨頭的關(guān)注,《荒野獵人》《火星救援》等熱門好萊塢電影均推出了VR體驗版,迪士尼、華納兄弟、環(huán)球影業(yè)等影業(yè)巨頭也紛紛成立VR電影開發(fā)部門,從制作熱門電影VR體驗片段、開設(shè)線下體驗門店、開發(fā)VR體驗設(shè)備等多角度布局VR電影產(chǎn)業(yè)。還有一種“章節(jié)電影”不得不提,它同時融合了電影、電視劇與短視頻的特征,將長達(dá)90~120分鐘的電影拆解為一系列7~10分鐘的短片播出,用戶可以在短視頻App Quibi上用豎屏或橫屏畫幅觀看,不同的觀看方式會配以不同的景別。由此可見,科技成為構(gòu)建電影新形態(tài)的主導(dǎo)因素,并影響電影的敘事方法。
二、電影的放映過程——消費形態(tài)的變化
電影的消費形態(tài)本質(zhì)上由存儲形態(tài)決定,從暗箱觀看到膠片存儲、數(shù)字存儲,甚至是5G之后的無線傳輸,電影的消費形態(tài)也隨之發(fā)生改變。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在他的《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寫到:“目前,電影仿佛仍處在手抄本階段……要不了多久,人人都會有一臺小型廉價的8毫米電影機,就像在電視屏幕上看電視一樣看電影。”[6]如今,數(shù)字技術(shù)不僅讓電影便攜,而且改變了電影的整個消費過程。從起初的影院到電視機、錄像帶、個人電腦,再到現(xiàn)在的手機和平板電腦,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徹底打破了電影消費的時空限制,人們可以隨意選擇觀看的時間與地點,媒介融合真正實現(xiàn)了電影放映的移動性和立體性。
總體來說,電影的消費形態(tài)目前處于跨屏觀影與互動消費階段。[7]互聯(lián)網(wǎng)重構(gòu)了消費者與電影產(chǎn)品之間的關(guān)系,電影的消費形態(tài)在時空上發(fā)生了變化,觀眾的觀影自主性與能動性逐漸增強,由此形成一種用戶需求主導(dǎo)的多屏聯(lián)動跨界消費。消費者可以根據(jù)需求選擇在電影院、電視機或任何移動終端上觀影,消費時間更加靈活、消費空間更加私密。當(dāng)技術(shù)的發(fā)展、用戶的需求遇到大量資本,一大批流媒體平臺如雨后春筍般紛紛上線,互聯(lián)網(wǎng)巨頭中亞馬遜推出Amazon Prime Video、蘋果推出Apple TV,阿里巴巴收購優(yōu)酷、騰訊開發(fā)騰訊視頻、百度控股愛奇藝。電影制片廠也不甘落后,從2019年起,好萊塢五大公司就紛紛開始布局流媒體服務(wù),迪士尼推出了Hulu、Disney+、ESPN+矩陣,華納傳媒于2019年7月正式推出自己的流媒體平臺HBO MAX,環(huán)球影業(yè)則宣布開啟流媒體服務(wù)平臺孔雀,當(dāng)然還有勢頭強勁的流媒體霸主奈飛(Netflix),影院和流媒體的“搶人大戰(zhàn)”愈演愈烈。加之突發(fā)的疫情導(dǎo)致院線電影紛紛撤檔,難以回收票房的電影制作方只能通過加速轉(zhuǎn)向流媒體業(yè)務(wù)來尋求生存。《囧媽》在2020年春節(jié)檔直接通過西瓜視頻和抖音免費上線;《肥龍過江》和《大贏家》也選擇在視頻平臺播出;好萊塢環(huán)球影業(yè)率先打破窗口期,在線上線下同步推出《魔發(fā)精靈2》,上映三周即成功收回成本;迪士尼的《花木蘭》和《心靈奇旅》也轉(zhuǎn)為流媒體播放,華納兄弟在旗下的HBO Max直接上線《神奇女俠1984》,并震撼宣布計劃于2021年上映17部新片,包括真人版《貓和老鼠》《哥斯拉大戰(zhàn)金剛》《沙丘》《黑客帝國4》等都將采取線上線下同步投放的模式,縮減甚至取消窗口期成為各大流媒體吸引新用戶的利器,也培養(yǎng)了用戶線上觀影的消費習(xí)慣。自2015年以來,全球電影市場在數(shù)字發(fā)行渠道的增長均高于在院線渠道;2019年,全球電影市場中流媒體數(shù)字發(fā)行市場占比為48%,而院線市場占比為42%;在美國,流媒體數(shù)字發(fā)行市場占比為56%,院線市場占比僅為31%。[8]與此同時,院線也更廣泛地應(yīng)用3D、IMAX、ScreenX、4DX等特種放映設(shè)備以及杜比等高級音效影廳,想方設(shè)法提升觀影的沉浸感來留住觀眾。
媒介融合和移動數(shù)字技術(shù)讓“互動”成為電影消費的關(guān)鍵詞。觀眾在觀影之前可根據(jù)媒介使用偏好查看貓眼、豆瓣、淘票票等APP上的“想看人數(shù)”、觀影評分以及觀影評論,對感興趣的電影直接在同一App上選座購買,完成消費之后即可通過相關(guān)平臺對該電影進行評分與評價,社交網(wǎng)絡(luò)上的口碑與互動成為影響觀影選擇的重要因素。即時傳播技術(shù)促成了即時交流,電影的社交價值從此不僅僅局限于結(jié)伴觀影,而是體現(xiàn)在社交媒體交流中的方方面面。觀眾不僅可以在觀影前后進行互動,甚至在觀影過程中也可以通過彈幕即時對話。奈飛(Netflix)研發(fā)的谷歌瀏覽器插件“奈飛派對”(Netflix Party)可以讓異地的好友同時觀看節(jié)目并在群組中聊天交流,愛奇藝和芒果TV等流媒體也開設(shè)了開房共同觀影等功能,加強線上觀影的社交連接。有很多影院也進行了“彈幕場”的探索,比如北京一家影院在放映《小時代3》時就允許觀眾在大銀幕上發(fā)彈幕,此時互動代替觀影成為觀眾的主要娛樂需求,這對于很多有爭議的電影不失為一種吸引觀眾走進影院的好方法。
三、電影的傳播方式——營銷形態(tài)的變化
在我國電影營收以票房為主導(dǎo)的機制下,實現(xiàn)電影的影院消費是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價值的核心,而營銷則是跨越生產(chǎn)與消費鴻溝的關(guān)鍵,媒介融合在改變信息傳播方式的同時必然影響電影的營銷形態(tài),由傳統(tǒng)的物料投放、首映禮舉辦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在的社交媒體口碑營銷以及短視頻病毒式營銷是必然的趨勢。營銷形態(tài)的改變本質(zhì)上源于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對普通用戶話語權(quán)的放大,改變了電影消費者之間的關(guān)系,讓原本只存在于線下的口碑傳播在線上發(fā)揮作用,從而輻射到更廣泛的目標(biāo)群體,進而影響電影票房。在這樣的媒介環(huán)境中,所有社交媒體用戶都可以參與價值共創(chuàng),而電影營銷則更多地借助用戶創(chuàng)造的口碑價值實現(xiàn)營銷效果的最大化,營銷公司只需要進行議程設(shè)置就可以撬動用戶分享的“杠桿”而不需要花大價錢“賣吆喝”。
網(wǎng)絡(luò)讓原本分散在電影銀幕、電視機、廣播、報紙等不同媒介的內(nèi)容,以數(shù)據(jù)的形式聚攏到互聯(lián)網(wǎng)上。于是,特定的內(nèi)容在內(nèi)部擁有了更強的解構(gòu)——重組性,在外部則具有更好的延展——連接性。電影可以截取成短視頻進行傳播,不同影視、音樂和文字重組之后會形成新的文化內(nèi)容。[9]由此,電影成為用戶參與價值共創(chuàng)的關(guān)鍵素材來源,主要包括觀影體驗的交互傳播和電影次生內(nèi)容的生產(chǎn)創(chuàng)造。一方面,由于社交媒體的普及,電影消費行為和觀影體驗本身成為消費者社交分享的內(nèi)容之一,以往隱性的、小范圍的觀影體驗經(jīng)過微博、微信、豆瓣、貓眼以及抖音、B站的傳播,對后續(xù)觀影行為的發(fā)生以及衍生觀影體驗產(chǎn)生深刻的影響,從而與電影產(chǎn)品的市場價值直接相關(guān);另一方面,消費者可以直接利用電影臺詞、音效、畫面以及情節(jié)等元素演繹故事情節(jié)、挖掘影片意義,甚至直接模仿、拼貼、重組出新的“跨媒介文本”,促成該電影在社交媒體網(wǎng)絡(luò)中的進一步傳播,比如最早由陳凱歌的《無極》衍生出的《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2018年票房黑馬《前任3:再見前任》在抖音中掀起的吃芒果模仿大賽等,因此電影營銷策劃會更加主動地尋求有效調(diào)動用戶參與積極性的方法,比如在線下路演、點映等活動現(xiàn)場設(shè)置亮點環(huán)節(jié)以便進行病毒式傳播,比如邀請KOL參與營銷視頻創(chuàng)作引導(dǎo)用戶參與模仿。這種對用戶參與的引導(dǎo)甚至直接影響到電影創(chuàng)作,編劇更加關(guān)注電影內(nèi)容與觀眾生活日常的相關(guān)度,希望通過引起觀眾的共鳴激發(fā)用戶分享的積極性,大量電影甚至通過旋律優(yōu)美、歌詞感人的配樂來吸引用戶模仿傳播。
四、電影的制作方法——生產(chǎn)形態(tài)的變化
數(shù)字化是媒介融合的技術(shù)底色,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可以直接應(yīng)用于電影生產(chǎn),數(shù)字?jǐn)z影機、非線性編輯軟件、CGI數(shù)字圖像技術(shù)、3D成像技術(shù)以及虛擬現(xiàn)實技術(shù)催生了虛擬與現(xiàn)實相融合的電影內(nèi)容生產(chǎn)方式。巴贊說電影是“外在世界的幻景”,克拉考爾說電影是“物質(zhì)現(xiàn)實的復(fù)原”,但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電影不再僅僅“再現(xiàn)”現(xiàn)實世界,而是把想象中的世界變?yōu)椤艾F(xiàn)實”,電影制作突破對客觀原型的依賴,將“拍攝”與“電腦特效”有機融合,甚至純粹使用數(shù)字建模與電腦合成技術(shù)將導(dǎo)演的想象更加逼真地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李安拍攝的4K、120幀電影《比利·林恩漫長的中場休息》曾被觀眾夸贊打開了視覺的新紀(jì)元,給人一種仿佛身臨其境的真實感;《雙子殺手》甚至直接采用“CG+動態(tài)捕捉技術(shù)”合成了一位更加年輕的威爾·史密斯;詹姆斯·卡梅隆也表示將使用“120幀+裸眼3D+激光全息”等技術(shù)拍攝《阿凡達(dá)2》,如果拍攝成功,該電影也將成為電影史上的里程碑。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還將使電影生產(chǎn)朝著云上多點協(xié)作的方向發(fā)展,奈飛于2018年推出了Prodicle計劃及其首款移動應(yīng)用程序Prodicle Move,可以讓劇組人員更高效地了解拍攝情況與制作進度,從而減輕管理的工作負(fù)擔(dān),甚至可以用大數(shù)據(jù)算法來處理預(yù)算、勘景、置景、日程安排等工作。隨著5G時代的到來,不同劇組云上協(xié)作拍攝也將大大提升電影的拍攝效率。
從電影消費的角度看,數(shù)字媒介生態(tài)影響著電影觀眾的視聽經(jīng)驗和審美體驗,讓用戶形成跨屏消費的習(xí)慣;而從電影營銷傳播的角度看,數(shù)字媒介生態(tài)改變了電影觀眾信息獲取與傳播的手段,擁有了主體性的觀眾開始利用電影元素進行內(nèi)容創(chuàng)造。這所有的轉(zhuǎn)變都反作用于電影創(chuàng)作,一方面體現(xiàn)在“院線電影”與“非院線電影”的分化,另一方面體現(xiàn)在以IP為核心的跨屏敘事。
在電影應(yīng)用新技術(shù)的過程當(dāng)中,實際上加劇了影院觀影與其他方式觀影的區(qū)別,比如在電視出現(xiàn)之后,電影逐漸開始強調(diào)視聽效果,最終促成《復(fù)仇者聯(lián)盟》等重視大場面、快節(jié)奏、粉絲向的“高概念”電影成為票房寵兒,而流媒體興起之后,其非線性傳播邏輯讓那些節(jié)奏緩慢、可以反復(fù)觀看品味的藝術(shù)電影、紀(jì)錄片有了更適合的播放平臺,“院線電影”與“非院線電影”的分化將會更加明顯,電影制片廠和流媒體會生產(chǎn)適合自身特點的類型電影。雖然影院更強調(diào)夸張的感官體驗、流媒體更適合細(xì)膩的情感表達(dá),但不排除影院為了提升營銷傳播效果而制作能夠產(chǎn)生共情、具有社會話題性的“情感炸彈”,而流媒體則會為了吸引眼球制作內(nèi)容低俗或者血腥暴力的影片,甚至迎合用戶縮短影片的時長。
“跨媒體敘事”是基于不同媒體平臺、不同傳播渠道融合而產(chǎn)生的新型敘事模式,它是媒介融合時代電影產(chǎn)業(yè)的重要經(jīng)營策略,也是大型媒體巨頭橫向兼并的用意所在。在該模式下,同一個故事IP可以通過電影、電視劇以及游戲等多種媒介形式進行講述,可能以電影為開端,隨后與小說、漫畫、動畫、廣播劇、電視劇、網(wǎng)絡(luò)劇、游戲甚至短視頻等共同拼湊出一個故事宇宙。比如夢工廠首先推出電影《馴龍高手》,在獲得觀眾認(rèn)可之后為保持電影熱度相繼開發(fā)了短片、游戲和動畫劇集《馴龍記》,在動畫即將結(jié)束時上映《馴龍高手II》,從而獲得了不錯的票房;再比如玩轉(zhuǎn)跨媒體敘事的漫威,用一部電影開啟一個角色,用電視劇演繹角色生平,最后用英雄集結(jié)引爆粉絲熱情,漫威宇宙第一階段的終章《復(fù)仇者聯(lián)盟4:終局之戰(zhàn)》甚至一舉超過《阿凡達(dá)》成為全球票房冠軍,可見跨媒體敘事給觀眾帶來的沉浸感之強。
結(jié)語
在當(dāng)今的數(shù)字時代,電影作為一種傳統(tǒng)的、積累了大量優(yōu)勢資源的內(nèi)容媒介,面對新興媒介的圍剿與滲透,不可能依舊維持高冷的姿態(tài),它必須選擇與電視、互聯(lián)網(wǎng)、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甚至通信產(chǎn)業(yè)融合,發(fā)揮自己的內(nèi)容優(yōu)勢與時代發(fā)展共鳴。不管是電影、電視劇、網(wǎng)絡(luò)劇還是網(wǎng)絡(luò)電影,它們都是虛構(gòu)敘事內(nèi)容在不同媒介上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當(dāng)觀眾感慨于“這電視劇拍得像電影一樣”時,也從側(cè)面體現(xiàn)出電影的本體論困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從內(nèi)容維度來定義“電影”是不可行的。那么,用影院放映來定義電影就是可行的嗎?答案可能依舊是否定的。觀眾在影院環(huán)境中的“體驗”與觀眾對電影內(nèi)容的“體驗”也是全然不同的概念,如巴贊所述,觀眾心理是否認(rèn)知為自己在觀看“電影”是判斷的關(guān)鍵。
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來勢洶洶,媒介融合在為電影帶來新發(fā)展與新成就的同時也為其帶來了不小的沖擊,新時代電影形態(tài)如何變化、電影產(chǎn)業(yè)發(fā)展何去何從,恐怕我們現(xiàn)階段尚且不能回答,可能正如巴贊所說“電影還沒被發(fā)明出來呢”!
參考文獻:
[1][5]陳曉云.電影研究:重建、延續(xù)與轉(zhuǎn)向[ J ].電影藝術(shù),2020(1):14-20.
[2][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體和舊媒體的沖突地帶[M].杜永明,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2:409.
[3]孟建,趙元珂.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 J ].國際新聞界,2006(7):24-27,54.
[4]張超,吳曼芳.重塑再造:智媒時代電影生產(chǎn)的再媒介化[ J ].電影文學(xué),2020(22):3-6.
[6][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論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1:359.
[7]楊越明,李莉.“互聯(lián)網(wǎng)+”背景下大眾電影消費新生態(tài)研究[ J ].當(dāng)代電影,2017(11):90-94.
[8]馬瑞青.美國流媒體平臺與非院線電影的興起和沖擊[ J ].電影藝術(shù),2020(04):14-21.
[9]司若,黃鶯.中國網(wǎng)絡(luò)電影發(fā)展脈絡(luò)與未來趨勢研究[ J ].電影藝術(shù),2020(04):22-30.
【作者簡介】 李大偉,女,山東青島人,山東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講師,博士;
王歡歡,女,山東威海人,中共成都市委黨校講師。
【基金項目】 ?本文系山東省(軟科學(xué))重點研發(fā)計劃“山東省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政策研究”(項目號:2019RZB43001)、山東省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項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項目號:17CZWJ0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