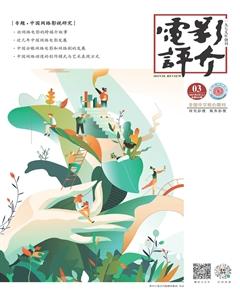“名聲的管理”:美國干預戰爭電影輿論操縱術
冷戰結束后,美國在海外的干預演變為所謂低烈度戰爭,和世界大戰事關國家主權或國家威脅不同,海外干預戰爭的正義性何在?這成為美國對內對外都必須解釋的一個問題。于是,美國干預戰爭電影作為傳播方式之一走上前臺,在商業電影的娛樂外衣下巧妙地承擔起意識形態責任。饒有意味的是,電影作為非暴力傳播形式,在傳播美國干預戰爭題材時不動聲色地打響了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輿論戰。
毋庸置疑,美國干預戰爭電影的解釋目的就是一個——戰爭有理/美國有理,從而在名義上維護國家道義形象以實現“名聲的管理”。但是,這些電影使用了什么樣的敘事策略和具體包裝手法,以及傳播的效用如何,都值得深入探究。
一、作為意識形態的戰爭電影
電影特別是商業電影,究竟有沒有意識形態在內,在不同群體中存在巨大的分歧。然而,受眾群體在認識上的分歧并不代表事實不存在,制片方的口頭否認并不代表作品本身內涵。“一切電影皆是意識形態的載體。”電影研究者雷吉斯·迪布瓦斷言,“無論是隱含其中,還是鮮明彰顯;無論是在不經意問,還是經過深思熟慮,每一部電影都歸結于一種主觀的、獨特的世界觀,因此它在任何情況下都承載著一種意識形態的信息:按照克里斯蒂安·麥茨(Christian Metz)的觀點,‘由于電影始終要選擇呈現和不呈現的東西,世界被其改造成一些論說,或者依照米歇爾·馬多爾(Michel Mardore)的獨到見解:‘本質上,電影圖像作為生活的再現,與生活本身一樣具有相等的介入性,也就是說完完全全的介入。”[1]
戰爭是國家對立的極端形式,當然也是意識形態對立的極端表現。因此,美國戰爭電影從最初就天然打上了極端意識形態的標簽。
一戰之前,美國奉行開國元勛確立的孤立主義,對世界大戰隔岸觀火。然而,威爾遜在1916年贏得總統連任后開始謀劃對德宣戰并成立公共信息委員會(或譯“公眾情報委員會”),向公眾灌輸思想稱,美國不僅是自由燈塔和共和典范,還要在全球范圍內擔當自由的“捍衛者”。至此,美國電影迎來稱霸全球的轉折點。“其中又尤以政治力量對電影業發展戰略的干預最為重要。這種干預并不僅僅基于電影能夠帶來的巨大經濟收益,更與電影自身的意識形態屬性密切相關。威爾遜總統就曾公開表明:‘(電影)如今已是全世界最高級的媒介,它不但能夠在最大范圍內傳播公共智慧,更可憑借全球通行的視覺語言將美國的計劃與目標呈現在世人面前。”[2]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發生后,美國政府“首次嘗試開展一個持續的項目,利用電影進行宣傳,通過好萊塢電影制片人來宣傳它的目標,強調它的成就,將戰爭說成是由群眾和士兵構成的一次不可忽視的,甚至是激進的試驗”。[3]到1943年末,好萊塢導演僅用兩年時間,“已經在超過300部電影中灌輸了有利于精神建設的信息,這些信息大多是他們從政府給出的建議中親手選出并且與劇本銜接的。”[4]
對那些否認電影尤其是商業電影隱藏意識形態的人來說,事實也許會令他們十分尷尬,因為美國官員和導演直白承認這一做法的例子并不鮮見。著名導演卡普拉就是典型例子,他明確說:“有些陳腐可笑的人會說你是在參加‘好萊塢的戰爭,不要和他們爭吵。這是一場大戰,需要用到可以想到的任何武器。你們的武器是電影!你們的炸彈是想法!好萊塢是一間戰爭工廠!”[5]
的確,美國深諳娛樂與宣傳相結合之道。學者杰拉爾德·瑟斯曼則將美國命名為“宣傳型政體”。他援引美國戰爭新聞辦公室主任埃爾默·戴維斯的話說:“把宣傳的思想灌輸給大多數人的最簡便途徑是讓它通過一個娛樂節目作為媒介進入。”[6]即使是非戰爭電影,好萊塢導演也會自覺地植入意識形態在內,“驚醒于珍珠港受襲事件,好萊塢中很多人開始相信即使是喜劇,幻想片和愛情片都或多或少可以貢獻一些關于民主、自由、集體犧牲或者‘美國式生活的言論和意見。”[7]
將干預戰爭電影作為一個類型來分析研究,目前還極為少見。聶欣如在《干涉戰爭電影及其意識形態》中提出,在冷戰結束之后,干涉往往是指大國對于小國國內所發生的種族滅絕或者恐怖主義事件的武裝干預,“出于人道和反恐的目的、合法(聯合國授權)或不合法地對他國進行武裝干預被稱為干涉戰爭。”但事實上,“在我們看來,人道主義干涉或反恐這樣的說法盡管在表述上有一定的新意,但并不能掩蓋大國自身的利益往往是干涉的實際出發點這一事實,只不過將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抗衡改換成了人道主義這樣的在表面上更具普世意味的西方文化價值觀罷了。”[8]
無論電影類型的集合關系如何變化,也無論電影類型隨歷史事件在時間上的線性關系如何變化,從電影到戰爭電影再到干預戰爭電影意識形態色彩如影隨形的性質是不會變的,變的只是敘事策略和話語方式而已。在變與不變中,有變動不居的時代色彩與名聲管理方式在內,也有沿襲既往敘事框架與深層次意識形態底色的穩定表現,體現出一種復雜的糾葛關系。
二、干預戰爭電影的“名聲管理”策略
干預戰爭和戰爭的不同在于:戰爭是交戰國雙方之間外交沖突的延伸,而干預戰爭是大國主動介入干預小國內部政治。如果按照二戰以后建立在主權國家基礎之上的國際秩序,干預戰爭顯然是不合法甚至等同于侵略行為,這就對大國提出為自己行為提供合法性解釋的挑戰。有趣的是,最早高度重視電影宣傳功能的美國總統威爾遜,也最早最成功地塑造了美國百年戰爭電影的敘事框架,在此我們可以借助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立新關于威爾遜在建構國家身份的修辭戰略研究來加以說明。“在威爾遜的公共話語中,世界被劃分為善惡兩大對立陣營:一方是美國代表和領導的、由民主國家組成的陣營,是‘善的和正義的力量;另一方是由專制與獨裁國家組成的陣營,是‘邪惡的力量。前者接受上帝的指引,而后者則受魔鬼的驅使。國際關系就是兩大陣營的斗爭,即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是善惡大決戰。學者菲利普·萬德稱這種修辭戰略為‘預言式的善惡二元論。”這樣,美國充當“自由衛士”的角色也就獲得了正當性。二戰后幾乎每位總統都采用這種修辭戰略來論證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世界各地“捍衛”自由的必要性。[9]
好萊塢導演弗蘭克·卡普拉為美軍拍攝一系列《我們為何而戰》的宣傳片。劇本創作團隊中的一個作家說:“所以我們需要扮演邪惡的化身了?”卡普拉回答道:“正是如此”。卡普拉對劇本的要求是,故事清楚明白,即使是兒童也可以理解。他期望這些電影展現的觀點非常簡單:美國人正在為一個自由世界而戰,裕仁(昭和天皇)和希特勤正在為一個奴隸世界而戰。他認為,對那些年輕的美國大兵來說,一段非黑即白的歷史“是你目前唯一可以傳遞給那些孩子的東西。你給他們太多‘另一方面呢的觀點,會讓他們覺得困惑”。[10]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威爾遜的修辭戰略中,他強調的是將美國美化為善的、正義的、民主的一方,這是一種說的策略;而卡普拉的“非黑即白”的表達方式和前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區別在于,他是從受眾角度來思考問題,也就是一種看的策略。卡普拉的這種受眾心理策略,顯然和《烏合之眾》等社會心理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即灌輸簡單結論最有效。的確,當今世界對美國反恐戰爭中的“邪惡國家”定義權并不陌生,但這種做法不是新鮮的發明,而是延續已久的美國傳統。
筆者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從威爾遜主義發展到今天的干涉主義有其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同時美國戰爭電影發展到今天的干預戰爭電影在敘事框架上也有其一致性。區別在于戰爭電影的善惡二元論是絕對宣傳策略,而干預戰爭電影的善惡二元論則已進化為國家“名聲管理”策略。正如國家品牌的專家沃利·奧林斯(Wally Olins)所說:“品牌是宣傳……歸根結底它就是操縱和誘惑。”沃利表示“品牌,這個詞煽起了大量的爭論”,他傾向于用“名聲管理”這個詞,似乎這樣可以少一些爭端。[11]
相應地,這種善惡殊死斗爭的立場宣傳轉變為國家價值觀輸出策略。從正面,以“人道主義/人道主義危機”“為價值觀而戰”“反恐怖主義”的名義來宣揚“美國精神”;從反面,則通過惡魔崇拜等傳統敘事手法來貶損被干預國家或相關群體的聲譽。電影憑借上述正反手法的運用,幫助美國政府悄悄地實現國家的“名聲管理”。
美國政府對好萊塢干預戰爭電影的政治指導是顯而易見的。據媒體公開報道,2001年11月11日,好萊塢電影界精英聚集在洛杉磯比佛利山莊開會,布什總統的資深顧問羅福以及白宮媒體關系聯絡人等也都專程趕來與會。美國電影協會主席麥克瓦倫迪在致詞中表示,好萊塢電影工業希望能以實際行動為打擊恐怖主義貢獻一份力量。與會者稱,好萊塢演藝圈有責任向國際展示美國是一個熱愛自由、民主、反對恐怖主義的偉大國家,建議制作增進海外認識美國立國精神等方面的宣導短片。重要的是,布什顧問不僅僅是與會,而是直接發表意見,他在記者招待會上透露會議涉及好萊塢應該考慮針對恐怖主義、美國的軍事行動是“對邪惡的戰爭”、如何避免流于宣傳等七大主題。
史宗歷認為,冷戰結束后,以反思為主的反戰電影幾乎被標榜美國政府和極力美化美國大兵的歌頌戰爭影片所取代。單邊主義徹底摧毀了美國戰爭片所應具有的現實意義。[12]
二戰后美國發動的歷次對外戰爭大多缺乏合法合理的道德基礎,及至2011年的利比亞戰亂更是讓全世界人民看清楚這點。“但在二戰后涉及戰爭題材的美國電影卻表現出另一番格局。一方面在銀幕戰爭英雄的塑造中有效地植入西方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在反省戰爭的影片中塑造著民主、自由、具有高度反思精神的美國……蘭博出動的地區均是美國試圖占領或者控制的地緣政治戰略要地。在那些地區,美國往往以金援和軍援相結合的手段扶植當地的親美政權,美其名曰支持當地的民主自由建設、要將當地的人民從邪惡的原教旨主義或者軍人專制下解救出來。”[13]
三、“名聲管理”的外在包裝手法
美國是如何在干預戰爭電影中包裝敵我形象從而實現國家“名聲管理”策略的呢?種族主義優越感是基礎,伴隨這種優越感的同時對對方采用了惡魔崇拜的包裝方式;但是,當優越感在全球觀眾中遭遇挫折后,美國又在這一基礎上進化出新的包裝手法,即美軍戰士折射出的人性光輝,并且再次強化民主自由價值觀的敘事方式。聶欣如指出,“今天的戰爭并非不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征,而只是將過去的主義意識改換成了今天的種族或文化意識。這樣一種具有文化特征的意識形態勢必反映到電影之中。”比如,在2002年影片《黑鷹墜落》中,一位中士小隊長在談到黑人的時候說:“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我尊敬他們……這些人沒有工作,沒有食物、教育和未來。我只是覺得我們有兩個選擇:幫助他們,或是眼睜睜看著他們自相殘殺……我是來改善世界的。”再比如,在2000年另一部電影《烈血的規條》中,一名美軍上校在也門美國大使館執行任務時,因3名美軍傷亡,即下令開槍打死83人打傷100多人。在美國人看來,只要美國人受到傷害,不論加之于對方的傷害有多大都是合理的。[14]
對美國而言,惡魔崇拜這種宣傳手段早在一戰期間就已經再熟稔不過了,拉斯韋爾在《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中對此做過總結。他說,當公眾相信,是敵人發動的戰爭并且阻礙了神圣的和平時,宣傳家就已經實現了他的目的;通過心理反應的迂回,有罪的人就是邪惡的,邪惡的人就是有罪的。[15]拉斯韋爾進一步指出這種大眾心理效應的后果,“惡魔崇拜引發了仇恨并延續了仇恨。上帝說,我要復仇,上帝與我們一道努力鏟除魔鬼。”而為了達到鏟除“魔鬼”的目的,任何不擇手段的努力都應該被贊美。[16]這就達到了歐洲政治學者所指出的“顛倒受害人”的目的,而為了鏟除“惡魔”,不擇手段不但不可恥反而應該贊美,這種邏輯令人不寒而栗。
《黑鷹墜落》影片伊始就預設了美軍行為的合法性,美軍乘直升機護衛救濟糧的發放,而索馬里武裝分子殘暴而囂張地開槍驅散領糧平民,先入為主地賦予美軍人道主義形象。該片特別注重通過視覺處理來達到敘事目的,一方面,交戰雙方膚色黑白對立,很明顯成為黑白兩個世界的較量,“一切溢美之詞都賦予了白人,一切蓄意貶低都送給了黑人。白人是強大的正義的,黑人是弱小的邪惡的。”另一方面,影片普遍運用了透視法則,它通過確定視點來奪取視覺權力。觀眾總是與銀幕中的美軍處于同樣的觀看位置,“換言之,我們與美軍就好像站在了同一‘立場上一樣。這樣做還有個好處,美軍的形象是近距離的、高大的,索方的形象則是遠距離的、矮小的。”[17]
惡魔崇拜的手法激起有色種族的憤怒,美國干預戰爭敘事手法趨向于突出人性光輝,2010年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拆彈部隊》就是典型例子。一方面,惡魔崇拜在《拆彈部隊》中依舊陰魂不散,銀幕中的伊拉克人無一不充滿敵意,表情冷漠,語言無法理解,舉動不可捉摸,似乎隨時都會引發一次襲擊和爆炸。影片最煽情的一幕是伊拉克小男孩貝克漢姆的死亡,這個男孩只因和拆彈專家詹姆斯產生友誼便被無情殺害而且制成人體炸彈。當詹姆斯從小貝克漢姆血淋淋的肚皮拿出炸彈時,幾乎讓所有觀眾都對恐怖分子的殘忍感到憤慨不已。另一方面,美軍充滿人性的形象則得到完美反襯。《拆彈部隊》里詹姆斯和小男孩貝克漢姆頗有交情,買足球一起踢,充滿歡聲笑語,這種充滿人性的生活化場景不會讓觀眾產生懷疑。后來,詹姆斯在取一名被殺兒童身體里的炸彈時一度不能自已,近乎瘋狂地追查真相反而被平民打得頭破血流,他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來。
鮑駿認為,《拆彈部隊》恰到好處地規避了戰爭發生的政治原因,成功實現了宣傳目的,人性的面孔只是美國自我辯護的一種魔術。“如果說邁入新世紀以來,美軍在海外作戰是事實性的軍事行動,那么,與此同步的好萊塢大片在全球每一個國家、每一個角落的擴張滲透,則是美軍乃至美國政府有計劃發動的一場文化戰、宣傳戰。在表現現實戰爭的好萊塢影片中,美軍士兵總是以正面形象出現,不僅作戰英勇而且十分注重保護平民,最重要的是,‘美軍永遠站在保衛世界的最前線。”[18]
頗為諷刺的是,當美國電影再三突出美軍英勇形象并渲染傷亡的時候,對手的傷亡是不會被展示的,戰爭的傷痛只屬于美軍而不屬于敵人。“在美國拍攝的伊拉克戰爭電影中,伊拉克人是沒有話語權的……影片中出現的反美分子都是如幽靈鬼魅般,陰魂不散地跟著美軍,巧妙地隱藏在人群中,讓美軍防不勝防。不知什么時候就會有蒙著臉的恐怖分子冒出來向美軍射擊,觀眾會不由自主地對美軍產生同情。”[19]對這種手法,我們再次從拉斯韋爾那敏銳而無情的洞察力得到證實。他說,“如果將戰爭中的可怕方面從公眾的注意中抹去,對戰爭合理性的論證就可以更順利地進行。”[20]
當代著名哲學家巴迪歐在點評《錯誤的證人》時尖銳地指出,“我們在電影中卻沒遇到一個黎巴嫩人。沒有任何一個人被關注到,只有好戰的傀儡們在荒謬地夸夸其談,或發表著極端的言論,或者只是進入攝影機畫框內被屠殺掉的不具有實體性的幾個人。沒有人來闡釋情境的基本事實,這使得整件事情過于簡單地歸因于普遍性的荒謬和歷史的夢魘,因為從一開始,導演就拒絕提供任何解釋。”[21]可見,美國干預戰爭電影對敵我生命的不對等處理,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或無心之失,而是有意為之。不讓對同樣鮮活的生命出現在鏡頭,或者鏡框里出現的只是“不具有實體性的幾個人”,是導演有意“拒絕提供任何解釋”的通行做法。
在人性話語的包裝手法中,美國導演除了突出塑造美軍戰士光輝形象之外,還對美軍的錯誤如殺人等反人性罪行進行辯護。
“影片中表現美軍犯錯誤都是有原因的,這是戰爭的錯誤,任何人處于那種狀態都有可能犯錯。”影片《節選修訂》通過表現美軍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做繁瑣枯燥的工作以及平時生活的無聊為后來他們心理扭曲犯下罪行做鋪墊。《綠區》則為美國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鋪墊,讓觀眾覺得這是戰爭將他們逼瘋了。[22]
四、名聲的幻境:扭曲的拉康鏡像
毫無疑問,根據現有傳播研究來說,美國干預戰爭電影的“名聲管理”策略應該會對部分觀眾產生一定的影響。麥克盧漢將電影稱為“拷貝盤上的世界”,他認為,“作家和制片人的職責,就是將讀者或觀眾從他自己的世界遷移到另一個世界——印刷和膠片造成的世界中去。這一遷移極為明顯,極為圓滿,所以身歷其境的人下意識地、毫無批判知覺地接受了這種遷移。”[23]當然,如今人們不再無條件贊成僵硬的“刺激-反應”模式或魔彈論。美國這種“名聲的管理”策略究竟在形塑受眾觀念中發揮多大作用,需要在調查數據基礎上作定量分析。在沒有相關數據可供參考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從多個維度來做一個初步的評估,看看美國干預戰爭電影“名聲的管理”效果如何。
(一)來自“他者”的反應
眾多研究者已指出,美國一而再再而三從外界尋找“敵人”,并且在全球傳播格局中掌握著絕對話語權,但被美國鎖定的“邪惡”的弱者依然會發表抗議聲音。
事實上,《黑鷹墜落》上映之后,軍方被批評為只顧自我感覺良好,卻嚴重傷害穆斯林世界的感情。美國明尼蘇達州“索馬里維持和平中心”曾表達強烈抗議,該中心主席奧瑪·加瑪爾說:“在這部影片中索馬里人變成了兇殘的野人,甚至根本不是人類。”他強調說:“索馬里人在這次戰役中,有將近千人陣亡,但片中完全沒提到這回事!我不知道美國人看完影片后,會怎樣看待索馬里人。”[24]
(二)來自“受眾”的反應
包括電影在內,美國歷次戰爭和對外干預戰爭的輿論動員機制表明,美國對內部受眾的控制是有效的。盡管美國國內有反戰聲音,但總體來說比例上不成氣候,美國主流社會真正反對的是嚴重傷害自身利益的失敗戰爭。
美國要實現國家“名聲的管理”,真正著力點在國外尤其是被干預國家之外數量龐大的第三方國家。“對于美國國內的觀眾而言,這種解釋是借以建構民族性與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徑;對于其他國家的觀眾而言,好萊塢的歷史片則更多地包孕著某種關于世界秩序的暗示或隱喻。”[25]
不過,對受眾的接受度或認同度也很難完全樂觀。一方面,20世紀前半葉被稱為“第一藝術”的電影如今已風光不再;另一方面,20世紀前半葉電影觀眾主要是容易被影響的底層大眾,現在的觀眾則觀點多元。
(三)來自“旁觀者”的反應
有一類觀眾是比較特別的,他們從來不是簡單的接受,而是包括研究者在內具備強大反思能力的精英群體,他們對美國干預戰爭電影保持著獨立清醒的評判。比如,法國是全世界公認反對文化殖民立場最堅定的國家。就中國而言,被動追隨美國話語的現象固然存在,但對美國兜售干預主義美化自身的動機洞若觀火的大有人在。《野戰排》被認為有一定的反戰色彩,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這場侵略戰爭的合理性,而只是將這場戰爭中敗露出來的邪惡呈現出來。易言之,影片對戰爭邪惡的表現,自覺不自覺地掩飾了對戰爭罪惡的揭示……《野戰排》即便是一部表現戰爭痛苦的電影,它所表現的痛苦,是美國人的痛苦,它所反省的創痛,也是對于美國人的創痛。”[26]
總之,盡管美國自認為找到了一種揚我抑他的“名聲管理”策略,也不過淪為自欺欺人的游戲而已。除了傳播評估的維度之外,我們還可以訴諸于拉康鏡像理論做一個簡單評估。選擇拉康鏡像理論作為參照物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該理論堪稱自我形象建構的奠基理論,這和美國借助“他者”建構帝國身份的干涉主義有很大的內在契合性;另一方面,該理論又促進了意識形態理論實現新突破,有助于加深我們理解美國干預戰爭電影背后的意識形態。
阿爾都塞是將拉康鏡像理論和意識形態結合起來的關鍵人物。在其1970年發表的著名文章《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阿爾都塞提出,一個國家的正常運行離不開兩種國家機器,即強制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那么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或者說某主體與這一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他的答案如下:‘通過意識形態機構把個體詢喚為主體。社會制度是先于個體而存在的,個體必須按照事先存在的位置進入社會制度中去。在社會機構中為主體設置的位置是維護這一社會秩序利益的。”[27]
因此,美國執著于借助電影等文化體系輸出價值觀念,目的就是“通過意識形態機構把個體詢喚為主體”把美國民眾乃至海外受眾納入自己設計的秩序利益之中。問題在于,美國陷入了一種想象的秩序難以自拔。“在拉康看來,一切確定的身份都是虛假的鏡像,主體一開始就已經踏上了一條充滿悖謬的‘不歸路。我們揭示了悖謬,卻無法解決悖謬。”[28]“在其他國家看來,所謂‘自由衛士和‘世界領袖的自畫像多半是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的招牌,其背后是對自私國家利益的追求和對其他國家內政的粗暴干涉。美國需要承認自己是一個與其他國家沒有什么兩樣的國家,美國的實力或許強大,但它既不是上帝選定的‘自由衛士,也不具有超凡脫俗的美德,更沒有與生俱來的領袖稟賦。與其他國家一樣,它既追求自私的國家利益,也渴望權力和榮耀,因此并不像威爾遜所說的那樣偉大,而至多是一個好壞兼具的榜樣。承認這一點對美國人來說可能會很痛苦,但卻非常必要。它可以使美國少一點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而多一些對其他國家聲音的傾聽和命運的同情。”[29]
所以,在美國通過干預戰爭電影實現“名聲的管理”中,與其說受眾是“夢幻人”,更不如說名聲是幻境。當美國滿世界尋找敵人的時候,卻不知道自己已成為他者眼中的敵人。
結語
必須指出的是,“干預戰爭”作為一個類型概念,本身很有可能就已經掉入美國意識形態話語陷阱。本文不得不借用這一概念作為相關電影研究對象,這不等于默認包括干涉主義等美國概念的合法性,也不排除未來人們在新語境下重新修正相關概念的可能性。
縱觀好萊塢各時期的表現,總體來說國家主義的立場是非常堅定而明確的,對干預戰爭電影的價值包裝也非常突出。
總的來說,美國干預戰爭電影“名聲的管理”策略效果是有限的。即使是美國政治學者也認識到,所謂人道主義干預本身就是反人道主義的。回顧半個世紀以前,我們不能不服膺于馬丁·S·德沃金那預言式的洞察力,“銀幕上反映出來的只是夢想。影院之外,還有很多實際的東西,要我們去反對或爭取。如果不能這樣做,那所有想象的東西,連同本民族自我崇拜的偶像,現在有意義的和有危險的,哪怕它們對人們精神所起的作用維持不久,都會徹底地垮臺。”[30]
參考文獻:
[1][11][法]雷吉斯·迪布瓦.好萊塢電影與意識形態[M].李丹丹,李昕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8,34.
[2][25]常江.帝國的想象與建構:美國早期電影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02,75.
[3][4][5][7][10][美]馬克·哈里斯.五個人的戰爭——好萊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M].黎綺妮,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12,13,210,132,170.
[6][美]杰拉爾德·瑟斯曼.西方如何“營銷”民主[M].忠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7.
[8][14]聶欣如.干涉戰爭電影及其意識形態[ J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
[9][29]王立新.我們是誰?威爾遜、一戰與美國國家身份的重塑[ J ].歷史研究,2009(6).
[12]史宗歷.單邊主義催生的好萊塢戰爭電影[ J ].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4(5).
[13]陳波.從利比亞戰爭反思美國戰爭題材電影[ J ].電影文學,2011(16).
[15][16][20][美]哈羅德·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M].張潔,田青,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73,87,88.
[17]陳書毅.虛擬世界中的現實建構——評電影《黑鷹墜落》[ J ].電影評介,2008(6).
[18]鮑駿.誰動了美軍的戰車——新世紀以來美軍與好萊塢電影合作軌跡初探[ J ].語文教學通訊(學術刊),2011(9).
[19][22]于林杰.美國伊拉克戰爭電影中的意識形態[ J ].軍營文化天地,2013(6).
[21][法]阿蘭·巴迪歐.論電影[M].李洋,許珍,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78.
[23][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南京: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譯林出版社,2011:325.
[24]史宗歷.單邊主義催生的好萊塢戰爭電影[ J ].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4(5).
[26]賈磊磊.被邪惡遮蔽的歷史罪惡——野戰排美式傷痕電影的文化視域[ J ].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3(3).
[27][美]尼·布朗.電影:意識形態的觀點[ J ].陳梅,譯.電影藝術,1988(3).
[28]王韻秋.中心錯覺與荒野錯位——盎格魯-加拿大民族身份建構的內在悖謬溯源[ J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
[30][美]劉易斯·雅各布斯.美國電影的興起[M].劉宗錕,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16.
【作者簡介】 ?肖郎平,男,江西人,貴州日報報刊社主任記者,主要從事區域經濟、輿論政治和媒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