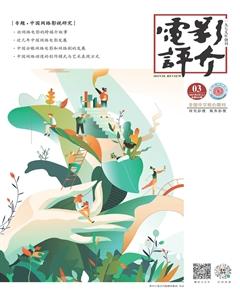數碼科技與社交網絡普及現實語境下的擴張型現實電影
陳雷
在“視覺爆炸”的當代社會,以視聽語言特性取勝的商業電影正在成為一種通行的大眾媒介和商品,不斷通過層出不迭的視聽奇觀影像制造“媒介事件”。尤其是日漸更新的數碼科技與社交網絡在通過各種超級英雄題材、科幻題材,以及媒介層面上的VR、AR、可交互形式混淆了“現實”與“虛構”的絕對界限之后,電影的精神內涵與附帶的感情必然會遭受一定程度的更改,傳統世界觀中展開的故事也正隨著故事想象力的變遷發生轉移與更新。在這一過程中,新的擴張型現實電影已然對人文學方法論本身同時構成了挑戰。
一、現實生活的虛擬故事敘境
無論是從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或是現實生活的經驗上看,作為客觀實在的“現實”世界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物自體”[1]。現實世界作為先驗的“自在之物”作用人的感官,是人的感覺的來源;但技術的進步與網絡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現代人對時空形式的感知方式和認識結論,從而人為地改變了對普遍性的“現實”和“真實”的理解,其結果在作為凝結人類想象力與美好愿望的電影中獲得了相當直觀和多樣的體現;與此同時,講述夢、回憶、幻想、虛擬體驗、電子游戲等媒介自反性主題的故事也同樣成為電影本身的比喻與最常講述的主題之一。在好萊塢電影的“夢工廠”,“吸引力電影”的制作者為了“哄騙”觀眾進入“美夢”進行了長達百年的探究,在對現實保持高度緊張關切的同時,對電影本身敘事功能進行著最大限度的開掘。在以創造奇觀化的夢幻世界聞名的好萊塢,不論是喬治·盧卡斯電腦特效下的《星球大戰》系列,還是斯皮爾伯格電影中的數字恐龍,抑或是詹姆斯·卡梅隆3D技術生產下的異色星球,都嘗試通過視覺奇觀的堆砌開發出新的文化樣式,引領大眾文化潮流。百年來的電影觀眾如癡如醉地沉醉于銀幕上展現出來的夢幻情形時,好萊塢這臺造夢機器也受到了電影批評家“庸俗媚俗”“麻痹觀眾”“娛樂至死”的批評。在開始厭倦童話般美好而不真實的“真實生活”后,電影觀眾開始熱衷于在明確虛擬的故事敘境中尋找真實感,而電影導演和編劇也發現了將好萊塢的撫慰效果與美國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隱藏在影像作品中的全新方式。20世紀80年代,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逐步從軍用領域向商用領域和家用領域滲透,多年以來主導經典好萊塢電影的單一的敘事模式首次從夢幻般的“虛擬現實”朝“現實虛擬”的方向延伸。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好萊塢,具有獨特虛構世界觀和超級英雄主人公的商業片是吸引美國和全球大眾消費的主力,全美及世界票房排名的前幾位包括派系龐雜的超級英雄電影,如《星球大戰》《異形》《奪寶奇兵》《哈利波特》及占領兒童市場的動畫電影《怪物史瑞克》《玩具總動員》等,這些電影呈現的景觀大都具有科幻或奇幻色彩,是明確疏遠或遠離現實中的都市生活;即使是發生在觀眾生活中的故事,也都做了陌生化處理。例如在成人與兒童市場都大受歡迎的《玩具總動員》系列影片,別出心裁地將玩偶動畫與真人出演結合在一起,以形象鮮明、性格各異的幾個兒童玩具為主角,在“現實”的場景中虛構出在小主人睡覺或外出時,家中的玩具具有各自的意識與活動能力,像真人一樣具有各種情感與行為動機的“虛擬”設定。為此,影片放大了兒童房間角落作為故事發生的主要背景,用大光圈小景深淺焦距的方式在美國觀眾熟悉的兒童房中劃分出一塊與眾不同的非現實角落。包括《玩具總動員》在內,這些故事的最后大多仍然是經典好萊塢影片中主人公在朋友的幫助下打敗敵人、名利雙收、外加抱得美人歸的標準大團圓結局,現實與非現實題材作品在感覺材料上雖然稍有變動,但虛擬故事敘境與敘境中的現實世界暫時沒有拉開差距。漫威公司的超級英雄系列電影《復仇者聯盟》(根據斯坦·李領銜創作的系列同名漫畫改編)及相關的單人超級英雄電影作為21世紀影壇備受矚目的現象級作品,也延續了將幻想“嫁接”在日常生活延長線上的做法,將這批誕生于20世紀不同階段、大多帶有冷戰世界邏輯的美國漫畫“翻新”成為發生于21世紀的全新故事。在這個系列中,商業巨子鋼鐵俠承載了資本主義的美國神話、科學家綠巨人和蟻人代表了驅動經濟發展的科技動力神話,就連剛與索尼達成商業協作、順利回歸漫威宇宙的高中生蜘蛛俠也攜帶著理想化觀念,其價值核心對應的仍然是現實中的“美國夢”“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道義意識與個人主義情懷。漫威宇宙系列電影的備受歡迎,意味著在現實生活中建立虛擬故事敘述路徑的做法已經有能力產出具有相當說服力、制作精良、水準出眾的高質量電影工業產品;DC公司近年制作的《超人》《蝙蝠俠》《神奇女俠》《海王》也證明了這點。如今,超級英雄電影以其特有的吸睛魅力,不斷影響越來越多觀眾的審美偏向,并且以純熟的敘事技巧和美國電影工業基礎的形式,在暗中取代了潛在的、可能的現實意義與批判空間。這批超級英雄電影的風潮與數碼科技的擴張密不可分,從“玩具擬人”到“你的好鄰居蜘蛛俠”,都以其巨量的色彩堆砌,摧毀了藝術創作形式的現實主義傳統,抹除了現實和幻想的邊界,使審美文化走向虛擬化和理想化。這些故事與20世紀80年代前好萊塢描繪的全然夢幻化的現實生活不同,同時也不意味著完全由假想中的世界取代現實世界,而是通過各種“現實虛擬化”的異質因素描繪出一個帶有現實因素的幻想故事,為現實世界虛擬化敘述的成長提供了某種可能。
二、數碼科技的現實擴張性
現代的數碼科技可以說是現實擴張性。這里所說的現實擴張性的東西就是現實和虛構的混在,“通過對現實的一部分虛構化而實現對于現實的擴張,并非在現實中做夢,夢與幻想溢出影響現實世界;而是現實通過‘非現實的轉化,向幻想與敘事的領域延伸。”[2]故事性想象力的潮流,隨著數碼化的風潮席卷全球發生了推移,這種變化也對應著“從假想現實到擴張現實”的變化。全球觀眾對于20世紀80年代以假想的機器人、外星生物或宇宙人類電影熱潮或超能力熱潮等形式成為主流的怪異現象、架空歷史以及最終戰爭的支持都相對地降低了很多。代替它們而受到支持的是一種充滿幻想的浪漫故事,有時候則會有廣義的幻想要素介入其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超級英雄力挽狂瀾、拯救人類生命、維護正義的影片,或者其他以敘事為主的藝術形式。在超級英雄電影的譜系中,以被譽為超英電影的天花板、諾蘭指導的《黑暗騎士》系列最有代表性。這一系列電影改編自DC公司的原創漫畫,以DC漫畫人物蝙蝠俠為核心角色,卻沒有在片名中出現“蝙蝠俠”一詞。影片以現實主義警匪片的手法包裝了一個極度寫實的超級英雄故事,其中的蝙蝠俠不再作為傳統意義上的超級英雄拯救世界,而是以一個普通的正義者身份去面對哥譚市諸多問題,比如官僚系統的腐敗和不作為,人性中與生俱來的惡與毀滅欲望,整個社會的不安和不滿情緒,這些現實性的問題都是用超級英雄的偉大力量無法改變的。通過強烈的現實主義情緒,諾蘭成功地挖掘出蝙蝠俠與小丑這一對角色的內在性格,并借此深入地討論了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等哲理問題,將漫畫改編的超級英雄電影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層次。2008年,諾蘭導演的《蝙蝠俠·黑暗騎士》在前期宣傳中采用了極具現實擴張性的手段:觀眾不僅在網上發現了《蝙蝠俠》世界觀中出現的“哥譚市新聞”的網站,甚至還出現了哈維丹特的地方檢察官選舉網頁。“在web時代,傳統的假想現實化已經呈現出了有如‘ARG(Alternate Reality Game,現實替代游戲)一般,即呈現出‘跨媒介敘事‘參加者社群化與‘現實代替感的特征。”[3]在“黑暗騎士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中,諾蘭直接將故事的發生地從哥譚市換成了紐約市,并在宣傳中暗示蝙蝠俠在現實中的“存在”,全然是指涉現實的意味。這種擴張現實性的宣傳與創作方式在現代具有更豐富的形式指涉和內涵意蘊,電影與生俱來的媒介屬性和歷史的文化特性,甚至創作者的意識形態性,都決定了其創新成果的巨大意義。正是在這層意義上,諾蘭通過“黑暗騎士三部曲”和《盜夢空間》的走紅,改造了好萊塢爆米花電影和超級英雄電影,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