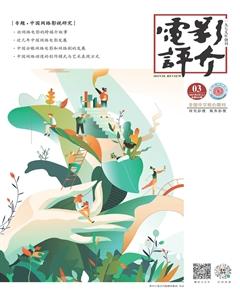中印公路電影美學(xué)塑造的跨文化解讀
康靜
20世紀(jì)50年代,公路片作為一種新興的類型片隨著新好萊塢的發(fā)展迅速崛起,“用眼睛思考”的新一代創(chuàng)作者,面對冷戰(zhàn)的政治格局與轟轟烈烈的全球革命運動用影像表達(dá)思維,并對其中的核心價值觀發(fā)起了反叛。20世紀(jì)50至70年代的公路電影繼承了西部片的部分形式要素,將目標(biāo)集中在了“邦妮與克萊德”式“心血來潮的主人公”和“無可奈何的哀愁”中,最終成為新好萊塢中美國文化精神與形象的代言;在全球歷史與現(xiàn)實的巨大變革中,公路類型電影也在其自身基礎(chǔ)上隨著跨文化傳播與交流產(chǎn)生著變化。在中國與印度,公路電影的美學(xué)塑造在不同的主體與歷史領(lǐng)域不斷拓展延伸,在相異的文化歷史背景與共同的全球化現(xiàn)狀下,對作為受美國霸權(quán)文化影響的中印兩國的公路電影進(jìn)行基于其特有文化特征的分析,或可為實現(xiàn)不同主體間的文化對話提供有效路徑。
一、公路電影類型的確立與跨文化傳播
類型電影是在美國好萊塢出現(xiàn)的在主題情節(jié)模式、人物類型、視覺造型和影像風(fēng)格等方面相類似的現(xiàn)象。作為與美國歷史與主流社會價值觀緊密關(guān)聯(lián)的電影類型,公路片的分析應(yīng)當(dāng)建立在與近代以來美國社會發(fā)展的對照上。在19世紀(jì)后期20世紀(jì)初期,大規(guī)模工業(yè)的急速發(fā)展推進(jìn)了資本主義理想的“美國夢”的形成。美國的白人新興資產(chǎn)階級在取得獨立戰(zhàn)爭的勝利后,發(fā)起了從東部的殖民地向西部遷移發(fā)展的“西進(jìn)運動”。在西進(jìn)運動中,“西部”成了勇敢自由和機會的代名詞,美國西部大片廣袤而富饒卻少有人煙的土地為一無所有的普通人提供了無限的可能。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成功的最高境界不屬于滿足安逸的人們,而是屬于那些在艱難險阻面前從不畏懼中終獲輝煌的人們。”[1]此時“美國夢”是建立在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基礎(chǔ)上“不可剝奪的生存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追逐幸福的權(quán)利”[2]。這一概念為美國擴(kuò)張主義者的意識形態(tài)提供了一個基礎(chǔ)的準(zhǔn)則,成為西部拓荒的動力。西進(jìn)運動塑造了美國人的冒險精神,“到西部去”的口號及西部題材小說和電影與個人成功的神話相關(guān)聯(lián),也成為了當(dāng)時“美國夢”的重要一環(huán);而地域遼闊的西部是美國之所以成為美國的歷史文化象征,也是美國“最美國化的部分”。“西部”既是一個物質(zhì)上的地理環(huán)境空間,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歸屬和指向。“西部遼闊的原野使人充滿自信和征服的力量,隨之產(chǎn)生的西部文學(xué)體現(xiàn)著美國夢的基本內(nèi)涵……同樣以西部拓荒為主要背景的西部片,直接繼承了西部文學(xué)的典型意象——牛仔、駿馬、獵槍;冒險、殺戮、馳騁;沙漠、荒原、小鎮(zhèn),這些已經(jīng)成為目前我們對西部電影最深刻的記憶。”[3]
20世紀(jì)50年代,好萊塢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日益擴(kuò)展的消費主義和其他因素,嚴(yán)重地打亂并重新界定了美國的生活方式。公眾對電影的忠誠以及好萊塢在美國和海外對電影工業(yè)的控制已經(jīng)日益衰落;加之海斯法典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干涉和限制,制片廠主要成為發(fā)行公司,資助獨立制作人制作小成本、針對特定市場的藝術(shù)影片。習(xí)慣收看電視的“讀圖時代”的新觀眾群不再滿足于傳統(tǒng)好萊塢類型電影陳舊老套的表現(xiàn)方式,迫切需要一種能夠反映更加復(fù)雜曖昧的社會與人生的新的電影形態(tài),于是,以小成本制片為基礎(chǔ)的新好萊塢誕生了。新好萊塢反映在新的類型電影上,便是公路電影。公路電影繼承了西部片的形式要素,擁有地理場景上滿足人煙稀少的西部圖征,同時改變了西部片公式化的敘事模式和情節(jié)走向及精神內(nèi)核:從20世紀(jì)60年代的《邦尼與克萊德》開始,美國電影制作者將目光投向那些與社會格格不入、對社會心存不滿的人的處事方式上,開創(chuàng)了美國電影反社會反主流的傾向,并深刻影響了新好萊塢的公路電影,成為新公路電影最基本的價值取向。《逍遙騎士》以40萬美元成本博得2500萬美元的商演成功更加刺激了以利潤為導(dǎo)向的發(fā)行公司,產(chǎn)生了大量小成本公路片的模仿之作。一望無際的公路、迷茫的流浪者和嬉皮士、破舊的旅館和汽車也成為戰(zhàn)后美國文化精神上新的文化隱喻與象征。
在1975年左右,新好萊塢隨著戰(zhàn)后經(jīng)濟(jì)的逐漸復(fù)蘇與思想運動浪潮的平息畫上了句號,曾經(jīng)在越戰(zhàn)期間高漲的反戰(zhàn)運動以及支撐著新好萊塢電影的民權(quán)浪潮開始消退。在新好萊塢十年黃金時期過去后,動作英雄重歸銀幕,巨片策略風(fēng)行好萊塢。這波以《陽光小美女》等公路喜劇為典型的作品只是借用公路形式與敘事框架,并不涉及20世紀(jì)60年代末期盛行的文化反思與批判,尋找美國精神的旅程被鬧劇和特技所代替,而“逍遙騎士”的精神內(nèi)涵卻伴隨美國文化與經(jīng)濟(jì)模式的全球化被帶入了歐亞非國家,并在此后的幾十年中持續(xù)發(fā)揮作用,其影片價值中對現(xiàn)實社會的游離和審視影響了全球幾代電影創(chuàng)作者。改革開放以來,電影制片、發(fā)行、放映等過程逐漸適應(yīng)了新確立的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創(chuàng)作與生產(chǎn)機制,這場“自上而下”的影視改制直接催生了包括公路片在內(nèi)的新型影視文化形態(tài),可以稱之為一種對照好萊塢意義上的“電影工業(yè)”,而印度在逐漸擺脫了英政府的殖民統(tǒng)治之后,新一代的電影藝術(shù)家要求更真實地反映現(xiàn)實,突出英國殖民統(tǒng)治期間不允許拍攝的、涉及國內(nèi)底層人民痛苦生活的影片。因此,遠(yuǎn)離主流秩序規(guī)范、反映個人精神迷茫與歷史記憶的公路電影也得以在印度扎根生長。
二、中印公路類型的接受和闡釋模式
在我國,“類型電影”一詞的引入源于20世紀(jì)80年代,一批年輕的電影學(xué)者以新的理論維度為娛樂片的創(chuàng)作正名。同一時期,印度也引入了主題情節(jié)模式、人物類型、視覺造型和影像風(fēng)格等方面相類似的好萊塢類型電影。印度電影人在傳統(tǒng)的歌舞電影的基礎(chǔ)上將這些偵探片、喜劇片等類型片種與本土歌舞片進(jìn)行融合,形成了一批在制作及發(fā)行上都是在其故事類型和電影傳統(tǒng)中完成的,同時具有歌舞片獨特形式要素和規(guī)則的“印度風(fēng)格類型片”。“電影類型很容易被理解為電影工業(yè)與其觀眾之間的一種‘對話,或者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商業(yè)利潤的兩者調(diào)和。”[4]公路片概念的確立和類型衍變是一個理論不斷建構(gòu)的歷史,它如同流動的影像本身一樣,處于多元文化類型的游覽中,其子類型在保持基本元素的同時,精神內(nèi)涵也在時代和文化思潮的影響下不斷伸縮與變化,在不同地區(qū)與文化背景的闡釋中表現(xiàn)出特殊性。
雖然是美國的“舶來品”,但中印兩國的公路類型電影不僅具有帶有地域與文化特色的形式要素,還具有公路類型特定的普遍特征。公路類型片有三個基本元素:公式化的情節(jié)、定型化的人物與圖解式的視覺形象。中印兩國的公路類型電影接受了這些易于復(fù)制甚至可以批量生產(chǎn)的基本題材、人物設(shè)置、敘事模式、敘事元素,同時又具有在某種特殊的生產(chǎn)和消費意識形態(tài)機制中通過類型價值的再闡釋體現(xiàn)出兩種與美國范式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在中國,公路片大致可分為三類:以《葉落歸根》(2007)和《人在囧途》(2010)為代表的現(xiàn)實主義喜劇,以《人在囧途之泰囧》(2012)和《港囧》(2015)為代表的笑鬧賀歲喜劇,以《無人區(qū)》(2009)為代表的黑色犯罪類型片。其中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與激變中的中國社會密切相關(guān)。《葉落歸根》改編自中國農(nóng)民工李紹帶著工友左家兵的尸體從深圳返鄉(xiāng)的真實經(jīng)歷,新生代導(dǎo)演張揚對于這個故事做了許多戲劇化的改變,讓它變得更加豐滿曲折。南下深圳打工的東北農(nóng)民老趙的好友老劉因為酗酒死在工地上,老趙依據(jù)與他生前的約定將老劉的尸體帶回家鄉(xiāng),途中引發(fā)了種種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影片采用遠(yuǎn)景和自然的中景鏡頭拍攝人物,畫面風(fēng)格清新明麗,用美麗的風(fēng)景搭配比較悲慘的故事,在平和的氣氛中帶有黑色幽默的感覺。《人在囧途》系列以徐崢飾演的外企高管與王寶強飾演的民工為對照性的主要角色,其角色形象在首部作品中尚貼近現(xiàn)實情境中的多面性格,故事內(nèi)容也涉及城鄉(xiāng)貧富差距等現(xiàn)實問題;而在其續(xù)作《泰囧》以超過12億的票房成績刷新了華語片票房紀(jì)錄后,《人在囧途》系列就加強了高管與民工角色的符號化特征,并刻意營造滑稽場景制造喜劇效果。在場景的選擇上,《泰囧》《港囧》與籌備中的《印囧》也將故事發(fā)生的背景從春運期間的中國轉(zhuǎn)移至充滿異國風(fēng)情的亞洲旅游路線中,大大削弱了影片對現(xiàn)實的反思意味與人文關(guān)懷的精神。除此以外,以黑色喜劇見長的寧浩導(dǎo)演的《無人區(qū)》重新回到廣袤的中國西部,片中的律師、卡車司機、偷獵者和加油站老板等人物在“無人性”也“無人監(jiān)管”的西部肆意展現(xiàn)人性的黑暗面,其中的沙漠和荒野景觀不僅沿承了西部片空間景觀的外在特征,還具有“遠(yuǎn)離現(xiàn)代社會及城市空間的自然和自由”的全新美學(xué)含義。
印度公路片則更善于將現(xiàn)實主義關(guān)懷、歌舞特色、黑色因素與喜劇因素自洽地融為一體,拍出了《喀布爾快遞》(2006)、《人生不再重來》(2011)、《在路上》(2014)等優(yōu)秀影片。《喀布爾快遞》將鏡頭對準(zhǔn)了2001年“9·11”事件后局勢緊張的喀布爾,兩名印度記者、一名阿富汗當(dāng)?shù)叵驅(qū)А⒁幻麃碜园突固沟乃辔溲b分子乘車同行,他們還遇到了一名來自美國的攝影女記者。拍攝紀(jì)錄片出身的印度導(dǎo)演卡比爾·汗在輕松詼諧的戲劇基調(diào)中流露出對殘酷戰(zhàn)爭下難民的悲憫。經(jīng)典好萊塢中全封閉的車廂往往是資產(chǎn)階級式浪漫愛情的發(fā)生場所,常使用前方固定機位拍攝穩(wěn)定的對稱鏡頭和同一場景中的人物表演;而《喀布爾快遞》中存在民族與宗教沖突的阿富汗人與巴基斯坦人、共同對美國價值觀存在敵意的中東人和美國人,以及看似中立實則尷尬的印度人被放置在與集體文化環(huán)境隔離的封閉車廂中,在抗拒美國引領(lǐng)的資產(chǎn)階級城市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同時,超越了身份限制的“人性”也綻放出新的光輝。《人生不再重來》中的敞篷車為角色營造了半開放半封閉的象征空間。拍攝機位除正機位外,還有車外的側(cè)鏡頭及后方的跟拍鏡頭,畫面中同時出現(xiàn)了載具、人物和自然風(fēng)光。三位男主角遠(yuǎn)離都市生活規(guī)范,與廣闊雄壯的自然建立了某種“聯(lián)系”,重獲生命力而一步步走向“覺醒”,完成了自我精神放逐及重新詢喚、從功利主義到返璞歸真的轉(zhuǎn)變。《在路上》則在關(guān)注印度尖銳的貧富差距與階級矛盾的同時,暴露出女性作為弱勢群體受到家庭及社會傳統(tǒng)倫理壓迫的現(xiàn)實。錦衣玉食但缺少自由、長期被叔父侵害的實業(yè)家之女因突然的綁架回歸象征自由的荒野中,大量下車露營的場景與環(huán)境音效的強化,加之綁架者與被綁架者之間的交談與相互理解,象征女主角被完全拋入自然空間,對現(xiàn)實社會的疏離和審視及與主流價值的徹底決裂。
三、全球化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背景下的主體對話
對于不同國家公路片的研究,從跨文化角度可以看做是美國電影在主體與歷史領(lǐng)域的類型中的衍生擴(kuò)展。從西進(jìn)運動時期到二戰(zhàn)后,公路片作為與新好萊塢同時誕生的基本類型與“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到全球反殖民運動的興起與冷戰(zhàn)結(jié)束,在“公路”框架下的敘事在保持基本元素的同時,其精神內(nèi)涵在時代和文化思潮的影響下不斷伸縮與變化。“公路電影”其實是一個非常寬泛的、伸縮性很強的術(shù)語,泛類型的公路片可以包括公路喜劇、戶外電影、成長片、黑色公路電影、朝圣電影等多個子類型。好萊塢絕大多數(shù)電影的制作及發(fā)行都是在其故事類型和電影傳統(tǒng)中完成的,都有其獨特的形式要素、規(guī)則、價值觀和扮演定型角色的影星;而觀眾經(jīng)過多年的觀影經(jīng)驗,對每一種電影類型也形成了一定的期待。在媒介情境理論中,美國學(xué)者約書亞·梅羅維茨指出,對人們交往的性質(zhì)起決定作用的是信息流動的模式,而非物質(zhì)場地本身。“電子媒介通過與現(xiàn)實情境相結(jié)合,從而創(chuàng)造出了新情境。在跨國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這個重構(gòu)的新情境中,用戶不但能對他國文化和生活進(jìn)行沉浸性體驗,還能與他國用戶進(jìn)行跨文化交流。”[5]作為一種典型的商業(yè)化電影樣式,公路片產(chǎn)生于美國好萊塢大制片廠制度及其明星制,同時其本質(zhì)上是電影工業(yè)化及商品化的產(chǎn)物。它在高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社會中通過電影媒介創(chuàng)造出一種流動的、互主體的、對話性的信息模式。
如果說西部片是經(jīng)典好萊塢時期最富美國精神特色的電影類型的話,那么公路電影就是新好萊塢時期現(xiàn)代文化精神與形象的代言,它所表現(xiàn)的正是現(xiàn)代電影中難得一見的自我反省與批評的自覺。公路電影是一種首先成熟于美國的現(xiàn)代電影類型,也是歐美現(xiàn)代電影運動和青年反文化運動的綜合產(chǎn)物。作為現(xiàn)代電影類型,公路電影的美學(xué)追求就是盡可能地表現(xiàn)流動的抗?fàn)幣c自由,表現(xiàn)一種歷史性的批判與反思。“就像西部片通過對文化歷史的神話編寫強化了它與社會歷史間的文化關(guān)聯(lián)一樣,公路電影通過對特定的空間場域的選擇與建構(gòu)從而確立起自身類型的文化歷史意義。大峽谷、落基山脈、大平原、大沙漠景觀……美國公路電影沿承了西部片外在的空間景觀,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地域的歷史文化意義的同時,更賦予了它們新的美學(xué)含義——遠(yuǎn)離現(xiàn)代社會及城市空間的自然和自由。”[6]研究公路片的跨文化傳播,就要關(guān)注不同文化、共同體之間的共同背景以及全球化趨勢中互主體體系的復(fù)雜性。現(xiàn)代性決定了公路片承擔(dān)著現(xiàn)代影像革新和文化批判的雙重時代使命,它的出現(xiàn)宣告了經(jīng)典好萊塢時代的結(jié)束和新好萊塢現(xiàn)代電影運動的開始。公路片中圍繞著高速公路而設(shè)計、以汽車為基礎(chǔ)的西部線性城市成為新時代城市的標(biāo)志,也是在不同國家觀念、認(rèn)知等方面差異和多樣性的基礎(chǔ)上展開的平等對話。高速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東方與西方,如同公路片中行駛在高速公路上的司機與乘客,是互為主體的。并且公路片由于匯聚了不同地區(qū)、不同價值觀的游蕩者,可以折射出世界各地的風(fēng)土人情和文化樣貌。處在和西方流行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國和印度,公路片的接受和闡釋模式也不盡相同。
面對這種現(xiàn)象,與其保持復(fù)雜的怨羨心理譴責(zé)好萊塢與美國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quán),不如轉(zhuǎn)換思維,由面對文化主體性的單向轉(zhuǎn)向批評間性思維下的“互主體性”理論。中國和印度作為世界兩大文明古國擁有豐富的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這些文化資本在好萊塢為主導(dǎo)的跨國影片中不免為迎合西方觀眾展現(xiàn)為一種奇觀化的東方鏡像,最終成為西方世界制造的東方主義他者形象。面對以好萊塢為中心的強勢的美國文化主體,中國與印度為了避免被控制或同化,有必要借助美國的既有電影類型進(jìn)行新的主體重塑。公路片作為一種成熟的電影類型,通常具有相對穩(wěn)定的系統(tǒng),它既有類型片的基本特征又有著某些局部的變奏。它根據(jù)主流觀眾的心理變化,在一定時期內(nèi)會以某一類型為制作重點,如對犯罪、喜劇、歌舞等因素的強調(diào)等,這種規(guī)范化和程式化,培養(yǎng)了觀眾的觀影經(jīng)驗和期待視野;而正是這些懷著特定觀影經(jīng)驗和期待視野的觀眾,又反過來給了類型片生存的空間。在全球化與跨文化、文本的互文性與融合闡釋的背景中,舊有的東西方對立、類型間對立的立場顯然不夠全面。進(jìn)入更廣闊的社會歷史空間,引入新的“互主體性”概念,重新建立開放、包容、自信的理論框架,以靈活的身份建構(gòu)參與國際化電影制作,是中印兩國公路片、同時也是亞洲電影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結(jié)語
盡管不同的國家存在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但可以利用文化現(xiàn)代性上的“共通性”實現(xiàn)文化轉(zhuǎn)譯與調(diào)試,從而達(dá)成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在經(jīng)濟(jì)和文化多重交流的全球化背景下,近年來,中印兩國的優(yōu)秀公路電影作品繼承了經(jīng)典公路電影的叛逆精神與現(xiàn)實關(guān)懷,有力地推動了現(xiàn)代公路電影類型的復(fù)歸和自主更新。這一起源于新好萊塢的經(jīng)典電影類型,在美國經(jīng)過低谷之后,在遙遠(yuǎn)的中國和印度顯現(xiàn)出了新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xiàn):
[1][美]西奧多·羅斯福.勤奮地生活[EB/OL].1899年4月演講稿https://wenku.baidu.com/view/b1f60a83e53a580216fcfeeb.html.
[2][美]卡爾·貝克爾.論《獨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M].彭剛,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8:17.
[3][4]張曉凌,詹姆斯·季南.好萊塢電影類型:歷史、經(jīng)典與敘事(下)[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0:748.
[5][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M].肖志軍,譯.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2:34.
[6]徐文松.空間·文化·流動景觀——文化地理學(xué)視野下美國公路電影的流動美學(xué)[ J ].文化與傳播,2013(2):17.
【作者簡介】 康 靜,女,河北張家口人,山西傳媒學(xué)院攝影系講師。
【基金項目】 ?本文系山西省高等學(xué)校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研究項目“文化人類學(xué)視域下的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研究”(編號:20180303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