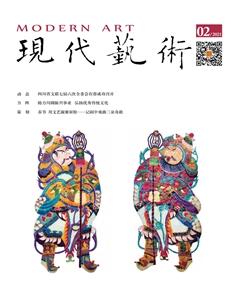抗戰(zhàn)題材的深入挖掘和獨特演繹
劉迅


現(xiàn)為成都理工大學傳播科學與藝術(shù)學院教授。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理事,中國電影金雞獎理論評論獎獲得者,享受國務(wù)院特殊津貼專家。
狼煙滾滾,尸橫遍野,短兵相接,血肉橫飛,這是《九條命》給人的最初印象,諸如此類的畫面似乎與其它槍戰(zhàn)片沒有多大差別。的確,這是一部戰(zhàn)爭片,是一部反映中華民族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情節(jié)動作片。然而,隨著故事規(guī)定情境的展開,立即讓人眼前一亮。透過銀幕上波譎云詭的陣陣硝煙,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生死搏殺和戰(zhàn)場奇觀,而且還看到了一群小人物在一場巨大的人禍面前的艱難掙扎與抗爭,更看到了一個由川人組成的特殊軍人群體所展現(xiàn)出來的“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使命擔當和民族精魂。
一部抗日戰(zhàn)爭史,既是中華民族飽受蹂躪、水深火熱的國難史,也是中華民族團結(jié)斗爭、抵御外辱的抗爭史。對于中華民族而言,那段集體記憶是悲慘的,更是悲壯的。其中,不僅有訴不盡的悲歡離合,道不完的愛恨情仇,更有華夏兒女的義薄云天,志士仁人的慷慨高歌,這一切,在建構(gòu)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和精神財富的同時,也孕育了當今我國影視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題材“富礦”。然而,對這座“富礦”怎么開采,挖掘的方向怎么把握,卻是一道嚴肅而沉重的時代課題。我們注意到,在表現(xiàn)重大歷史題材方面,僅有全景式的宏大敘事很難完全滿足當下廣大觀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的欣賞需求。于是,像《九條命》這樣在題材挖掘和敘事視角上獨辟蹊徑的作品應(yīng)運而生,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的審美體驗。
為了講好川軍抗戰(zhàn)的故事,影片編導(dǎo)首先在題材的挖掘上探索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徑。它沒有像前不久公映的《八佰》那樣集中圍繞淞滬抗戰(zhàn)中國民黨政府軍固守上海四行倉庫陣地的戰(zhàn)例來展開緊張激烈的情節(jié)演繹和視覺沖擊,更不像以往某些表現(xiàn)抗戰(zhàn)題材的影片那樣有一個固化的模式和既定的套路,而是見常人之所未見,力圖將一支衣衫襤褸、裝備簡陋、貌不成軍然而卻特別能打仗的川軍戰(zhàn)斗小隊呈現(xiàn)在觀眾的面前,讓人刮目相看卻又震撼感動,使觀眾被那些驚險的情節(jié)和凄婉的細節(jié)深深地吸引。從影片的社會意義而言,挖掘川軍抗日的題材,更能夠讓人感受到取得那場偉大的勝利實屬不易。它可典型化地展現(xiàn)一個貧弱的國家和人民如何依靠巨大的精神力量和頑強的意志品質(zhì)戰(zhàn)勝那些武裝到牙齒的法西斯侵略者,并讓今天的中國人從中獲得不畏強敵、奮勇抗爭,努力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強大動力。從影片的審美價值而言,影片將鏡頭對準一群川軍下層抗戰(zhàn)軍人的艱難之旅,自然形成一個個困境和沖突,使情節(jié)的走向形勢并舉,跌宕起伏。同時,它突出了大背景下的小視角、大場景里的小節(jié)點、大故事中的小人物,將藝術(shù)的辯證法貫徹始終,使得影片充滿了強烈的戲劇性。影片沒有概念化地表現(xiàn)國民黨政府軍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治國理念左右下無原則地向后方潰退,卻在展現(xiàn)國軍某師部接到上峰命令后倉促撤退的同時,把斷后炸橋的重任留給了川軍某團,更把身陷敵后出生人死的戰(zhàn)場C位留給了這個團被打散的九個戰(zhàn)斗人員身上,讓他們在危機四伏的情境中上演了一場迎敵而上、以死相博的壯烈大戲。這樣處理,正是編導(dǎo)在挖掘和演繹題材方面的高明之處,它既不動聲色地將那些假抗日真反共的國民黨政府軍與一心抗日期待勝利后早點回家的川軍士兵形成鮮明對比,又順理成章地將全民抗戰(zhàn)匹夫有責的主題彰顯出來,更把這個由鐵血川軍草根士兵用軍魂鑄就的民族英雄故事鮮活地呈現(xiàn)在觀眾的眼前。它突出了偉大的抗戰(zhàn)精神,卻沒有沿襲過往的章法僅用鏡頭展現(xiàn)戰(zhàn)爭的奇觀和搏殺的驚險,也沒有大量使用特技視效以表現(xiàn)抗日將士的玄乎神勇和蓋世武功,而是刻意挖掘“武戲”中的人文精神,于緊張懸疑的情節(jié)線索和出其不意的劇情突變中融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元素,并將其藝術(shù)化地呈現(xiàn)出來,使慘烈的戰(zhàn)爭場景平添了大氣磅礴的文藝色彩。它謳歌了英雄主義精神,卻沒有只是將著力點放在某個英雄人物的驚人之舉上,而是極力表現(xiàn)這群抗日英雄極其草根的一面,以凸顯鮮明獨特的人物個性,又通過這一個個草根英雄迥然各異卻又打動人心的言行詮釋了英雄主義的豐富內(nèi)涵;它弘揚了愛國主義精神,卻不是公式化地將這一群人物描繪成時時處處都高喊愛國的符號,而是深刻地揭示出在不同身世、不同覺悟的人物身上所體現(xiàn)出來的不同層次的愛國情操和人文情懷,最終以他們?yōu)閲柢|慷慨赴死的大義凜然完成了愛國主義精神的壯麗升華。在觀看影片時,我們強烈地感受到,雖然影片沒有正面描繪一場改寫歷史的著名戰(zhàn)役,也沒有讓劇中人物轟轟烈烈地干一番足以彪炳史冊的英雄業(yè)績,但卻用融合創(chuàng)新的影片類型和極富張力的鏡頭語言講述了九位川籍下層軍官和士兵歷經(jīng)磨難、萬死不辭、舍生成仁的悲壯故事,展現(xiàn)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和犧牲精神,以及川湘人民互相支持、休戚與共的骨肉深情。
尤其是對于戰(zhàn)爭題材“武戲文寫”的獨特處理,《九條命》給我們演繹了一個個極為精彩的場面。這不僅僅是在戰(zhàn)爭題材的底色上敷上了勞軍團舞女們令人眼花繚亂的舞姿及其生離死別的故事,也不僅僅是讓戰(zhàn)斗中的崔老板、老鬼等人時不時來上一段川劇唱腔和川人幽默,片中多種元素和多條線索的交織極大地增強了影片情節(jié)的豐富性和視聽語言的觀賞性。瑤族祠堂前那一幕重場戲可謂全劇最為出彩的一筆,其規(guī)定情境如下:日軍追擊秦浩忠所帶領(lǐng)的川軍小部隊在一個瑤族村落展開激戰(zhàn)。對于這樣的“武戲”場景的處理,如果按照慣常做法,只要讓動作導(dǎo)演設(shè)計好武打動作和將煙火、槍械、炸點等布置到位,導(dǎo)演再做一番富有動感的場面調(diào)度即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編導(dǎo)在此采用了分切鏡頭,一邊表現(xiàn)堅守祠堂的宋先生點燃掛在祠堂里寫滿《楚辭》的白布條,并慷慨激昂地吟誦其中的名句,另一邊則剪輯了秦浩忠?guī)ьI(lǐng)川軍士兵正在與日寇浴血奮戰(zhàn)的畫面。鏡頭來回之間,讓我們強烈地感受到,祠堂的火勢越來越猛烈,《楚辭》的吟誦越來越激昂,敵我的戰(zhàn)斗越來越殘酷,一步步將川軍抗日的戰(zhàn)場氛圍渲染到了極致,最后宋先生和秦浩忠相視一笑的畫面在烈火中隱去。這一“文”一“武”與亦“文”亦“武”的場面設(shè)計和交叉蒙太奇建構(gòu),不僅強化了影片戲劇動作的節(jié)奏,而且凸顯了影片悲壯沉雄的氣勢,更深化了影片的英雄主義題旨,為本片的觀賞疊加了更為豐富的欣賞元素和審美價值,也為情節(jié)動作片的類型設(shè)定注入了鮮明的民族風格和文藝氣質(zhì)。這不能不說是《九條命》在民族電影類型化創(chuàng)作上的一次創(chuàng)新探索和有益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