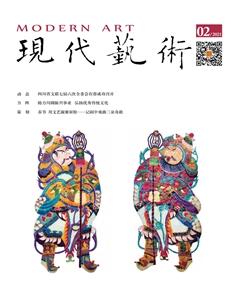器和道:一匹馬的前世今生
(一)
趙曉夢的長詩《馬蹄鐵》發表在2021年01期《十月》雜志詩歌頭條,讀《馬蹄鐵》就像讀一本深奧無比的宗教經書。里面豐富的歷史場景、歷史人物、歷史細節和歷史典故,以及由此而幻化出來的紛繁華麗的詩歌意象,組成了這部長詩的基本骨架。而用一匹馬作為中心意象貫穿全篇,不僅打通了中國漫長的歷史,而且也讓整部長詩氣息飽滿,氣韻生動。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匹馬開疆拓土、征戰殺伐的歷史,也是一匹馬做為主要戰爭工具慢慢退出戰爭舞臺的歷史。中國最早的關于馬的文字記載出現在甲骨文中,而最早的馬匹馴養則發生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人類第一次把馬匹作為騎乘工具是在公元前3500年-3000年。在青銅文明時期,馬就已經作為戰車的“發動機”來使用了。
而歷史從來不會厚此薄彼,一棵樹,一匹馬,一座江山,一座城,都曾經是構成歷史的平等元素。而當人類賦予了這些元素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權力的、利益的、制度的力量時,它們就變成了歷史發展中的核心要素。如果一匹馬可以決定江山的起伏,朝代的更替,君王的輪換,甚至生命的存在和消失,這匹馬就已經不再是普通的動物,而是一種精神、權力和利益的象征。
《易經·系詞上》說,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器道關系既是一種融合平衡的關系,又是器中有道道中有器的依存關系。諸子百家時重道輕器,而隨著國家的統一,重器輕道或者器道并重或者重道輕器,都是統治階層和政治人物玩的移花接木的把戲。
當“接骨木還未開花,鳳凰還沒找到梧桐樹,馬的鐵蹄還在風中積蓄力量的時候”,“不同膚色的馬,追逐著風的青春草的青春,滿山飛奔。”
這個時候的馬是自由的,放任的,充滿了原始的活力。它同時也與草地上隨意放養的牛和羊沒有任何差別,只是一個普通的動物,一件純粹的“器”,既不驅使別人,也不被別人驅使。
但“世俗的束縛由來已久”,“人的到來打斷了馬的前世今生”。詩人也不禁好奇地問道:這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人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是有思想、有欲望的一群高等動物。如果馬是器,那他們毫無疑問就是馭器者,使器者。而他們最初只是認馬為騎,以為憑胯下之力就可以馭力驅使。沒想到,他們成了率先“跌落馬背”的一代。而廣大的草原,需要天馬行空的斗士,更需要一個個馬背上的民族在草原上崛起并開啟他們的野心之途。
五胡亂華,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黑暗的年代,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南進之旅的開端。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少數民族試圖揮戈南下,飲馬中原。這個時候,比的就是矛堅馬快,而不是誰的思想先進,誰的戰略得當。馬也就成了南北對峙的唯一力量。很顯然,北方占了南方的便宜。此時,“黃昏與黎明,任何時候看都在以舊換新”。一個風起云涌的時代,你方唱罷我登場,新舊更迭,王權就像蕩漾在水面上一樣。
而馬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宮殿,你的國土。英雄們縱馬馳騁,血拼疆域。戰亂一開,綠草如茵的土地上,處處白骨露野,殺伐驚心。馬也就成了天下的象征。然而,“對權力的把握和擁有”永遠“不是一匹馬的邏輯”。當忽必烈的鐵蹄,撞開世界歷史的時候,馬依然只是他座下一個生龍活虎的工具。
但這是一匹真正的馬,有血性有戰力的馬,沒有象征,也沒有隱喻和暗喻。它就是一匹熠熠生輝的馬,日行千里的馬,一匹馬的前世。一個個馬背上的王朝,也被這樣的馬馱著,走過了人類最蠻荒的時代。
詩到第7節,一匹形而下的馬似乎變成了一匹形而上的馬,真正的馬漸漸隱去了身形,而“馬蹄鐵”卻以它堅硬無比的形象,異軍突起,成為了壓倒一座又一座城池的“稻草”。這個時間,也是中國古代皇權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初建的時代,一匹馬從器至道,剛脫了韁繩,又套上了更為沉重的枷鎖。
當掠奪和永不滿足的私心和欲望成就了君王的本性,廟堂之上和廟堂之下便形成了兩個水火不容的階層。一個卑微的、壓抑的、受盡苦難又沒有任何生命保障的群體,他們埋首黃土,任勞任怨,成為了統治階層治下最隱忍的“器”。但這又是一種野起來,可以掀翻桌子、激起波瀾、馬踏飛燕的力量。先是劉邦項羽,后是陳勝吳廣,再是梁山英雄,白蓮教,此起彼伏,沉重的歷史一次次揭開新的篇章,也一次次撕開了血的口子。
而宋朝尤勝,民富國弱,當“席卷天下的馬蹄意外止步于一塊石頭”,茍延殘喘的南宋也走到了斷崖的盡頭。當他們集體投向大海的那一刻,一個王朝只是化作了幾個小小的泡沫。“刀劍濫竽充數”,軍士們吃著“發霉的豌豆”,再勇猛的馬匹也拖不住一個腐朽朝代的退縮。靖康之恥只是一塊小小的癬跡,而“攘外必先安內”“莫須有”“僧道高于官史儒生低于娼妓”“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卻已經是一個嚴重擴散的膿包了。
每一寸江山都是鐵蹄踏出來的,無論統治者和政治家們有多少移花接木的手段,黃河也必須回歸故道,歷史必須回歸正義。只有這樣,一匹馬才活得出迷茫的人間。
大約到第11小節,詩人又從所謂的道回到了器,一匹真正的馬似乎又開始活躍起來。那些強勢得一塌糊涂的將軍,鐵蹄所至,一馬平川。然而,強大的帝國卻抵不住漫長邊關的日日騷擾和夜夜烽火急。無論是強漢還是盛唐,當一個政權軟弱到只能犧牲女人的幸福才能換來國土平安的時候,唐朝詩人李山甫就曾經發出過振聾發聵的驚天一呼:“誰陳帝王和番策,我是男兒為國羞”。“龐大的和親隊伍”只是無奈地“省略了馬蹄鐵的背影”。而我們強大的軍隊不能裝著什么都不知道,我們奔騰的戰馬不能只顧仰天長嘯。
雖然“凝視久了,馬也能包容所有草的委屈/也能抽走每個人做夢的梯子。”人喚醒了馬的野性,而馬能喚醒人的良知嗎?作為底層草根所遭受的痛苦和委屈,難道只有馬可以包容?
詩人再度發問:這又是些什么人呢?
皇帝,大臣,政治家,將軍……他們手握重兵強權,貪戀個人小利,絲毫不顧及民生疾苦,反正國破了山河還在。殊不知人去了文化就斷了,所謂的世態平穩不過是羌笛已遠,白雪連窗格上的一小塊月光都不能撼動。大音希聲的年代,沒有石頭喟嘆英雄氣短,臥槽之馬也已無力嘶吼和悲鳴,鐵腕治下盡是一片安寧祥和。而表面的和平卻掩藏不了紅塵滾動,“歷史的邊界從來不在地理上,而在文化里”,愚昧的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制約了一匹馬的發揮,也把一個又一個朝代送上了不歸路。
但這是一匹馬不能回避的現實,也是一匹馬必須面對的今生今世。
“貧窮和富有的那些人啊,有誰知道馬的去處和歸宿?”
從15小節開始,全詩進入尾篇。詩人不得不正面直視馬的一生,從道回到器。它們用鐵蹄打下的一個又一個界樁、疆土,沒有人珍惜,幾千馬蹄銀就可以換走燦爛的經卷,用生命夯筑的宮殿最后不過是紙上的幻影。
馬還有存在的意義嗎?這天下還值得打嗎?打天下的人已經下馬解鞍,他們雖然在古老文明的進程中曾經立下過汗馬功勞,但電腦、高鐵等現代文明卻又像一陣風吹滅了過往。
詩人認為,放得下和放不下的雜念都是被一頭長發所累。難道一頭長發代表的僅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
從17小節開始,詩人對傳統文明和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率先發出了靈魂的拷問:難道我們祖先用血與淚打下的疆域,最后就只剩下了幾處景點和幾件古董?山川舊情,情何以堪呀。
詩人的第二重拷問更是觸及民族的靈魂:看不到歷史的縱深又怎配為歷史牽馬墜鐙?歷史的縱深里又豈止是一匹馬在奔跑,文化也在奔跑,思想也在奔跑,有生命和沒有生命的都在奔跑。他們為我們這個民族和民族的歷史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詩人以馬為象,在表達馬沒有欺世盜名、不叛逆、也沒有不安的同時,也揭示了一匹馬的精神:無論歷史走到哪一步,無論高坐廟堂的是誰,只要一聲召喚,千軍萬馬依然應者云集。這是一群從不計較也沒有任何覬覦之心的馬,只可惜它們投下的身影越來越小,再也不可能分疆裂土。而馬背上的天下也變得越來越黯淡,長弓的力量早已土崩瓦解。
再優良的馬也跑不過四個輪子的鋼鐵,這雖然與馬毫無關系,但馬的四蹄里卻充滿了尷尬和歉意。這就是作為工具的馬、作為“器”的胸懷和悲哀。但“馬從不會將自己歸入某個陣營”。馬就是馬,它傾盡一生供你驅使,鐵蹄所至,萬骨成灰。但馬永遠是馬,它既不會功高蓋主,又不會心生反叛,它也永遠成為不了“統治階層”的一員。而作為“道”的馬,卻能為統治階級鋪開一條坑洼不平的道路,讓統治者千里躍進,在溝壑上飛奔。這難道還是馬嗎?這是一匹隱喻的馬,象征的馬,有精神指向的馬。
但“人和馬最好的結局都不過是一抔黃土”。
我們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等到那些消失的名字從古道西風中歸來”時,“請聽我口令:帶酒的出列,打鐵的繼續”。
然,誰是帶酒的?誰又是打鐵的呢?
(二)
寫長詩就像喝大酒,是有癮的。曉夢自《釣魚城》后似乎欲罷不能,在2021新年到來之時,又為我們奉獻出了一篇策馬奔騰的長詩。
但創作長詩,首先需要足夠的材料和思想的準備。其次再是文學的準備。說實在的,《馬蹄鐵》這樣的長詩和其他性質和題材的長詩不太一樣,它沒有一個貫穿全詩的故事,其敘事性和抒情性都缺乏必要的依托,唯一能夠撐起這部長詩的就是一些史料。但史料放在歷史中,和史料放在文學中,又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難度。在歷史中,要的是對史料的尊重和守真,在文學中則不一樣,尤其是詩歌,它不允許你引用大段的史料,也不允許你把來龍去脈都說清楚,它要的只是某個細節、碎片、意象,要的是其中包含的思想和美感,這為寫作者帶來的難度顯然更高。
更為重要的是,讀者還不能依賴注釋和翻閱歷史才能讀懂作品。我之所以說,《馬蹄鐵》像一本難懂的經書,是指我們不再可以像讀其他詩歌一樣,順著一口氣就讀完它。必須一邊讀一邊思考,讀得慢,讀得辛苦。從讀者的角度,也能想象寫作者的大不易。
趙曉夢用一匹馬作為詩歌的中心意象,這匹馬是撐得起的。尤其是中國的歷史,有一多半是馬背上的歷史。幾乎從南北朝開始,就圍繞著北族南進和中原北望而展開。在南北對峙的冷兵器時代,馬是決定雙方勝負的重要法碼。強漢盛唐時代,哪怕擁有如此強大的軍隊和國力依然無法平息北方之亂,就是南方無好馬的緣故。而中國唯一一個馬放四海、打開世界歷史的時代也是由北方民族開啟的。誰擁有優良的馬隊和優秀的騎士,誰就有了開疆拓土的本錢和資格。另一方面,北方惡劣的自然條件和貧脊的自然資源,也迫使北方民族為了生存而南進企圖不滅。
馬除了作為戰馬之外,還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和運輸工具。中國古代的陸上絲綢之路,其實就是一條“馬”路。同時,馬也是重要的信息工具,各種信息都是通過馬在驛站上傳遞。所以,詩人選擇馬作為同時貫穿歷史和全詩的中心意象,是經過了認真思考和謀劃的,絕不是簡單為之。
上面說的是明線,還有一條暗線隱蔽在“馬”這個形象的背后。他們是當牛做馬的底層百姓,像馬一樣被統治者驅使,而得到的是畜牲的待遇。當然,馬不會反抗和背叛,但他們會。陳勝吳廣,梁山英雄,白蓮教,李自成……而歷史就是在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較量中,艱難地向前推進的。《馬蹄鐵》里面,既有明線又有暗線,因而思想性得到了升華。
此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馬道”更多的屬于統治階層的范疇。只有懂馬的人才駕馭得了馬,而馭馬術就是一種“道”。治馬之道和治人之道,是一個道。
全詩筆墨的重點放在了宋朝。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民富國弱的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北方馬蹄掀翻的政權,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在一首以馬為中心意象的長詩中,宋朝是當之無愧的。
我之所以說《馬蹄鐵》像一本經書,除了難讀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也是詩人趙曉夢在這首長詩中所做出的建設性貢獻。他用活了許多歷史典故,并為其賦予了文學的魅力,詩性的魅力。一般來說,歷史典故用在現代抒情詩中會是一種詬病。因為很難復活和翻新。而且歷史典故所涵蓋的文化和史學內涵十分的豐富,很難有創造性和自主發揮的空間。但趙曉夢幾乎不直接用典,而是先把這些典故進行詩化處理,再結合具體的詩境和語境,完全在詩歌中融化。這是用典的創舉。這樣用典比起直接用典,雖然增大了閱讀的難度,因為他已經把典化在詩歌中了,歷史知識不夠豐富的人就會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是卻保證了詩意的蓄積和擴散,維護了詩學和史學的平衡。詩中有史,史中有詩。
比如下面的句子,每一句里都包含著一個甚至幾個典故,詩人要么隱去了具體的人物,要么隱去了具體的事件,然后用文學和詩學的手法,創造性地把它們變成詩歌中天然的構件。甚至你如果不愿意去深究它的來龍去脈的話,完全可以不考慮它作為典故的因素。它就是一個作者精心構置的意象,一個洗盡鉛華的詞,一條通向詩境的路。
“將軍的馬鞍已過江,留給江東父老的背影/劍吻不倒,風吹不倒,血拽不倒”
“刀劍濫竽充數,發霉的豌豆哪守得住城池”
“孤掌難鳴的烽火臺哪能不交出印璽和圖紙”
“放浪形骸的崇山峻嶺剛嘗到權力滋味/附庸風雅的暖風又在馬蹄中破碎”
“這一次失去的就不止人花獨立雨燕雙飛”
“當瘦金體的月亮將涼州城的孤獨坐牢/將軍又帶著御賜的美酒和廚子馳出城門”
“就像手握救災文書和手握貴妃荔枝的人/到底誰跑得更快?”
“馬作的盧也會在三千丈惆悵中敗下陣來”
……
幾乎滿篇都是這樣的句子。缺乏歷史常識的人像讀天書,而即使是讀天書,我們也讀出了詩意,讀到了美,領略了其中深刻的思想。而每一個典故的根都在“馬”上,不必去翻閱史書,查證資料,你就像一首正常的詩那樣去讀,自有一匹活力四射的馬,帶著你沖破詞語的牢籠。
趙曉夢的詩歌語言有著極強的表現力和畫面感,而且天賦神性。柏拉圖說,“詩人是一種輕飄的長著羽翼的神明的東西,不得到靈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沒有能力創造,就不能做詩或代神說話”。柏拉圖認為詩歌是詩人代神說話,是宗教和經書。我倒不認為,詩人一定是在代神說話。語言的神性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妙處。就像兩個互相深愛著的人,一定會有心靈感應一樣。詞與詞之間,句子與句子之間也是有秘密,也是有感應的。
在《馬蹄鐵》這篇長詩中,幾乎每個詞語所對應的精神指向都得到了極致的鋪展和延伸,也正是因為某個詞語或者句子的存在,一首詩歌才擁有了心臟和動力一樣。“白骨露野的大地/陽光剛好走過了一點,似曾相識的廢墟里/掩埋了太多曾經相濡以沫的身影”,“陽光剛好走過了一點”不僅指實,而且還藏有一個更大的隱喻空間。正因為有這一句,才夯實了前后句子的根基和力量。“文化的價值就在于沒有更新聯系人,你有你的泰姬陵我有我的莫高窟,筷子和刀叉不過是吃飯的兩把刷子”,詩人寫東西文明的滲透和融合,用了一個“聯系人”,一下子就打開了通往詩歌內部的道路。“崎嶇的山路上,被枯樹壓低的創傷已經找到/墓地,挑燈看劍吹角連營的一世功名/也已化身城市雕塑”,其中“被枯樹壓低的創傷”讓整個句子一下子充滿了靈性,像有了靈魂一樣。
而是否能夠打開句子和詞語的隱喻空間,也決定了我們的閱讀感受和詩人創作時的主觀感受差距有多大。詩人不擔心你是否讀懂,擔心的是你扭曲他的主觀意圖。尤其是《馬蹄鐵》這樣帶著語言神性的詩歌模本。讀者和作者之間應該建立起一種起碼的閱讀感應,你至少能感覺到詩人創作時的心理狀態,并順著他的精神指向去理解每一個詞語和句子。
《馬蹄鐵》里還有一個突出的語言特色,就是詩人對語言處置的合理性。“半野生的秘密都在草的根部隱身”,“半野生的秘密”就是詩人自創的語言,如果沒有“草的根部”作為依托,誰都不知道他說的什么?正是因為詩人創造性地使用了“半野生”和“草的根部”,全句就顯得自然合理了,就有了邏輯的關系。“即使花椒樹的嘴唇開滿鮮花/也阻止不了被頭發所累的時間站起來說話”,一個“花椒樹的嘴唇”,一個“被頭發所累的時間”是兩個難以理解的新奇意象,但“時間站起來說話”一下子就托起了前面兩個意象,實現了邏輯和情感互通。
“在速度、力量、視線所不能抵達的地方/黎明出其不意地與黃昏的方向保持一致”。
唐政TANG ZHENG
當代詩人、評論家,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