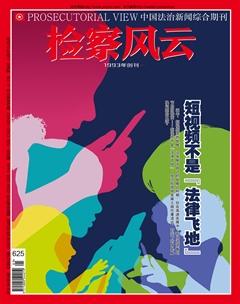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未成年人保護
宋偉哲
古往今來,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很大程度上由于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有些未成年人甚至連最基本的親情關愛也沒有,自然容易做出違法犯罪之舉。這些未成年人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愛和溫暖。從這個角度來考量,做好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其實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之關鍵。回顧法律史,古人同樣重視未成年人的保護問題。既有國家律令典章的保障,也有民間社會力量的協助,更有最高統治者的關注監督,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法律文化,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律令典章
談起未成年人的法律問題,人們往往最先想到刑事責任年齡制度,這是現代刑法的重要內容。在歷代王朝的法典之中,大多會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作出規定,其立法思想和內容與現代刑法大致類似,都以降低和減輕未成年人犯罪者的刑罰為宗。其中《唐律疏議》中的相關規定,堪稱歷代典范,被后世王朝沿用多年。除此之外,古代法律針對未成年人犯罪還有一些照顧性的規定。比如,《唐律疏議》“議請減老小疾不合拷訊”條規定,“十五以下,并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違者以故失論。若證不足,告者不反坐”。又如,唐朝《獄官令》規定,“年八十及十歲,并廢疾、懷孕、侏儒之類,雖犯死罪,亦散禁”。所謂“散禁”,就是不需要戴枷鎖、鐐銬之類的刑具,以減輕服刑者的痛苦。
與此同時,古代統治者對于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問題也有清醒的認知,并把這一思想納入國家的法典令章。例如販賣人口犯罪,特別是拐賣未成年人,歷來為百姓深惡痛絕。唐朝重刑打擊販賣人口犯罪,《唐律疏議》“略人略賣人”條規定,“諸略人、略賣人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當時,窮苦人家賣兒賣女的情況并不罕見。越是年幼的兒童,售價越高,買者也越多。《唐律疏議》嚴厲打擊這種犯罪,規定凡是十歲以下的兒童,即便家長同意出售,也與拐賣同罪,以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清朝時期,立法者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打擊力度空前加大。《大清律例》規定,“凡誘拐婦人子女,或典賣,或為妻妾、子孫者,不分良人奴婢,已賣未賣,但誘取者,被誘之人若不知情,為首者,擬絞監候,被誘之人不坐。若以藥餅及一切邪術迷拐幼小子女,為首者,立絞”。“伙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藏匿勒賣事發者,不分良人奴婢,亦賣未賣,為首……擬斬立決。”以上犯罪為從者,也都會被處以流放發配的重刑。
又如孤兒撫養問題,唐朝《開元令》規定,“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付鄉里安恤”。在實踐中,不少孤兒或貧窮人家的孩子往往以被收養的方式解決基本生活。為了保障被收養兒童的權利,《唐律疏議》“養子舍去”條規定,“諸養子,所養父母無子而舍去者,徒二年”。李唐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王朝,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的國家法律制度無不以儒家思想貫穿始終。儒家思想極為重視血緣宗祧,因此唐朝法律對收養異姓孩子有著非常嚴苛的限制。為了保障失親幼兒的權益,《唐律疏議》特別規定“其遺棄小兒三歲以下,雖異姓,聽收養,即從其姓”。事關宗法倫理,在“疏議”部分,立法者特別對此進行了立法解釋,“其小兒三歲以下,本生父母遺棄,若不聽收養,即性命將絕,故雖異姓,仍聽收養”。十分有趣的是,《唐律疏議》還規定“如是父母遺失,于后來認識,合還本生;失兒之家,量酬乳哺之直”,顯得非常人性化。

未成年人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圖/網絡)
到了明朝,統治者更加關注包括未成年人在內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這主要表現在以立法的形式明確基層政府的救助職能。《大明令·戶令》規定,“凡鰥寡孤獨,每月官給糧三斗,每歲給棉布一匹,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體察”。這條簡單法律的背后,蘊含著重要的意義,代表著立法、執政水平的提升。其一,明確政府承擔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弱勢群體的救助職責;其二,明確最低救濟金額,包括每個月三斗糧食,每年一匹布,使得救濟有可操作性;其三,明確監察、司法官吏的監管職能,保障法律的有效實施。在此基礎上,《大明律·戶律》也作了配套規定。其“收養孤老”條規定,“凡鰥寡孤獨及篤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克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到了清朝,在延續明代法律規定的基礎上,對上述制度進行了完善。在《大清律例·戶律》“收養孤老”條中,規定基層州、縣都要使用國家財政修建“養濟院”,同時將詳細情況向“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匯報。凡入住養濟院者,官府必須詳細核實,然后發給每人一面腰牌,上面印著每個人的年齡、樣貌。每一季度,州、縣官必須親自到養濟院視察,先逐一核對腰牌,再發放救濟品。如果州、縣官到期因公務繁忙無法親自赴院,法律允許其選派忠實可靠的副手代為核查、發放,但事后必須向上級詳細匯報。同時立法者特別規定,總督、巡撫要認真履行監管職能,如州、縣有冒名頂替、克扣錢糧等舞弊犯罪情形,必須立即上奏中央,進行嚴厲查處。
育嬰堂
在傳統社會,人們沒有現代科技和人權觀念,兒童生育率很高,但是成活率、健康率卻很低,遺棄、溺死嬰兒的事件層出不窮。特別是在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下,女性兒童的權益更難得到保障。清朝乾隆年間,湖廣總督孫嘉淦、福建巡撫周學健、山西布政使胡瀛等官員都曾上奏朝廷,痛陳轄區內溺斃女嬰之惡俗。這些久經歷練的封疆大吏不約而同地指出,單純依靠法律禁止和道德宣教,往往無濟于事。他們主張修建育嬰堂解決此類問題,并用現實案例證明,育嬰堂“全活者甚眾,溺女之家從此漸少”。其實早在雍正二年,皇帝就曾下旨對北京廣渠門外的一家育嬰堂予以褒揚,并要求向全國推行。“夫養少存孤,載于月令……為世俗之所難,朕心嘉悅,特頒匾額并賜白金,爾等其宣示朕懷,使之益加鼔勵……再行文各省督撫,轉飭有司,勸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煙稠集之處,照京師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惻隱之心亦可感發而興起也。”在雍正的大力倡導下,全國各級政府展開動員,一方面依靠政府財政,一方面依靠社會捐助,大力進行育嬰堂建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比如湖北武昌的育嬰堂,根據乾隆四年巡撫崔紀奏折所載,自雍正九年設堂以來,共收養過嬰兒一千三百六十余名。
當然,育嬰堂的建設也面臨著一些問題,除去經費緊張之外,管理低效、貪污腐敗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乾隆六年,江蘇巡撫徐士林上奏朝廷,表示蘇州城內的育嬰堂房屋不足,又毗鄰道觀,育嬰堂的奶媽不便在堂內生活,因此當地的做法是讓奶媽把棄嬰抱回家,官府按月發給奶媽工資、糧食以及嬰兒生活所需的物資。奶媽多為窮苦人家,自己也有孩子,得到錢糧衣物后,往往優先給自己的親生兒女,漠視他人棄嬰,導致養子成活率“十無二三”“民間皆言不便,而人心未齊,募捐難集”。漕運總督常安給朝廷的奏報中也表示:“訪聞各處育嬰堂,委任不得其人,而地方官又不能時加督察,以致在堂司事勾同本地棍徒,將附近生子貧家其母即指為乳婦,其子即指為嬰兒,間遇官府查驗,人數無多,復以近地襁褓之兒暫為應點。其實父母無存、貧窮無力者,不得與于其內。所有一年籽粒房租,皆為此輩烹分入己,任意冒銷。”
隨著朝政日漸廢弛,就連京城的育嬰堂也變得弊病叢生。嘉慶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嗣龍奉旨巡查普濟堂施粥情況。認真負責的他一并將育嬰堂進行了檢查,結果令人大失所望。他在給皇帝的奏報中寫道,“育嬰堂在東城僻處,非土著之民幾不知尚有此局,而順天府尹公務殷繁,其地非所常經,亦鞭長莫及。聞其中給發官項多侵漁胥吏,支銷用度又干沒于鄉耆積弊,已非一日。曾訊諸禮部尚書紀昀,紀昀言實有其事。為臣具言其弊甚詳。”這里的紀昀,就是大名鼎鼎的“鐵齒銅牙”紀曉嵐。嘉慶帝覽奏后,遂令“巡視東城御史隨時查察,以昭核實”。兩年之后,巡視東城御史書興、秦維岳曾向嘉慶帝匯報,破獲了一起盜竊育嬰堂去世兒童棺木內陪葬品(包括十多件衣服和四雙銀耳環)的案件,系育嬰堂工作人員監守自盜,案情“殊屬殘忍”,請求嚴辦示警。這既說明了嘉慶帝的舉措收到了成效,也再次印證了育嬰堂管理的問題。
到了晚清時期,西方法律制度與文化開始大量傳播到中國,未成年人保護制度依然如此。在清末法制改革大潮的影響下,育嬰堂的管理制度也開始了由傳統到近現代的過渡。光緒三十三年(1907)四月,清廷頒布了《京師育嬰堂章程》。該“章程”完全以西方成文法的體例制定,共十章十四條,包括“收嬰”“抱嬰之限制”“撫育”“堂中人員及責任”“奶子規則”“堂夫規則”“奶房規則”“運葬殤嬰各項規則”等內容,是一部良好的未成年人收養機構管理法規,對當代相關立法也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