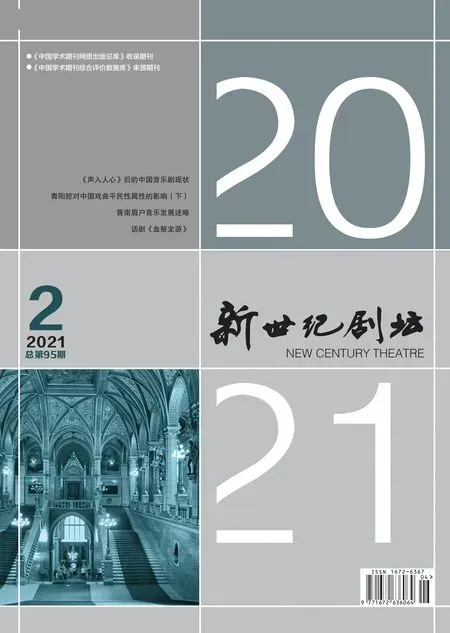晉南眉戶音樂發展述略
文/荊 晶
清代前中葉,各種民間戲曲形式豐富,有明時期盛傳流行的昆腔、花雅之爭興起的多劇種花部,眾多從當地民歌小調發展起來的小戲秧歌等,形態多樣、喜聞樂見、廣受青睞。晉南眉戶,便是從這之中發展而來的一種。
晉南地區,歷來文化生態繁榮,各種文獻古籍廣泛記錄著其厚重的傳統文化積淀。此地興盛了多種藝術形態,被譽為梆子腔發源的“金三角”地區。關于當地眉戶小調的音樂,很早就有記載。“清乾隆九年(1744),京都永魁齋刊行的《時尚南北雅調萬花小曲》所載的十二首曲調中,[兩頭忙][銀紐絲][醉太平]等都是晉南民歌的主要曲調。”[1]可見,此地民間曲調很早就已相當豐富且成熟,這種曲調詞曲皆備,朗朗上口,內容形式兼具,為小戲秧歌等當地民間戲曲的發展提供了土壤。

晉南眉戶劇《焦裕祿》劇照
晉南眉戶在登上戲曲舞臺之前,人們都更愿稱其為“竹馬子”。據老藝人們講,“竹馬”就是鄉村中農民鬧社火時所騎的竹馬燈。我國民間歷來崇尚民俗社火活動,社火是多種民間藝術形式的“集成”,保有深厚的文化內涵。這種傳統活動傳沿久遠,藝術特色濃厚。藝人們騎著竹馬燈邊走邊表演,在跑場中變換隊形,尋求花樣;抑或在跑場結束后坐定下來,唱上幾個單獨的當地小調。這其中的曲調就是晉南眉戶音樂的濫觴。“據運城市宋玉景(1898-?)老先生所講,它們為竹馬子幫唱時就唱的是[剪剪花][采花]等調調。”[2][剪剪花][銀紐絲]等就是晉南眉戶最早的單個曲調。
晉南眉戶屬明清俗曲腔系,其唱腔體制從孕育至成熟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單個曲調即是其孕育的最初時期。在“清光緒年間,陜西富平王敬一編著的《羽衣新譜》中,收錄有眉戶單曲詞與聯曲詞240余首。”[3]據此猜測,在清代末年,眉戶已經由單個曲調過渡至聯曲形態。
對于晉南眉戶的了解,大多數人都知道它起始于地攤形式,但其應是眉戶音樂發展的第二階段。據姚德利《晉南眉戶音樂》中記錄“眉戶老藝人李清齊、衛芳庭講‘眉戶地攤子演唱有自彈(三弦)自唱的形式;也有一人彈唱,而另一人用四頁瓦(四塊竹板)擊節的形式;還有技藝高超者,不僅自彈自唱,且腳踩桿以木魚、碰鈴擊節;再有即是數人操家具(樂器)的演唱形式。’”三弦,一種以三根線而得名的樂器,音色清亮、顆粒感強、富于節奏,更便于攜帶,常受藝人們的喜愛,也是早期地攤眉戶的“發家”樂器。
據1988年出版的《民族音樂概論》記述:“將許多曲牌連綴起來以表現故事內容的說唱音樂,可以說很早就有。宋代的諸宮調就是這類形式。現在尚流行的曲種為河南大調曲子、單弦牌子、四川清音……這些曲種所使用的曲牌有許多是共同的。如[寄生草][馬頭調][剪剪花]等。此外,他們的樂器多用三弦伴奏,在曲式上結構也有類同性。可見,曲牌類音樂與三弦樂器具有很強的共融性,而三弦也在此類樂種中頗具廣泛性與依附性,這些特點與晉南眉戶的曲牌體音樂結構、伴奏樂器相洽和。文章中還提到“許多曲牌連綴起來表現故事內容,宋代諸宮調就是這類形式”[4],這種形式的延伸流傳即是眉戶地攤演唱形式的來源。
地攤時期的眉戶音樂迥異于濫觴期單個的曲調音樂。民間地攤有一種比較流行的“十八扯”演唱,即將不同的曲牌組合起來填上含義不同的唱詞,起初的這種沒有固定的“套數”而言,唱詞間也無情節的連貫性,但其單個曲調到多個曲調的連貫結串,足以見得眉戶音樂的簡單脈絡與初級程式。無論音樂結構,抑或伴奏樂器,這些演唱形式的轉變,已能映襯出眉戶音樂的變化發展。幾件簡單伴奏樂器的融入改變了“眉戶”依附于鬧火紅的附屬地位,進而內容漸豐,自成品類,獨自成形,上升為一種形式獨特的小型民間藝術。這種藝術在當時頗受大眾的喜愛,更有喜好者對其曲調形聲加以評價和贊賞。在清光緒年間著《羽衣新譜》收集曲詞之時,稱眉戶戲音樂“集幽雅于時調,演歌詠之新聲,修短合度,風雅宜人”。
彼時的民間藝術,談不上是專業的從業者,它們亦貧亦富,富者以自娛而居,貧者為討生活而做。作為以地攤生存為主的眉戶戲顯然遠離了正統的文化勢力,與群眾保持著密不可分的人緣聯系。在這種大眾化的人文環境下,所唱所演的皆為民間故事,主要是勸善棄惡、祭祀求愿等,與人們的生活和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其內容通俗、婦孺皆愛,《十八扯》《百戲圖》《五更鳥》都是眉戶戲地攤初期所唱曲子。經不斷豐富,曲牌間的連結性則勾連更緊,故事、情節等內容成為其搭連在一起的串連線,一個完整故事的產生竟促使眉戶升華出“清曲劇”這一形式。當地人更親切地稱它為“清唱劇”。
“眉戶清曲劇”從一定意義上而言已經初具“戲”的模式。它用唱曲來演故事,曲中無道白,唱腔連貫且一瀉千里,宣泄不止,酣暢淋漓,這種形式人們更愿叫它“念曲子”。“劇”這一概念一旦產生,笛子、板胡、馬鑼、鐃鈸等與之相適的傳統樂器也隨之而入。地攤期簡單的伴奏樂器難以滿足“劇”的需要,而多種樂器構成的“有調亦有鑼”,使“眉戶清曲劇”形成了與單個曲調期截然不同的曲風,呈現出初具成熟的小戲狀態。
眉戶戲的形成應該說是民間說唱形式發展起來的,但也不排除社火活動在其形成中的助推作用。“分角色”“化妝演唱”“加入表演”,此時的眉戶已經做好了登上舞臺一展風采的前情準備。
眉戶從地攤藝術搬上舞臺,可以說是其成為劇種的顯性標志。但對于眉戶戲何時搬上舞臺卻一直沒有明確的說法。據《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載:“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在陜西,有人把唱曲與民間秧歌、社火相結合,以小調曲子為主,發展成為小戲,逐步由地攤子搬上舞臺。這一時期,在晉南也有地攤子藝人吳小寶、王喜榮、王勝才等開始把眉戶搬上戲臺演出。同治、光緒年間涌現出一批藝人和一些專業戲班……”《中國戲曲志·山西卷》載:“據老藝人李卜、段全忠、楊海生等聽父輩相傳:清道光年間,解州社東村段耀功與河南靈寶民間藝人組織了第一個眉戶家戲班(即業余班社),逢年過節,在本村廟臺演出,亦曾應邀到解州(今屬山西運城解州鎮)、虞鄉(今山西永濟市)等地演出,其劇目有《走南陽》《皇姑出家》《探情郎》等。《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西卷》記述:“其時眉戶業余班社演出多是亦地攤亦舞臺,演出劇目是反映民情鄉俗或家庭生活內容的小生、小旦、小丑三小戲。其舞臺伴奏類同蒲劇,亦分文場、武場。”以此內容推斷,眉戶戲大約于清中后期組建專業班社并登上舞臺,已具有了小戲標準的行當角色、劇目與情節等內容。更可發現,這種小戲深受當地大戲“蒲州梆子”的影響,并臨摹了其伴奏樂器、曲牌唱腔等形態,此類形態至今仍然是眉戶音樂的重要內容。不僅如此,眉戶戲在發展中還漸次吸收了蒲州梆子的念白、鑼鼓經,甚至吸納有梆子中典型板腔體結構組織,建立“板式”唱腔,彌填了曲牌體溫婉柔美之曲風。這些都得益于清晚期光緒年間“風攪雪”式的同臺演出之勢。
清光緒初年,眉戶民間自樂班(后亦稱“同樂會”)登臺演唱已十分普遍,其多與蒲州梆子同臺(民間稱之為“風攪雪”)。在同臺演出過程中,它大量吸收和借鑒了蒲州梆子的鑼鼓經、絲弦、鑼鼓曲牌及[滾白][間板]等板腔體唱腔,并學習了蒲州梆子念白,使眉戶戲曲藝術不斷發展,劇目日益豐富,行當漸趨完善,表演技藝日臻成熟。
20世紀20年代伊始,眉戶戲在橫向攝取蒲州梆子養分的同時,促使其進入了發展的繁盛時期。此體現于職業戲班的涌現與藝人的輩出,由小生、小旦、小丑為主的三小戲,遂擴大為生、旦、凈、丑行當俱全的擔綱體制,更在表演上衍生了帽翅、靴子、鞭子、梢子、水袖等技藝,致使劇目隨之延展至本戲與連臺本戲。當然,隨著眉戶戲在坊間的風行,不僅傳播力不斷擴展,本體實力也在日漸增強。出現了著名鼓師尿罐、吉子林、王萬喜;三弦琴師閆士峰、張登娃;板胡琴師光景、石德茂、曲天喜等,大肆助益了眉戶戲的發揚。據傳當時所演劇目,可達200余本。
不幸的是,生不逢時。正在發展中的眉戶戲恰遇抗日戰爭。日軍入侵晉南屬地,迫使藝人生存受迫,班社被迫解體。藝人們為生計著想,再次“撿起了”發家時的地攤藝術,以賣唱為生。為接地氣,拉攏觀眾,藝人們所唱內容接近時下形勢,又采取小戲形式。它們部分加入抗日劇社,有的自編自唱,在廣場和戰地中宣傳抗日。這不僅在藝術和技藝上傳承了眉戶戲的發展,并助推抗日、大力宣傳時政;在很大程度上,與現實題材的結合與排演現代戲的傳統也從此拉開了帷幕。這一時期,大量的現代戲作品涌現并開始傳播,如晉綏七月劇社的《王德鎖減租》《十二把鐮刀》等劇目。它們代表了這一時期眉戶戲的基本風格與特點,來源于對現代生活的體驗與再創造,尤其適用于當時的演出形態。很顯然,眉戶現代戲的創作在演出中積累了大量的藝術手段和創作經驗,牽引著劇種不斷以此為創作路徑,在之后的十幾年間,兼收劇種的時興性與亦結合的精神,不間斷地創作出《虐待長工》(又名《算賬》)《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等,直至20世紀50年代初仍呈現出獨具魅力的藝術個性,其中的個體更成為眉戶劇種的代表作品。
作為在辛亥革命前后以京劇演出為主的現實生活類題材,時裝戲一度受到追捧,并影響到各類小戲中,當然也包括晉南周邊的小戲。晉南眉戶時裝戲,在當地又稱為“包手巾戲”,隨著時代的發展與進步,其吐故納新的強大包容力更彰顯了劇種傳承與創新的多面性。自20世紀30年代眉戶戲上演現代戲以來,晉南鄉村戶社的職業戲班和家庭戲班就開始重新恢復編演劇目。據張峰著《晉南眉戶音樂》中記述:“當時猗氏縣(今臨猗縣)156個農村業余劇團,即有130多個(多半是演時裝劇的)單純或大部分是采用眉戶形式出演。”大量的時裝劇的演出,產生了相對固定的本體格式特征,它與傳統戲某些特征既相似又相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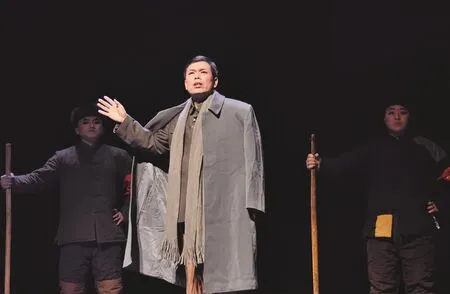
晉南眉戶劇《焦裕祿》劇照
戲曲是一個具有較強程式性的藝術品類,尤其對于曲體詞韻,更是遵從嚴謹的格律習慣,一以貫之而深入人心。時裝戲時代的眉戶戲,依照傳統習慣,嚴格遵守了曲牌體時期的運用法則,繼承了“風攪雪”演出中形成的蒲州梆子式既定性板腔體結構,采用[滾白][間板][流水]等板式,叫板、起板無一遺失,行腔風格繼而延續。不僅如此,它還吸納了蒲州梆子的伴奏模式,共用如鑼鼓經、嗩吶曲牌等,并在此基礎上衍生出幕間曲、器樂曲的少量創作曲調,使已經有一定群眾基礎的眉戶戲快速傳播,廣為流傳。當然,眉戶戲的流播推廣,除了需要受眾的接納,很大程度上更依賴于主體自身的突破與更新。最顯而易見的是原始形態的文武場樂器已難以滿足主客體群體的需求,它努力求索,突破傳統格局,構建了三弦(領奏)、板胡、笛子、二胡、鼓板、鐃鈸、馬鑼、梆子、小鑼的小型樂隊場面。
眉戶戲作為典型的曲牌體音樂體制,有自己相對固定的牌子規式,包含有絲弦曲牌《割韭菜》《西京牌子》、唱腔牌子《茉莉花》《戲秋千》,但容量較少,從蒲州梆子吸納后仍不過30余個,致使唱腔曲牌的運用仍需借鑒絲弦曲牌,進而促使曲牌結構生發出靈活多變之感。唱腔曲牌的繁雜運用又無意生成了一套唱腔牌子的程式性鑼鼓經,如《反片尾》《花音崗調》等。
眉戶在時裝戲時代,又稱“精溝子”戲。其不受傳統服飾的限制,沒有古裝穿戴的嚴苛要求,并在傳統戲上有某種程度的創新。念白的生活化、韻白與表演技藝的松弛化、曲調的更新等,使眉戶班社大肆開展并出現了繁花似錦的繁榮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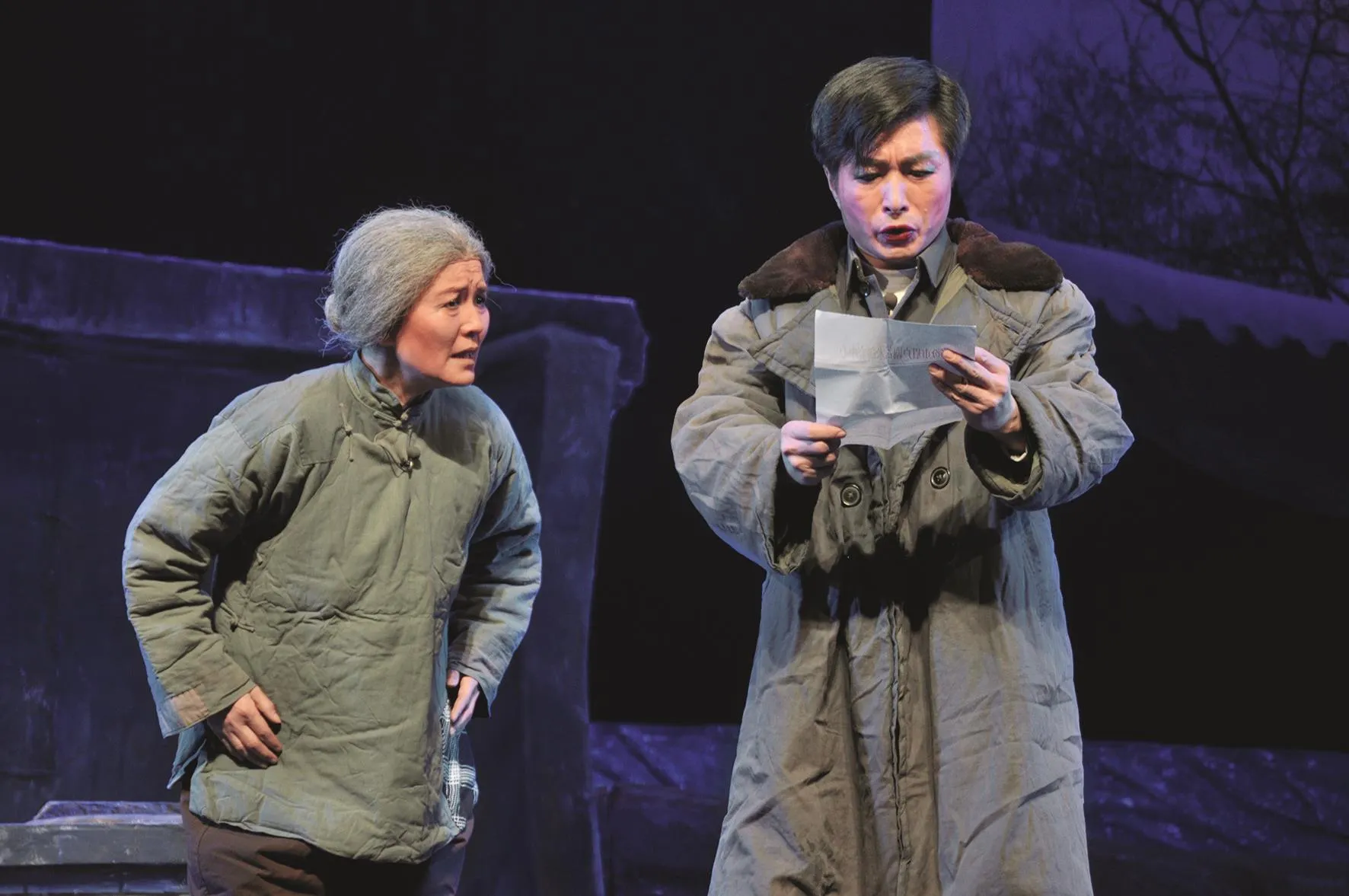
晉南眉戶劇《焦裕祿》劇照
晉南眉戶具有相對穩定的藝術形態與固定的演出模式,肇始于山西臨猗縣眉戶劇團與臨汾市眉戶劇團的出現。眉戶的發展在全國區域內雖分屬于不同分支,但作為活躍于全國前三位的眉戶院團來說,晉南地區兩個專業團體的成立無疑使晉南眉戶戲的獨特藝術風格與音樂格局逐漸條分縷析并成熟起來。兩個劇團同于1952年籌建,其中歷經變化,但始終是晉南眉戶戲曲的重要實踐和傳播者。自兩院團成立后,大規模的排演與廣范圍的流動傳播使得眉戶戲日漸成為晉南地區小戲的典型代表,獲得了直接而廣泛的關注。
專業劇團的建立,為晉南眉戶戲的音樂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兩個專業劇團也為眉戶戲的藝術傳承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晉南眉戶戲音樂發展的新變化,應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這一時期,全國的新音樂工作者紛紛加入戲曲劇團中。尤其在晉南眉戶專業劇團建立之后,新音樂工作者的加入更顯得尤為重要。晉南眉戶在早期的傳播和傳承中以口傳心授為主要方式,雖唱法、流派特點鮮明,但對傳承較為不利。因沒有專門的樂譜記錄,部分不常演唱的唱段已經失傳。從專業劇團建立之后,劇團開始普及文化、教識譜,對部分唱腔記譜,并在此基礎上培養了專職唱腔設計,改變傳統套腔方法,為劇目個別設計唱腔,建立了頗有規范的音樂創作體制。特別是以張峰等為代表的新音樂工作者的加入,充實了晉南眉戶的音樂隊伍,也使唱腔與器樂音樂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飛躍。
20世紀50年代前,“男角”占據了眉戶戲舞臺中心,為適應劇中人物需要,常以真假聲互換發音。50年代后,女演員的加入改變了較高的唱腔定調,由原A或bB調轉為F或G調,真假聲互換改為真聲演唱。60年代后,晉南眉戶現代戲大量增多,唱腔旋法迸發出了新的時尚音調,包括骨干音的轉移,變奏形式的增加,合唱、伴唱、氣氛音樂、襯樂等的運用,使眉戶音樂富于傳統又飽含新意。
1966年后,全國開始上演現代戲。為模仿現代戲交響樂隊的模式,樂隊先后添加了小號、長號、圓號、海笛、單簧管、雙簧管等樂器,建立了小型中西混合樂隊,設立專職指揮,專業化總譜配器由此肇始。在移植樣板戲的過程中,眉戶音樂借鑒了京劇【回龍】【緊打慢唱】等板式,與曲牌體唱腔交織應用,在豐富音樂的同時更能準確地表現劇情。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晉南眉戶在“化大革命革”后漸漸展露生機。他們排演了大量劇目,催生了一批專職戲劇人才,在對眉戶音樂的研究中,也歸結出了一定的理論成果。出版了《運用眉戶音樂反映現代生活的幾點嘗試》《眉戶音樂的繼承與革新》《是羽是商還是徵》,完成了《中國戲曲志·山西卷》《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西卷》的晉南眉戶的編纂工作。
21世紀以來,晉南眉戶戲的發展更是顯而易見,其整體向上的趨勢帶動了音樂的大幅度提高。近20年間,晉南眉戶在新創劇目中探索出了一套較為專業并程式性較強的音樂設計手法。它們利用傳統眉戶曲調,生出多種變體,衍變出一定的新曲牌。并在此基礎上,大量運用音樂主題創作方法,創作出了諸如《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父親》等作品,老曲牌也在新作品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和提升。
作品引發的效應使劇種受到了多方的關注,近些年晉南眉戶產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從曲牌的應用看晉南眉戶戲音樂創作的演變》《晉南眉戶戲唱腔音樂創作略析》《晉南眉戶戲之詞曲研究》等,都比較深入地剖析了晉南眉戶戲的音樂。一些專業院校的學生,在畢業論文中也談到《眉戶音樂特色研究》《曲牌體、板腔體兩種戲曲音樂對比研究》等,較為專業,也有一定深度。這些可透視出不同層次人員對晉南眉戶這種小戲音樂的關注。
晉南眉戶作為山西的小劇種,深受當地觀眾的喜愛。從初始的單曲小調,到如今的集曲成套;從地攤眉戶到搬上舞臺,到如今的精良制作,歷經輾轉但成就不斷。本文粗略記錄眉戶音樂的發展軌跡,記述其變革歷程,以使眉戶音樂的文字資料更加完善與更新。
注釋:
[1]《中國戲曲志·山西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戲曲志·山西卷》,中國ISBN中心,1995年版,第124頁。
[2]姚德利編著:《晉南眉戶音樂》,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版,第4頁。
[3]姜德華、曹希彬編:《傳統曲子匯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頁。
[4]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民族音樂概論》,人民音樂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