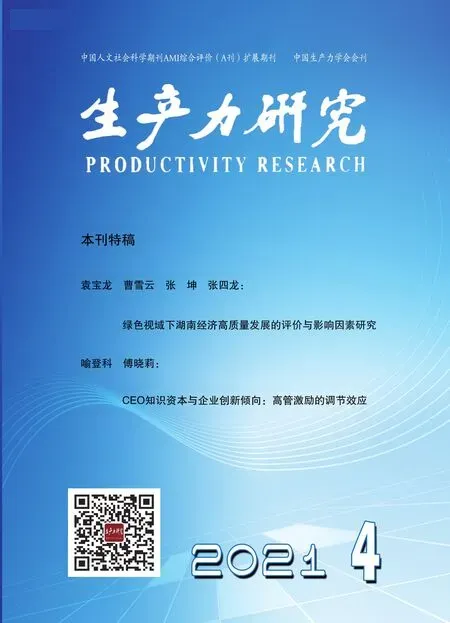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 貿易效應研究
(浙江工業大學 之江學院,浙江 紹興 312030)
一、引言
中國政府與企業的對外投資和對外貿易都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且規模不斷擴大、比重不斷上升。同一個地方的國家可能有著不同的進出口貿易經歷,同一個行業的人可能面對不同的貿易規則。科技不斷進步、世界大規模發展,目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也許遠未臻于完美,但正是因為如此這般緊密的聯系,才能在時代的洪流中改善各國經濟發展,促進世界和平、繁榮昌盛——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及實踐意義。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內外學者開始展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分析。通過研究,使中國政府更加明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及合作的相關影響因素,使中國更規范、快速地“走出去”,并且制定符合自己國家貿易現狀的貿易政策。
二、理論基礎
(一)蒙代爾——貿易替代理論
起初,由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HO 模型的基礎上修改了部分理論框架,對生產要素是否能隨意流動、要素稟賦的差異等條件進行了部分修正,在其著作《國際貿易與要素流動》中貿易替代理論有了良好的體現。
他認為現實社會中的替代效應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出口的替代,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參與貿易的一國可根據自己國家的產品優勢等最終確定自己進行貿易的產品及產量從而投入高回報率的另一國。東道國一旦擴大了此種產業的規模,就意味著抑制了母國的產業出口。第二,進口的替代,為了母國的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一般情況下母國會選擇將自己國家的資源密集型產品在要素豐富的資源國進行開發設廠、投入生產,這樣一來,就減少了對該要素的進口[1]。
(二)小島清——貿易互補理論
小島清(1978)《對外直接投資論》書中,注重國際分工——即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重要性,并提出對外直接投資應建立在一定的國際分工基礎之上進行。
20 世紀70 年代被小島清(1978)選取的日本及美國跨國企業投資、貿易數據樣本研究結果顯示:一國應在國外投資設廠、開發創造自己的劣勢產業或產品,然后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借助東道國的優秀的資源稟賦,縮短成本差距、擴大貿易規模、促進雙邊國際經濟與貿易合作。因此,小島清(1978)的想法與蒙代爾不同,他認為通過投資帶來的是貿易創造互補效應而不是貿易替代效應[2]。
三、中國“一帶一路”沿線OFDI 及貿易的現狀及特點分析
(一)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點
1.規模宏大,增速快。“一帶一路”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開辟了新的道路,自2008 年金融危機后,中國OFDI 數據一直以螺旋向上的趨勢增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表明,該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的流量在全球的規模分布十分廣闊,在跳躍了這十余年的期間內,數據資料飛速增長。正因為如此,才吸引了無數精英跨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投資。由此可見,中國跨國公司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
從投資存量角度分析,截止到2018 年,我國OFDI 存量達到了1 727.7 億美元,相比2002 年提高了66.3 倍,由此可見其規模之宏大。

圖1 2009—2018 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 存量(單位:億美元)
2.投資地區分布面廣。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可得,中國政府及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截止到2018 年為止,已覆蓋了全球188 個國家及地區,并且也有超過2.7 萬的中國企業在國外創立約4.3 萬家的公司。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額中,居于首位的是東南亞區域[3]。
3.投資方式創新。在投資模式下,海外投資模式的革新浮出水面,跨境電商作為主要投資手段逐漸取代了綠色領域投資。因為“一帶一路”的建設集中在能源和基礎設施上。投資的焦點逐漸擴大到生產、進出口貿易、網絡、旅游等方面。新經濟領域的投資比例大幅增加。2019 年,中國電商巨頭也紛紛對“一帶一路”的高端行業進行了投資,例如華為5G 對阿聯酋地區的投資建設等。
(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的現狀及特點
中國對整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呈平穩向上趨勢,它滿足了多個沿海國家經濟貿易發展的需求,幫助所有需要發展貿易的沿線國家,在時代的發展洪流中,起著很好的引導作用,同時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現狀及特點。
1.貿易規模不斷增加。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區域的貿易從2009—2018 年都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其中,東盟跨度最大,2009 年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額僅有2 154.08 億美元,在經歷了2015 年的下降之后,便逐年上升,直至達到了2018 年的5 000億美元,詳(見表1)。

表1 2009—2018 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貿易額 單位:億美元
2.貿易地區分布廣,但存在差異。2018 年同樣也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蓬勃成長的元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國家(地區)的貿易往來頻率都十分高,且分布面極廣,中國行業內的各大龍頭企業也都在積極地全球布局,展開更多新的規劃。其中亞洲大洋洲區占比最高,有56.8%;非洲及拉美地區、中亞地區相對靠后。
3.貿易商品結構廣泛。從2018 年出口商品種類來看,中國對外出口產品中,電話是最多的,占8.39%,其次是計算機,占3.21%。由此可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然成為中國運輸機械通信設備的重要場所及地區。出口額位列第三的是集成電路,出口額為226.3 億美元,占比2.92%。由此可見,中國出口的商品結構單一且集中,皆屬于電器、機器設備。
由進口商品結構分析,最主要商品是集成電路和石油產品,共32.43%。其中,礦物燃料的進口額是400.0 億美元,占比17.11%;電氣設備其次,占比15.31%;鍋爐、機器、機械在中國對內進口額中排名第三。
4.沿線國家的貿易交流不斷增多。從當代社會大數據可以看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對各個沿邊國家的參與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這表明沿線國家確實可以與中國進行更加細致的合作乃至分工。這無論對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是一件好事,不僅有利于增加產業附加值,還能提高這些國家在全球的地位。
正是在這樣的不斷發展中,中國才能不斷創新、節省供需雙方(即“一帶一路”沿線骨架)交易成本及瑣碎繁復的交易環節,打開并占據各個國家的目標市場優勢地位,整合及優化行業乃至全球的產業資源分配。在現代經濟發展下,改革已然成為主流,同時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不處于對立面的情況下,增加的不只是世界經濟,還是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緊密合作。這樣的緊密合作才是未來發展的正確途徑,也是中國在“一帶一路”基礎上對外貿易的一大現狀及特點。
四、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貿易效應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及數據說明
1.核心解釋變量。OFDI 對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效應的核心解釋變量如表2 所示。

表2 核心解釋變量
2.控制變量。結合前文所述影響因素,本文采用:(1)東道國實際GDP 代替東道國市場規模;(2)東道國勞動力總人數(LABOR)代替為自然資源稟賦;(3)東道國與中國首都(北京)的距離(DISTANCE)來衡量東道國與中國的便利化程度。
3.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09—2018 年,除波黑、黎巴嫩、新加坡、阿聯酋(勞動力人數數據不足)、黑山(GDP 數據不足)、格魯吉亞、老撾、越南、馬其頓、土耳其、捷克(進出口貿易額數據不足)外的48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面板數據的樣本。數據來源于聯合國Comtrade 數據庫,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統計年鑒》。
(二)模型構建
對于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的衡量指標和關鍵要素主要基于物理學的萬有引力定力的貿易引力模型,模型如式(1):

公式(1)中,表示實體之間的交互作用,A 為常數項;Ya與Yb分別表示了a 與b 之間的質量;Da,b表示兩個主體之間的摩擦;α1、α2、α3分別表示為對兩個主體之間交互作用的影響程度。
基于基礎的貿易引力模型,假設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a 代表國家;t 代表年份;Yat代表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貿易總額;OFDIFat與OFDISat分別代表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GDPat代表了東道國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規模;DSITANCEat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首都北京的距離;LABORat代表自然資源稟賦;εat代表隨機擾動項[4]。
(三)實證分析與檢驗
本文實證研究均采用Stata1 6.0 統計軟件完成。
1.相關性分析。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其回歸關系的必要前提,只有變量間的相關關系成立,其回歸關系才有可能成立。而相關性分析可清楚地反映變量之間是否有關系以及關系的精密程度。本研究采用Pearson 相關系數作為測量指標。相關系數的絕對值越大,說明相關性越強。
為了分析變量間兩兩的線性相關關系,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直接投資流量、直接投資存量、貿易國市場規模、距離、勞動力因素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
由表3 可以看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貿易進出口量的相關系數是正的,且相關系數在0.7 以上十分顯著,即直接投資流量、直接投資存量和進出口總額同方向變動且顯著相關,直接投資流量、直接投資存量增加,進出口總額增加;反之,則進出口總額減少。且GDP、勞動力人數和進出口的相關系數也是正的,說明貿易國GDP、勞動力因素和進出口總額同樣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表3 相關性分析
而距離與進出口總額的相關性系數為負值,說明“一帶一路”沿線貿易國與中國的距離和進出口總額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2.面板模型識別——Hausman 檢驗。Hausman 檢驗——原假設為隨機效應模型,為驗證顯變量與不可觀測變量是否相關。由檢驗得兩者均為固定效應模型,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Hausman 檢驗
3.直接投資貿易效應回歸分析。回歸分析利用回歸系數確認兩者的顯著性及線性關系,以印證假設理論模型[5]。
對于“一帶一路”沿線48 個樣本國家,采用最小二乘估計法對模型(2)與模型(3)進行回歸分析,探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回歸分析
回歸結果可得,模型(2)和模型(3)的擬合度R2分別為0.633、0.222,擬合效果較好。
對于核心解釋變量OFDIF、OFDIS 的回歸顯示,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直接投資流量及存量與出口總額同方向變動,對外直接投資類流量增加,則出口額也增加;反之亦然。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每增加1 萬美元的投資流量,會增加30 253.292美元的出口貿易額,45 150.272 美元的進口貿易額;而每增加1 萬美元的存量,會增加13 815.422 美元的出口貿易出口額,11 691.673 美元的進口貿易額。由此可見,存量對進出口貿易效應的影響更大,其原因可能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值較小,輕微的變動不能對貿易效應產生很大的影響。
GDP 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東道國市場規模增加1 萬美元,而進口效應與出口效應都會增加。而勞動力人數在出口效應方面1%的基準上顯著為正,進口效應在5%的基準上為正,由此可見勞動力資源對出口的貿易效應大于進口的貿易效應。
但在距離方面,雖距離與進出口額有顯著的相關性,LNDISTANCE 的系數為負,但并未顯示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的進出口效應有顯著的負影響,出現這樣的原因可能是各國綜合國力、貿易量大小并不為與中國的距離遠近而改變[6]。
五、政策建議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上,中國不斷擴大自身對外投資及貿易合作。同一個地方的國家可能有著不同的進出口貿易經歷,同一個行業的人可能面對不同的貿易規則。通過闡述上文現狀及數據分析后,借助理論知識,深入探討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并對此提出建議。
(一)建立良好的雙邊合作關系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目前處于一個比較快速、穩定的發展階段,這樣的發展相較于傳統貿易,交流的規范性和先決性還不夠完善。只有參與貿易的一國與中國保持良好的貿易關系,才會建議一個穩定的市場[7]。一旦兩國關系惡化,在政治角度上,就會帶來很多問題及危險。因此政府能否處理好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友好關系、保持政策的穩定性,直接決定著我國能否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二)把握政府政策,增加貿易交流
目前就中國對外投資形式來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占大頭。因此中國應該在保持原有傳統貿易合作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政府出臺的政策創建一個貿易平衡系統,在合作中獲得更多發言權[8]。
因此加強政策方面的引導,鼓勵企業“走出去”,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量越大則進出口貿易額度越多,因此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有利于我國貿易的發展。因而政府應出臺優惠政策,鼓勵我國企業對沿線國家的投資,通過簡化通關手續等方式,減少中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路上的困難,幫助企業擴大投資規模,更好地發揮貿易創造效應。越是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越是做得好越是能從眾多合作國家中脫穎而出[9]。
(三)加強對重點國家及區域的貿易合作
“一帶一路”倡議路線廣闊,因此,涉及的國家無論是距離、對外出口商品、政府政策等都是不相同的,因此中國應按照這些不同因地制宜,制定符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策略,才能更有效地促進雙邊貿易發展。
東南亞地區,應加強貿易合作,從而實現更好的互利共贏;中亞地區,中國應多極投資資源類產品;南亞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中國企業應多投資設廠;西亞北非地區,中國應與其多進行技術資源合作,如提供相應石油燃氣提取技術支持等;中東歐地區,中國應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多多投資航空、航天領域;對于獨聯體地區,中國投資重心大多集中在俄羅斯,俄羅斯作為我國最重要的經貿合作伙伴之一,中國要牢牢抓住機遇,加強合作[10]。
(四)抓住勞動力資源等優勢,理性投資
目前國內的上市公司遍地開花,大批的貿易公司涌現出來。下面是對中國企業發展的一些建議:勞動力資源與市場規模都對進出口貿易效應有促進效應,因此中國企業應牢牢抓住這樣的優勢。中國企業只有存在企業自身的競爭優勢,才能在對外直接投資機遇來臨時,準確地抓住時機,進行貿易交流與合作。中國企業如果沒有一定的實力,就失去了同其他企業競爭的機會。因此,只有在國際市場上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樹立讓人信服的品牌形象,才可在“一帶一路”的政策紅利下抓住機遇,獲得收益[11]。
(五)提高風險應對能力
“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國家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不僅表現在自然條件上,例如距離、自然資源儲存量,更表現在人文環境中,例如少數國家還存在投資環境不安全的情況,這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部分問題。因此,中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之前應了解東道國的整體貿易環境,如宗教信仰、自然資源等,做好相應的突發情況的防患措施。這樣做的好處是:一方面中國企業可以對貿易國家事無巨細地了解到位,還可以提前制定一些應急方案避免發生嚴重的損失;另一方面,中國企業還可以與其他組織根據此種情況進行深入交流,通過其他渠道做到自己的風險最小化。
(六)實施策略性投資
不同的企業類型在與外商合作時應有著不同投資重點及投資方案。對于市場尋求型的企業而言,應把投資重點放在中東歐、東盟等擁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可將自身的生產技術、設備、勞動力等提供給東道國,擴大貿易交流,使雙方都能從中獲利。而對于資源尋求型企業,中國企業可以把投資重點放在中東、蒙古及中亞這些盛產石油、礦產品的地區,只有母國的技術支持及生產設備,就可以同時滿足中國國內的資源需求和東道國的開發需求。
對于效率尋求型企業,中國企業可以把投資重點從勞動密集型產業上轉移,中國勞動力的福利已經不復存在,不如借用諸如東盟、中亞、南亞的勞動力人口,這樣既可以減少投資成本,還有利于提高自身國際市場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