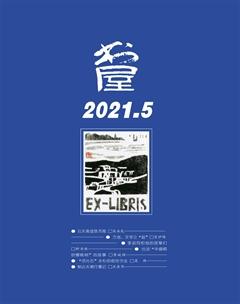黃河邊上的愛情
黃全彥
1839年夏天,詩人龔自珍乘坐一舟渡過黃河,打算回到家鄉,過一種平平常常的日子。這次回去,可能再也不會回到北方,同時也意味著,自己的平生抱負都將消散。回首這十幾年的京華生涯,詩人無限感慨,提筆寫下一詩:
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
誰分蒼涼歸棹后,萬千哀樂集今朝。
這是一首自傷之詩,詩很好地抒發了龔自珍內心的寂寞、憂傷和痛苦。龔自珍一生自視甚高,他年少得志,對自己不可一世的才略和鵬程萬里的抱負充滿了自信。龔自珍尤愛用劍、簫兩種意象來比喻自己生平懷抱,“劍”指的是胸懷遠大的功名事業,“簫”則是狎昵溫柔的兒女懷抱。他少年時代仗劍入京,夢想一展高才。只是在那樣一個黑云壓城萬馬齊喑的時代,崢嶸突兀的龔自珍同周遭一切是格格不入,要想嶄露頭角一鳴驚人,進而建立一番功業真是太難。十余年中間,歷經與外界無數次碰壁和內心千百次交戰之后,此時的龔自珍早已收斂了那份少年的鋒芒畢露和意氣風發。“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橫,淚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既負簫心亦負劍名,曲中就滿含酸楚寫了這種兩頭踏空的無助與哀苦。面對這功業無成的痛苦和自我內心的沖突,龔自珍甚至用逃禪的方式來消解,他深受佛教天臺宗影響,追求靜心息性的癡定入定來化解心中這劇烈的水火之沖,“心藥心靈總心痛,寓言決欲就燈燒”,意欲借助佛教的力量,將這所有苦痛一并燒卻。
在這般心境之下,渡河還家,回想這十幾年覓食京城的風塵奔走,大好光陰就這般隨手擲去,怎能夠定下心來?萬千哀樂不由自主涌上心頭,一抹蒼涼繚繞心間、盤旋不去。
六月間,船到清江浦,朋友在亭樓設宴款待詩人。歌舞助興,一個叫靈簫的歌伎氣質如蘭,引起了詩人的格外矚目。簫是龔自珍平生最愛歌詠之物,他一直認為簫有一種難以言說恰與意合的靈氣。此時他和靈簫的這段相會,似乎有著冥冥當中意味。靈簫明媚艷麗,更兼有慧心靈氣。兩人一見傾心,龔自珍那沉睡已久的心靈仿佛一下也被喚醒,他心潮起伏,為靈簫賦詩一首:“天花拂袂著難消,始愧聲聞力未超。青史他年煩點染,定公四紀遇靈簫。”龔自珍號“定庵”,所以自稱“定公”,這首詩寫的就是龔自珍遇上靈簫的怦然心動。據《維摩詰經》載,天女散花,將花撒在諸菩薩和大弟子身上,當花瓣落在菩薩身上,紛紛墜地。而花瓣落在大弟子身上,卻粘住不動。天女說,對那些超脫世情四大皆空的人,花瓣無法附著其身,而對那些積習未消的人,花瓣就會附著在他的身上。龔自珍詩中用這個佛教典故,說自己盡管學佛修禪多年,但最終仍沒有擺脫塵緣,一旦遇上靈簫這樣一個紅顏女子,便如天花著衣,難以忘情了。
龔自珍對靈簫是傾注了真心真情的,這次兩人心靈的碰撞,蕩起了他心底深處絲絲漣漪,久久不息。“功高拜將成仙外,才盡回腸蕩氣中。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這是怎樣一種豁然開朗喜悅無限之情,劍氣簫心,眼看又要重新回來。
九月間,詩人又專程來到清江浦,再度探看靈簫。為此詩人一連寫了二十七首《囈詞》敘說這段愛情,愜意之情仿佛夢囈,盡是溫馨和喜悅。
龔自珍走南闖北,閱人無數,獨獨靈簫喚醒了他心中沉睡的簫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和其他任何女子不一樣的是,靈簫極具英姿颯爽之氣,頗有一種巾幗不讓須眉的氣度,在這般簫心吹拂之下,終于也喚回了他胸中那消散已久的“劍氣”。且看詩人的歌吟:
風云材略已消磨,甘隸妝臺伺眼波。
為恐劉郎英氣盡,卷簾梳洗望黃河。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象征,龔自珍對黃河別有一種特殊情感,他早年于黃河的治理多有留意,寫有不少有關治河的上書。黃河自金明昌五年(1194)決口后,分兩支出海,明弘治后全部南流,經江蘇奪淮河故道出海,至清咸豐元年再度北徙。北徙以前,黃河流經清江浦之北與運河交匯,因此在清江浦登樓北望,便可看到黃河。靈簫掀開簾子,眺望黃河,希望的是詩人能夠重現昔日那份英氣。
古往今來,身具英氣者女子可謂不少,但其中的英武大氣,絕難有超越“卷簾梳洗望黃河”的豪壯。兼具劍氣與簫心的靈簫,仿佛是紅粉中的另一個龔自珍,滿足了詩人的所有心愿。只是這樣的愛情對手,鋒芒確實太過逼人。備嘗人生艱難辛酸,如今進入恬淡自足的龔自珍,雖有一時少年狂氣的釋放,但實際是再也不能重拾當年那份劍氣了。簫劍一體,劍氣既已不在,簫心自然也就擱置一邊。他和靈簫的這段愛情,仿佛一場暴雨落入深井,在一陣心潮澎湃之后,詩人終于又回到古井無波當中。在一個烏云蔽空的凌晨,詩人和靈簫連一句道別的話也沒有,徑自乘舟,離開了這一溫柔鄉。面對無邊江流,將最后一縷劍氣簫心都沒入茫茫云水當中,不可追逐。
十月,船到順河集,詩人已經靜心息欲,寫詩一首寄予靈簫敘說心意:“閱歷天花悟后身,為誰出定亦前因。一燈古店齋心坐,不似云屏夢里人。”和靈簫的這段愛情,自己那本已入定的心再次出定,這也許都是前世今生的一場無果因緣。如今孤身一人寄住旅舍,一燈熒然,仿佛形影對答,詩人捫心自問,今日之我已不復前日之我,再不是云屏之畔美人之夢的心上之人了。他的心終于又重新入定。
只是這電光火石的感情,如此耀眼奪目,真的就這般相忘江湖了嗎?真的就那么“心心寂滅,自然流入大涅槃海”了嗎?
顯然不是。兩個月后,當詩人再度來到清江浦,禁不住悄悄打聽靈簫下落。聽人說,靈簫已經回到蘇州老家,從此閉門謝客,再不出入風月之場。靈簫此舉,顯然更多出于心碎和無奈。其實這種酸楚和傷懷,內心多有愧疚的龔自珍何曾沒有?此刻的他,寫下一詩,描畫的正是這無盡的酸苦:“明知此浦定重過,其奈尊前百感何?亦是今生未曾有,滿襟清淚渡黃河。”
當年揭開畫簾眼眺黃河,是那樣的雄姿英發,顧盼生輝。如今卻是清淚滿襟,黯然神傷,默默渡過河去。這滿溢的河水,載著的盡是哀愁,無邊無際,充塞天地。
凄美愛情,恰如這般,不是捧在掌心,而是掛在云端;不是喜心翻倒,而是憂傷如河。讓當事人遺恨一世,亦讓后來者徘徊千古。即如詩人自己所言:“美人沉沉,山川滿心。落月逝矣,如之何勿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