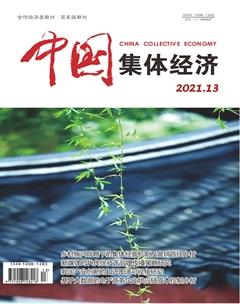國有企業的制度性反思
李澤宇
摘要:隨著國有企業改革逐漸深化,關于國有企業性質的討論對于確定國企改革的目標與路徑有著重要意義。文章首先以企業的一般性質入手,討論“合約理論”及其衍生的企業性質理論,旨在理解國有企業性質的一般與特殊。然后對于已有的國有企業解釋框架進行梳理,并結合當下國有企業改革的最新動態,基于合約理論提出對于國有企業性質的最新解釋。由于行為主體“多重目標”的存在,當下國有企業的性質是不完全的市場合約性組織。
關鍵詞:企業性質;國有企業改革;多重目標
國有企業的性質始終是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無法回避的問題。什么是國有企業?與一般意義上的現代企業有什么本質性的異同?這些問題左右著國有企業為何經營、如何經營,影響著國有企業的最終目標,進而決定了國有企業實現目標的路徑與方向,這也就是當下國有企業改革深入的路徑與方向。
國有企業首先是企業,無論其性質如何特殊,將其置于一般性的現代企業制度之中進行考察都是必要的。與一般意義上的企業進行比較研究有助于同時把握國有企業的本源性質與特殊性質,即在企業的一般性特質之外,國有企業因何而成為一個特殊的存在。其次,對于國有企業性質的解讀方向仍無定論,無論是以新古典范式為坐標,還是以反新古典的企業理論為基礎,不同的理論取向間難以達成對國有企業的一致性看法,因而尋求新的解釋路徑可能在理解國有企業性質的問題上產生新的突破口。最后,對于國有企業性質的理解必須回歸實際問題,在當前國有企業改革深入的環境下,國有企業的目標到底應該是什么,繼續改革的后續措施應當是什么。本文將從以上三部分展開,分別討論一般性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的特殊性質及國企的目標修正和改革深入的方向。
一、企業:一組合約關系的聯結
企業理論始于科斯,他認為企業是市場中節省交易成本的組織,“通過建立企業而盈利的重要理由是利用價格機制要花費成本”,企業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市場的替代。張五常對科斯的觀點進行了發展,他進一步認為企業的性質在于用要素市場代替中間產品市場,進而提高交易效率,同時企業可以被理解為一組由各種資源所有者所締結的合約,這也是企業合約理論的發端。在這里,資源所有者可以自由選擇合約的競爭性市場經濟是不同經濟組織與生產交換方式共同存在的基礎,權利(產權)的清楚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資源所有者可以根據自身判斷,將自己擁有的資源直接投入生產,并將產品投入市場出售,以換取收入;或是形成合約將資源的使用權部分讓渡給代理人,并在保有所有權的同時換取收入。當資源擁有者依照后一種方式來投入要素,“企業家或代理人依據合約賦予的有限的要素使用權直接指揮生產,而不是根據瞬時的價格變化來組織生產并向市場出售產品”,企業就產生了。
那么資源所有者為何要轉讓資源而不選擇直接進入市場進行生產呢,科斯認為利用價格機制進行生產需要花費交易成本,而在組織內部生產則可以有效降低這種成本。與此同時,組織內部的協調也會產生組織成本,組織越龐大越復雜,產生的組織內交易成本也越多。“當企業節約的交易費用在邊際上與其支付的組織費用相等的時候,企業的邊界就確定了”。而資源所有者在進行交易費用與組織費用的比較時,必須在一個可以自由進行合約交易的競爭性市場環境中進行決策。這是因為資源所有者也有做出錯誤決策的可能,而糾錯機制就要依靠合約市場對于不同企業的優勝劣汰而實現,最終保證留下的企業都更加具有競爭優勢,資源因而找到流動的方向。而當私有產權被完全抹除,完全的公有制經濟下,市場對合約的生存檢驗沒有施行的根基,糾錯機制無法實現,相對價格配置資源的機制被歪曲,效率損失也就更容易發生。因而競爭性的合約市場是這一理論體系得以實現的重要一環。
現代企業的另一個特征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由于二者主體不一致,導致利益不一致,對經營成果承擔的責任也不對等,加上客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了委托—代理問題的產生。林毅夫認為,能夠為此提供解決方案的仍然是市場——在完善的市場中,利潤得以成為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指標”,而這種充分信息又催生了職業經理人市場,該市場使得經營權持有人間通過經營績效形成競爭,從而降低了兩權分離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此外,用于事前監督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也被用來解決這種信息不對稱的狀況。
科斯對企業的界定難免有模糊和疏漏之處。張五常認為,科斯所理解的企業是市場的替代存在偏差,更確切的說,企業的性質應當在于以要素市場取代中間產品市場,代理人根據合約所賦予的有限要素使用權直接進行生產。謝德仁以要素交易合約入手,將合約劃分為四個部分,包括要素使用權交易的不完備合約、資產與服務交易合約、人力資產與非人力資產具體配置合約及組織資本與組織資產創造和使用的隱性合約,這四類合約包含了企業的交易功能與生產功能,進而將企業定義為“市場中由要素所有者簽訂的一組不完備的要素使用權交易合約的履行過程”。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對合約理論下企業性質解讀的改進與補充。
二、國有企業改革歷程中的爭論與探索
隨著國有企業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具備的特性的改變,對于國有企業的討論框架也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的不斷邁進而變化。
“兩權分離”框架,即“所有權經營權分離”,是曾經較為流行的分析框架。兩權分離并非國有企業獨有,而相反是國有企業模仿一般性私有產權企業的一次制度嘗試。國有企業的兩權分離是指企業和政府一同分享決策經營權,其基礎仍是公有制。國有企業的兩權分離使得政府和企業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趨于一致,降低了二者由于利益沖突而導致的交易費用,但并未解決國有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面臨的最重要的監督與約束問題,制度實行的方向與目標產生了錯配,因而也就難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委托—代理”框架也同樣可以用于分析國有企業。關于國有企業的最終委托人身份仍有爭論,姑且將其視為國家政府或是全體人民。由于公有化程度很高,最終委托人與最終代理人之間的環節多,委托—代理鏈很長,使得大量交易成本在委托代理過程中被耗散,國有企業的效率因而受到較大損失。然而無論企業采取何種所有制形式,都無法避免委托—代理問題的存在,對于許多大型企業而言,委托—代理鏈同樣很長,這并非國有企業面臨的獨有的難題。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不以委托—代理鏈的長短而發生變化。因而采用這一框架分析國有企業同樣存在漏洞。
“法權與事實產權不一致”框架拋棄了“兩權分離”和“委托—代理”的思路,對于國有企業進行了新的理解。該觀點認為,在法權上否認個人擁有生產性資源產權的基礎上,公有制企業的性質是非市場合約性的組織;但由于人力資本在事實上仍然屬于個人,公有制企業于是采用國家租金激勵機制代替市場交易和利潤激勵機制,以充分調動人力資本。因而該框架將公有制企業的市場化改革最終指向了承認和界定個人產權的改革,并由此確立了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化改革路徑。該框架能夠清晰地解釋市場化改革前公有制企業的性質,但也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在經歷了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今天,個人產權在國有企業中的界定的確得到了革新,但“公共領域”依然存在,“福利攫取”也并未停止,法權與事實產權的不一致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變。那么如何使法權與實施產權相一致?若該分析框架最終指向所有制問題,那么接下來的國企改革應走向何處?
“產業定位與產權特性相對稱”框架提供了一種新思路。該觀點認為,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是自然存在的兩種產權結構,并且對應于不同的產業定位有著各自不同的分工。私有產權作為市場運行的基礎,在競爭的環境中更加具有生命力,而公有產權的重要功能在于彌補市場缺陷和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而國有企業的本質恰恰是“反市場”的,與其將其視作一個企業,不如直接把國有企業看作是國家宏觀調控與政策的外化。因而,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在于產業定位與產權特性的嚴重錯配,將大量本該采用私有產權結構的產業定位于公有產權領域,進而提出解決方案,界定需要完全國有和不需要國有的企業,并分類進行改革,向兩極分別推進市場化和國有化進程。可以看到,該框架提出的方案最接近于當前普遍認識的國有企業深化改革路徑,但其實質還是主張產權的變革。關于如何界定適合國有的與適合市場化的企業,難以形成具體的可實施的標準,除一般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外,政府仍有比較大的操作空間,人為的不可控的因素仍然較大。而關于某種產業定位僅適配某種特定產權特性的論述直接否認了不同產權種類在同一市場中競爭的可能性,為不同產權在不同市場條件下的效率做了過于草率的結論。
“利益相關者”概念則將問題引向了企業的一般性質,作為一組市場合約的企業是相關參與人的契約的集合,因而各個契約方的共同利益最大化才是企業所要面對的目標。該概念對于理解科斯的企業性質定義很有幫助,并且發現了契約參與各方目標的差異性與多元性。但問題在于將個體的目標簡單加總上升為企業目標。在分散決策過程中,個體很少會考慮到整個企業的目標,并且個人的最大化選擇與整個企業在邊際量上相比很小。個人目標或行為的加總不應直接導出為企業目標,分層次討論或許更加合適。
“身份治理框架”則更偏離于經濟學理論體系之外。通過對單位制企業的考察,該框架歸納出我國大量企業獨有的單位化特征,具體可歸結于三個方面,一是單位化企業的身份屬性決定其可獲取的社會與政治資源;二是近乎無限的長期勞動合約和由其帶來的資源的低流動性,這使得員工對組織產生高度依賴性;三是家庭被“嵌入在”單位制企業之中。科斯的企業模型將一般員工的目標函數抽象為單一的工資待遇,忽略了升遷、地位、福利等實際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想要借此理解現代企業制度就會十分困難。“而身份治理框架”指出了多重現實因素對于員工目標的重要影響,塑造了國有企業的社會性方面。然而“身份治理”的解釋并不能推翻合約理論,即使將委托—代理關系視作是身份賦予與履行身份的過程,也忽略了“身份”的賦予其前提是合約的訂立。企業的市場合約性本質仍然是理解國有企業必要角度,并且各種社會性因素在國有企業形成與運作過程中的機制仍有待進一步挖掘。
三、合約過程上游的關鍵偏差:多重目標
基于合約理論框架理解國有企業性質仍然可行,國有企業作為“企業”的一般性仍然得以保留。理解的關鍵在于微觀主體的“多重目標”。
在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后,國有企業的合約性質是部分存在的。這個“部分存在”可以被分解為兩層含義,一是要素所有者對于要素使用權的交易合約是不完備的,它還應當包括在企業中和市場中進行的一系列履約過程;二是訂立合約的各方存在著多重目標,而這些目標中包含著相當程度的社會性因素,因而使得合約的選擇過程存在著社會性偏差。
對于員工、要素提供者這一身份而言,由于多重目標存在,使得其需求并非僅僅由收入決定,而是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包括福利、風險、社會地位、社會關系網絡等。資源提供者對于是否進入企業、進入何種企業的考量,或者說對合約的選擇,是基于一組相關因素的整體水平而進行的。在對現實的企業進行分析時,將資源提供者的目標設置為收入最大化的單一變量是對行為人的過度簡化,如此得到的分析結果可能與現實狀況有著較大的偏離。
在國有企業中,對于委托人力資本的員工而言,國有企業能夠提供更加穩定和長期的合同關系及更好的福利與配套生活設施(這在單位制企業中體現得尤為充分),這對于普遍而言更加厭惡風險的員工而言就意味著更低的失業和收入流斷裂風險;國有企業“政企不分、企社不分”的特征雖然隨著其市場化改革逐漸消退,但依然能帶給內部人員更有能量的社會關系網絡,進而使得員工有更多提升社會資本的機會,這背后可追溯至費孝通關于中國社會“家國同構”的分析;國有企業也能夠提供在大致相同的收入水平下相比于一般企業有更高的職業聲望和社會地位,這通常是由習俗文化等因素決定的,而背后也與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的歷史地位、福利、風險的總體考慮有關。而對于提供非人力資本的委托人而言,上述因素組合依然存在,但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國有企業的公有制性質決定了其背后是由整個國家,或者說國家政府進行擔保,這使得國有企業對于風險的抵抗程度是其他非公有制企業所難以企及的,自然也就意味著諸如國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和股份制國企等后改革時代國企資方的極低風險;國有企業所構筑的更緊密的政企關系同時也會使得資方考慮權衡此次委托所能帶來的社會資本。這也就解釋了即使在脫離了計劃經濟環境,在市場經濟中的國有企業為何仍能吸引大量的資本和人力資源。但在并非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即使資源所有者擁有充分選擇締結合約對象的權利,并據此選擇了進入國有企業,也可能并不意味著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效率,或者說無法肯定國有企業擁有著更優的產權結構和制度安排。
而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其行為和決策主體并不單一,而且對于其所面對的不同的目標,不同決策主體之間的利益也并不一致。相比于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的目標已不再是單一的完成國家計劃任務,部分國有企業經過市場化改革之后,追逐利潤也同樣成為其目標的一部分。而在現實環境中,國有企業的目標甚至還包括員工利益以及社會責任等。在多重目標的國有企業中,名義上的最高委托人是國家,國家擁有著國有企業的最高決策權,但企業的實際管理者也擁有著部分企業決策權,可以在指令實施層面部分影響企業行動。二者擁有不相同的目標側重,甚至可能由此產生利益沖突:國家以國家計劃和經濟政策為主要目標,將國企變成政策的外化實體,而管理層等高層代理人則要面臨國家計劃、個人利益最大化及企業盈利等的多重目標權衡。客觀存在的監督和激勵成本又使得代理人攫取公共利益和偷懶的機會主義行為機會上升,造成國有企業目標的不明晰和對目標的偏移。有學者據此提出,國有企業的目標應分類看待,競爭性國有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優先于社會福利最大化目標,而非競爭性國有企業的社會利益最大化目標應當優先于利潤最大化目標。這種觀點承認了國有企業目標的多重性,但仍然沒有充分考慮社會因素對于國有企業目標的重要影響。在對企業行為主體進行分析后不難發現,行為主體的內在不一致使得國有企業目標不能簡單地以“競爭—非競爭”的行業二分法來劃分,而應將其理解為決策主體間由于目標不一致而經過一個博弈過程產生的結果,目標決策部分取決于國家強制的行政命令,部分由市場篩選,其結果差異就體現在競爭程度不同、對于國家統籌計劃重要性不同的各個行業之中。
四、結語
經過一系列漸進式的制度重構與市場化改革,國有企業正從計劃經濟時代的“非市場合約性組織”,向以市場合約性為本質特征的一般意義上的企業靠攏,具體表現為以下兩點。首先,要素所有者能夠部分自由地選擇是否進入、進入哪家國有企業——人力資本所有者可以通過市場途徑受雇于國有企業,國家指派不再是為國有企業調用人力資本的唯一路徑;非人力資本要素所有者則可以通過市場化導向下進行了新的制度設計的國有企業進行委托。其次,國有企業除完成國家計劃外,擁有了更多元化的經營目標,并且在部分行業中,國有企業加入了市場競爭,從而能夠調用相對價格體系對于其經營狀況進行評估與糾錯。然而,當下國有企業的市場合約性仍然是不完全的,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要素所有者的合約選擇受到其個人多重目標的干擾,而多重目標背后的社會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有企業相對于一般意義上的企業的特點決定的,這也就導致了價格機制難以完全準確地運作決策糾錯機制和對國有企業的效率水平的反映;其次,企業的目標并沒有完全拋棄國家指派的計劃任務,在部分市場化程度較低的行業中,完成國家計劃任務的目標仍然是國有企業最主要的目標。據此,本文認為當下國有企業的性質是不完全的市場合約性組織。
多重目標影響之下的國有企業不完全市場合約性的性質也就決定了,國有企業的目標不能是效益導向和國家利益導向的簡單二分法,而應根據行業和企業經營狀況的不同,權衡各種目標在企業綜合收益中的權重,對國企的目標和經營決策進行安排。同時,對于進入競爭性行業的國企來說,建立更加完善的競爭性外部環境,硬化預算約束,使得利潤能夠成為更加準確反映其經營狀況的指標。在這些前提之下,繼續探索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目標的國有企業的更優組織方式和制度模式,使得國有企業改革走得更深、更遠。
參考文獻:
[1]羅納德·哈里·科斯.企業的性質,論生產的制度結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1-24.
[2]CHEUNG S.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6(01):1-21.
[3]周其仁.公有制企業的性質[J].經濟研究,2020(11):3-12.
[4]羅納德·哈里·科斯.聯邦通信委員會,論生產的制度結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45-96.
[5]林毅夫,李周.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與國有企業改革方向[J].經濟研究,1997(03):30-34.
[6]謝德仁.企業的性質:要素使用權交易合約之履行過程[J].經濟研究,2002(04):84-91.
[7]楊燦明.產權特性與產業定位——關于國有企業的另一個分析框架[J].經濟研究,2001(09):53-59.
[8]崔之元.美國二十九州公司法變革的理論背景[J].經濟研究,1996(04):35-40.
[9]周業安,高嶺.國有企業的制度再造——觀點反思和邏輯重構[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04):38-47.
[10]李新春.單位化企業的經濟性質[J].經濟研究,2001(07):35-43.
(作者單位:云南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