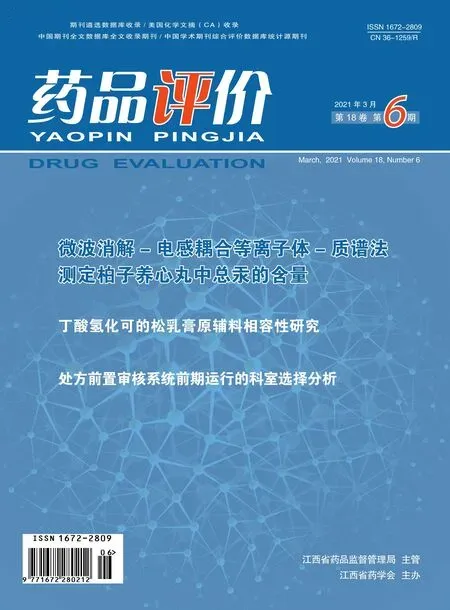新生兒敗血癥500 例病原菌分布及耐藥狀況分析
張倩
蘇州市立醫(yī)院,江蘇 蘇州 215008
新生兒敗血癥屬于新生兒時期發(fā)生的感染性疾病,對新生兒的生命安全威脅較大[1]。病原體侵入到新生兒血液中不斷生長,可造成全身性炎癥反應,也就是敗血癥的主要癥狀[2]。新生兒敗血癥一般情況下缺少特異性的臨床表現,同時病原菌的分布較為廣泛[3]。基于此,新生兒敗血癥的早期診斷及治療難度較高,需要探尋有效的診斷參考[4]。本次研究中,以500 例疑診為敗血癥的新生兒為例,開展病原菌分布及耐藥情況的分析。
1 材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對2016 年1 月至2018 年6 月期間蘇州市立醫(yī)院接診的500 例疑診為敗血癥的新生兒血培養(yǎng)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500 例新生兒中:男320 例,女180 例,日齡(15.26±3.05)d,日齡范圍1~27 d;早產兒120例,足月兒380 例。體質量(3 584.15±50.28)g,體質量范圍2 305 g~4 658 g。
1.2 方法
所有新生兒均在無菌條件下采集外周靜脈血2 mL,分別注入血培養(yǎng)需氧瓶和厭氧瓶中,在半小時內送往微生物室置入Bact/ALERT 3D 全自動血培養(yǎng)儀。培養(yǎng)18 h~24 h 后分離出單個菌落應用微生物全自動鑒定與藥敏分析儀分析鑒定病原菌種類與耐藥性。
1.3 統(tǒng)計學方法
本次研究當中的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 17.0 統(tǒng)計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采用表示,以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表示,以χ2檢驗,P<0.05 表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病原菌分布情況
本組500 例新生兒中,敗血癥血培養(yǎng)陽性70 例,分離病原菌70 株。其中革蘭陽性菌42 株,所占比例60.00%,革蘭陰性菌28 株,所占比例40.00%;革蘭陽性菌中表皮葡萄球菌7 株,所占比例16.67%,溶血葡萄球菌5 株,所占比例11.90%,金黃色葡萄球菌1 株,所占比例2.38%,革蘭陰性菌中大腸埃希菌檢出率最高為6 株,所占比重21.43%,其次為肺炎克雷伯菌4 株,所占比重14.29%。早發(fā)型新生兒中表皮葡萄球菌與大腸埃希菌檢出率最高,其次為肺炎克雷伯菌。
2.2 新生兒敗血癥耐藥性分析
選取檢出率較高的大腸埃希菌與肺炎克雷伯菌以及表皮葡萄球菌進行耐藥性分析,結果如表1 所示,大腸埃希菌與肺炎克雷伯菌對氨芐西林的耐藥性最高,均為100.00%,表皮葡萄球菌對氨芐西林的耐藥性為85.71%,大腸埃希菌與肺炎克雷伯菌對復方磺胺甲唑的耐藥性分別為83.33%與75.00%,對慶大霉素的耐藥性也超過了50.00%。

表1 新生兒敗血癥耐藥性分析結果[例(%)]
3 討論
本研究按照革蘭染色法把病原菌分為革蘭陽性菌和革蘭陰性菌。沒有按照需氧和厭氧分類,是因為大多數病原菌系兼性厭氧菌,專性需氧菌和專性厭氧菌較少見。關于新生兒厭氧菌敗血癥,目前認為多數為菌血癥或系污染,一般多為自限性,致命的不多。如僅血培養(yǎng)分離出厭氧菌而無任何臨床表現者只能稱為菌血癥,而不是敗血癥。
新生兒敗血癥是一種死亡率較高的疾病,其中易感新生兒為低體質量兒與早產兒[4-5]。新生兒受到感染的關鍵因素在于出生前幾天還沒有建立完善的正常菌群,免疫功能還不成熟,在感染后比較容易進一步擴散,進而發(fā)生敗血癥。新生兒敗血癥可分為早發(fā)型與晚發(fā)型,其中早發(fā)型多在出生后7 d 內發(fā)生,感染多在出生前或是出生時,此類型敗血癥患兒病情危重、死亡率較高。晚發(fā)型多在出生7 d 后發(fā)病,感染多出現在出生時或是出生后幾天,多伴隨肺炎情況,病死率相對較低。新生兒敗血癥在臨床中多采用抗生素治療與支持治療等,抗生素治療作為主要環(huán)節(jié)存在。而抗生素藥物選擇與給藥途徑以及用藥劑量控制如何將會直接影響到治療效果,甚至于增加對患兒的危害。為此,有必要由精準的監(jiān)測來指導治療方案的設計。關于此問題,以往有大量研究資料顯示,病原菌監(jiān)測應該作為新生兒抗生素治療的有效指導方向[6-10]。本次調查結果顯示,革蘭陽性菌占比60.00%,革蘭陰性菌占比40.00%;早發(fā)型新生兒中表皮葡萄球菌與大腸埃希菌檢出率最高,其次為肺炎克雷伯菌。肺炎克雷伯菌與大腸埃希菌屬于條件所導致的致病菌,基于新生兒機體內環(huán)境紊亂與自身免疫力不足等因素,致使敗血癥的發(fā)生,這也是出現革蘭陰性菌檢出較多情況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另外一個結果也證實了敗血癥病原菌對于氨芐西林與復方磺胺甲唑的耐藥性較強,應該結合實際檢測結果選擇適合的抗生素。建議在治療新生兒敗血癥過程中,需要調整傳統(tǒng)理念,盡量詳細地開展細菌培養(yǎng)與藥敏試驗,同時結合地區(qū)以及醫(yī)院病原菌等時機情況,設計出具有針對性的抗感染治療方案。
綜上所述,新生兒敗血癥病原菌以表皮葡萄球菌為主,主要病原菌對氨芐西林與復方磺胺甲唑以及慶大霉素的耐藥性較高。建議臨床強化對血培養(yǎng)的檢測,結合藥敏結果精準使用抗生素,控制新生兒敗血癥的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