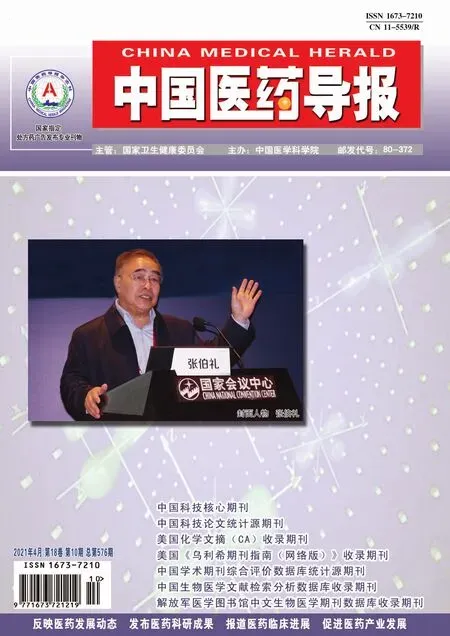針刺聯合椎管內鎮痛在分娩鎮痛中安全及有效性的meta分析
稅林輝 何慧鑫 彭 賽 鄧超文 滕永杰 雷華娟 李子奎
1.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麻醉科,湖南長沙 410007;2.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婦產科,湖南長沙 410007
分娩疼痛不僅增加軀體疼痛,而且會加重患者心理負擔和增加產后抑郁的風險[1-2]。椎管內鎮痛(包括連續硬膜外麻醉和腰硬聯合麻醉)已經作為治療分娩疼痛的首要選擇[3-4],但目前其仍然存在鎮痛不全、影響子宮收縮力、延長產程,甚至由此改變生產方式等問題[5-8]。針刺作為我國古老的治療手段,能否彌補椎管內鎮痛的不足,是否影響產程進展及其潛在不良反應仍不明確。因此本研究進行meta分析評估針刺聯合椎管內鎮痛治療分娩疼痛的安全和有效性,以期為實施針刺聯合椎管內分娩鎮痛提供循證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研究類型為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的中英文文獻。②研究對象為要求分娩鎮痛、擬實施椎管內分娩鎮痛的產婦。③干預措施為試驗組實施針刺聯合椎管內鎮痛,對照組實施單純的椎管內鎮痛治療。④結局指標為陰道分娩轉剖宮產率、產后出血量、宮口開全時視覺模擬評分(VAS)、第一產程活躍期時長及椎管內用藥量。
排除標準:碩博士學位論文、重復發表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國知網、萬方、CBM和維普網中相關文獻,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0年8月。中文檢索詞包括:“針刺”“體針”“新針療法”“耳針”“電針”“分娩”“鎮痛”“無痛”。英文檢索詞包括:“Acupuncture”“auriculotherapy”“point,acupuncture”“electroacupuncture”“Labor,Obstetric”“labor”“obstetric labor”“pregnancy”“gestation”“parturition”“accouchement”“analgesias”“analgesia”。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兩名研究者各自進行文獻篩查、提取數據并互相核查。當意見不能一致時,必須與第三方共同協商后共同決定。資料提取內容包括: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和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干預措施和結局指標等數據。
1.4 文獻質量評價
按Cochrane系統評價手冊干預類研究對納入的文獻進行質量評價,具體內容包括選擇、實施、測量、隨訪偏倚、報告和其他偏倚。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RevMan 5.3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差(mean difference,MD),二分類變量資料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OR)為效應分析統計量,選用95%可信區間,采用I2判斷納入研究間異質性大小。使用固定效應模型(P >0.05,I2<50%)或隨機效應模型(P ≤0.05,I2≥50%)進行meta分析,當某項結局指標的納入研究數≥10個時,則需要使用漏斗圖進行發表偏倚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初檢共獲取了750篇文獻,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了10篇文獻[9-18]。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圖
2.2 納入文獻基本特征
納入了10篇文獻[9-18],共包括872例患者,其中試驗組439例,對照組433例。見表1。

表1 納入文獻基本特征
2.3 文獻質量評價
納入的10篇文獻[9-18]中,5篇文獻[9-10,12,17-18]報告了隨機方法,評定為“低風險”,其余評定為“未知風險”。所有納入文獻均未提及使用分配隱藏,評定為“未知風險”。1篇文獻[17]提到了盲法,評定為“低風險”。所有文獻結局指標完整,失訪與脫落評定為“低風險”。所有文獻選擇性報告評定為“低風險”,評定其他偏倚風險為“未知風險”。見圖2。

圖2 文獻質量評價
2.4 meta分析結果
2.4.1 陰道分娩轉剖宮產率 共7篇文獻[9,11-12,14-15,17-18]報道了陰道分娩轉剖宮產率,包含了658例病例。選用固定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異質性檢驗χ2=6.37,P=0.38,I2=6%。試驗組陰道轉剖宮產率明顯低于對照組[OR=0.45,95%CI(0.26,0.77),P=0.003]。見圖3。

圖3 兩組陰道分娩轉剖宮產率比較
2.4.2 產后出血量 共4篇文獻[9,12,13,16]報道該指標,包含了374例病例。異質性檢驗χ2=47.95,P <0.000 01,I2=94%。選用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試驗組產后出血量明顯低于對照組[MD=-45.14,95%CI(-85.32,-4.96),P=0.03]。見圖4。

圖4 兩組產后出血量比較
2.4.3 椎管內用藥量 共5篇文獻[10,11,13,15,16]報道該指標,包含了398例病例。異質性檢驗χ2=8.37,P=0.08,I2=52%。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試驗組椎管內用藥量明顯低于對照組 [MD=-4.35,95%CI(-5.97,-2.74),P <0.000 01]。見圖5。

圖5 兩組椎管內用藥量比較
2.4.4 宮口開全時VAS共7篇文獻[10,11,13-17]報道該指標,包含了536例病例。異質性檢驗χ2=4.83,P=0.44,I2=0%。選用固定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兩組宮口開全時VAS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MD=-0.19,95%CI(-0.45,0.07),P=0.15]。見圖6。

圖6 兩組宮口開全時視覺模擬評分比較
2.4.5 第一產程活躍期時長 共5篇文獻[9,11,13,16,17]報道該指標,包含了332例病例。異質性檢驗χ2=8.78,P=0.06,I2=55%。選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兩組第一產程活躍期時長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MD=-15.79,95%CI(-32.83,1.24),P=0.07]。見圖7。

圖7 兩組第一產程活躍期時長比較
2.5 發表偏倚檢驗
由于納入文獻數未超過10篇,因此本研究未對發表偏倚進行檢驗。
3 討論
分娩疼痛因其劇烈程度且持續時間長被認為是最難承受的疼痛之一[19]。當前麻醉醫師參與下的椎管內分娩鎮痛仍然是國內外分娩鎮痛的首選鎮痛方式[4]。雖然能緩解大部分產科疼痛,但該技術仍存在鎮痛不全、延長產程等潛在不良影響[5,8,20-21]。本研究顯示針刺聯合椎管內鎮痛能減少椎管內藥物用量、降低陰道分娩轉剖宮產率、減少產后出血量。但針刺聯合椎管內鎮痛與單純椎管內鎮痛比較,二者在第一產程活躍期時長、宮口開全時VAS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
針刺作為祖國醫學的特色之一,已經被大量研究證實可用于圍術期抗焦慮、加強鎮痛、圍術期器官保護、促進術后器官功能恢復,加速患者康復[22-25]。傳統中醫學認為,疼痛的產生氣與血及七情密切相關。故疼痛病機有不榮則痛(虛痛)、不通則痛(實痛)、神志異常(情志)三方面。《黃帝內經》有言:“用針之要,在于知調氣。”“凡刺之真必本于神。”針刺鎮痛的機制主要是調氣血與治神[26]。現代醫學研究中,針刺鎮痛的原理涉及炎癥因子、傳導通路和神經遞質等方面,包括中樞情志調節、嘌呤信號通路及刺激腦內阿片肽及外周生物活性物質等[27]。本研究顯示兩組椎管內用藥量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便間接提示了針刺的鎮痛作用。陰道分娩轉剖宮產率的降低也提示了針刺聯合椎管內鎮痛時不會減弱子宮收縮。本研究提示了針刺聯合椎管內鎮痛比單純椎管內鎮痛減少了產后出血量,可能是由于減少了椎管內用藥。如何在滿足產婦鎮痛需求的前提下將椎管內鎮痛對產力的影響降至最低,針刺在這個平衡點上體現了其獨特優勢,并且為圍術期醫學提倡的多學科協作、多模式鎮痛理念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納入的研究樣本量不大,研究質量不高,同時也未有文獻報道研究過程中是否存在尿潴留、惡心嘔吐等不良反應。故還需更多高質量研究對結果加以驗證。